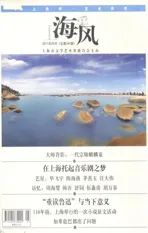情缘胡万春
2011-11-06张锦江
文/张锦江
情缘胡万春
文/张锦江

1985年秋胡万春(前排右)与陈伯吹等访问泰州

张锦江海洋小说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大学、华东师大教授,上海锦江经济文化学院院长。著有《童话美学论稿》《海王》《张锦江文集》等
我第一次见到胡万春时,他是在钩钢。他是这样一副模样:身穿一套白色已泛黄泛黑的帆布工作服,汗迹从背脊处透出来,头戴同样色调的长舌工帽,从帽沿处一直搭拉下的白毛巾一角,被咬在嘴里,手执一粗长黑色钢钩。这是一种简单而笨重的劳动。火红滚烫的钢条从滚动的轧机口吐出来,沿一钢槽滑动,延伸,到尽头再卷起来,有时在途中滑出钢槽,必须用钢钩钩进糟内。人在远处就能感觉到钢的热烫,那一角毛巾是挡脸的,或是擦汗的。我能闻到那钢的气味,也能闻到他身上的汗味。这是1968年初秋里的一天。
一晃四十二年过去了,我还能闻到这熟悉的味儿。那时,我是这家钢厂的一名电工。准确地说,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班毕业的学生,与那时代所有我这样的人命运一样,到工厂、部队农场,或务工或务农,这叫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的打扮与胡万春无多少差异,只是工作服我是蓝布的,腰间多一根皮带,串吊在屁股后的电工傢什,扳头、锣丝凿子、老虎钳、电工刀之类,走起路来哐当哐当像武士。我修理电气可以厂里四处游晃的,他却一步不能离开。
老胡是个纯粹的工人。他不是体验生活,他不是做做样子,他身上的汗臭与其它工友没有二异。他就是这家厂的老工人。当年这爿厂叫上钢二厂。他是从上海作家协会回到厂里来了。在这之前他已是驻会的专业作家了。他为什么回厂,来重干这种粗重、蠢笨的活儿,我不清楚。不过,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影响了我的生命轨迹。
老胡,自我认识他就这么叫他,虽然,他名气很大,他的《骨肉》获得过世界优秀小说奖,由小说改编的电影《钢铁世家》《激流勇进》《家庭问题》家喻户晓,毛主席还接见过他,与他握过手,我在他家里看到过这张大照片挂在显眼的地方。老胡笑嘻嘻的,没有架子,很亲切,我与他在一起不拘束,我就这么叫他。上海文学圈子的人喊他老宁波,他说一口宁波普通话。这厂也算大厂了,头两千人,个个熟识他,他是普通工人的样子,普通工人也愿与他交朋友。他起先家住控江路离厂子不远,时常有工友去他家玩,我就是一位工友带我去的。记得,当时他似乎己不再写作,他在画画,画的是水墨国画,竹子与熊猫。凭心而论,画作的水准是稚嫩的。不过,他自鸣得意。是的,这种年代作家已没有发表作品的地方了,只能画画自乐悠哉游哉,自我欣赏了。那时,我己结婚,与妻挤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内,他也曾来过我这里坐过聊过天。老胡在厂里不分老少都谈得来,连他的家事,工友们都一清二楚,有一位工友对我说,老胡一连生了五个女儿,他想不通,非要生个儿子,结果第六个如了心愿,是儿子。孩子弄了一大堆才罢休。说得听者哈哈大笑。
我们虽在一个厂子,也并不常见面。但是,一个莫名的遭难,让我们紧紧连在了一起。那年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恐怖随影相伴,今日是革命者,明日是反革命,今日审查别人,明日就会被别人审查。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惊人事件常发生。那时,我因能写写弄弄,被吸收为一个车间的专案组成员,是属审查别人的,是属可靠的对象。不料,一日,车间的墙上刷了一条鲜目的大标语:把隐藏得很深的“五一六”分子张锦江揪出来!我头皮发麻,脚步灌铅似地呆站在那里,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我怎么突然变成了隐藏的阶级敌人,我几乎晕倒。我的问题似乎很严重,还开过一次车间批斗大会,那是夏天,我劳动了一天,工作服汗湿一大片,腰扎皮带,挎着电工傢什,就这么站着,我脑子一片空白,有人指着我鼻子,要我老实交代。我交代什么,我没有什么交代,我参过军,我忠于党与毛主席。有一个老师傅揭发我:上厕所用信纸擦屁股,上面有毛主席语录。他说,他亲眼看见的。我想起来了,我说,我擦屁股前,把毛主席语录撕下来了。他坚决说我反对伟大领袖。我恨不得当场把心挖出来,给他看看我是不是反对伟大领袖。主持会议的说,还有防扩散的材料,你要老实交代。接着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斗会开不下去了,散了。车间书记找我谈活,神秘兮兮,抖落出防扩散材料,这是一张泛黄的纸,仔细一瞧,是一份油印的歌曲,题名:好个屁。我都忘了,但那字是我刻的,抵赖是没有出路的。原来,1966年夏季运动初期,我正在南京为江苏省锡剧团写一个剧本《农奴戟》,后来团里都在忙运动,剧本停了下来,一天,有人说,你字写得好,帮刻张腊纸,就是这首好个屁的歌,南京对许世友的态度分成两派,一派说许世友好,一派说许世友好个屁,形成了好派与屁派两个阵营,这个剧团的人员多数是屁派。其实,我根本不管你是好派还是屁派,我是消遥派,不过,人家求你,就帮个忙吧,于是留下了祸根。铁证如山,有口难辩。书记用沉重的语气又说,“五一六”是穷凶极恶的现行反革命,你的问题还未弄清楚,要相信党组织,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天啦,我怎么与穷凶极恶的现行反革命搅在一起了。我的内心痛苦之极。随即,我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清洗了出来,我成了异己分子,班组会也不让参加了。因为中央常发文件,一直传达到班组,我是没有资格听文件的,幸好有一个人与我为伍,这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不过,我极不情愿与他在一起,我不理睬他,我想,我不是反革命,他才是反革命。这时,传出了一个消息,胡万春也是“五一六”分子怀疑对象,他也被剥夺了参加班组会听文件的资格。驻厂军代表在召开的全厂阶级斗争大会上,没有点名地暗示了我与胡万春问题的严重性,告诫全厂阶级斗争形势是严峻的,不能掉以轻心。
我在厂里浴室洗澡池内碰到过几次胡万春,澡池不大,一股钢铁的气味,水是冶炼炉的余温,又热,又烫,我与他没有说话,笑一笑,点点头。眼前都是白晃晃的光身子,我觉得我的身子怎么也洗不干净了。我不知道老胡心里什么想法。我心里没有鬼,也仿佛有了鬼,我与老胡都是被怀疑的鬼,鬼与鬼说话是犯禁的。内部传出的信息,我与老胡都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我们又都是文化界混进工人队伍的人,疑点极大。专案组找到我妻,要她揭发,妻手里抱着女儿说,他当过兵,我觉得不是坏人。来人搜了屋子,这是厂里分我的婚房,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只有一木柜,一方枱,一竹书架,一床,两张木椅,床下一马桶,一目了然,密藏不了什么。不知老胡有否享受这等待遇。这段往事不堪回首,轻微触动,都会隐隐作痛。每天照例有繁重的体力活儿,头上还有一顶悬着的帽子,对于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悲惨世界。这时,我才感觉到,在我们的国度里,除了自然的生命,还有政治生命。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去了政治生命比失去了自然生命还痛苦。胡万春是小说家,他终究没有来得及写这段痛苦的故事。四年之后,我离开了这家厂,我的审查不了了之,同意调走,就算落实政策,没有一句道歉的话。
1975年我借调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我正写我的第一篇小说《检验》。我求教胡万春。我将素材给他说了,这是一篇写工厂生活的题材。他帮我编织人物与故事,他坐在椅子上,闭着眼晴,绘声绘色地说着。我佩服他超人的虚构能力。可以这么说,他是我的小说创作的启蒙老师。写完这篇小说之后,我病了一场。最后这篇小说刊载在《创造者的歌》短篇小说集中。这时候的文坛似乎有些松动,胡万春也能出来走走了。我记得,我与老胡,还有赵自、唐铁海一起去过大屯煤矿、铜陵铜矿,写学大庆的作品。我还与老胡、陈伯吹先生去过衡阳自行车厂,这是上海作协组织的。在去的火车上,我与老胡讨论了上海的小说创作。我们的话题是上海作家应该关注的主体人群,老胡说,上海是工人群体最大的城市,却没有多少写工人的作品。我说,我们一些作家本来就那么一点插队落户的生活积累,对工人不熟悉,后来只接触一些里弄婆婆妈妈,或者翻资料写写小姐太太,当然无法表现这个大都市的真实面貌了。火车的车轮轰隆着,我们就这样一路畅谈着。到了衡阳,我俩又通宵达旦地继续这个话题,特别是如何理解城市文学的内涵与作品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后来,我与老胡的讨论内容,发表在1988年第三期的《上海戏剧》上,题目是《要对改革题材作深层次的思考——关于“城市部落纪事”的通信》。
那时,我为《上海戏剧》主编一本电视剧专辑,胡万春将自已的小说《城市部落纪事》改编成了电视剧,先前小说发表以后已引起不小反响,电视剧播出后也普遍好评。我将这个剧本收入其中,并由此剧谈起,说了我们曾讨论过的一些想法。这篇通信也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这时,我与老胡都在努力写自已的东西,也常常互相关注对方的创作情况,他写了电视连续剧《蛙女》也曾热议于上海街市。我这里有几本他签赠的书,如长篇小说《女贼》《苦海小舟》等,都是他这个时期写的。记得,我在他家里喝过一次酒,喝得很厉害,那时,他住在外白渡桥旁的一所老房子中,我被老胡逼灌了一茶杯,老胡也喝了不少,当然,比我多一倍,他无动于衷。他喜欢喝酒,可谓一生嗜酒,喝了酒趴在桌上睡一会儿又能写。我不行,我天旋地转了,我喝了许多杯浓茶也还不行,睡在床上像在船上颠簸翻腾,整整在他家的一张小床上睡了一下午,才昏沉昏迷地乘车回了家,这一次的酒醉一辈子都忘不了。
时间到了1992年的一天,那是一个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上海戏剧》的主编赵菜静打来的,他说,老兄你在忙什么啊?我说,在写长篇《海王》。他说,还写什么小说呀,人家胡万春在中越边境做生意弄了一百万啦!好了,不要写呐。这是一个致命的电话,这是一个催我下地狱的电话,这是一个让我九死一生的电话。我的意志极不坚定,我是容易走火入魔的人,我的心血来潮了,胡万春又在作家中先走了一步,投身经济大潮了。人的命运有种偶然性,这种偶然,又让我与老胡有了牵连。胡万春用他小说家的思维来创办公司,他为公司起了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名字,叫“万家春贸易公司”。据说,他在做中越边界的边贸生意,将一些积压的清仓物资压价收购,然后好价抛出,连连得手,生意兴隆。我被传说疯狂地鼓舞着,也与家乡的报社合办了一家公司。文人的富于幻想与极易膨胀,这是涉足商海的致命弱点。我的失败是无疑的、是注定的、是必然的。都说钢材能蠃钱,我就到处找钢材,电话不绝,信息乱飞,跟踪追击,捕风捉影,弄得热闹非凡,疲惫不堪。我的周围全是虚假的货源信息,我被一群骗子包围着。我的第一笔水泥生意被骗了人民币十八万元,我给了货,骗子给了我一张空头支票,支票是十八万元支票,银行内是一分钱没有的。接着做期货生意,又被一新加坡商人卷款而去。再去黑河边境做鞋子生意,还是被骗了货没有收到钱。之后,是没完没了的请律师、上法院打官司,官司打蠃了,钱是追不回来的。我陷入了灭顶之灾,我的头上也有了白发。但是,我依旧风光,我与胡万春常常被作为文化人下海的典型,被刊登在同一份杂志或同一份报纸上。《文学报》曾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头版刊的是江迅写的“张锦江下海记”,最后一版是胡万春谈作家在经济大潮中的感受文章。
我与胡万春也有时碰头,还谈文学。诗人刘崇善在家里办了一个文学沙龙叫“泉舍”,在那里开过张士敏、胡万春还有我的作品讨论会,有一次宗福先、李楚城还有胡万春、刘崇善与我,一起在“泉舍”吃饭、喝酒。一沾酒,老胡话就多,他说到作家做生意具有创造性思维,他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冰箱内食品吃了常得“冰箱病”,他要发明一种保鲜膜。确实,他与一家厂合作了,至于现在流行的保鲜膜是不是他发明的,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他说这话时,市面上是没有这种东西,至少是他早就想到的。还有一个想法也有趣,乘火车时可供应一种盒装的食品,除了零食,再放一本微型的小说书,有得吃,有得看,可打发旅途的无聊。他的想象与构思都是富有创造性的。胡万春在生意上,也曾与我有过合作,但都不成功。一次是他托刘崇善邀作家张士敏与我一起在“泉舍”碰头,想合办一个公司,我与张士敏、刘崇善都是董事,也就是说开一个筹备的董事会吧。结果,张士敏有家事没有来,这个董事会未成立就流产了。还有我开了一家书店,胡万春也在做书的生意,他拉来了许多书放在我的店内,书店开在一个弄堂内初中学校门口,只有少数学生来,大多数的零花钱都用在校门口的烤羊肉摊上,书店关了门,老胡让他老婆把书拖回去了。
俗话说,买卖不成情谊在。那时,我虽下海开公司,大学里应该上的课还是要去讲的,我在大学讲授《文学写作》课,我请老胡来讲过一次小说创作,他用宁波官话讲得很生动,也有点理论色彩,受到了学生欢迎。我还邀请老胡参加了一个作家访问团访问泰州,是泰州市文联组织邀请的,泰州是我的家乡,那里出了柳敬亭、梅兰芳、王艮。同行的有陈伯吹、哈华、费礼文、周明等。在泰州两天内,下榻在历史名园“梅园”内,参观了梅兰芳纪念馆,吃了大闸蟹,陈伯吹先生嘴上吃出了一个泡,老胡痛痛快快喝了两壶泰州名酒“梅兰春”,老胡还在“梅园”与我以及我的姐姐、姐夫合了影,他们都知道胡万春的《骨肉》与《钢铁世家》。这一次访问印象深刻。
老胡的舞跳得好。有一次,作协组织舞会,老胡与程乃珊跳了一段探戈,技惊四座。后来,他有了一个固定舞伴,叫小陶,个头高高的,常与他出入舞厅,之后,形影不离。记得,老胡一个人住在香花桥的房子,在那里写作,我与刘崇善去过,也碰到小陶,当场在家里跳过舞,在桌、椅之间转来转去。老胡的女朋友传闻时有,小陶算一个。还有一个是偶然碰着的。那时,我已弃商从教,开办一所大学,还算成功。有一天接待一个报名的学生与家长,这是一个男孩,眉目清秀,填表时,父亲一栏中写的是胡万春,女的是一头短发的中年女子,朴实而娟秀,称是男孩妈妈。我说,我是胡万春的老朋友,他们听了很高兴。我疑惑的是那女子,老胡的老婆我认识的,不是这女子。他们走后,我打电话给老胡,说,今天你儿子来报名了。他说,这次高考考得不好,只能想其它办法了。我证实了这儿子是他的,那女子也是他的,不过,我没有问。他儿子终究没有来我的学校,另外择校了。老胡却因女朋友婚外生子,添了麻烦,这是他去世之后的事了。

胡万春作品
老胡一向身体硬朗,却突然住了医院。心脏出了问题,这都是嗜酒的因果。这是1998年5月初的一天,一位朋友的女儿电话告诉我,胡万春没了。我怎能相信,我随即赶到老胡家里,老胡家设了灵堂,灵堂悬挂他一幅半身像,这是真的,这是事实。他老婆说,这张照片是他六十岁照的。他是那么年轻,神采奕奕,怎能说没有就没有呢。我向遗像三鞠躬,喊一声:老胡,便情不自禁泪流满面、号啕大哭起来。老胡死得太冤,他还有许多小说好写呀!他老婆陪我哭着喊着:你说走就走了,叫我怎么活呀!老胡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因为这时发生了他的老婆与婚外的儿子争夺香花桥一套房子的官司,新闻媒介报道了这个消息,称作家胡万春写作《家庭问题》的新家庭问题。老胡死了也不得安宁,我很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