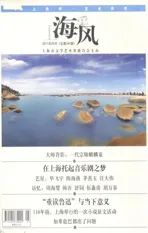毕飞宇: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
2011-11-06刘莉娜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毕飞宇: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早春三月,南京的早晚虽然依旧春寒料峭,中午时分却是暖意融融的,日渐淳厚起来的阳光铺撒在鸡鸣寺下盛放的早樱花瓣上,玄武湖畔的杨柳树也抽出凝汁般的绿芽,春色让这座城市里的人都忍不住慢下脚步来。可是三月的毕飞宇却很忙,刚刚飞去参加完热闹的北京书虫国际文学节,他便迅即飞往香港出席英仕曼亚洲文学奖颁奖典礼。他2001年出版的小说《玉米》被中国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翻译成英译本《Three Sisters》(《三姐妹》),去年8月份由哈考特出版集团出版,就凭借这本书,毕飞宇和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日本作家小川洋子、印度作家曼努·约瑟夫和塔毕什·卡尔一同进入了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决选名单。
英仕曼亚洲文学奖(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创立于2007年,与英国“布克奖”一样受到英仕曼集团资助。早期奖项颁发给未以英语出版过的亚洲小说,2010年以后改为颁给当年度首次以英文发表的亚洲小说。它的第一届获奖作品是姜戎的《狼图腾》,第二届获奖作品是菲律宾作家米格尔·西乔科的《幻觉》,第三届获奖作品是苏童的《河岸》,英译为《救赎船》(The Boat to Redemption) ,也就是说,毕飞宇是英仕曼亚洲文学奖4年历史中获奖的第三位中国作家,也难怪毕飞宇一开始对自己获奖并没有抱任何期望。“这个奖颁了三次,已经有两届给中国作家了,另外这次还有大江健三郎在,一个正常的判断就是我肯定不会得奖的。”毕飞宇说,“我之所以过去,主要是特别渴望和大江健三郎见一面。”然而当晚的颁奖晚宴,两位入围的日本作家也许是因为地震的原因都未能前来,毕飞宇并没有如愿见到大江健三郎,但是,主持人报出的获奖者名字却是他。因此,有香港媒体报道称毕飞宇“击败了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此毕飞宇表示很不认同:“我很反对这种说法,我非常尊重他。”而对于为什么最终是毕飞宇获奖,该奖的评委主席大卫·帕克说:“这个奖项并非奖励终身成就,而只是为了一本小说。毕飞宇这本书英文名是《三姐妹》,我觉得他在书中对人性认识的严肃程度让我联想到一位严肃的俄罗斯作家——同样创作了戏剧《三姐妹》的契诃夫。”
据悉,用一本已出版的小说带走3万美元奖金,这在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还是头一遭,因为之前的三年奖金都还是1万美元而已。记者笑问奖金何去何从时,毕飞宇大笑表示:“奖金都给老婆了,我是好丈夫!”不过,奖金虽是笑谈,但“在金钱面前不动摇”,毕飞宇说,他真的可以做到——直到现在毕飞宇都有一个习惯,不管条件多么诱人,他绝对不为合同而写作。比如这次得奖的《玉米》就可以说是这样一本拒绝金钱诱惑写出来的作品,因为当年为了写《玉米》,他谢绝了20集、5万一集的《青衣》电视剧的编剧邀请,为此夫人一个晚上没和他说话。《玉米》出版之后,毕飞宇把书拿在手上,给夫人看,对她说,《玉米》这本书不是100万可以衡量的。“所以,即便现在获奖后回头看,《玉米》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毕飞宇说。
过去的一年来,中国的长篇文学创作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因此毕飞宇的这次获奖也让中国文坛有了扬眉吐气之感。对此毕飞宇呼吁说:“我们对中国文坛要有耐心,毕竟每年都有好作品出现的概率太低了,几乎不可能。”他拿自己举例说,自己在这20年里一共写了3部长篇,10多个中篇,不到50个短篇。“20年间只写了这么些作品,读者和评论界都觉得少了点,特别是如果我两三年没写一部作品,人们就会不断追问,是不是我的创作不行了?灵感枯竭了?”毕飞宇对此有点郁闷:“真是开玩笑!我一直在往前冲,这只有我自己知道。写了一二十年,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总是将耐心用到最强才写。”在他眼里,作家的耐心是抵抗浮躁的手段,只有具备耐心,才能才会发挥,判断才会可靠,感受也才不会变形。比如写上一本长篇《推拿》,他就耐心用了几年时间,走遍南京的十几家盲人按摩中心,与一位位盲人师傅聊天、谈心,之后用了十八万字,去讲述这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盲人的人生有点类似于因特网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就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盲人的人生是似是而非的人生。面对盲人,社会更像一个瞎子,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毕飞宇说,所以他写《推拿》,摒弃了传统习惯中对特殊群体“自上而下的悲悯与同情”,以一个推拿店里一群盲人的生活为中心,去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这部小说的叙述非常有特色,以不同的盲人按摩师为题,以很小的切口入手,以每一个或几个不同的人物特点形成的故事作为小说的章节,把盲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书写,写出了残疾人的快乐、忧伤、爱情、欲望、性、野心、狂想、颓唐,打破了我们对残疾人认知的单一和平面。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无不表现了尊严、爱、责任以及欲望在人生中的纠结与暗战,而这些人生的矛盾与挣扎在黑暗的世界里似乎显得愈发敏感、清晰与沉默。虽然,这部小说的主角们都是盲人,但是读完小说的每个人都会扪心自问,毕飞宇仅仅是写盲人吗?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无可奈何的错位,那种微妙复杂的真实情感是那样令人感触乃至震撼。而毕飞宇自己的收获则是:“通过写盲人,我最大的欣慰就是知道了自己的局限,我不会为这个痛苦。局限是恒定的,正视自身的局限对我们有帮助,有时候,也许正是我们的局限在挽救我们。”正是因为这样的细心观察,静心感受,耐心书写,去年,这部《推拿》在中国台湾高票获得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的“开卷好书奖——中文创作奖”。

《三姐妹》英译本
问到最近的创作动态,毕飞宇说他正在写新的长篇。写的是什么内容?书名想好了没有?他坚决不愿透露半点。但他透露说,是一部当代现实题材作品,“写得比较困难,因为我对社会比较茫然,这不仅仅是我一人如此,当下的很多中国人两个眼睛都不能聚焦。但反过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因此,我有耐心边想边写。”为了更好地观察和思考,他还从2009年就开始尝试一种“转型”,就是把自己的时间更多地花在“一线”上。他经常在各种工地一呆就是很长时间,他非常喜欢和那些“一线”的工人们聊天,他说,那是直接触摸现实社会最好的方式。“我曾经说过,我渴望隐姓埋名。因为人们一旦知道你是谁——比如你是记者或者我是作家——真话就少了,人们脑子里的那个过滤器就开始自动启动了。好在那些工人并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和我什么都聊。这样的聊天很有意思,比方说,聊得好好的,他突然左看看,右看看,再向后看看,我就知道了,他打算说老板的坏话了。”
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毕飞宇已将文学创作视为生命,即便在人们对文学前景并不乐观的情况下,他还是抱有坚定的信念:“文学可能会边缘化,但文学不会死。”他认为,文学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正如人类永远热衷于偷窥心理和饶舌那样。“作家和长舌妇唯一的区别就在于,长舌妇是对某一个人说话,而作家是对整个社会说话。”
记者:好像你是颁奖现场唯一穿唐装的,是为了参加颁奖典礼特别定制的么?
毕飞宇:没有,我去之前完全没有获奖的期望,我去参加颁奖原本就是想去和大江健三郎坐着聊聊天以及向他表示祝贺的,可惜他没去。要说还有另一个目的么,也是为了要做给我儿子看,在国内的评奖中他经常看见我体面的上台领奖,所以这次我原本准备让他看到,即便爸爸没有获奖,也仍然可以像个男人一样体面地站在那里。
至于唐装,当然不是定制的。去香港之前他们特别致电我,明确要求了颁奖典礼的服装:黑色正装配领结,或者是选择民族服装。为此我和夫人特地去商场挑西服,可是相中的那套价值3万多,我自认为自己是不可能获奖的,所以想就不要花那个冤枉钱啦。后来忽然想起来夫人曾经在高淳给我和儿子一人买了一套唐装,只花了150元,平时我和儿子在家经常穿了表演功夫片,效果不错,所以就穿着那个去了。
记者:听说评委主席大卫·帕克说你让他想到契诃夫,而你的获奖作品《玉米》的英译本叫《三姐妹》,亦和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同名,这是个巧合么?
毕飞宇:其实得奖结果出来以后,评委之一,哈佛大学文学教授霍米·巴巴也问了我相同的问题——为什么用《三姐妹》做英译本的书名,和“玉米”有什么关联。我告诉他,其实我小说的原名和契诃夫作品无关,在汉语里,“玉”和“米”这两个字搭配在一起,正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女孩名字。但是到了英文里头,一个姑娘名字叫“棒头”是很不像话的;并且《三姐妹》是根据我的单行本《玉米》翻译的,书里面包括了《玉米》、《玉秀》、《玉秧》三个篇章,所以译者葛浩文把它翻译成了《三姐妹》,我觉得挺合适的。——我之前的《青衣》被翻译成《月亮的歌曲》《月亮女神》什么的,西班牙版的《玉米》居然叫做《王家庄的压力》……那才叫千奇百怪呢。
记者: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三部获奖中国作品好像都与“文革”时代有关,你注意到这点了么?
毕飞宇:可能是巧合吧。但我个人觉得“文革”是不该被遗忘的。我对“文革”最深的记忆是父亲的名字,我一直以为父亲的名字是“爸爸”,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在喊“打倒毕明”,我才知道我的爸爸叫毕明。一个男孩子以这样的方式知道父亲的名字,他在长大后不能不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