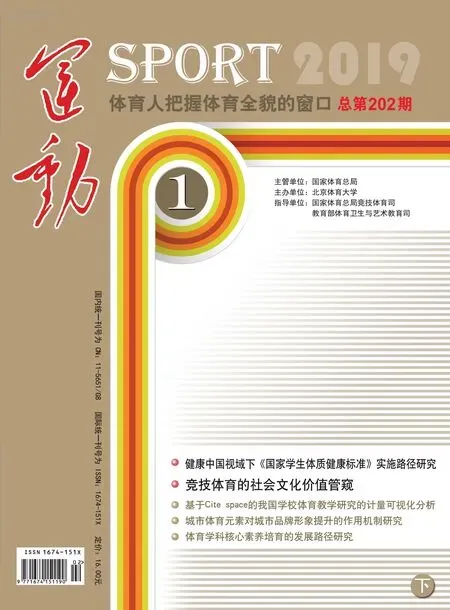对我国竞技体操人才培养训练效益问题的探讨
2011-09-28刘红波
刘红波
(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对我国竞技体操人才培养训练效益问题的探讨
刘红波
(河南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为提高我国竞技体操的训练效益,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的社会成本与收益、私人成本与收益、训练时间效益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竞技体育领域淘汰率较高,而收益率普遍较低;较高的机会成本是人才短缺的重要影响因素;注重训练时间效益是体教结合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
竞技体操;人才培养;训练效益
1 前 言
目前,竞技体育成绩不断被刷新,对训练设备和条件要求越来越高,竞技体育的投入也随之提高。不仅如此,随着我国体育市场化、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竞技体育的多元化投资方式必追求较高的人才培养训练效益。竞技体育社会和私人的投入与收益相关问题成为热点议题。同时,运动员教育和就业面临困境,使得训练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不同人才培养模式的训练效益问题应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我国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的投入、产出、训练时间效益等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中国知网与体育人才培养相关期刊和著作等文献资料。
2.2.2 访谈法 针对我国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社会效益、个人收益、训练时间等相关问题,广泛访谈教练员、专家学者、体操运动员等共40余人,从而为研究确立观点、收集数据。
2.2.3 逻辑分析法 对人才培养收益和训练效益相关问题,运用归纳、演绎、推理等逻辑分析方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我国竞技体操注重训练效益的必要性
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产生于计划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追求国家管理的高度集中性与计划性,强调竞技体育的政治效益,忽略其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在此背景下,竞技体育被定位为社会事业,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需要,并归为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因而完全由公共财政投入。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引发上层建筑相应的转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的竞技体育管理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不仅是运动员培养过程的行政管理模式改革,还应包含重视成本业绩的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管理。同时,随着竞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团体、个人等社会资本投资于竞技体育领域,也势必要求体育资金的管理按市场化发展需要,注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加强成本效益管理,以适应竞技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趋势的需求。
3.2 我国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的投入与产出
人力资本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1960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中提出的。[1]世界范围内教育领域的人力资本投出与产出以及收益率问题是人力资本研究的核心领域,而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深入研究还比较薄弱。
3.2.1 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的社会成本与收益 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的社会成本包括因提供人才培养所使用的物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包含获得成本(招生、选材、培育等)、开发和使用成本(训练、比赛、学籍管理等)、保障成本(医疗保健、意外伤残保险、训练学习生活等),换言之,不仅包括向运动员支付的工资和奖励费用,教练员、管理人员、保障人员的工资与福利费用,还包括培养设施的使用、维修以及训练设施所包含的资本利息和折旧费用。
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社会收益除包含被培养者的个人获得外,还应包括3类收益者:(1)与地域相关的收益者。目前,大部分体校和运动学校多实行三集中管理,场地设施资源、竞赛资源对外开放较少,因此,周围民众相关体育活动的收益相对较小;(2)与职业相关的收益者,包括体育实施、器材、服装等生产者,以及教练员、管理人员、保障人员等人员的收益,这部分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体育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水平;(3)全社会共同收益,包括获得优异大赛成绩时国家或地区的精神振奋和认同感、竞赛观众的观赏享受以及带动社会体育健身、娱乐参与等精神和身体健康方面的收益。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社会投资与收益,可以从国家投资竞技体育的人才收益率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淘汰率两个方面来分析。
杨再淮利用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收入函数法计算得出1999年我国竞技体育业余体校收益率为5.34,运动学校收益率仅为3.09[2](注:2000年之后《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未列出输送人数数据,最新收益率无法计算),而一般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都高于10%(表1)。从淘汰率角度看,即便是后备人才数量较少、世界冠军较多的竞技体操项目,也表现出高淘汰率,我国竞技体操运动员到15岁左右淘汰率已高达90%以上(表2)。随着体育科技的发展,竞争激烈的加剧,竞技人才培养的投入也越来越大。而且,由于竞技体育运动员文化缺失,导致人才培养个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因此,建立国家竞技体育投资成本业绩管理,调整投资结构,积极鼓励和扶持社会资金投入竞技体育,促进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解决运动员文化教育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是应对我国竞技体育竞技人才的高投入低产出、高投入效益单一(社会健身、产业等收效低)状况的根本措施。

表1 世界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收益率[3](%)

表2 体操运动员淘汰率[4](%)
3.2.2 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的私人成本与收益 从家庭或个人角度看,竞技体操人才培养投资的私人成本包括两部分,即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竞技体育的直接投资成本包括训练费、服装费、营养费、交通费等与训练相关的家庭投入,但在个人(家庭)投入的培养成本中,奖金等必须从私人成本中扣除,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转移支付。由于国家对运动员训练补贴较多,所以这种家庭或个人的直接投资较少。训练投入的机会成本是指一个人因从事训练而耽误文化教育等机会,从而影响到以后的经济收入。一些社会或学校参与竞技体操后备人才培养形式,尽管收费比普通业余体校要高得多,由于文化教育和成长环境优于业余体校,所以生源要明显好于普通业余体校。因此,机会成本是家庭投入竞技体操训练总成本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换言之,导致我国竞技体操后备人才数量萎缩的因素不是直接成本,而是机会成本。
家庭或个人投入竞技体育的收益或回报,除包括部分前期增强体质等健康收益,最为重要的收益是全国或世界冠军以及相关的丰厚奖励,相关研究表明,1994年我国竞技体育3883.5人的投入才能产出1个世界冠军,1995年需要3162.3人,1996年则需要4399.1人才能产出1个世界冠军。[5]由于世界冠军的成材率较低,极大地增加了家庭投资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再加上文化教育缺失引起的较高机会成本,竞技体操领域有关伤病、人文关怀不够、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的媒体报道的因素影响,直接关系到家长对子女培养的价值取向。
3.3 我国竞技体操人才培养的训练时间效益
王文生教授从竞技体操运动员培养时间和贡献时间角度定义竞技性运动训练时间效益为运动训练主体成员所投入的培养时间与获得的贡献时间和在贡献时间内所达到的贡献层次之间的比例关系。[6]
为保障体教结合的有效实施,促进竞技体操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良好运行,本研究从微观角度探讨训练时间效益,将训练时间效益定义为投入训练时间与产出的训练效果的比例关系,即单位时间内的训练效果。训练效果虽不能从短时间内直接评价和衡量,但可以通过一段训练时期后的比赛和竞技能力等方面综合衡量。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认为,体教结合必须由虚到实,要真正做到运动员在高校学习,必须精简训练时间,加强科学训练,提高训练效率和质量。[7]如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就规定,运动队一周训练时间不得超过20小时,否则就取消该队参赛资格。如果不从制度上落实“少练多学”,即使以后运动队真正融入教育系统内部,高校运动队也会变成现在的体工队。[8]因此,追求运动训练时间效益不仅体现的是科学化训练过程,也直接关系到运动员文化教育保障,是体教结合推行和实施的前提条件,还涉及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全面发展,打破传统的专业竞技培养体制,推进我国竞技体育改革进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为保证竞技体操运动员文化教育质量,竞技体操训练应该在有限时间内提高训练效益,以实现不逊于传统专业化训练效果的目的。优先考虑运动员文化教育,针对最佳的训练时间,地方队和国家队教练员、专家学者、具有执教经验的体院教师认识有所不同(表3),地方队教练员更是认为优秀运动队应该为7.2小时/天,说明地方队教练员更倾向于体操训练必须专业化,文化教育与训练在时间上很难兼得的传统认识。而体院教师和专家则认为各级体校和运动学校训练时间为2.5~3.5小时/天左右,比传统的体校最少4小时/天和运动学校每周9个训练单元(即3个半天,3个全天)的训练时间明显偏少。值得提及的是,访谈的体院教师多数在体院执教过专业运动员,曾经的竞技体校体操队靠半天训练来完成专业队全天候训练任务,且最后训练效果也较理想。

表3 保证文化教育前提下最佳训练时间的认识(单位:小时/天)
从训练时间效益的实践案例来看,几种新型的竞技体操人才培养形式的训练效果和运动成绩一般都明显好于普通业余体校,但有的形式主要依靠明显多于业余体校训练时间的方法来提高运动成绩,且很大程度上训练时间与普通文化课时间发生冲突,如朝阳区体操训练基地,这种办学形式很难保证运动员文化教育质量。有的培养形式依靠普通学生放学后的课余时间,这种开放式培养模式在有限的训练时间内获得较高的训练效益,如李宁体操学校和江西新钢一小试点学校(表4)。北京体育大学等原六大体院体操队通过半天训练达到省运动队全天候训练效果。美国等国家学校体操队和体操俱乐部运动员也尤其重视单位训练时间的训练效益(中学训练时间2~3小时/天[9]和大学训练时间不超过20小时/周),从而促进运动员文化教育和竞技能力的全面发展。这些例证都为我国竞技体操体教结合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也有力地证明了竞技体操运动员(尤其是初级训练阶段)文化教育和竞技训练同步发展的现实可能。

表4 新型办学模式的训练与学习情况
4 结 语
无论从社会、私人角度,还是具体的训练时间来看,我国竞技体操投入与产出的效益都较低,这也势必造成我国竞技体操运动员教育缺失,数量规模受限,致使传统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缺乏生机。因此,积极鼓励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体育人才培养,引入体育投资成本业绩管理,注重训练时间效益是促进我国竞技体操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1]朱舟.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6.
[2]杨再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44-47.
[3]Balbir Jain.Return to Education: Further Analysis of Cross Country Data[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91,10(3):12-15.
[4]颜天民.竞技体育的价值活动代价[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25(3):430-432.
[5]郭经宙,倪湘宏,张志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分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2,35(2):18-20.
[6]王文生.竞技性体操运动训练时间效益的探讨[J].中国体育科技,2001,37(6):12-13.
[7]林麟.“体教结合”该如何结合?——透视胡凯现象的现状[J].体育师友,2006(3):22-23.
[8]新华社.北京大捷 喜中有忧—从北京奥运会看中国体育的收获和走向[DB/OL].:http://xh.xhby.net/html/2008-08/25/content_8242687.htm,2008-8-25.
[9]丁海勇,郑燕飞.上海市与国外学校体育后备人才训练及竞赛现状比较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29(6):33-37.
G80
A
1674-151X(2011)02-020-03
投稿日期:2010-11-01
刘红波(1980~),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体操训练与管理、体育教学。
10.3969/j.issn.1674-151x.2011.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