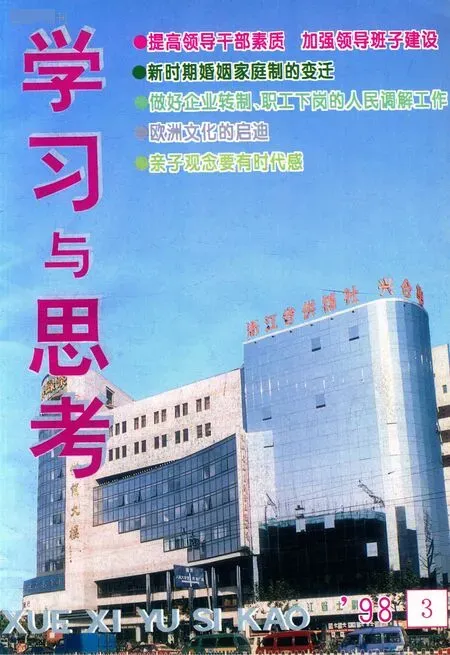两个织造小老板的“十二五”
2011-09-20
观察记者(特约) 夏 燕
两个织造小老板的“十二五”
观察记者(特约) 夏 燕
有人叫“家庭工业户”,有人叫“个体经营户”,相关的称呼还有“小老板”、“微小企业主”。他们的生产经营场地就在自家的空余房屋或院落,参与劳动的也大都是家庭成员或农村剩余劳力,尽管规模小、投资少,却以一技之长捡拾着大工业之遗,填补市场供应之缺。这就是所谓的家庭工业。

消费者在市场选购的围巾,大多产自一些家庭小作坊。newsphoto
有人叫“家庭工业户”,有人叫“个体经营户”,相关的称呼还有“小老板”、“微小企业主”。
他们的生产经营场地就在自家的空余房屋或院落,参与劳动的也大都是家庭成员或农村剩余劳力,尽管规模小、投资少,却以一技之长捡拾着大工业之遗,填补市场供应之缺。
这就是所谓的家庭工业。
曾几何时,正是诸如此类社会化的小生产推进了浙江现代化进程,也带动了浙江长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时至今日,在强调现代大工业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之际,这一趋势再度受到关注也成了学者们眼中的应有之义。而对更多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或转左,或往右,下一个五年,如何在市场激浪中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早已成为他们自身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切正悄然发生变化。
赚围巾的小钱
德清县新市镇加元村。
陈新祥家十几台“剑杆提花机”不停地运转着,嗡嗡的声音单调而沉闷,一垛垛人造棉纱、纺织袋堆在院落,使这个本就不大的地方显得有些拥挤。另一间屋子里,两位女工分别坐在一摞色彩斑斓的围巾面前,将它们一块块仔细地检查,按同样的手法折叠好,再装进准备好的包装袋里,这样的动作不断重复着一遍又一遍。虽然辛苦,但对她们来说,每个月一千五六百元的收入,有钱赚总比失业好。
对于自己目前的状况,陈新祥感觉还过得去。按照现在的生产规模,十几台机器再加上十七八个雇佣工,每年的产值可以做到200—300万,虽然利润只有不到8%,但是积少成多。陈新祥家的围巾95%以上都销往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这在当地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提供花型,对方看中之后下了订单就开始做。”陈新祥说,“从原料粗加工到半成品,再到成品,整个都做。”对于陈新祥来说,这样的方式可以多赚一些,不像自己5年前刚开始时只做加工,辛辛苦苦下来,拿到手的钱却少得可怜。
如今,在给义乌市场供货的同时,陈新祥也会零星接一些外贸单子,但总体而言数量并不多。前两年的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很大的影响,此间,陈新祥还借机将设备进行了升级,把剑杆提花机由1.8米宽的换成了3.6米,用电量不变,产量却提高了,同样规格的围巾用新的机器可以一次生产4条,整整比之前多了一倍。
新市镇韶村村。与陈新祥类似,金国良家的围巾也主要依托义乌市场进行销售,所不同的是,他是由做真丝而转向做围巾。
对于自己的的改弦易辙,金国良的记忆是,六七前真丝价格跌得太厉害,“根本就没有利润可言了”。现在,他的厂里差不多雇了四五十人,规模在当地家庭工业中也算是比较大的。按照金国良的说法,因为之前卖过纱线,所以在刚开始做围巾的时候就直接到绍兴去进原料,中介、差旅费省了,成本也降低了不少。
现在金国良的家庭作坊里,当地“50、60部队”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围巾包装、打结,这些活儿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干,做包装的每月拿到手差不多有1000多元,打结的则是每条2米的围巾4毛、4米的围巾7毛,掂量掂量,赚得也不少。对于自己的现状,金国良的感觉是“还过得去”,至少目前每天还能维持24小时不间断开工,尽管和以往相比,做围巾的利润已经变薄了许多。
存活难题
“主要是竞争太激烈。”金国良说,金融危机中反而没受什么冲击,倒是去年7月份以来,当地许多小型的家庭企业都相继倒闭了。
“(我们)这行进入门槛太低。一块很小的场地,五万块钱,就可以开始做了。”金国良的记忆里,最多的时候,仅新市一个镇,做围巾织造的家庭工业户就达到一百多家。原材料价格一涨,许多竞争力低的家庭作坊就生存不下去了。
现在,围巾的主要原料人造棉纱的价格是每吨35000元,而仅在几个月前,这个标准还停留在每吨22000元。估算下来,一条围巾的成本涨了一块五六,但市场售价仅涨了一块左右,之间的差额,则需要家庭工业户自己去消化。
对此,金国良的方法是,节约、再节约。除了老板的身份,他还兼任厂里的司机、装货工,虽然累了点,省下的真金白银却是实实在在的。
成本的上升也让陈新祥头疼不已。
“之前利润都是15%到20%,现在几乎减少了一半,8%还是做得很好时才能达到的标准。”现在陈新祥家雇着的工人,早7点晚7点,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比较熟练的工人每月挣3000元不成问题。但困扰他的一个问题是,工人的流动性太大,只要订单少了闲下来,他们马上就会跳槽到其他家去。
“一旦闲下来,工人就要走。万一他们刚走就下来一个订单怎么办,临时找人太难了,一个生手至少要做一个月才能熟练。”陈新祥说。
让两人同样感到纠结的,还有商家赖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老外赖,买家也赖,如果货款两个月不到账,资金周转肯定会出现问题。”就在不久前,因为买家无故失踪,金国良一笔6万元的货款打了水漂,想打官司,却由于涉及金额太小,法院根本不予以立案。
不仅如此,土地问题也是金国良面临的一个障碍。想扩大厂房,但现有的土地已经质押出去,根本没有可能。租赁是一条出路,只不过看来看去始终选不到合适的位置,至于获得新的用地指标,更是难上加难。“当前各地政府招商选资,首要考虑的是一些大型企业,家庭工业规模这么小的,自然看不上眼。”金国良颇有些失落地表示。
在家庭工业户们看来,目前自身能够享受到的政策扶持确实少得可怜。
这其中,陈新祥惟一能够清楚记得的一点就是交了多年的工商行政管理费取消了。按照以往的标准,他家的每台剑杆提花机都要缴纳500块的费用,十几台机器就是好几千块,而现在每年的费用仅仅是20块。
“我们也希望被重视。”陈新祥说。
坚守者的变与不变
目前,有一个粗略统计:义乌市场上40%左右的围巾都产自德清新市镇—尽管数量巨大,做产品、闯市场的种种压力还是让家庭工业户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变的重要性。
“从长远来说,家庭工业还是要往大发展”,金国良的想法是,“不然很难生存,因为抵抗风险的能力太弱。”
而对于家庭工业来说,低门槛意味着好进入、易模仿,同时也意味着低产业进入壁垒必然导致过度市场竞争,高同质性低异质性的廉价劳动必然导致低利润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企业规模提升产业集中度确实也是出路之一。
只不过,现实往往比理论复杂一百倍,更何况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我目前是先求稳,再做大。”在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扩张经历之后,金国良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吃不过大鱼,只好吃虾米。现在他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就好。“其实我们这行做大很难,即使做大了,没有资金、土地又能怎么办?”他不无茫然地表示。
欣慰的是,长期依赖订单还没有让金国良失去对市场的嗅觉和判断力。为了稳中求胜,他在生产围巾的时候也往往会比别人多用几种料,多做几种款式和花色。
和金国良对于将来的保守态度相比,陈新祥的想法则是“两条腿走路”。
在历经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之后,他认为单做义乌市场的利润太薄,风险也大,由此便想到了给大企业做配套。“一则有了平台,生意就固定,二则也希望将来能把这块做大。”关于接下来几年的发展,陈新祥同样有了筹划,目前在德清新市镇和钟馆镇交界处,他为做配套而添置的另一处厂房就正在改建当中。
之于现在普遍提及的大工业,陈新祥觉得和自己所做的家庭工业其实也并不冲突。“他们吃鱼,我们吃链子上某个环节的小虾米,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按照他的设想,等自家的企业真正做起来了,还要做网站、做品牌、直接和外商打交道,但首要的还是踏踏实实把眼下这一步走好。
“只是我的文化水平不高,管理方面也不是很懂,这样以后可能会比较累。”谈话间,陈新祥虽然忍不住担忧,但眼神中的坚定,一直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