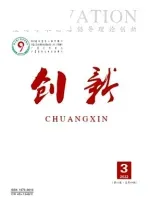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转型
2011-08-15徐翔
徐 翔
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转型
徐 翔
网络文化中主体认同面临“灵韵”消褪以及朝“离化认同”的转变。这与其说是由于网络场景的内容变化,不如说是由于主体所处的电子信息场景在性质上的根本转变,表现为:“场景性”从仪式性向景观性的转变,“场景间性”从总体性向分离性的转变,“场景——主体间性”从卷入性向观看性的转变。
网络文化;认同;场景;电子景观;主体
一、网络文化主体认同的转型
如果说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面临本雅明所说的“灵韵”(aura)的丧失,那么主体在网络文化时代也面临着一种灵韵的丧失,也即认同中的深度卷入,从而使得主体在意识形态认同和主体性“询唤”(interpellation)中发生朝“离化”的转变。这里的认同并非指身份认同研究中的Identification,而是强调葛兰西所说的“同意”和文化领导权(hegemony)的层面。离化并非简单地仅指利奥塔所述的“宏大叙事”的消解或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而是对中心采取一种距离化反视,对认同采取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延异和游离、再表征姿态,其内涵在下文还有详述。麦克卢汉曾强调,“也许,印刷术给人馈赠的最重要的礼品,是超脱和不卷入的态度——只需行动而不必作出反应的能力。”[2]但在从印刷文化向网络文化的转变中,这种超脱而不卷入的态度经历在程度和性质上更剧烈的深化和质变。印刷文化的超脱是一种关于思考和行动的分离所带来的理性,它塑造和强化了麦克卢汉所说的偏于思考的主体,而网络文化则基于认同而非理性的层面塑造了一种不涉入而观看并且更确切地说是摇摆于涉入和观看之间的主体。它不是主观意义上的认同危机或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狂欢化”、“游牧化”等主体表征,而是由于网络媒介所营造的电子场景其本身特性对主体所造成的种种分离,使得网络媒介中出现认同主体的自我游离和自我再审视。
利贝斯和凯茨曾在对《达拉斯》受众的研究中作出了参照式解读/批评式解读、热的/冷的解读的区分,“参照式解读将这部节目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批评式解读(雅各布森所说的元语言学解读)将这部节目当作一部具有美学规则的虚构作品来进行讨论。”[3]实际上网络文化主体的游离式认同也具有批评式的解读内核,同时,它也不是热解读的高情感涉入性的而是偏向于冷解读的认知性的。电子文本不是被作为一种现实书写,而是作为类似于鲍德里亚所谓的“仿象”文本,对它们的接受不是对文本自身而是互文性的参涉。在这种互文性的参照中文本的封闭性被打破,视角游移到文本本身的书写方式和效果。游离式接受把文本的内容、主题、寓意乃至语法等层面与其它文本进行关切和视域的融合,读者此时实际上已经跳出文本之外,把对文本独语性、封闭性的评断转化为与其他潜在、虚拟主体的潜对话,把解读和接受从主体性的存在转向主体间性的诠释存在,把单纯的接受也隐然带入展示性的潜对话和嬉戏。在此基础上,网络主体对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接受、认同也带上了更为鲜明的跨文本性和超主体性征属。
就性质而言,离化认同很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种“元(meta-)认同”。在参照式解读中,强烈地渗透着生活现实和价值规范,即使这种现实和规范可能也只是中立、相对的;而批评式解读则体现了超越文本及其现实内容的“元解读”。在这里,罗兰·巴特的“含蓄意指”(connotation)符号学可为我们提供有利的理论准备。巴特根据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的二级系统理论(ERC)论述道,符号学中同样存在着“含蓄意指”的二级系统,它也是意识形态“神话”的符号学构成模式。
而事实上离化认同之所以体现出既在场又不在场、既卷入又无涉的征属,与这种相似的二级系统也有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就意义的灌装或生产而言,而后者则是就对象意义的接受而言。离化认同并非对内容本身的直接审视而是一种往后拉的距离化审视,但是又不是完全超然于内容之外的嬉戏。在游离性的接受和认同中,一级系统的接受认同转化为类似于含蓄意指的二级系统。本来的意指——认同关系现在成为对这种认同关系的再审视和二阶认同。这里也体现了离化认同的“批评性解读”的策略方式。这种模式中,对对象文本的认同不再是直接的而是中介化和间接化的,对某种蕴有所谓的意识形态“神话”性质的文化文本的评断,不再直接指向该文本本身的内容,而是半嬉戏的元(meta-)话语指向。对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巴特著名的“神话”文本理论是对接的,其接口就是神话意义上的“符号(意指)”。如果说大众文化在意识形态生产和制造上已经超越了直接性的层面而进入含蓄意指的符号操作,那么网络文化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认同上,同样超越了直接性的层面,进入元认同和超认同的质属指向。
二、网络文化主体认同转型的原因
关于电子媒介对社会人的影响,梅罗维茨在其名著《消失的地域》中,结合戈夫曼和麦克卢汉的理论指出,电子媒介带来各种生活场景的边界的模糊和移动、融合,“将从前不同的社会场合组合在了一起,将私下行为和公开行为的分界线移向了私下一方,并且弱化了社会位置和物质位置之间的关系”,[4]并造成这种新的“信息场景”中社会主体行为模式和认同的变化,如男性和女性气质的融合、成年和童年的模糊、传统政治权威的瓦解。
有必要强调,网络媒介中的主体认同朝离化的转变,其原因不仅是主体所处的场景内容的变化,更是这种环境的性质转型,还包括主体与网络环境以及环境之间的交互方式和构型(formation)的转变。网络文化在营造主体环境的同时,也营造游离于这个环境、潜藏在这个环境外的背景和阴影处的“异环境”和“潜环境”,加深了该环境的外景和景深。也正是如此才会带来前文所说的认同与认异、认同与非认同的关系及其所关联的游离性问题,它使得这种信息场景环境既是自身的总体性(totality)而又包含着居于该总体性之外的潜在和异在,其中的主体既作为这种环境的书写又处于一种超书写和自我书写的位置。下面从三方面说明网络环境的性质改变及其所带来的主体认同效果的转型。
(一)“场景性”的改变:从仪式性到景观性
仪式由行动、主体亲历和身体在场所构成,虽然可以重复但主要指物和事件的此时此地性所构成的原真性,有具体的时空系参照,宗教和节日等仪式都具有专属的独特的神圣氛围。但在景观中,复本脱离了原本,其仪式化的“光晕”以及“它置身于其中的传统关联”[5]被割断。从仪式向景观化的转型主要在以下维度中得以呈现:
首先,从此在到此在的消解。仪式具有本雅明所意指的时空上的独一无二和本真性、神圣性,也具有物和场所的依附性;而景观则体现为信息的外在堆积,它缺乏这种整体论视域上的辩证存在方式。仪式具备生长、融合于环境的氛围和气质的不可移植性尤其是不可复制性,它只是当下的、历史的;而景观则是可复制的、移植的。在仪式性时间和场景中,主体作为存在具有“被抛”的存在论意义,并把存在变为一种“此在”(dasein)。而信息场景在网络文化环境中的“被抛”则是消解这种此在性的,这种景观游移于道路之外而非与道路相融,或者说电子屏幕开辟了另一游动风景。相比于仪式化场景的自我卷入,景观化场景是自我分离的、分身化的,不具备原来的神圣本体光晕,从而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也是从一向多的转变。如果像本雅明所述,机械复制曾经把艺术作品的存在从仪式的神圣惟一中解放出来,那么电子媒介则把仪式本身从仪式中解脱出来,在朝网络景观转化的过程中趋向于消解实在的所指而转向能指链以及仿象,把此在本真性转化为仿象化、可复制和可移植的游离于自身外的反(anti-)此在。这里所谓此在的消解并非指直接的主体此在的消解,而指场景作为“场景的场景”中的此在的间接消解,但这种转型也恰恰系联着该景观中的主体之在及其对场景的依附。
其次,从时空到时空的虚化。网络景观转型的另一维度问题是时空参照系的电子复制导致的解时空化、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此中的时空趋于内爆(implosion)和所谓“脱域”化,但这种脱域(disembedding)不仅如吉登斯所指是社会关系对时空关联的脱离和穿越,[6]更指时空维度从物的关系以及人和物的关系中的抽离。景观由于电子速度因而是解距离的,远近、新旧景观相互消融和聚集而体现为同一的堆积,主体不是参与而是曝光于场景间。这种解域化景观使传—受者、受—受者之间既靠近又分离。曾有研究者指出电子时代的主体与游牧社会中的类似,认为两者都缺乏“地方感觉”,具体活动和行为并没有固定具体的物质场所及其边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电子社会和游牧社会的解域化的根本不同在于物的依赖关系、仪式的依赖关系和符指的依赖关系的不同,仪式场景和景观场景分别作为所指性和能指性的两极在复制、分离、多重化等方面有着根本的时空性质差异。戴扬和卡茨所说的“媒体事件”[7]中对节目的现场直播和节日化收看在网络时代潜在的重要后果是事件本身性质的改变,使得仪式化媒介事件在电子保存和拷贝中破坏了生活场景的现场性和独一无二性,从而也转为伪仪式和反仪式。这种脱域也是海德格尔所分析的具有自己历史和存在境遇的“农鞋”向华荷的作为与所在完整世界没有关系的“死物”的“钻石灰尘鞋”的改变,在复制和挪移、变形、拼贴中呈现出缺乏历史有机性的“死灰”感。[8]时空参照的电子镜像所产生的,是行动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品在复制中的光晕消褪和膜拜价值的瓦解。
(二)“场景间性”的改变:从总体性到分离性
场景间性的游离特质可从以下两层面的间性关系考察:
首先,就场景——潜场景的间性架构而言:从融合到拼凑。仪式性场景中,场景作为“此在”的物化表征具有时空上的有机性,它们不仅直接依附于道路也相互依附,相互在对方的存在中确认自身的坐标和意义。这是一种融合的“间性”特质,我们无法把仪式进行切割分离而依然保持它原有的灵韵和意味。但是网络电子环境则呈现多向度的聚合和拼凑,这种马赛克式的文化片段可以制造自己的复件和分身投影并呈现为解(de-)此在的存在。信息片段不是聚合于并建构原来意义的社会场景,而是聚合于屏幕和链接。它使场景从“物”性存在转化为一种“像”性呈现,从集中性的融合转化为离散性的拼凑。场景在此可以被打散和漂移,它实际上把所指的凝聚转换为拉康式的能指链。这不仅仅是本真性灵韵的消解,也是在铺延自己的景深,使得原来同一的文化前景分离出隔景和潜景,制造出游走于呈现和隐匿之间的半在场和潜在场的话语背景。这使得场景不仅是其显见的部分也包括不具直接当下性的潜环境及其在幽暗中的绵延,从而主体视域由于“场景——潜场景”的间性架构而呈现出分离化的表征。这种拼凑不能简单地从去中心、深度的缺失等后现代理念去理解它,它是我们生活境遇深处的一道深渊。借用尼采的话:“当你长久地窥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在窥视着你”,这种深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敬畏、诗意与缺失。
其次,就场景——异场景的间性架构而言:从同一到张力。电子场景不仅蕴涵着潜场景的分离,还持续生成着异场景的张力。仪式式的场景作为相互的物性聚合从而呈现为同一性的表述,运行的是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在场的逻辑。这个环境内的规则具有统合性,各个单元自我的“语法”只有在场景整体中才能建构和确立自己的“使用”。而网络的电子场景则在自身的“仿象”言说中生成异己的信息后果,借用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说的,“从生活的每个方面分离出来的影像群(images)汇成一条共同的河流,这样,生活的统一便不再可能被重建。”[9]景观使自身分离为场景——异场景的间性构架,因而它不能对自身的总体性进行言说。梅罗维茨已经向我们指出电子媒介背景下场景的分化及其边界的模糊、融合,但在这些前台的显像场景的变化背后,作为类似于克里斯蒂瓦所提出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概念的“场景间性”却依然未得到足够重视。它关心的不是那些显在的场景之间的内容上的交互关系,而是显与潜、近与远、同质与异质场景之间的关系架构。实际上此在场景既是其他场景的复制也蕴含着其在“他在”的分身,同时还处于与异场景的间性关联中,因此它的显像只是以整一体所表现的截面,在同一中蕴含着分离张力。若说“生活在别处”,“场景——异场景”的间性架构则更把别处的生活映入此处。
(三)“场景——主体间性”的改变:从卷入性到观看性
在仪式性社会和场景中,主体受到物的压迫但也依附于物性环境,作为行动者和情境的思考者隶属于当下及其延展,然而网络文化的信息环境把主体从这种依附中吸出并使之漂浮于其上。网络文化中信息和主体不再依附于情境,而是屏幕和信息框架内的游动隶属,制造着环境和环境、主体和环境之间的游移和切口。印刷文化尽管把行动朝思考转变,把信仰朝理性转变,但由于仍未改变主体与环境间物性的交互方式,因而它并未改变主体在情境中的卷入,而网络中的电子化主体则把情境的主体延伸改变为主体的情境延伸。主体体验也从亲历转为代历和转历,或者说体验由其缺失呈现为公共性文化观感和符号记忆。在前网络文化中,行动和主体性是环境的延伸,借用马克思的著名划分,体现出所谓的“人的依赖关系”或“物的信赖性”,[10]这也是对自我、行动及事件的嵌入;网络文化则抽身于主体间性以及场景——主体间性的役使,从依赖关系转向分离关系。
在卷入式主体情境中,主体的认同具有强外在和意识形态性基础,而观看式的主体则从这种非自觉状态脱离成为超情境位置,带上一层“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不是完全卷入到某种现实环境中而是在视域中始终有其潜环境和异环境的存在,不是只固定在自身的视角观察环境而同时也在环境之外对这种视角本身有着审视。身份在由实转于虚实之间,对规则的遵守也不再意味着完全的认同。这都与其所处的环境及环境间性的特点密不可分,仪式在向景观转型的同时,主体也从仪式内的内主体而生成景观外的外主体,从物化的行动者转向象化的观看者。如果说赛博空间就主体间性而言制造了“中介化的类交往”[11](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那它则就主体性而言制造了一种“中介化的类主体”。这种主体并非直接依赖和生长于物以及行动、事件,而是以景观为其中介,人对物和环境从卷入关联转化为间接关联,从剧场内疏离到剧场外。正如有研究者对网络所评说的,“信息创造了一个事件丰盛但体验匮乏的世界。体验逐渐在我们身外发生,获得了自主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奇观(spectacle),而我们则成了这种奇观的观众(spectator)。”[12]
三、结论
如果说工业和印刷文化生产技术性和理性的主体,那么网络文化生产艺术性和离化的主体。这种主体并非缺失一般意义上的认同,而是缺失了传统认同中的“光晕”和此在的神圣性,它是介于“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认同,是严肃的嬉戏,是认同之外的元认同和超认同。离化认同并非“认同危机”或认同在内容上的碎片化和多重化,而是传统深度认同在网络文化时代的性质改变;不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沦丧或崩塌,而是网络时代的电子场景特性的外在客观意义上的后果。其背景原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场景性”从仪式性向景观性的转变,二是“场景间性”从总体性向分离性的转变,三是“场景——主体间性”从卷入性向观看性的转型。这些分离性的力量使得主体与自我、认同与认同自身出现潜在分离势态和去中心化的偏转。由于场景特征及其与主体关系的转变,主体生活的境遇发生了从物性到像性、从仪式性到景观性、从依赖关系到分离关系的种种改变,主体处于某种被“抛离”的状态,这种间于此处和彼处之间的主体位置充满了网络文化时代本身所制造的疏离效果和内在张力。
[1][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泰玛·利贝斯,艾利休·凯茨.意义的输出[M].刘自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4]汪民安.罗兰·巴特[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5]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
[8]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0.
[9][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Thompson,John B.Ideology and M odern C ulture:C ritic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 ass C ommunication[M].C ambridge:Polity,1990:228.
[1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文 晴]
G 0
A
1673-8616(2011)02-0109-04
2010-07-28
徐翔,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