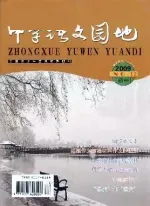管窥陶渊明不得已的隐痛心理
2011-08-15彭菊
彭 菊
千百年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备受人们推崇。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言:“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敬佩之情,无以复加。
的确,《归去来兮辞》不仅语言清新,辞采华美,结构严谨,而且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感情充沛而感染力强,直抒胸臆。宋代李格菲评介说:“《归去来兮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之痕。”
文中,作者强烈地表达了对自己过去误入官场的痛悔之情,今日辞官归田的决心:“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途之中归心似箭:“恨晨光之熹微”。返家时欣喜若狂:“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家中妻贤子孝:“稚子候门”、“有酒盈樽”。然后,作者以大量的笔墨铺叙了闲适自在的归隐生活:“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真是潇洒自在,其乐融融。最后,卒章显志,表达了自己回归自然、乐天安命的思想,“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通观全辞,我们似乎强烈感受到的都是陶渊明热爱自然、淡泊名利、安贫乐道、其乐无穷的隐士情怀,似乎陶渊明“性本爱丘山”,生来就不喜做官,躬耕田亩是他的追求,琴书诗酒是他的最爱,采菊望南山是他生活的全部。
非也!笔者从《归去来兮辞》中却管窥蠡测到了陶渊明不得已的隐痛心理。
“奚惆怅而独悲”,他为什么要惆怅伤悲?“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太阳都下山了,天地一片昏暗,他为什么还要手抚孤松,呆望远方,徘徊忘归呢?“乐琴书以消忧”,他为什么要通过看书抚琴来消忧?忧的是什么?“已矣乎”意思是:唉,算了吧!他为什么要发出如此无奈的叹息?仅仅是因为“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吗?可是他刚刚41岁,正年富力强啊?
经此反复追问,我们发现,陶渊明辞官归隐其实是不得已的行为,他心中有着不便为人道的隐痛心理。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他的曾祖陶侃因为军功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由于受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着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他在《读史述·屈贾》中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他也是希望能做稷契一类的人物。在《咏荆轲》一诗中,他热情地歌颂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同样豪情万千,意气风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心中同样燃烧着“兼济天下”的熊熊烈火。
可惜的是,陶渊明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是对他十分不利的。这时,封建门阀制度已发展到了顶点。自三国时代的魏国开始,政府评定州郡人才高低,分作九品,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这就是九品中正制。后来评定品级,首先看门第,名门大地主大官僚的子弟,总是被评为上品,世世代代做大官,把持了中央或地方重要官职,叫做“士族”。士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非常注重门弟身份的高低。他们生活腐化,很多子弟平时不读书,考试请人代笔,涂脂抹粉,头戴高帽,脚登高屐,出则乘车,入则扶持。有些人身体虚弱,不但不会骑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梁朝的建康令王复,出身士族,一见到马喷气和跳跃,就吓得要死,他对人说:“这是老虎,为什么叫马呢?”可见,士族是一群腐朽的社会寄生虫。“士族”以外的地主叫“庶族”,士族与庶族之间界线分明,门阀森严。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总是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加之东晋末年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肃朝纲,又不想收复失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出身庶族、家道中落的陶渊明要想实现其“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客观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才出仕,以后十多年里,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等职,不仅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特别是应酬那些胸无点墨,生活腐化又窃居高位的士族官员,这一切只能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和“违己交病”。陶渊明志行高洁,头脑清醒,正所谓“粗心人好过,细心人‘心’苦;糊涂者易混,清醒者痛苦”。在那个黑暗污浊的官场上,陶渊明既不愿做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也不愿当得过且过的昏官,因而他是最痛苦的,他无法忍受官场对人的本性的扭曲,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下,陶渊明早年便有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思想。当他仕途不得志的时候,就更怀恋这种生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所以,这十多年来他一直“一心处两端”,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三十九岁时,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此后,陶渊明因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又一度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去职,赋《归去来》。 ”(《宋书·陶潜传》)(督邮:官名,汉代各郡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唐以后废。《辞海》)从此,他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隐田园的道路。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这时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他放弃了“大济苍生”的理想,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同时也是勇敢果断的。因为陶渊明清醒地认识到:一旦辞官归隐,他的生活必将再陷困境,请看,尽管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地里的庄稼仍然“草盛豆苗稀”;他“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家居环境呢,“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而衣食住行更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尽管如此,陶渊明仍然勇敢地选择了归隐,决不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去来兮辞》可以称为陶渊明与污浊的现实勇敢决裂的宣言书。
归隐后的陶渊明,虽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解脱;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虽有“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洒脱,但他一直没有忘却现实,常常流露出对腐朽的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我们也终于明白了他在归隐后,为什么要“奚惆怅而独悲”,为什么要“抚孤松而盘桓”,为什么要发出“己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的长叹。这正是陶渊明在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为了保持高洁的节操,万不得已放弃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后,一种不便向外人道也的隐痛心理的反映。
陶渊明是伟大的,这不仅在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更在于他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后,或厌倦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出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处选择的自由,而平淡自然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