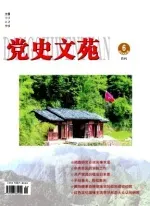湘赣边游击区留守人员的心路历程探析
2011-08-15唐颖华
黄 化 唐颖华
(南湖革命纪念馆 浙江嘉兴 314000)
湘赣边游击区留守人员的心路历程探析
黄 化 唐颖华
(南湖革命纪念馆 浙江嘉兴 314000)
留守人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以湘赣边游击区为个案,对该群体的心理和思想变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该群体长期处于心理危机的状态中,是主力情结、苏维埃传统和对组织的信仰支撑他们坚持下来,保证了湘赣边红旗不倒。
湘赣边游击区 留守人员 心理和思想变化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留守人员是一个特殊群体。目前对他们的深入研究还比较缺乏,经学术检索,尚未发现对该群体的心理和思想变化进行专题研究。本文以湘赣边游击区为个案,对此特殊群体的心理和思想变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1931年建立的湘赣省是中央苏区的重要侧翼。在敌人步步为营的第五次“围剿”中,湘赣省先于中央苏区遭遇生存困境。1934年4月30日,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必须及早突围”的建议并达成共识。会议还提出由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西征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大转移探路。[1]8月7日,红六军团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从遂川县突围西征。由此,湘赣边的革命斗争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一、生存危机、孤独感和主力情结的增长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带走了湘赣省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层和军队主力,同时也带走了红军学校、野战医院、制弹厂、修械厂等军事斗争的辅助机构。几乎抽空了湘赣边区的人力、物力、军力等革命和战争资源。[2][3]P29留守湘赣省的领导大都是临时越级提拔[4],在经验、威望、能力等方面与先前有很大差距,再加上职务竞争和斗争策略分歧,影响了领导层的关系和谐。以上因素导致战争的行政、人力和物力资源进一步枯竭[5]。虽然红六军团引走大批敌军,但留守人员仍然要面对10余倍于己的敌方正规军,周围都是敌人,留守军民被分割在十几块狭小的根据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
为掩护主力突围,留守军民必须伪装主力与敌周旋,怀抱着坚守战略支点的英雄主义豪情。随着周围地区迅速陷落,大量难民涌入尚存的小块根据地,各种失败传言开始传播。为稳定军民情绪,湘赣省委三天两头开祝捷会。“那些日子,不管识字的不识字的,手里都会捏一张套红的《红色湘赣》油印号外,在凉亭里,树荫下,南货铺里,津津乐道红军的辉煌战绩。”[6]P27人们沉浸在人为渲染的胜利气氛中。然而,主力红军越走越远,难民越来越多。祝捷会改变不了形势的快速恶化。10月,留守的湘赣省委和军区被迫突围,12月,湘赣苏区全部沦陷。由祝捷会到苏区全陷,在军民中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英雄主义豪情迅速下降。处于敌人重重包围和追击的情况下,他们的孤独感与日俱增。在突围中,为服从保留革命队伍的大局,被迫放弃难民[6]P33,军民分离使留守人员成为无源之水,陷入孤军作战的状态。留守人员大部分是本地人,这种剥离使他们背负沉重的内疚感,内疚使他们的内心更为孤寂。
主力越走越远的消息,在催使孤独感迅速攀升的同时,也强化了留守人员内心的主力情结。留守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主力回归坚守战略支点,主力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主力凯旋成为他们最大的精神寄托。湘赣苏区全陷后,面对敌人的屠杀,留守人员期盼主力回来报仇,他们的主力情结达到了最高点。留守人员的二把手谭余保在重病时整日呓语,叫唤着:“任胡子(任弼时)”,“王胡子(王震)”;[6]P40独立一团团长刘日患严重的肺病,临死还不忘恢复边区,时常大喊“红军回来了!”[3]P49由此可见留守人员对主力的渴盼之情。
二、主力情结受到打击与领导层思想分歧
一支屡战失利且日益缩小的孤军,与上级的联络成为他们在孤独中顽强战斗的精神动力。然而,1935年2月9日,仅有的一部电台在战斗中损失,自此,湘赣省委与中共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联系。4月上旬,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派一支小分队找到湘赣省委,转告中央红军已远征,中央苏区全部失陷,留守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已分5路突围,蔡会文率领的是其中一路,并且损失惨重。[3]P389这大大出乎湘赣边留守人员的意料,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3]P60,也发自内心的不愿意听到。他们的主力情结因此遭到沉重打击,失败主义和悲观情绪开始扩大。“反水”(叛变)像瘟疫一样迅速漫延。[6]P47
在主力回归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自寻出路并重树信心成为湘赣省委需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留守人员的出路主要有4种:叛变、开小差、游击战争和白区工作。第一次棋盘山会议(1935年4月初)虽然在失去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召开,但湘赣省委执行的是中央“七·二三训令”(1934年)加强游击活动和秘密工作的指示,其现实意义是为迎接主力回归起内应作用。从几天后蔡会文派出的小分队告知的情况分析,湘赣省的游击战争既失去迎回主力的内应作用,也丧失作为中央军区侧翼的价值,在敌人“民尽匪尽”政策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对留守人员的生存和发展远不如到白区工作资源丰富,白区工作有可能会大有作为[7]。实际上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13日给留守的中央分局电示“选派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工作”[8],但湘赣省的电台于4天前的2月9日损失,已不可能收到中央分局转达这一指示。蔡会文派来的小分队也未传达这一指示。在这种情况下,5月下旬,湘赣省委召开太平山会议。
太平山会议是一个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事件,它对湘赣边斗争的影响并不亚于第二次棋盘山会议。以游击战争还是城市白区工作为导向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这使谭余保和陈洪时矛盾激化。谭余保坚持游击战争是在严格遵循先前的中央指示,陈洪时提议的白区工作则是有利于留守人员生存的可能方向,因为国民党在乡村可以搞“民尽匪尽”,在城市则不能这样搞,这是白区工作的现实有利条件。然而,谭余保指斥陈洪时是“右倾逃跑主义”[6]P50。一旦戴上这顶帽子,在当时情况下下级也可以把上级当成动摇分子肃反。最后,太平山会议决定坚持游击战争,但谭陈二人的思想分歧以及“右倾”帽子成为陈洪时叛变的催化剂。太平山会议造成了留守人员坚守与逃离两种心态的断然分野。
三、生存绝境和对苏维埃传统的精神寄托
1935年6月14日,湘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陈洪时投敌。陈洪时叛变使湘赣省最高领导机关陷于瘫痪。他为敌人提供了大量机密,并带敌人前来“清剿”,许多群众和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先前形象光辉的最高领导人转瞬间变为反革命屠夫,“叛徒比疯狗还要可恶”[3]P53,这让留守人员愕然。在红军内部,“不少干部、战士心里都在考虑着今后向何处去的问题,部队出现混乱”[3]P99。由此引发第二次“反水”高潮,领导系统和党政军各级组织全面解体。零散的部队只剩下不足200人,湘赣边的斗争到了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
在湘赣边斗争趋于绝境的情况下,谭余保的固执和坚韧使他成为凝聚队伍、扭转斗争形势的关键人物。他尽最大可能,派人找到分散在各地的30来人召开第二次棋盘山会议(1935年7月)。会上怒斥陈洪时并清算其恶劣影响,坚定“不怕死,不动摇”的信念,重建湘赣边党政军组织系统,整编部队并坚持游击战争的策略。同时,纯洁内部,加强肃反。并发布《告群众书》,使湘赣边的红旗屹立不倒。棋盘山会议是重树红旗的关键,但也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一是彻底批判陈洪时,也就基本放弃了白区工作的可能选择,使剩余人员在出路上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离,对外界的戒备和心理隔膜增加。二是敌人以省委机关为目标,一旦发现就连续追杀十天半月,有时“七八天都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3]P331,这使队伍陷入生存的绝境。
1935年下半年是留守人员最艰难的阶段。长期处在被敌人追杀的环境中,也可能被战友认为是动摇者加以误杀,还可能随时病死、饿死,每个人的心态都很难维持健康。如何解决封闭环境下的心理变异成为维系这支队伍的重大难题。谭余保按照苏维埃时期的规矩为段焕竞和李发姑举行婚礼。他说:“就是再艰苦,也不能使我们陷于绝境,也不能使我们从心理上丧失正常生活的能力。”[3]P70谭余保充分利用“苏维埃传统”这个手段,逐渐把队伍的心理拉上正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列宁室,每日正常操练,培训党政军干部,鼓励士兵为将来革命发展时当干部而努力学习。这些措施,使队伍的心态开始由畸变向积极上进的方向调整[3]P142。
四、草莽英雄主义和自我封闭心理滋长
敌人经过一年多的搜山“清剿”,以为红军已被消灭,便把主力撤出山区,这使游击队得到喘息机会。为改善生活和改变恶劣的敌我态势,游击队开始打土豪、杀敌方县长和保甲长,以恐怖对付恐怖[3]P113。并搞两面政权、两面岗哨,派卧底,发展商人党员,改善了游击队生存的小环境。此外,还救济困难群众,带着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打土豪,打完后立即分钱分物,并为受欺负的群众主持公道[3]P180。这些措施,大大密切了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使游击队又成为有源之水,在群众的支持下再度生根发芽。1936年到1937年,日子逐渐好过起来,同时队伍的思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与中央和上级隔绝太久,游击队开始由着眼于全国的革命团体向地方会党转变,先前的革命战士也增加了许多草莽英雄主义情结。从先前因渴盼中央却得不到消息而产生的失落情绪和被主力“抛弃”而产生的怨气中逐渐走出来,同时对中央和主力的印象也开始淡化。而地方山头主义色彩却有所滋长,游击队领导人成为队伍的权威和感情寄托。
1937年6月,湘赣临时省委副书记、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仅次于谭余保的二把手曾开福叛变。曾开福原是肖克手下的老团长,很能打仗,为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已经渡过最艰难的时期,他却受外来人员的影响丧失革命信心转而投敌。这在情感上让许多人不能接受,造成“很多同志的思想非常混乱”[3]P213, 感到所有人都不能信任,于是,内部戒备之心增强。同时,为防止外界因素影响队伍稳定以及害怕上外来人员的当,谭余保下令采取封锁外来消息并警惕外来人员接近队伍的严厉措施,这使队伍再次走向自我封闭。
五、政策冲突、爱怨交加与回归中央的激动
与中央失去联系3年时间,游击队的主力情结已经相当淡化。在这个时候却传来越来越多中央指令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消息。这使队伍的主力情结再度复燃,思想出现新的波动,但在感情上却难以接受中央的新政策,去和“清剿”屠杀自己队伍的国民党搞合作。而且这与支撑他们坚守三年的“苏维埃传统”政策背道而驰,因此“认为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他们拒绝下山”,并把这些消息看成是反动宣传。有了曾开福的前车之鉴,他们更是绷紧了对外来人员的警惕之弦。这导致陈毅派出寻找他们的多位同志被当成“叛徒”误杀[9],陈毅只好自己冒险进山。
见到陈毅,谭余保大骂他是叛徒,并进行公审,还扬言要毙了他。陈毅被迫进行宣传鼓动,这使本已思想浮动的游击队分歧更大。谭余保只好派人下山证实陈毅身份的真假。当得知误会陈毅时,谭余保声泪俱下,挑了三年多的坚守湘赣边的重担终于可以向中央交差了。即使到这一步,谭余保仍然十分谨慎,当天深夜再去诱诈陈毅,却被陈毅进一步说服。谭余保又想了三天三夜[3]P378,方才允许陈毅下山。
谭余保经过痛苦挣扎,从怀疑到相信中央代表,最终以坚定的组织信仰战胜了个人情绪。在下山时,整个队伍充满了对热血浇灌的土地和生死相依的群众恋恋不舍的离别心酸与久经禁锢而渴望下山的复杂情感。[3]P148当项英和曾山代表中央来看望坚持到最后的留守人员时,“我们像一群久别亲人的孩子,忽然见到慈爱的母亲,泪水湿润了双眼”[3]P149。历经三年磨难,坚持到最后的留守人员终于找到心灵的归属,重回中央的怀抱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心理安慰。
[1]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M].香港:大风出版社,2009:85-86、90、93.
[2]编写组.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132-133.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湘赣边游击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第二卷上册[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481-483、495-497、505.
[5]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卷)[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715.
[6]刘健安.湘赣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几乎误杀陈毅的人[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1898~196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90.
[8]王辅一.项英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92.
[9]编写组.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02.
黄化(1975—),男,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馆员,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苏区史研究。
唐颖华,女,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馆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