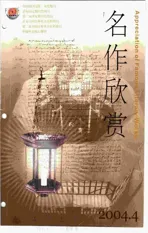仇恨的背后是控诉,是批判
——巴一小说《复仇》之命意探幽
2011-08-15重庆李安全
/[重庆]李安全
仇恨的背后是控诉,是批判
——巴一小说《复仇》之命意探幽
/[重庆]李安全
巴一的中篇小说《旋转的火光》发表在2003年第1期《红岩》头条;2004年第1期《中华文学选刊》头条转载;2004年《小说月报》转载;《新安晚报》《颍州晚报》2004年5月-7月连载。《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自由谈》《小说评论》《作品与争鸣》等报刊均对此小说发表了文学评论,后收入作品集《故乡在晚风中》。作家巴一坚持要将“旋转的火光”改名为“复仇”,我想,其中一定会有重要的原因。比如,在文本之中,有多处在字面上就是“照应”了复仇的。而且,小说所写的故事也就是于天成、于天良二十年后星夜兼程奔赴故乡“复仇”。但是,我们把小说读完,一直读完最后一行文字,“……在燃烧的火焰里,恩重如山的父母和他们的音容笑貌,再一次向天成天良兄弟俩走来……”就不得不做更深入的思考:作家所主张的“复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小说中的天成天良兄弟到底要向谁复仇呢?要到哪里去复仇?将怎样复仇?
自然,首先就是要向于庆复仇。是于庆奸污了天成的母亲,是于庆打死了天成的父亲于自海,是于庆毒死了天成家里的两头猪,因此也就杀人不见血地“杀”了天成的母亲。一句话,正是于庆害得天成一家家破人亡。所以,天成的第一大仇家就是于庆。所以,天成二十年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仇人,天大的仇人,就是于庆。所以,二十年后,天成要马不停蹄地回到故乡“于围子村”去“报仇”,首先就是要找于庆报仇。
如果就是这样一个“复仇故事”,那这篇小说顶多也只能成为《故事会》里的篇目,和“地摊文学”几乎是一个档次。但是,“绝不写地摊文学”的巴一不可能是这样的“简单”,这样的“肤浅”。所以,用心的读者就会发现,除了这样的“仇人”之外,似乎还有一个隐形的“仇人”,那就是“做官的”。小说开篇用了近五千字的篇幅来写于天成在广州羊城酒店接待从故乡颖城县来的马县长一行的场景。于天成断定,这马县长一行,如果不是骗子,那就是来请他于天成回家乡“投资”的。就在牛副县长说明了请“于总能不能投点资或在家乡办个厂什么的”来意之后,天成非常阔绰,一口许诺要在故乡投资三千万办一个中药厂。可是,这不过是一个“玩笑”。为什么会是一个“玩笑”呢?试想一想,这马县长一行到底是什么样的“官”呢?“我们老家至今仍然贫困,而这帮人在广州吃喝玩乐住酒店,花费的是谁的钱?”天成明白,他们花费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以为他马县长是我的恩人啊?”肯定不是“恩人”。不是“恩人”是什么?是“仇人”。所以,他从骨子里厌恨这些“官”。说到这里,或许我们就不会忽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那就是马县长问于天成的父母的那一个“细节”:
“于总许多年都没回老家了吧?”马县长见于天成默不作声,话锋又转向了他:“于总,你老家还有什么人啊?父母都在哪里呢?”
马县长无意中的这一句问候,却宛如一把尖刀剜进了于天成的心窝里。顷刻间,于天成的心口汩汩地流淌着鲜血。是啊,我的父母现在在哪里呢?如果父母真的在天有灵的话,此时,于天成肯定会大声地呼喊着:“爹,娘,咱们的县长来看你们二老来了!爹,娘,你们在哪里呢?”
于天成的面部刹那间痉挛着,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二十年,并不是“弹指一挥间”,而是非常漫长的,中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几乎是“换了人间”,可是,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官”,谁也没有为他的父母亲“平反昭雪”,谁也没有来追究那一桩离奇的强奸案,骇人听闻的“斗殴”案,令人发指的“投毒案”。就是“今天”这些“马县长”、“牛副县长”之类的“官”来找于天成,根本的目的也是要“招商引资”,为了“钱”,哪里有一点“公仆心”呢?所以,“于天成的面部刹那间痉挛着,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所以,天成要拿马县长一行来开涮,要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玩笑”。其实,这“玩笑”本身就是深刻的嘲讽,就是一种特别的“复仇”。
除了对现时的这一群“官”的描写之外,小说之中还写了一些过去的“官”,数得出“名字”来的是妇联主任、区里的头头即于庆的大哥,还有一群“官府”里里外外的人、“大队干部”、“区派出所穿制服的人”,还有县公安局、县政府。这一些大大小小的“官”的所有言行举动,构成一个主题,也就是《窦娥冤》里的那句话“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
再进一层,我们不能不思考,二十年后,于天成为什么不选择通过“告官”的方式来“复仇”呢?难道是作者故意要编制一个悬念丛生的“复仇”情结来吸引读者?其实,只要我们将二十年前的那些“官”,和二十年后的以马县长为首的这些“官”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官”和“官府”的深刻的“失望”。这隐隐约约的、散散淡淡的、看似可有可无的叙说之中,隐含着的是怨恨,是无声的控诉。
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应该是很多背井离乡的漂泊者的美好的梦。可是,小说中的于天成在“发迹”之后,并没有“衣锦还乡”,也没有主动回报乡亲父老,或许,表面上,他承受着思乡病的煎熬,可是,在骨子里,他却讨厌那一片故土,讨厌生活在“于围子村”的那一群“乡亲”,因为他们是那么愚昧,那么冷漠,那么软弱。
且看,在于天成家的猪吃了生产队的红芋之后,这些“乡亲”的表现是多么刁蛮,多么凶暴:
第二天早上,天成娘朦朦胧胧中,就听到窗外的红芋地里一片嚷嚷声。她一骨碌爬起来,让她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是谁不讲良心毁坏大家的粮食?”
“瞧瞧吧,这鲜水水的红芋都被踩毁了。”
“叫他赔偿!咱生产队里的人都去他家吃饭去!”
你一言我一语的愤怒里,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谩骂。
天成的母亲被生产队长于庆欺侮了,可是,那些“乡亲”没有同情,没有可怜,而是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将这不幸演绎成一个有滋有味的“桃色新闻”,到处传播:
“于自海的媳妇被于庆强奸了!”这种桃色新闻在农民的口中,几经创作和演变,成了有头有尾有故事的趣闻。田头间,杨树下,饭场里,三五个一堆,无不窃窃私语着于庆强奸未遂的“惊心动魄。”
在天成的父亲被于庆他们打死之后,这些“乡亲”以“闲嗑牙”、“骂大烩”的方式来“笑话”:
……而今年的腊月间的人场里,村人们“闲嗑牙”,“吃小名烩”的内容,全离不开于庆和于自海两家的“寒门艳事”。当然,“闲嗑牙”、“骂大烩”的人场里,没有他们两家的人在场,若有他们两家亲戚路过人场时,刚才还是妙趣横生加油添醋的笑谈,便会戛然而止,待他们两家的亲戚过去之后才能继续着谈笑……
如果将小说之中的这些片段“对应”起来,“联系”起来,你或许会觉得,这些“乡亲”尽管也是受到有钱有势的近乎黑帮的“于庆”的辖制,尽管也似乎是“敢怒而不敢言”,尽管也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忍气吞声,但是,对于天成来说,或许,他从这群“乡亲”的目光里感觉到的更多的还是冷漠,是麻木,是袖手旁观,是趋炎附势,是落井下石……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乡亲”们给了天成精神上、心灵上最沉重、最深沉的伤害。所以,于天成对故乡的思念里,似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悲凉,一种无法言说的怨愤。那一群“乡亲”,那记忆中的“故乡”,似乎也是他的精神的隐痛,也是他心灵的“仇敌”。
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在写到于天成乘坐火车回故乡时,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列车员和乘警们一起拿着票夹本清查铺位,乘警问他是哪个铺位的,于天成并不吭声,只是用手指了指旁边的下铺。“他心里厌恶这些乘警和乘务员。当年,他因为逃票被乘警打过多次,被乘务员拉进餐车跺过多少脚,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些只要塞给他们小费便能买到卧铺的记忆,酸楚而又清晰。”可以想见,于天成曾经是遭受过那么多的欺侮,那么多的痛苦。
“往事并不如烟”,几乎所有的记忆都是“愤懑和失落”,都是痛苦和愁怨。如果把以上的分析综合起来,我们似乎可以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于天成的仇人有于庆,有“官”和“官府”,有愚昧的“乡亲”,还有那些曾经鄙视过他的列车员和乘警之类的“陌生人”……这样推延开来,这于天成似乎就是仇视社会了。其实又未必,或者说,于天成虽然胸中填满了“仇恨”,但是,他并不主张“复仇”。准确地说,是作者巴一并不主张复仇的。
根据作家的艺术构思,二十年后,于天成千里迢迢赶回故乡“复仇”,可是那卑劣无耻、作恶多端的“于庆”却是被“善恶果报”的“潜规则”判处了“死刑”。尽管“天良不等老人说完,他已上前对准土堆的顶部,拼命地踩起来。他用不堪入耳的土话咒骂着,发泄着”,但是,那也不过就是“发泄”,不过是潜意识之中的“本能”。
如果作者主张的是“复仇”,那么作家就不会让于庆“死”,而是要让于天成用某一种既非法又合法的很特殊的方式去“复仇”,比如给他以精神的凌辱,或者让他进监狱,或者让他羞愧而自尽,或者是用类似于韩少功的“非法法”之类的方式来处置。自然,也有另外的“可能”,比如,看着老态龙钟的、行将就木的于庆,于天成兄弟或许也就心生悲悯,似乎在瞬间受到某种神秘的人性的感化,将“复仇”的情结消解,同时,小说之中人性的一面得以升华,仿佛是幻觉之中的佛光普照。
再说,作家所刻画的“官”也只是局限在“故乡”的那一片天地,局限在“乡村”,而且,作者对“官”的“复仇”也就不过是“记得”,或者是叫“怀恨在心”,对“官府”则是“无所作为”,甚至是“忘记”那些“无心正法”的“官”或“官府”。至于对“马”、“牛”之类的县长或副县长,作者也仅仅只是让于天成和他们“开玩笑”,即使是有嘲讽,有愚弄,有凌侮,但是,也毕竟是含蓄的,委婉的。或许作家就希望那些“马”、“牛”之辈能够由此警醒,悔悟,廉洁奉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可是多么善良的愿望啊。
对于那些愚昧的乡亲,那些曾经嘲笑过他们,讥讽过他们,在感情上是“零度”同情甚至是“负”同情他们的乡亲,于天成是无言以对,而且也无“颜”以对。于天成似乎是除了心生悲悯之外,也毫无怨恨之意。你看,小说的结尾写道:“全村男女老少几乎是全家出动,黑鸦鸦的一片人都在注视着于天成、于天良这两个苦命的兄弟。”有同情么?似乎有。看热闹么?似乎也是。有庆幸么?似乎也有。然而,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作者对这些“乡亲”的感情是复杂得很。有怨,有恨,有同情,有“哀其不幸”。但是,作者所采取的却是最简单的“群像”、“白描”的方式来处理,回味悠长。小说结尾部分中写到了一个“铁锤”:“铁锤一下子把天成抱住,哭个不止”;铁锤“抓住天良的手,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又放声大哭着”;铁锤媳妇的眼泪和鼻涕纵横满面;铁锤告诉天成,“于庆的腿被人家打断了,瘦得像个猴子一样。病死了……”在所有的“乡亲”之中,似乎只有这“铁锤”还是心存善良,这仿佛是有那么一点点“亮色”,让人感觉到那么一点点“人性”的温暖,可是似乎来得很“突然”,而且,在小说的前面一直都没有一个“铁锤”的影子。但是,我想,这不完全是叙事的需要,在“铁锤”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他希望天成的“乡亲”都会像“铁锤”那样有情有义,多情多义。
至于前面说到的乘务员和乘警那一类的“陌生人”,那是曾经歧视过、甚至欺侮过于天成的那些“陌生人”的“代表”了。但是,当乘警和乘务员“偏偏站在了他的跟前”,以责备的语气说“关灯这么久怎么不睡”时,“财大气粗”的于天成的“复仇”也不过就是“视而不见般地将目光投向了窗外”。于天成的“视而不见”中似乎包含着轻视、藐视、蔑视,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的“仇视”。虽然他并没有将曾经受过的“打”和“跺”忘记,但是,他似乎也不希望那些“仇恨”再延续。
总之,从这些“仇恨”和“复仇”的叙说中,我们分明地感觉到,文本之中最深刻的“意义”,最“永恒的意义”,不是“复仇”,而是隐藏在复仇的背后的“意义”,那就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控诉,对现实人性的一种批判,非常深沉的控诉,非常冷峻的批判。而这批判则源自于思考,源自于作家深刻的人性关怀,源自于作家内心的悲悯,源自于作家内心智慧精神的觉醒。换言之,我们透过小说的“复仇”看到的是作家对“复仇”的否定,再进一层,看到的是作家对社会、对人性的批判,以及对美好人性的期待。
小说采取的是双线交错并进的结构方式,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相互纠缠,城市与乡村相对应甚至对立。这样一来,“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就通过于天成及其一家的命运连接了起来。是“乡村”毁灭了于天成一家,又是“城市”成就了于天成一家。但是,小说的重点却是在于表现以“于围子村”为代表的“乡村文明”。二十年的历史变迁,于天成的家已经成为“已经坍塌的一大堆旧砖头,还有被风吹雨淋已经腐烂的木棍子”,“屋子废墟的周围,已长满了齐腰深的蒿草,蛐蛐发出嘶鸣声”,“跳来跳去的土蛤蟆,窜来窜去的大耗子,这一切,都无言地告诉他:这里早已是荒无人烟,这里早已是无人问津的地方……”这甚至让人联想到古诗《十五从军征》中的句子:“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从这里,于天成感觉到的是家的破败,破落,家破人亡,而我们读者,隐约地感觉到的是“乡村文明”的没落。一切都似乎“荒芜”了:纯朴的乡村文明没有了,或者说纯朴的民风民俗似乎从来就没有过,曾经的野蛮也似乎没有了。可是,新的“乡村文明”似乎也没有形成。乡村只是,仅仅只是一片“废墟”。
对于与“乡村”相对的城市,对于与“乡村文明”相对立的“城市文明”,作者或者故意地“淡化”了,或者是故意地回避了,或者要以“乡村文明”的衰落来“暗示”“城市文明”的兴起与发展,或许是因为要刻意表现“乡村”,所以也就刻意地“淡化”了“城市”。在这“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立之中,隐含着作者对“乡村文明”衰落的惋惜,留念;也有对“城市文明”的陌生与期待。或许,这正是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严肃思考与困惑的艺术表达。
真正聪明的读者,一定不会忽视,作家是用一种非常客观甚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冷峻在叙说这个让人痛苦、愤怒、深思的故事。特别是作家巴一对于天成的“感情倾向”几乎也是“零度”,作家并没有将于天成刻画成一个“高大全”的成功者形象,而是刻画成一个对过去耿耿于怀、却又无能为力的“成功者”,尽管他最后是完成了“复仇”,但是,他借助的却是“天意”,却是“因果报应”的世俗伦理。从于天成身上,我们分明地看到的是性格的矛盾,是“精神”的分裂。一方面,于天成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成功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复仇的失败者;一方面他对“于围子村”有着深刻的厌恶,另一方面,他对“故乡”又有着潜意识里的眷恋;一方面,他在城市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他在城市里又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甚至是一个落魄者,似乎缺少了一种精神的依归;一方面,他坚强,勤奋,精明,沉着,冷静,富有现代人所需要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偏执,狭隘,缺乏民主观念……或许,这也是“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相互纠缠的结果,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或一面。我们和作家一样,期待着“乡村文明”的复苏,期待着“城市文明”的发展,期待着“人性”的复归与完善。而且,我们希望,一切都不会是那么的遥远。
“什么样的作家可以称之为大家?我想,除了要有公认的杰作存世,还要以良知和公共关怀济世。”(丁东:《章诒和出山记》,《名作欣赏》2010年第7期)巴一曾经说过:“我绝不写那地摊货。”我想,阅读这篇小说,透过那文字,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描述,这些控诉,这些批评,这些期待,也分明就是作家的“良知和公共关怀济世”的艺术表现。我想,有了这样的“良知和公共关怀济世”,外加在艺术上的孜孜以求,作家巴一在不久的将来也就会成为真正的“大家”。
作 者:李安全,研究员,重庆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
编 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