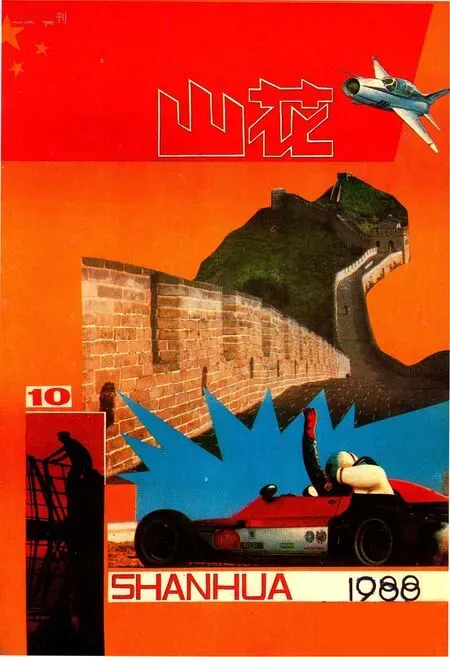人事二章
2011-08-15云亮
云亮
人事二章
云亮
感动
与朋友们在一起,总觉得日久天长,慢慢来,别着急。终于有一天,朋友们一个个不可挽留地飞走了,心境有些茫然的同时,禁不住慨叹一句:时间这东西,真是没治。
从主观上讲,我不希望交一些朋友,觉得朋友多了是一种负担。当然负担是多方面的,有时好事也是一种负担。可生活执拗得很,根本没有让你挑拣的份儿,结果我还是被一张巨大的朋友网罩在里面。
认识陈,是在一所大学中文系的作家班里。开学第一天,瘦高个的陈走上讲台,对着全班的人问:“谁是云亮?”
我先是一愣,接着慌乱地站起身,回答:“我就是。”
原来,作家班的录取通知书是由地区文联的一位副主席亲自送到我们文化局的。我们地区共录取了两名学员,就是我和陈。陈去领通知书时顺便打听到了我。
我和陈去买饭,因在操场逗留了一段时间,走进食堂,卖饭师傅很不耐烦,把我们冷得有些狼狈。盛饭时,陈把饭盒给我,说饭盒盛饭后热得没法端,去找张旧报纸。离开食堂,陈将一个沉甸甸的西红柿塞给我。
我吃惊地问:“从哪里弄的?”
“食堂里。”
我想起卖饭师傅那张拉得很长的脸。
陈笑着说:“就算是对他服务态度的一点小小的惩罚吧。”
我和陈躲在楼角吃西红柿,看见陈的西红柿明显地比我的小了一大圈,心里有点小小的感动。
都说文人相轻,但我和陈一直处得很好。来作家班两个月后,注意过我作品的文友见面后直呼我“诗人”。我和陈来自同地,年龄又相仿,听别人这样称呼我,他真心为我高兴。一次,我俩独处,陈说:“见别人诗人诗人地称你,我心里真有些嫉妒,可又嫉妒不起来,说实话,你的诗写得太棒了。”我谦虚道:“别提那称呼了,文兄们跟我闹着玩哪。”陈的脸一沉,认真地说:“你可不能这样想,应该发狠写出些有分量的东西,别负了人家。”他那种恳切的表情着实令我感动,心想陈真够朋友,可以长此以往地交下去。
半年后,我收到原工作单位的一份公函,言及单位缺人,要我迅速离校,不然将停发工资。我还没拿定主意,陈站起来坚决不同意我退学,并发誓说经济问题不用考虑,钱有他花的就有我花的,把我狠狠感动了一番。怎奈我这人虽然境遇一直不佳,偏偏改不了那股穷酸劲儿,不愿接受别人的恩惠,几经犹豫,还是决定退学。
离校那天,陈冷着脸送我。一路上,他挖空心思,发动了好几次思想进攻,差点使我离校的防线崩溃。临上车,陈气急败坏地说:“目光短浅!”
这个用了感叹语气带有贬义色彩的短语,在那时的我听来多么亲切,多么令我感动啊!
回到单位,我常常收到陈的来信和他新近发表的作品。我在为他的进步感到高兴的同时,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真挚的朋友而庆幸。陈得知我在写诗之余开始试着写小说,便要我把完成的小说稿寄一份给他。我把小说稿《焚》寄去,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说他对我的小说稍加整理后转给了一家文学期刊,估计刊发问题不大。后来因为选材的缘故,那家文学期刊把原稿退还给我,附信作了几分肯定,建议我另寄他刊。看着字迹熟悉的小说稿,我感动不已,这哪里是“稍加整理”,是陈改过几个错别字和句子后,重新认认真真地誊写了一遍啊!
我的小说在一家刊物发表后,我将一份复印件寄给陈,回信中得知他已转学到一所海滨大学,并邀我过去走走。我欣然前往。
客居岛城的时日,我和陈形影不离,谈不完的话题,叙不尽的童年趣事。一个黄昏,我和陈在岛城清新而略带腥咸的气息里漫步。陈提议说:“我们去读海吧!”
涉过湿淋淋的沙滩,绕过深深浅浅的积水湾,我和陈坐在退潮后的礁石上交谈。彼此虽然早已没有了初次见海的兴奋,但面对博大、深邃、波澜壮阔的大海,我们还是压抑不住来自生命深层的那种波及心灵的律动。不觉中,夜色加重,水天一体,陈低头惊呼一声。原来涨潮的海水已悄悄逼近了我们所处的礁石。我和陈匆忙离开。
回来的路上,陈讲起一个悲壮而美丽的爱情故事:一双恋人在退潮的礁石上逗留,忘我的倾谈中,潮水没膝,猛然发现四周茫茫一片海水,没有了归路……
讲到这里,他突然停住脚,测试似地问我:“你说说,他们该怎么办?”
我不假思索地说:“什么也别想,静静地等待被海水淹没!”
陈笑了:“这就是那个故事的结局,你的回答又一次证实了你我弟兄骨子里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
陈冲动地握住我的手。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他瘦高的躯体里蕴涵着的真诚、热切、亲近和感人的力量。
好人老童
老童是我的朋友中较年长的一个。
那年暑假,应文友之邀到外地参加笔会,我、写通俗小说的老童和写散文的小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
老童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不下田的农民。说他像农民,完全因了他的装束,老童穿着朴素,还习惯性地折起裤脚。说他不下田,是因为老童的皮肤虽然有些黑,但很细腻,细腻中透出点润泽,风里来雨里去的人很难保养到这种程度。
老童的文人气质集中在他的眼神。比如停电了,房间里燥热得难受,打开窗子,一阵风迎面扑来。一般人受了这凉风的爱抚,立刻会心旷神怡,喜形于色。老童则不想,一脸的凝重,仿佛那风根本没吹到他身上。但此刻如果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眼上,你会发现凉风带来的惬意正在他的眼里舒枝展叶呢。
刚与人接触,老童总是先定定地看一眼对方,这一眼是短暂而忙碌的。之后,与对方谈话,老童便将目光彻底从这个人的身上移开,仿佛他对对方的形貌早已烂熟于心。我曾跟老童开玩笑,说他初与人接触总是先用眼睛消化一番的。
我和老童的交往从他为我即兴表演的一段幽默剧开始。中午休息,我被老童一连串起床动作发出的声响惊醒,睁开眼,老童也在看我。他压低声音,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小心着小心着还是把你弄醒了。我摇头道,没有事,我也该起了。老童看看表,又扭头看看那边正在熟睡的小于,朝我使了个眼色,扯起床上的白床单,蹑手蹑脚走过去,把白床单平平整整地盖在小于身上,然后屈身坐在床沿,抬起手背作擦泪状,同时上身很有节奏地抽搐起来。我问老童做啥。老童掩着脸哭腔哭调地说,没看见我在向遗体告别啊!
我抑制不住哈哈大笑。
惊醒的小于看看我,又看看老童,皱着脸自言自语问道,童老师又表演啥节目了?
和小于并肩去会议室的路上,我说童老师真有意思,也别说,他演得倒挺像。小于笑了,说演员出身嘛,弄这个还不跟闹着玩一样。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老童来。
原来小于和老童是同一地区的,以前认识。老童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现在做区文化馆馆长,是地区电视台的特邀演员,常常在地区电视台表演山东快书。说着,小于忍不住夸赞一句,老童是个大好人啊!我问小于老童好在哪里。小于说,待人热情,诚恳,没坏心。
因了这些话,我对老童格外留心起来。很快便发现大家离开宿舍后,老童总是落在最后,侧着身依次推几下各个房间的门。我有些不解,过去问。老童说,看弟兄们有没有锁好门,有些小青年做事马虎,关不好门,让不法分子乘虚而入。
望着老童推门时一丝不苟的神态,我对他的好感倍增。
由于平时很少看通俗小说,我没留意老童的作品,便问他有没有带作品复印件啥的。老童连忙摇头,说他写的东西是给人看热闹的,没啥价值。小于插嘴道,童老师写得精彩着哪,侦破题材,一会儿动刀一会儿动枪,猛不丁冒出个死尸啥的。
笔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大家喝了不少酒。小于醉得东倒西歪,非要老童给我表演一段山东快书。老童说,醉儿咕咚的,演不好叫人家云亮笑话,以后有的是机会。小于不依,说朋友们聚在一起不容易,今朝分手,不知何时相见。
我和老童费了好大劲才把小于安顿在床上睡了。老童把脱下的白衬衣浸在脸盆里,撒了洗衣粉,哼着小曲说要回家了,穿得干干净净,让老婆高兴高兴。
一觉醒来,我看见老童守着浸着衣服的脸盆发愣,便问,看啥看得这样出神?
老童转过脸笑着说,小于把他的衬衣染成蓝的了。夜里听见哗哗响,没在意,小于把他的脸盆当成了尿盆。我凑过去一看,衬衣真的变成了淡蓝色。老童打趣道,颜色倒还可以,就是这印染方法不大有美感。我被老童逗笑了。老童嘱咐我不要把这事告诉小于,免得他知道了脸上挂不住。
和老童分手后,虽然没再见面,但我俩的书信交往一直没有中断。
那年,我在单位值夜班时接到老童的电话。说春节前省里要举行文艺调演,他们地区选送了他的节目,届时省电视台要转播,并告诉我转播的大概时间,要我看后谈谈看法。我向他表示祝贺后,问他准备得咋样了?老童说他本来准备了一个长段子,省里来通知缩短了时间,领导要撤下一个青年演员的节目,他觉得应该多给青年演员一些锻炼的机会,主动提议给自己换了一个短节目。
我禁不住脱口说道:老童,你真是一个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