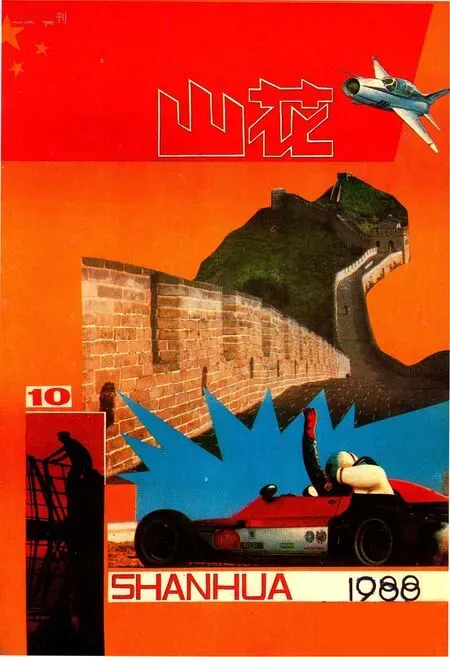废墟上的梦幻
2011-08-15宋茨林
宋茨林
废墟上的梦幻
宋茨林
青年作家丁杰邀请我重访胡家湾,重访双凤山。
他这是要我通过时间隧道返回39年前。那时,我不到20岁,在双凤山上那座清幽而又恐怖的古庙里教书,是胡家湾的村办小学老师。
我于1965年7月在原安顺地区二中高中部毕业,同年8月到原安顺县旧州区詹家屯人民公社苏吕堡生产大队插队当“知青”;次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倒流”回城,与宁谷和北坟两个公社的知青集中造反闹户口闹返城。后被安顺县的“走资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于是作鸟兽散搞“非法大串联”。说是“非法”,那是因为我们作为“知青”,已经成了“新社员”、“新农民”,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已发出联合通告,禁止农民进城造反,禁止农民大串联。不知当时的八亿农民怎样想,反正我们知青已经知道自己被愚弄、被欺骗、被抛弃、被歧视、被取消了“造反”的资格。1968年夏天,我串联回来了,玩够了,疯够了,到处武斗,百业凋零,无处安身;家里养不起,插队点回不去;造反填不饱肚子,城里没有什么活路可干。官办的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倒是农村里的贤达人士深知教育的重要和文化的可贵,纷纷由生产大队出面筹办乡村小学,所聘教师,大部分来自城市中学的毕业生,其中不少是重点学校的尖子学生。这些尖子学生不能继续深造,成为国家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流向农村传播城市文明,为若干年后的农村体制改革,做了悲剧性的文化准备。这些尖子学生在乡村担任民办教师,报酬极为低廉,仅够糊口而已。他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传播精神文明,与广大农民同甘共苦,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页。
我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于1968年8月来到普定县化处区化处人民公社胡家湾生产大队的民办小学教书的,时年20岁。胡家湾的这所学校设在山上的一座古庙里,山名为“双凤山”,庙名即为“双凤山寺”。我那时对这一庙名颇有“腹诽”;寺因山而名者多有之,如蒋介石先生故里溪口镇背靠雪窦山,山上有庙,名“雪窦寺”;胡家湾的这座庙名为“双凤寺”即可,何必多一“山”字?不仅略显累赘,含义也窄了许多!当然,“雪窦”二字引人玄想,非“双凤”二字可比,文野之分,不言而喻。但“双凤”二字多民间色彩,具平民格调,符合芸芸众生之口味,含“凤仪来朝”的吉祥之意。在双凤山下,离胡家湾不远有座古庙,名“仙人寺”。我在双凤山上教书时,要到化处场坝去必须经过仙人寺,但讹为“轩辕寺”。设若此寺与轩辕始祖有关,岂不伟哉大哉?后来才知道,“化处”者,乃“仙人坐化”之处也!在化处场坝边上建立庙宇并名之为“仙人寺”,是纪念仙人坐化也!仙人选择此处坐化,说明“风景这边独好”!但是问题来了:“仙人”是道家的“尊者”,道家讲“羽化登仙”,佛家求“立地成佛”。而“坐化”也是佛家的概念,好像道士是不讲“坐化”的。此外,一般来说,佛家的宗教场所名为“寺”,道家的名为“观”。为纪念“仙人”建寺且名为“仙人寺”者,殊不多见。再说,既已成仙,何谈坐化?
后来才知道,在我国,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儒教、释教、道教和祖先崇拜常常混为一体,互相掺和,多元并存,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在普定猴场的仙马,苗族同胞信奉天主教,与左近信奉儒、释、道教的汉民相安无事。这些现象,正好能够说明中国农村的广阔和中国农民的宽容,无伤大雅,也无须上纲上线的!
有趣的是,上述“双凤山寺”与“仙人寺”都曾办过农中,办过民校,“仙人寺”还办过幼儿园。书香与佛韵使这两座古庙,也使化处这个古镇显得文化绵远、韵味悠长!
双凤山寺办过一个大型的农中,据说还有师生宿舍和食堂,这就能够充分说明它曾有过的宏阔与轩昂。我在此处教书时,佛殿与禅房已被农中改造成教室与宿舍。但可以看出,它曾经有过的恢宏。殿宇高朗,系石木结构,用料及做工都极为讲究。二进天井为石板铺就,严丝合缝,平整得可以经受现代水平仪的检测!而周围的保坎与水道也通用料石砌就,有棱有角,该圆则圆,该方则方,经得起量角器的挑剔!难得的是,天井中植有桂树一株,中秋时节,桂花闲落,清寂无声。山雨之后,你可以身着白衫在天井的石板上静卧,绝不染半点纤尘!后山有鸟啼鸣,鸟鸣寺幽,实为化外之境!另外,寺庙前有一空坝,植有银杏树五棵,高可参天,浓荫覆地,树围均在四米以上!传说五棵银杏都已成精,常化作人形到云南四川作怪,故银杏树下有阴森恐怖之感,经过时须埋头疾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经二进天井拾级而上,是“玉皇阁”遗址,在半人多高的野草和灌木丛中,兀立着五根高及两丈的石柱,底座为石狮,柱均为整石整料,可以想象它们当年挺举着宏阔殿宇时的辉煌。后来殿宇毁于兵匪之火,空留有石柱与衰草,养育着狐鬼与神怪,诉说着人间的沧桑,酷似圆明园的景象。所谓“废墟文化”,此处应为“胜景”,使人体味到时间的苍茫!
那时,双凤山寺周围没有人家,寺庙离村寨较远。晚上,只有孤灯一盏伴我夜读,常闻寺庙的浓影之处发出怪异之声。入睡之后,常从梦魇之中惊吓而起,起坐四顾,月华如水,桂香盈寺,蟋蟀哀鸣,而远处隐约传来武斗的枪声,乃感极而泣,竟不知身在何处?这些景象,我都写在长篇纪实散文《庙与学校》之中了。
三十九年过去了,我的学校,我的庙,我的双凤山啊,你如今该是怎样的景象?
这一天多云间有分散阵雨。是一个热情之中裹夹着忧郁的日子,我与文化学者杜应国先生以及普定县的一些文友,到化处——这个“神仙坐化之处”做客。我以忐忑的心情期待着与胡家湾、双凤山的重逢,去寻找我失落的青春。因为那里的神秘和美丽,我的青春也因之神秘和美丽;如果那里变得平庸而丑陋,我的人生也将变得平庸而丑陋了!我曾向钱理群教授和杜应国先生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胡家湾和双凤山的神秘和美丽,就像描述我旧时的恋人,就像阿Q对人炫耀自己也曾经阔过。在我那样的年纪,有人在哈佛大学读书,我则在双凤山古庙里教书;哈佛的辉煌与阔绰自不消说,但双凤山的神秘与美丽举世独有,我由此找到了心理平衡,找到了生活的信心,找到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
双凤山,我的旧日的恋人啊,你能替我争口气吗?
天下着雨,化处的朋友买来了雨伞,我们,十多个男男女女撑着各色各样的花伞,在淅沥的雨中行进,是一朵朵行进的彩色蘑菇。胡家湾距化处场坝不到两里路,过去是羊肠小道,现在已经有乡村公路相通。我们安步当车,一边听着头顶上雨点的轻叩,一边移动脚步一边想着心事,变成了忧郁多情的年轻诗人!胡家湾在山槽里,双凤山寺在它东面的山顶上。乡村公路在村口分为两岔,往右进村,往左上山。在分叉口,我看见一个似曾相识的老者,精瘦而矍铄。我轻声对丁杰说:“这个老者我认得!”丁杰遂对老者喊话:“喂,老者,这个人你认得不?”老者笑扯扯地看了我好一阵,遗憾地摇摇头说不认得。我说你是不是叫张兴昌,他说是呀!我说你再好好看我是哪个?他走上前又用老花眼从上到下仔细把我过滤了一遍,最后还是抱歉地摇了摇头。丁杰急了,大声喊道:“这是你们的宋老师嘛!”那老者“哦”了一声说:“几十年了,记不得了!”
我当年在双凤山教书时,这个张兴昌的儿子是三年级的学生,张兴昌是贫管会的负责人,常与我打交道的,怎么就记不得了呢?我想他该有八十多岁了,一问,果然,八十三岁了!当年聘我到胡家湾教书的是大队支书胡光奇,志愿军复员战士。我问张兴昌胡光奇可好,张兴昌说走了,走几年了!当时的大队会计叫王义元,比我大七八岁的样子,与我比较相好,就是他把农中留下的几本书——《教育诗》、《堂吉诃德》、《费尔马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反杜林论》“偷”来送给我的。我特别问起王义元,张兴昌说也走了,前年走的!当年有个学生叫王正强,乳名“小国妹”,他的父亲叫王正忠,他的爷爷叫王什么,搞忘了,一家人对我都很关爱。特别是他的爷爷,每逢我到他家吃饭,老人都要换上干净衣服陪我,说老师是孔孟子弟,怠慢不得的。我想,这位尊师重教的老人如果在世该有百岁了吧!比他年轻得多的王义元都走了,想这老人已经大归,也就不再问了。
张兴昌问:“老师们不到家里去坐一下?”语气淡淡的,并不热烈。丁杰大声武气地说:“不去了,还有事!”
别过张兴昌,往左上山,走了不到百米,遇上两个背着背篓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时,觉得好生面熟。我对丁杰说这是我的学生,丁杰说几十年了你还认得?我说有印象。丁杰遂回头喊正在下山的妇女:“喂!你们在双凤山的学校读过书吗?”其中一个穿花格子衣服的回头说:“读过,我读过的!”丁杰说:“这是你们老师哩!”那女的想了想问道:“是从安顺城里来的吗?”丁杰说:“就是!”那妇女问:“是叫宋茨林吗?”丁杰说:“就是就是!你的耳性真好!”那妇女往坡下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我到场坝上去买点东西,一会就回来,老师到家里去坐吧!”语气也是淡淡的,也并不热烈。我想,三十九年前我来此地教书,只不过是为了生计为了糊口,并不是什么“志愿者”或“支教者”;我如今成了编辑、记者和作家,而胡家湾的乡亲和我当年的大多数学生依然是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年的幸苦劳作还挣不来我一个月的收入,我现在重返此地也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福音,我凭什么要他们记得我、欢迎我?生活的常态本来就是“淡淡的并不热烈”的,这是一种在苦难中练就的定力所呈现的常态啊!
但我依然感激这个学生事隔三十九年还记得我。她那时可能是一年级的学生,是我教她认识第一个汉字的。我叫丁杰问问她叫什么名字,那妇女回头大声说:“我叫张顺兰!”
通往双凤山寺的公路看来还刚刚修筑,是一条“毛路”。这是新一届化处镇党政班子的“新政”,听说他们要重新保护和发掘化处的地方文化了,双凤山寺也列入其中的一个项目了,这应该是一份迟来的爱吧?我闻此感到欣慰,亦复感到辛酸。
一行人撑着各色各样的花伞漂动着来到了双凤山寺,仿佛是一种彩色的朝拜,又仿佛是一次时髦的考察,旅游的热闹妨碍了心灵的体悟,大家都明白自己只是双凤山的过客,绝不是我三十九年前来到此地是为了避乱、为了生存、为了寻求精神的皈依。这体现出时代的进步,但也许同时体现着心灵的麻木。
哦,到了!但是,我呆住了,我为双凤山和双凤山寺的变化震惊得无话可说!寺庙前空旷的坝子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结实而又粗陋的农家房屋。原先那令人神往令人恐怖的五棵参天古银杏树只剩下两棵了!同行的普定朋友打量了一下,说剩下的这两棵银杏树其树围当在四米以上。在我的记忆中,不知所踪的那三棵银杏比剩下的这两棵还要高大!古老人留下话说这些白果树都是成了精的啊!砍伐它们是一定要遭到天谴的呀!三十九前显得那么宏阔轩昂的双凤山寺啊,如今在许多鄙俗的农舍的挤兑中显得那么衰朽!我问一个站在门口看过客的中年农妇是多久在山上建房的,她说有二十多年了。那语气也是淡淡的并不热烈的。我这才想起三十九年该是多么的漫长,世界能不变吗?人心能不变吗?
既然来了,进庙里面去看一下吧!
当年,这双凤山寺虽历经沧桑,屡遭破坏,而且还曾被改建为农业中学,但基本保留了大体模样,保持了石木结构,没有掺进砖和水泥,更没有那些丑陋的瓷砖。而今,许多木制构件没有了,西侧的禅房原先是木窗木地板,而今木作全部消失,代之以断砖乱墙了。东侧的禅房在当年幽静无比,共三大间六小格,其中一个面对天井的房间就曾是我的办公室兼卧室。就是在这卧室里,我曾挑灯夜读,艰难地寻求精神救赎之路,同时在夜半时分,立在窗前凝望天井里如水的月光,看桂花无声的闲落,听怪鸟忧伤的啼鸣,让灯花灿开出青春的梦幻……而今,东侧的房屋统统垮塌了,只留下佝偻的木屋架,还有我那间卧室的坚固的石窗。杂草在丛生,荆棘在疯长。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从我三十九年前的卧室里,神秘莫测地长出了一棵叫不出名的小树,就像是我当年的魂灵,倔强地从石窗里向外挣扎,仿佛要与今天的我握手,当年的我与今天的我在此相遇了,一个倔强的守望者终于迎来了同属他生命的另一部分——一个漂流回来的过客!
我把这棵树指给同在现场的杜应国先生,连应国也感到十分的骇异了!
但令我更为骇异的是,天井里那些平整如镜的石板没有了,天井中间的桂花树没有了,那些有棱有角经得起角尺检测的石砌保坎也没有了……那美丽的天井变成了一个凹凸不平的水泥坝子,显然是一个粗陋的晒谷场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能溢满那如水的月光吗?还会荡漾那醉人的桂香吗?
我心里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忍住眼泪,仰头去看高处的玉皇阁遗址,因为大门被人封闭,我们已不可能拾级而上了。依然是杂草疯长,王皇阁的废墟上依然是杂花生树,但是,令我更加骇异的事情出现了!酷似圆明园遗址的玉皇阁原有五根高及两丈的石柱,全系整石整料打制而成,而今怎么只剩下两根了?另外三根跑到哪里去了啊?
这已不是昔日的双凤山!这已不是昔日的玉皇阁!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这是什么?这是过客的梦幻?还是双凤山的梦幻?
我们都是过客,只有江山是主人。
如果江山都成了废墟,成了梦幻,我们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