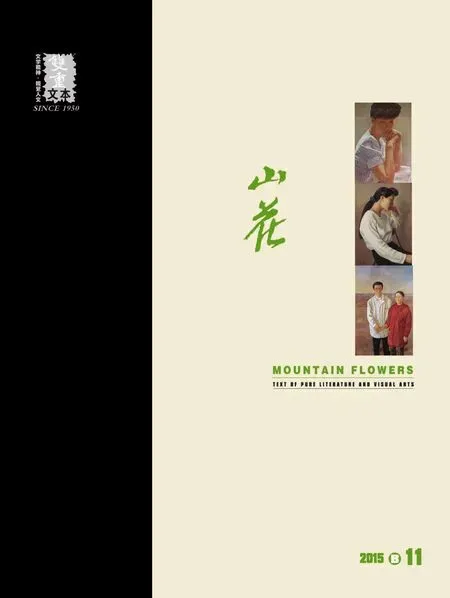论新月派对“五四”文学感伤情调的反拨与批评
2011-08-15
“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动了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和风行,对自我内在精神的关注与主观情感的表现,成为“五四”青年共同的心理倾向。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和青春意识的张扬,使其对情感的推崇走向了不加节制的放任状态,对情感的夸饰性描绘成为众多作家尤其是一般文学青年趋之如骛的写作风尚。“五四”作为历史的过渡期本就浪漫感伤的氛围因此更加浓重地在整个文坛弥散开来,加之中国文学内部源远流长的抒情主义传统对作家们潜移默化的浸润和他们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主动吸纳,“浪漫感伤”甚至成为部分作家内心深层的美感意识和自觉的审美追求,并进一步促使了“感伤情调”在不同文体的写作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感伤情调的风行一时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将思想启蒙作为首要的时代使命,因而使得与“五四”新思潮密切相关的新文学创作显示出了张扬理性的时代品格,但身处时代大潮的一代文学青年在作品中以理性精神进行批判和探索的同时,也以其青春的热情以及青年所特有的多愁善感抒发着自我的主体情怀,既有昂扬向上的情绪表达,也有浪漫感伤的情感流露。就文坛的整体情感氛围而言,“感伤”作为浪漫与理想的重要表征尤其浓重而鲜明地弥漫开来,甚至成为创作的主体情调。以诗歌而言,即便是郭沫若气势磅礴的《女神》也在豪情狂放的抒发中夹杂着哀伤的意绪;同期的哲理小诗也在对宇宙人生的深沉思索中流露出淡淡的感伤的余味;就是在理论上反对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前期新月派主将——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诗也并未摆脱惆怅和沉郁的情绪。相对地说,小说在一般意义上并非以抒情为宗,但“五四”时期的小说作者也在其创作中涂抹上了浓重的感伤色彩。盛极一时的“问题小说”在表现并讨论人生问题时,也低吟着隐约的感伤;较早呈现出流派风范的乡土小说也在审视宗法制农村市镇的同时抒发着渺茫的乡愁和感伤的意绪;而郁达夫引领的自叙传浪漫抒情小说更是热烈地诉说着伤感、哀怨的情绪。同样,这一时期创作实绩颇丰的写景抒情散文所抒写的也大多是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而田汉的“新浪漫主义”戏剧创作也充满着哀感和悲伤;甚至此期的文学批评也以其夸饰和激进的文风而呈现出情感泛滥的浪漫特征。尽管感伤情调在“五四”文坛的流行有中外文学资源的深刻影响、时代氛围的浸润,以及作家的美学意识等多方面合理而必然的因素,但“滥情”的倾向也导致了“五四”文坛“浪漫的混乱”。[1](P13)普遍弥散于文坛的感伤情调开始遭到试图以建构文学纪律和理性规范为目标的新月派文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新月的态度”——以理性节制情感
尽管新月派成员激烈地指摘文坛的浪漫感伤风气,倡导“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但实际上,新月派的诗歌创作最初也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他们与“五四”的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前期创造社有着很深的关系。郭沫若就认为,有些欧美派留学生,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多是受了创造社的影响。闻一多也曾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称赞郭诗“动的精神与反抗的精神”。在艺术主张上,前期创造社和新月派都认同“为艺术而艺术”,都将“美”作为艺术的核心。在诗歌情感的把控上,前期创造社注重主观表现和情感抒发,新月派也十分推崇情感,闻一多早期的诗集《红烛》就放纵着沉郁感伤的情绪,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也将忧郁和感伤融化在了空灵和潇洒的字里行间。但是,新月派注重诗情的抒发并不意味着完全任由感情的泛滥和对感情的过分依赖。他们追求的是情感表达的规范化和诗歌形式的完美。因而,闻一多又强调诗人不应在感情强烈时作诗,要求含蓄地抒写自我情愫或将主观情绪客观化;而徐志摩的诗也以精巧的构思和新颖的意象巧妙而含蓄地进行诗情的表达,从而避免了直抒胸臆可能引起的滥情倾向。可以说,新月派普遍不满前期创造社的“放纵”和“缺少理智”,而较自觉地遵循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和合精神和艺术古训,追求“节制”的美学精神,以期将艺术情感控制在适度、中和的境界。因此他们反对火山爆发式的抒情方式和诗情的不加节制,认为一味沉浸在情感的旋涡中而不能给诗情营造一个具体的境遇,这样的创作只会是无病呻吟或者言之无物。徐志摩更是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我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智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2](P404)新月派的同道中人陈梦家进而声明:“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3]这其中所追求的“本质的醇正”,实际上就是对新诗写作中情感抒发上的极端自由和放纵倾向的调整。
批判矛头——“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
以“理性节制情感”为美学目标,新月派开展了对浪漫主义的诸多反拨,并将其“病症”概括为所谓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首先发难的是新月派在诗论上的奠基者闻一多。他在著名的《泰果尔批评》一文中严厉批评了流行诗坛的小诗创作中出现的感伤主义倾向。认为,小诗深受当时时人崇拜的文学大师泰戈尔的影响而导致的缺憾和“短处”,使其创作普遍地只流于对人生的印象的单调的记录——“摘录了些人生的现象,但没有表现出人性中的戏剧,”使得新诗创作普遍地流于“空虚”、“纤弱”。[4]类似地,新月派另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梁实秋也明确甚至不无嘲讽地指出,小诗的唯一效用只在于记载零星的思想片段和印象,并且无论深刻还是肤浅,这些片段和印象都是零乱浮泛的。他进一步认为,小诗的这种“印象主义的趋势”在小说、游记、文学批评方面均普遍地存在着,其原因正在于感伤主义的流行和抒情主义的弥漫。并且由于未能对感情的质地进行理性选择,结果导致了“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 的泛滥。[5](P15)针对文坛风行的此种感伤主义症候,梁实秋提出了确立“文学的纪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希冀文学创作者们能致力于以理性来节制情感不加节制的放纵,倡导情感向理性低首,实现对古典主义“节制”的艺术精神的追求与践行。
客观地说,梁实秋对五四文坛的批评有其充分的学理性,而他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反思也有其深刻的启示意义。“五四”时期文学创作中婚恋题材作品的发达、爱情诗的大量出现,自叙传浪漫抒情小说感伤的无病呻吟,以及散文写诗、小说抒情而导致的廉价的人道主义同情等现象,在显示新文学勃勃生机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学纪律的丧失和文坛的“浪漫的混乱”。不过,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如此严厉的斥责并不意味着梁实秋对于浪漫派的完全否定。基于其学者型批评家平和的批评智慧和中庸合度的批评立场,以及一种植入骨髓的英美派绅士风度,梁实秋较为客观地对浪漫主义兴起的必然性进行了论说,并对浪漫派在“五四”文坛的价值予以了肯定。只是,倡导古典主义艺术精神和文学境界的梁实秋显然更为推崇超越情感因而更为可贵的理性和纪律,因而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场浪漫运动“其结果是过度的,且是有害的。”[6](P113)对于这种过度且有害的后果,曾经参加过创造社文学活动而后来加入新月诗社的饶孟侃也深有同感。他将当时盛行于文坛的感伤主义倾向看作是“新诗途径里绝大的危险”,认为这一倾向滋生和繁衍了一批“假感伤”的作品,宣告了新诗的“死刑”。[7]同样,曾自称“我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8](P3)的徐志摩也明确指出放纵感情的创作虽然使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但也导致了“无政府的凌乱”,因而有损于文学的“健康”和“尊严”。[9]而作为新月派叙事诗论的重要阐述者之一,朱湘也通过对“五四”诗歌创作的整体观照与审视,得出了“抒情的偏重”与“浅尝的倾向”是“新诗之所以不兴旺的两个主因”的结论,并进而指出,除抒情诗之外的叙事诗、史诗、诗剧等也“值得致力于诗的人去努力”。[10]
“新月”批评的学理高度和文学史意义
徐志摩等新月派文人对浪漫感伤的反拨和对“理性节制情感”的践行,在理论上是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及其诗歌审美趣味的一种反拨,而在实践上,则对克服“五四”新诗感情直露和泛滥的倾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新诗开始摆脱诗情泛滥的混乱状态,进入某种规范化的创作实践。但同时,这种节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诗作的现实批判力度的弱化。如朱湘的《还乡》,通过一个复员老兵的遭遇,一方面以反讽的叙事手法展示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不失其嘲讽现实、暴露黑暗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有意地运用辞藻与典故加以过滤,因而他的这些“工稳美丽的诗”,“缺少一种由于忧郁、病弱、颓废,而形成的扩悍兴奋气息,与时代所要求异途”。“作者那种安详与细腻,使作者的诗,在一个带着古典与奢华而成就的地位上存在,去整个的文学兴味离远了。”[11](P197)
但从整体上而言,新月派对“五四”文学感伤情调的批评,有着深厚的学理背景和文学史意义。尤其是梁实秋对于五四文学“滥情”倾向的指摘,实际上援据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作为批评展开的学术背景,显示了其批评实践的学理高度。白璧德是20世纪初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梁实秋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所倾慕的恩师。早在20世纪初,以白璧德为代表的西方新人文主义学者就曾强烈地抨击浪漫主义思潮,在白璧德看来,人性是善恶并存的,放纵情感和欲念产生恶,理智控制引导欲念产生善,所以为了将人性导向善的一面,就需要用理智控制欲念和情感。因此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学者十分反感浪漫主义者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过于肯定和对情感欲求的过于推崇,他们甚至将浪漫主义的精神楷模卢梭称为“罪魁祸首”,认为浪漫主义者放纵情感是病态的,其危险性正在于助长了人性中恶的因素。作为白氏虔诚的中国弟子,梁实秋秉承其“二元人性论”为理论依据,也认为情感应该向理性低首;而“五四”文坛过于推崇情感,轻视理性,因情感的泛滥导致了文学混乱局面的出现。因此,出于对文学纪律的自觉,梁实秋激烈地抨击“五四”文学的浪漫感伤与滥情之趋势。同样,闻一多指摘其时文坛的感伤主义流弊,也以《泰果尔批评》、《律诗底研究》、《诗的格律》等诗论中系统的理论表述为根基,可以说他是新月派的诗艺探索中最为积极而清醒的。而且,闻一多对于浪漫感伤的批评并不只是停留于理论反拨的层面,更为有力的抨击实际上源自其写作实践。他的诗集《死水》处处体现着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对于“五四”新诗情感泛滥的流弊,起到了药石之用。而朱湘对于新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的抨击,更是有着明确的理论方向,他对“滥情”倾向的理论反拨和在写作中的规避,实质上是对中国现代叙事诗论建设的自觉探索,显示了独特而重大的文学史意义。
就整个新月派而言,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人纷纷以新月派成员的身份整体介入到对浪漫感伤的批评与指摘中,并且又体现了相当一致的流派观点,因而似乎有门户之见、派性意识。但应该看到,在新月派一种普遍深刻而温文尔雅的绅士气度之下,他们更多的是企图在理论上为文学纪律和秩序的建设与维持,提供一种以理性精神为内核的情感制约机制,从而推动中国新诗的规范化运动。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才会对造成“文学的混乱”的浪漫与感伤情调大加抨击。因此新月派对“五四”过犹不及的滥情倾向的反拨在相当程度上有其合理性。而随着20年代后半期文学环境变化的影响,出于对时代使命的自觉,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的、感伤浓重的“五四”作家们纷纷转换了文学的方向,进而举起“革命文学”的大旗,反过来积极地展开了对浪漫主义尤其是感伤型浪漫主义的猛烈抨击,感伤情调文学开始在创作中消退。尤其是随着更为激进的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等革命文学阵营对浪漫主义的大清算和粗暴否定,“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感伤情调全面呈现出收敛之势。
[1]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之趋势[A].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9]徐志摩.新月的态度[A].徐志摩文集(中)[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
[3]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A].《新月诗选》[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4]闻一多.泰果尔批评[N].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3-12-3.
[5]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A].中国思想史论(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6]梁实秋.文学的纪律[A].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饶孟侃.感伤主义与“创造社”[N].晨报副刊·诗镌,1926-6-10.
[8]徐志摩.落叶[A].徐志摩文集(中)[M].北京:长城出版社,2000.
[10]朱湘.北海纪游[N].小说月报,1926-9.
[11]沈从文.论朱湘的诗[A].方仁念.新月派评论资料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