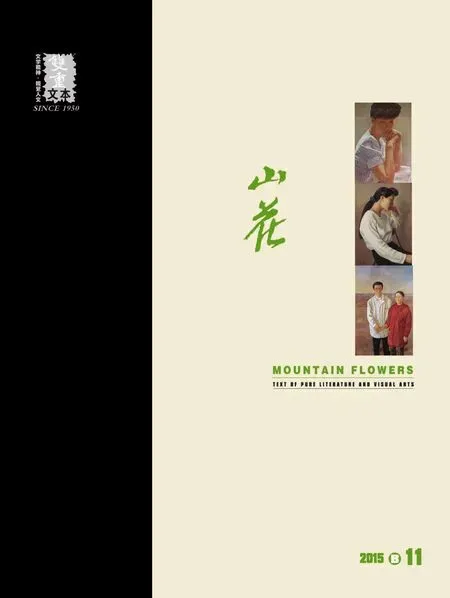孰是硬汉孰是夜莺?——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之比较
2011-08-15
前言
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与欧内斯特·海明威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外形相差甚远的二者有着不少共同点:年龄相仿,称得上20世纪20年代的代表作家;拥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均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层家庭,菲茨杰拉德来自于明尼苏达的圣保罗,而海明威出生在芝加哥郊区;都有一位性格懦弱的父亲和意志坚强的母亲;都经历失败的初恋并化伤痛为文学创作的动力;人格上都有着浓郁的自恋色彩。学术界中比较研究两位大师的专著、文章不计其数,然而从心理学角度,运用自恋理念探讨二者的文章却是凤毛麟角。
自恋(narcissism)一词源自希腊神话,汉语意思是水仙花。美少年那西斯(narcissus)因爱上自己水中的倒影导致憔悴而死,后化为水仙花。精神病学家及临床心理学家借用这个词,用以描绘一个人爱上自己的现象。自恋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作家有着特殊重要性,深刻影响着他们创作的思想与实践。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的人格虽然都属自恋人格,但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正常健康的自恋,后者超出正常范围,被纳入自恋人格障碍的范畴中,不同的属性分别对各自的人生和创作产生不同的影响。
理想的父母意象
自体心理学家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强调自体(self),它是一个空间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时间上是持久的,是创始的中心和印象的容器。自体是指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核心。自体客体(self object)则指“被体验为自体的一部分,或为自体提供一种功能而被用于自体服务的人或客体。”核心自体有两个主要成分:夸大的自体(grandiose self)和获得父母的理想化意象的需求。夸大的自体涉及儿童的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他对于被赞美的异常喜爱。科胡特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恋的。如果自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导致正常发展必需的夸大自体和理想的父母意象的缺失,个体就将维持防御性的和膨胀的自我意象,并且在成人的关系中寻求镜映和需求的满足,如果得不到成人的适应反应,这一需求就会发生变异扭曲,驱使产生病态的妄自尊大追求,从而形成自恋人格障碍。[1](p192-195)
菲茨杰拉德出生在美国圣保罗市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母从小对他十分关爱,母亲尤其对这唯一的儿子宠爱有加、有求必应。米勒(Neal E. Miller)认为自恋的发展是被父母给予过高价值感的结果。……他们被父母当做一个特殊人物来对待,受到过多关注,于是他相信自己是可爱而完美的。[2](p14-15)这种溺爱导致年少的菲茨杰拉德产生夸大自体的自我价值感,但是幻想很快被现实无情地粉碎。由于自身家庭在上中产阶层的暧昧地位,让他很小就尝到痛苦的滋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位于上等街区的下等住宅,”[3](p74)他“因自渐形秽而痛苦万分……因为……他是一个在富家子弟学校里就读的穷小子,”[4](p9)因此,他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产生了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对父母也产生了反感,之间的感情有了隔阂。幸运的是,积极鼓励和扶持菲茨杰拉德从事文学创作的新人学校的校长——西里尔·费神父,以其完美的代理父母形象及时弥补了他受损的父母意象。成年后的菲茨杰拉德能够把理想化的父母意象转化成现实意象,客观评价父母,肯定他们对自己成长的正面影响,这在他的短篇《作家的母亲》(1936)和未完成之作《父亲之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在菲茨杰拉德自恋发展过程中,父母意象是良好而积极的。
相比之下,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橡树园的海明威则是不幸的。根据科胡特的观点,自恋来源于共情的母亲功能的创伤性失败,以及父母的拒绝或冷漠所导致的正常理想化过程发展的失败。[2](p13)海明威与双亲,尤其与母亲的关系极其紧张。在他心目中,“母亲一直都是在暗中主宰着他内心世界的凶恶女王”,[5](p72)一直粗暴地干涉他的人生。小的时候不仅被母亲当作女孩来打扮,还被迫学习音乐,不管是年少还是成人的他从未得到过所期待的母爱和照顾。母亲的性别模糊教育和共情功能的失败严重地损伤了海明威健全的心理结构的发展。对于父亲海明威医生,他的情感是复杂而纠结的。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海明威是第二个。他与父亲之间的感情随着家中人口的逐渐增多经历了一个由最初的崇拜热爱到疏离恶化,再到最终的轰然崩溃的过程,父亲的自杀行为给他带来的是持续一生的恐惧和焦虑。理想化的父母意象的严重缺失阻滞了海明威的自恋人格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他滋长被父母之爱遗弃的无归属感和低自尊感,这种精神创伤给他的成人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人际关系
心理学家认为孩子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关系会影响到孩子成人后与他人建立有价值的依恋关系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一点,菲茨杰拉德与海明威各自的人格魅力特征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友谊从亲密互助、逐渐冷却到最后的充满敌意,令人欷歔不已。
菲茨杰拉德为人谦和,豁达大度,乐于助人,从不自命不凡,善于倾听他人并提出中肯评价。这种在他人角度体验他人苦与乐的出色的共情能力使他胜友如云,在他有生之年,他与许多活跃在20世纪文坛上的文学艺术家结下深厚的友谊,赢得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景仰。此外,菲茨杰拉德还大力扶持许多文学新秀的成长,譬如不遗余力地主动提携海明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菲茨杰拉德早期的指引和帮助,就没有后来成功的海明威。两人之间的友谊曾在美国文坛被传为佳话,菲茨杰拉德视它为自己生命中的亮点。但是成名后的海明威对待这位好友却是毫不客气,曾以不能容忍他醉意蒙胧的来访而干扰自己正常的创作为借口,居然在搬入新居后拒绝给他留下地址;在专著《非洲的青山》(1935)中虽没有指名道姓,却把菲茨杰拉德描写成一个文思枯竭、失败的作家;在另一短篇《乞里马扎罗的雪》(1936)中菲茨杰拉德的形象更是直接遭到贬损。相比之下,海明威为人强势得多,采取一种超出正常范围的乖戾的交友方式。在科胡特看来,与父母之间创伤性的情感失败带来的发展滞固着在原始的婴幼儿的无所不能的精神结构里。随后,作为一个未满足的原始需要,残留在成人的真实自我里,消耗自我的能量,作为一种补偿,以对赞美无限的需要来证明自己的无所不能,临床中表现为病人的无满意感,低自尊,丢面子。对赞美成瘾和忧郁症的倾向或较明显的攻击性。[6](p413-425)海明威苛求他人,对妨碍他的创作或违背他的意愿的人常常毫不留情,只要他认为“不够格”的人都会被他从朋友名单上“勾销”掉。[7](p132-133)。尤其是成名后的他无限夸大自己的长处,无视自己的短处;也听不进他人的批评,刚愎自用。不仅奚落、嘲弄朋友,甚至攻击、辱骂恩师和前辈,安德森、斯泰因、福克纳、刘易斯、艾略特、德莱塞、沃尔夫、赛珍珠等文学名家都在他的名单之上。
两者对待爱人、家人的态度也是天壤之别。菲茨杰拉德耗尽一生的浪漫和精力,勇于承担责任义务,照顾患上严重精神病的妻子珊尔达。尽管是红颜知己的职业影评人希拉·格雷厄姆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他也不忍心抛弃在医院饱受疾病煎熬的妻子,将两人的婚姻走到了最后,并悉心抚养、教育女儿司各特,成为一名尽责、合格的父亲;海明威则是家庭观念淡薄,讨厌家庭的束缚和被干涉,不能尽到做丈夫甚至做父亲的责任。他一生都在选择逃避面对问题:用离婚来解决婚姻问题,无论过去的妻子是富有还是忠贞、是温顺或是独立;用离家出走来躲避做父亲的责任,尽管孩子才刚刚出世。
可见,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得菲茨杰拉德夸大自体正常发展的需要在成人关系中得到了适应和满足,使其自恋人格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促进其艺术创作。海明威则恰恰相反,貌似体现他魅力无穷的的四次婚姻暴露出他对女人情感的不确定,内心的胆怯和自卑;而强势的交友方式无法满足其膨胀的自我意象的需求,导致妄自尊大的追求,最终演变成自恋人格障碍,给自己带来人生悲剧。
男主人公形象
作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创作过程中会有意识或潜意识地以自我为中心来衡量和评判一切事物,这种现象是自恋人格的一种表现。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凸显自我,其自恋人格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是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
海明威的“硬汉”形象深入人心,“硬汉”们坚守“在重压下的优雅风度”的道德准则(moral code),冷峻坚毅,永不被打败。“一战”后的美国经济繁荣发展却又百废待兴,人们处在一个信仰缺失而又急需重建精神家园的困境,极度渴望帮助和引导。海明威塑造的“硬汉们”的适时出场恰好满足这种心理需求,成为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性无能的杰克·巴恩斯(《太阳照样升起》,1926),从战场逃跑的弗雷德里克·亨利(《永别了,武器》,1929),义无反顾去炸桥的罗伯特·乔丹(《丧钟为谁而鸣》,1939),还是孤身与鲨鱼苦苦搏斗的圣地亚哥(《老人与海》,1952),都被赋予了无限的力量和至高的勇气。然而精神上的胜利实际上暴露了内心深处的懦弱和自恋,“硬汉”们矫揉造作的行为超越了真情实感,成为折射海明威的自恋人格障碍的一面面镜子。作家本人却一直沉醉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身体力行,特别是在1954年登上创作生涯的巅峰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之后的他更是无法摆脱对荣耀和高大形象的患失。海明威这种病态的自恋让他无法正视残酷的现实:衰老、疾病缠身、性功能丧失、精神抑郁……这一切最终使他追随父亲的脚步,选择了饮弹自刎,企图给世人保留完美的“硬汉”形象,殊不知这一行为使他内心极度的无助、畏惧和恐慌暴露无疑,也无力反击别人指责的怯弱和维护他珍藏的男子汉声誉。
“如果说海明威到后期在他自己创造的假象中越陷越深的话,那么菲茨杰拉德则始终是清醒的。尽管他也常常沉溺于幻景无法自拔,但即使是这种时刻他也没有丧失批判的能力。”[8](p192)20世纪20年代是强调个人享受、提倡自我满足的时代。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男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灯红酒绿中的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绅士,他们是“爵士乐时代”狂欢者的代表。然而这些外表奢侈、放纵、不羁的绅士内心中却始终保存一份超越庸俗价值观的自尊。从道德困境中突围的尼克·卡罗韦(《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到对爱情充满浪漫幻想并为此付出生命的杰·盖茨比,再到错将移情当真情、最终孑然一生的迪克·戴弗(《夜色温柔》,1934),他们无一不是作者人格的立体写照。但菲茨杰拉德健康的自恋性质使他避免了海明威的那种过度自恋的倾向,在《崩溃》系列文章中,他直面自己的文学生涯和心路历程,深刻而又坦诚地解剖自己的缺点和过去。在公众看来,“都市俊男”的菲茨杰拉德在性格上似乎比“粗犷”的海明威懦弱很多,但在面对厄运和灾难时却比海明威坚强很多。他坚强承受30年代后期的贫困、凄凉和种种不幸,直到因过重的生活压力导致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正是“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了。
结语
揭开自恋人格这层面纱,我们看到两种风格的男主人公形象,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家本人的自恋人格特征并迎合了那个时代的美国大众的心理需求;我们也看到两个迥然不同的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评论家亚瑟·密兹纳的话是对前者最好的注解:“他的身上虽然有着一些明显的错误和缺陷,但是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9](p8)在这个意义上,菲茨杰拉德无疑是硬汉。而假如海明威能够像菲茨杰拉德一样正确对待自恋,冷静面对现实,尽可能避免自恋带来的诸如狭隘和偏执等消极影响,他可能会带给世人更多的期待。但海明威正如斯泰因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 “他用残忍当盾牌,以掩盖其惊人的胆怯和敏感,”[10](p27-29)却是受伤的夜莺。硬汉与夜莺合曲高歌,给美国文坛留下一段传奇的变奏曲。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硕士科研启动资金项目 文号:F-407
[1]〔美国〕米希尔·克莱尔著.贾晓明,苏晓波译.现代精神分析“圣经”——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2]章娅.自恋人格一生发展特征及自恋者自我提升策略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07.
[3]〔美国〕库普曼(Cooperman S.) 弗.斯科特著. 王小梅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英汉对照[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4]吴建国.菲茨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美国〕肯尼思.S.林恩.海明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Heinz Kohut. The Disorder of the Self and Their Treatment: An Outline.Int. Psycho-Anal.1978.
[7]〔美国〕A.E.霍契勒著.蒋虹丁译.爸爸海明威[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8]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9]〔美国〕菲茨杰拉德著. 巫宁坤等译.菲茨杰拉德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10]卡洛斯·贝克著.林基海译.海明威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