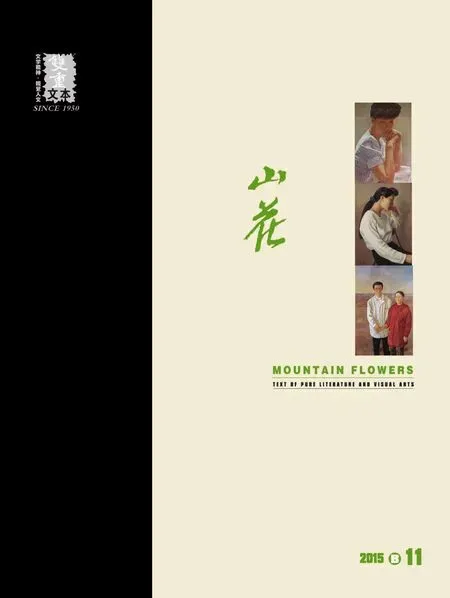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三死》和青年时代托尔斯泰的生死观
2011-08-15于正荣
于正荣
《三死》是托尔斯泰1858年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那年他30岁。作品无论从篇章结构、故事情节乃至人物形象等方面跟托尔斯泰以后体现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无法相比,但在这部小说里,托尔斯泰并不只是简单地介绍三个生灵的死亡过程,而是透过死亡过程来诠释如何看待生存与死亡的这样一个永恒的题旨。小说篇幅不长,但道出了青年时代托尔斯泰对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思考。
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从头至尾讲述了三个生灵的死亡,但读后却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所谓的三死是指三个生灵之死:生病的贵族地主太太玛特廖莎、贫穷的马车夫费多尔和大树。
玛特廖莎天生丽质,生活在上流社会,家境殷实,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身体不好,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本打算到国外去治好病却没成功,就死掉了。马车夫费多尔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孤苦伶仃,是个没家没业的异乡人,他也得重病死了。年轻的马车夫谢廖佳在收下病入膏肓的马车夫费多尔送给他的靴子时,曾许诺给死后的费多尔买块石碑,但因经济状况窘迫,他只能砍下一棵树,给费多尔的坟上立个十字架来代替石碑。虽然谢廖佳部分兑现了诺言,但却牺牲了自然界一个无辜的生命。
下面我们来厘清一下小说的脉络。我们先从分析贵族地主太太、马车夫之死的过程演进,来考量两种不同阶层的人对死亡截然不同的态度:贵族地主太太玛特廖莎惧怕死亡,而马车夫费多尔平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两种生死观形成鲜明的对照。
托尔斯泰认为,“贵族地主太太一方面可怜、可悲,另一方面又自私、虚伪、撒谎、可憎”,一生都不能直面自己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现实。她不顾丈夫和家庭医生的极力劝阻,执意要到意大利和德国治病,认为到了国外身体就会很快复原。但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受不住这长途跋涉、车马劳顿的折腾。从一开始她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却不敢承认,甚至听到“死”(умереть)这个词都会令她毛骨悚然:“别吻我的手,人死了才吻手呢。”[1]她一直在忍受着病体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煎熬。尽管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故意隐瞒自己的病情,为的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极力在众人面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她不想就这么死掉:认为自己还年轻,有权利享受丰裕奢华的贵族阔太太的生活,有权利对自己的家人指手画脚、对自己的下人吆三呵四,有权利享受这种生活给她带来的无穷的乐趣。虽然她家缠万贯,但金钱却买不来健康。日益加重的病情使她变得敏感和歇斯底里。她成了一个十足的自私者。只要自己不高兴,只要认为自己被冷落,她就会和家人、下人过不去。她把一切身体上的不适和痛苦归罪到家人身上,埋怨家人,呵斥下人,嫉妒周围所有健康活泼的人,包括自己的一双儿女:“他们谁也不管我…… 他们身体好,所以他们不在乎”,[2]“孩子们没病,可我有病!”[3]“周围的一切都糟糕透顶,人也让人厌烦——因为他们留下来活着,我却要死了。对丈夫,她不住地责备;而孩子呢,死前她都不想看上一眼。”[4]
与这种生存对立的是一个马车夫费多尔深刻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与死亡。费多尔蜷缩在空气闷浊的厨房里——壁炉边上的一角,“时间不短——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既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又要忍受厨娘纳斯塔西娅无休止的埋怨和唠叨以及周围人对他冷漠的白眼。厨娘不满意,他整天无所事事,还占着厨房的一角。尽管这样,他也不拒斥死亡。他知道死之将至并顺从地接受。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太穷了,没人可以帮助他并挽救他的生命,他也指望不上任何非亲非故的人。他只是担心自己会妨碍那些健康人的生活,怕成为大家的负担。他又是一个善良的人,当感到生命垂危时,把自己唯一的“家产”——一双新靴子给了年轻的马车夫谢廖佳,同时要谢廖佳在他死后在他坟前立碑,并让小木屋里的其他人做个见证。虽然他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但在他的心里并没有泯灭一个朴实的庄稼汉的良知和做人应具备的善良品质。
费多尔死得安宁,在夜里,在大家酣睡声中默默地死去。费多尔对生存与死亡看得比较开,洒脱自然,内心宁静,不拒斥死亡,所以他死得淡然。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什么信仰可言。但他有着另一种生活信仰,尽管他也在言称信仰上帝。他相信他所崇尚的大自然,遵循生老病死的规律,因而能心态平和地面对死亡。一个行将就木之人滞留在这个世界上,耽搁了一会儿,这是自然的真实。马车夫费多尔临终前说了一句“我就要死了”(Смерть моя пришла)[5],同样体现着自然的真实。朴实而简洁的话语充满哲理,平静自然的态度让人感觉到内心的恬静。以劳动为内容的生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和真实再现。[6]费多尔认为,死是对病痛折磨的解脱,也是落叶归根、朝见上帝的有效途径。正如叔本华说,“如果死亡终于到来而解散了意志这一现象,那么死作为渴求的解脱,就是极受欢迎而被欣然接受了”。因为此时“在这庄严、圣洁和伟大的死亡面前,一切不和、一切怨恨、一切误会都烟消云散”。[7]从这个角度出发,地主太太的一生都是在欺骗、谎言和幻想中度过,其实早在死神降临之前,她的灵魂已死。
至于“大树之死”则是托尔斯泰描写“死亡”的一种新体验。相对于贵族地主太太和马车夫之死,大树之死则完全是“无辜的”,但是它不是人,只是植物,一个生灵而已。它在强大的人类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如此软弱无力,以至于根本无法预知自己的死亡,一切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而它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它显得异常平静。托尔斯泰说:“……树死得泰然,诚实并美丽。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不撒谎,没有扭捏作态,不弯曲,无所畏惧,无所惋惜。”树死得平静、诚实、壮丽:“大树浑身一阵战栗,歪斜一下:又迅速挺直了腰杆,惊恐的战栗渗透到了它的根部。顷刻间一切都沉寂下来,可只过了一会儿,大树又弯下腰,在它的枝丫间,又响起了一阵阵斧斫之声。随着枝干“咔嚓咔嚓”地断裂,这棵大树一头栽倒在大地上。斧斫声和脚步声静了下来。一只红胸鸲啼叫了一声,拍打着翅膀飞上了另一处高枝,而它刚刚驻足的树枝,摇晃了一下,带着满身的叶子,和其他树枝儿一样,一动不动了。”[8]
托尔斯泰一生都崇尚简单的自然、真实,在《琉森》中他向往自然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在《三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树死得壮烈且死得其所,它死于为人所用。托尔斯泰高度赞美树之死,因为他悟到:这棵大树并没有像人的肉体那样彻底消亡,因为“树被砍光了,还会长出来”,只是转化为永恒大自然中另一种生命的形式而已。在小说中,这一植物生命的消失与价值,显然是被作家用来对照不同阶层人物的精神世界:贵族心灵的虚假、卑琐,劳动者心灵世界的质朴、博大。 “是一种最高级的真理和必然,农民与之趋近,地主太太则与之无缘,与之对立。”[9]
从小说中,我们还会感受到,玛特廖莎并不笃信上帝,虽然声称自己是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具体表现为:1.她时而表现出对上帝的虔诚和笃信:“别做我的思想工作了。也别把我当小孩子。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什么都明白的。我知道,我活不长了 。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的罪孽都很深重,这一点我知道。可是我相信上帝的仁慈。人人都会得到上帝的宽恕的,应该是这样的……我的罪孽也很深重……”[10]“我现在的心情真的好极了,我所体验到的甜蜜感是多么不可言喻呀……上帝是多么仁慈呀!他既仁慈又万能,难道不是吗?”[11]她一边说着,一边满怀热切地祈愿,用饱含泪水的眼睛凝视着圣像。2.时而又表现出对上帝、对基督教义的怀疑。她自以为自己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可是“我受了多少苦啊。我一直在忍受我的苦痛……”[12]反过来却埋怨自己的丈夫,“你从来就不愿意按我说的去做……我说过多少次了,这帮庸医都是废物,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倒是有一些很平常的女郎中,她们能治好病人的病……神父不是说过……有个做小买卖的,……去把他找来问问呀。”[13]她默默不停的祈祷却无法换来上帝与大自然对她的垂怜,因为她虽然“热烈地”祈祷了很久,但“她的胸部还是那样疼痛,喘不过气来;天空、田野和道路还是那样阴霾,那同样的秋雾,既不密,也不稀,依旧落在泥泞的道路上……”[14]当发现上帝不再赐福于她的时候,她便开始抱怨上帝的不公,甚至在临死之前也无法释怀“当一个人想活的时候,上帝为什么非要让他死去呢?”所以,玛特廖莎对上帝的信仰只限于表面工夫而已。可见,作家早期的思想就认为,基督思想的关键不在于仪式,不在于你是否是个信徒,而在于你有没有爱的精神,爱你周围的人,爱这个世界,有没有以爱为理性支撑的对人、对世界的认知!
在这些人的生活和行为中,“上帝是缺席的”,尽管他们常常口口声声喊着上帝!他们只是到了生命危机或者陷入生活不如意时才会想到上帝的存在,他们兴许也会定期到教堂做礼拜,也会跟着神父念些祈祷词,可是上帝和基督教的真谛是什么,也许直到死神降临,他们,包括地主太太,还是对此懵然无知。所以在小说第三部分结尾处,作者描写了一个诵经士在为地主太太诵经以超度她的灵魂:“掩住你的脸吧——不然,别人会发窘的。摄走他们的灵魂——他们就会死去,变成灰烬。注入你的灵魂——他们会重生并让大地焕然一新。愿上帝荣耀永存”。[15]这首圣诗所隐含的永恒的、普适性的基督教真理也许是地主太太永远无法理解的,所以才有了作家“关于她是否会明白圣诗中的伟大真理”[16]的追问。
地主太太玛特廖莎的家里充斥着谎言和虚伪。丈夫与她一样,对上帝的信仰也只限于语言的形式,对妻子的关心和呵护是不真诚的,除了“哎,你怎么样了?我的朋友?累了吗?”[17]他什么也不会说,除了“安静地等待妻子的死亡”,他什么也没有做,尽管也会惺惺作态地流几滴眼泪。在妻子临终时,“他甚至也没有让孩子们同母亲作最后的告别:死亡面前只有谎话,这就是虚伪生存的结果”。[18]玛特廖莎想从亲人那里获得同情和安慰,可是亲人们不是忙着自己的事情,就是对她漠不关心,甚至自己的一双儿女也不关心妈妈的死活,只在院子里玩耍,没有给妈妈任何安慰、关心和爱:“那个六岁的男孩在拼命追赶他的妹妹”,“男孩站了一会儿,凝神瞧了瞧爸爸的脸,突然翘着蹶子,兴高采烈地嚷嚷着向前跑去了……”[19]这一切让她心灰意冷。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死。于是,就产生了像贵族地主太太这样的人恐惧死亡、拒斥死亡、掩盖死亡、竭力忘却死亡(其实她没有忘却,始终惦记着,生怕死掉!)“常人不知有死”的现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换言之,即“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贵族地主太太和马车夫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贵族地主太太富有,马车夫贫穷落魄。尽管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不同,但人固有一死。不论贫富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不论生前有无过失,上帝都是爱他们的。
总之,研究托尔斯泰早期的作品《三死》,其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探寻托翁生死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继《三死》以后,我们发现,托尔斯泰的生死观不断升华:从《三死》所体现的人类生命的短暂性、有限性、速朽性,到后来作品所体现的人类生命的永恒性、无限性、不朽性。
应该指出的是,在《三死》中,托尔斯泰并不是从惯常的阶级的角度,而恰恰是从人性的角度,对贵妇人和马车夫的死进行剖析,对贵妇人死亡态度的嘲讽,对马车夫死亡态度的同情与怜悯,从自然界之朴实与永恒对大树之死的崇高礼赞。正如托尔斯泰在写给姑妈的信中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三个生灵死去了——地主太太、农民和树。——地主太太既可怜又可恨,因为她一辈子说谎,至死都在说谎……农民平静地死去了,正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信奉的是另一种宗教——自然,他活着的时候也是顺应自然的。他自己砍树,种黑麦收黑麦,宰羊也养羊,生养孩子,送走老人,他清楚地明白这个规律,也从来没有像地主太太那样回避过,而是直面死亡……树平静地死去了,死得诚实而优美。优美——因为没有说谎,没有做作,既不畏惧,也不抱怨。”[20]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项目号:2009JX003。
[1][2][3][10][11][12][13][14][16][17][19]〔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芳信译.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65-77.
[4] [9][20] 〔俄国〕C.A.尼克尔斯基著.米慧译.生与死:托尔斯泰哲学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以早期作品为例)[J].俄罗斯文艺,2010(3):14.
[5]Л.Н.Толстой.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ХХIХ).М:Слово/ Slovo,2008г.стр.:172.
[6][18]戴卓萌著.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宗教存在主义意识[J].外语学刊,2005(2):107-108.
[7] 张一方著.托尔斯泰的人生经历与对死亡的深刻描述和感悟——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1(3):70.
[8] 于正荣译.2009年元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俄罗斯文学期末考试试卷.
[15] 张建华译.2009年元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俄罗斯文学期末考试试卷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