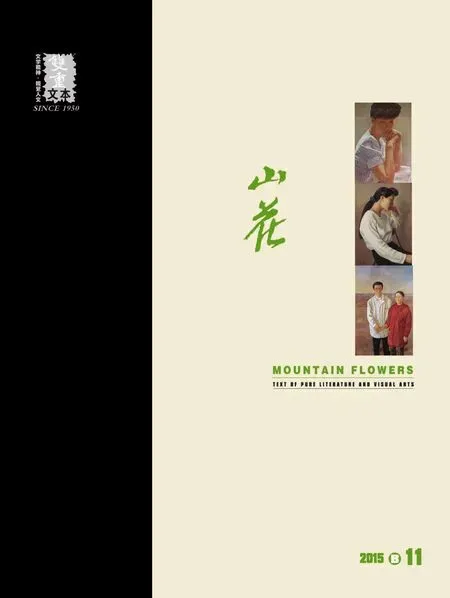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外一篇)
2011-08-15石华鹏
石华鹏
靠简约独特的短篇小说赢得世界声誉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出版过一部短篇小说集,书名叫《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个长长的不像书名的书名,它仿佛一下子穷尽了我们关于爱情话题滔滔不绝且没完没了的空洞的谈论,它还有些武断地暗示我们,在所谓爱情的话题面前,最好闭嘴。
所以,当我有一天发觉,尽管我们时不时会因各种情形发出巨大的笑声其实笑声背后往往空无一物甚至笑不由衷的时候,我便想到了雷蒙德·卡佛的那句话,并模仿他的口吻,偷梁换柱,将它改成: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穷尽我对所谓发笑话题的想象。
一天,我即将幼儿园毕业的儿子在电脑前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很夸张,响亮而有爆发力,不像六岁孩子的笑声,惊动了另一个房间的我。我过去,他正在网上看动画片《神奇宝贝》,我问他:“你笑什么?”显然我的吸引力比不上《神奇宝贝》,他并不在乎我,我只有将我的声音提高几个分贝,企图盖住动画片的声音,“我问你你在笑什么?”儿子被我的声音吓得一愣,显然意识到了异常,抬起头来,他满脸兴奋,说爸爸太搞笑,太搞笑了。原来体重460千克的打瞌睡神奇宝贝卡比兽在树下打瞌睡,它的朋友来把它叫醒了,卡比兽一醒来就开始吃,吃完身边的东西后又睡着了,它的朋友跟它说什么它都听不进去,朋友只好再将卡比兽摇醒,刚醒来的卡比兽又开始吃,把一盘菜全吃下去了,最后连盘子都吃下去了,吃完后又睡着了。
我儿子笑的是懒洋洋的、吃饱就睡的卡比兽。我问儿子:“这很好笑吗?”“很好笑。”我问:“有什么好笑的?”“你不觉得好笑吗?”他反问我。我又问:“你为什么笑呢?”“不为什么。”他对我的问题已然没有了兴趣,看都不看我一眼,又重新投入《神奇宝贝》里去了。
你为什么笑呢?我的问题对一个六岁小孩的确很无聊。一个超级胖子,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对他来说就是好笑,或许不因为什么,或许因为这事件太夸张,太不平常了。但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好笑的,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这是事实,其中并没有幽默的成分。我每天傍晚去超市买菜,都可以碰到一对中年夫妇。这对中年夫妇的胖像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胖,女的爱穿紧身衣,身上的肉被挤成一圈一圈,从上到下套了好几个救生圈。每次碰到他们,都是坐在超市门口吃。从超市买出来的盒饭不贵,但量足,他们的嘴一刻也没停过,手边是叠在一起吃剩的空盒。我进去时他们在吃,出来时还在吃。有一天我在离超市很远的地方碰到了他们,他们手上提着馒头,嘴在不住地咀嚼。我猜想,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可能就是吃,然后就是长肉。这对夫妇的吃和胖并不能让我发笑,而是让我产生种种想象,比如,他们吃饱了后会不会迅速睡下去?他们不吃时的样子是怎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儿子见了这对夫妇,会不会像看到卡比兽那般大笑呢。
生活中,我们会发笑,我们会不断地听到各种笑声。有爽朗的哈哈大笑,有清脆的银铃般的笑,有不露齿的微微笑,有心满意足的眉开眼笑,有皮笑肉不笑的冷笑,有神经不正常的傻笑,有泣极而喜的惨笑,有黑着脸的讥笑,有装模作样的假笑,有势不两立的对笑,有追逐打闹的嬉笑,有勉强装笑不得不笑的干笑,有欣喜若狂的狂笑,有耸起肩膀谄媚的谄笑,有戏弄人的耍笑,有不得意不知所措的苦笑,有让人息怒的赔笑,有不知世故的憨笑,有小品相声演员的逗笑,有色鬼起淫心的奸笑,有放荡凶恶的狞笑,有动机复杂的暗笑……
真可谓:笑尽天下所笑之人,笑完天下所笑之事。如此多的笑,真让人一惊。仔细想来,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可能都会将这些“笑”经历一遍或许多遍吧。“笑”的本意是,脸上露出愉快的表情,嗓子里发出欢喜的笑声,一个“喜”字便可以概括。而当我们将“冷”、“傻”、“惨”、“讥”、“假”、“嬉”、“干”、“狂”、“谄”、“苦”、“赔”、“奸”、“狞”、“暗”等字与“笑”组合起来时,我们发现“笑”的本意已经不见了踪迹,而变成了生活的“悲”之种种。
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其实,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笑,我们更多的是在悲叹——悲人事之微妙,叹生活之多艰。对着上级,我们会谄笑、干笑;对着下级,我们会冷笑、讥笑;对着对手,我们会对笑、苦笑;对着仇人,我们会假笑、狞笑;对着旁人,我们会耍笑、傻笑;对着异性,我们会憨笑、奸笑;对着同性,我们会暗笑、嬉笑;对着客户,我们会逗笑、赔笑。这些笑容的背后、笑声的里边,藏着我们趋利避害的生活本能,藏着我们避重就轻的生存哲学,藏着我们“主子奴才”二重交错的劣根性,藏着我们来自生活压力的无赖选择。
我发现,笑最终成了我们生活中离“喜悦”、“欢乐”最遥远的东西,它被“冷”、“讥”、“假”等词语修饰之后,就如“笑”的基因发生了变异一样,与纯真欢快的“笑”已经没有关系了。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学》里说,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后来人们发现,人之外的许多动物,也能用声音和表情表达喜怒爱惧,就是说笑不只是人的专利。但是能将“笑”发展成二三十种形态,并能微妙而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二三十种形态的,我敢肯定地说,只有我们人类才有这种本领。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化,或许“笑”的进化还将继续下去,“笑”的分支越细,“笑”的内涵越丰富,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离“笑”本身越来越远。
有一天,我听到有人这样评价一座城市,说这是一座没有笑容的城市。把柔软的笑容与坚硬的城市联系起来,感觉就像让清亮的水流过干枯的石头,的确是一个发现。回过头来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每个人的脸孔都是疲惫而凝重的;在逼仄的电梯里,每个人的神态不是心事重重就是一本正经;在人流如织的广场上,每个人脚步匆匆一脸麻木;在居民区的楼道里,邻居擦肩而过视而不见。这就是我们居住的所谓的现代化的城市,冷漠而麻木代替了轻松笑容的水泥森林。所以,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会场的屏幕上出现2008张世界各国儿童的笑脸时,那一刻所有人脸上都绽放出了美丽的笑容,城市在那一刻才真正品尝到了笑容的滋味。人们为这一创意叫好,因为久违了的发自心灵的轻松快乐的笑容回到了人们脸上。是孩子们那天真灿烂的笑容照亮了成人世界那早已暗淡了的心灵世界,只有内心的世界是灿烂的,人们的笑才是灿烂的。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人们会说这是一座面带笑容的城市。
隔壁房间又传来了我六岁儿子响亮而夸张的笑声。我为他的笑而笑,似乎那才是真正的没有污染的笑,我怀念那幼稚、没有内容的笑,那不为什么而笑的笑。
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笑了,似乎又什么都没笑。
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张照片
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张照片?
这不是个问题。这也是个问题。有人喜好照相,一万张也嫌少;有人没此爱好,一张也嫌多。
我属后者。我不喜好照相,也不痴迷收藏照片,无论自己的还是家人的,我都不爱收集整理。因此,我常招来家人的白眼和恶语:怪古董。
我是“怪古董”,但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一,任何东西,一多就泛滥,一泛滥就成灾,一成灾就好事变坏事。数字技术发展,电脑普及,让人人都成为摄影师,人人都成为成百上千张照片的拥有者。如今,有几家不闹“照片灾”的——电脑硬盘塞满,U盘装满,刻录的光盘一大本。可以预见,“照片灾害”还将继续闹下去,生命不止,拍照不止,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手机随身拍,数码机专业拍,你拍我,我拍你,不停拍拍拍。
在胶片时代,“照片灾害”还不至于此,买胶片,冲照片,既麻烦开支也不小,很多家庭就三五本相册,有空时翻看翻看,勾起往事回忆,是一种回味无穷的人生体验。现如今不同了,照片实在太多,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翻看起了,就只好不看了,让那些灿烂的笑容美丽的景致藏在数字的世界里吧。说到底,这些照片没人翻看,也就没有人生的回忆了。拍照留念之目的是给自己和别人看的,多得连自己都懒得看了,照片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七年前,我和太太花大力气花大价钱,照了一套婚纱照——甚至当时为一张照片的我没有笑太太还与我争吵一通,搞得浪漫不成,斯文扫地。我印象中,拍照至今的七年里,我们没有再翻看过那些照片(婚纱照总把自己拍得不像自己),现在不知道它们躲在柜子的哪个角落,等待尘埃降临。
关键是现代人还有个毛病,舍不得丢弃也不会丢弃。拍吧,拍得多多的,也没有错,但从需要的角度说,留下来的相片并不需要那么多,那就舍弃一些吧。说到舍弃,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历,积累一段时间后,坐下来准备清理清理照片,可是当鼠标点到这一张时,心想这张说不定留着有用呢;当鼠标点到那一张时,心想那张还是留着吧,拍得挺滑稽的……结果,清理到最后,无论是确实值得留下的,还是应该舍弃的,一张也没删掉。其实,这是一种糊涂的人生观,通过照片一事就能反映出来。尽管人的年龄和经历在做加法,但我们的生命和需要是在做减法的,学会舍弃,轻装上阵,就是做减法,这与每天都在消逝的生命才是对等的。
第二,任何东西,以稀为贵,一贵就有价值,一有价值就值得留恋。照片也是如此。我爷爷那辈人,照相是一生的奢侈,只有富贵人家才照得起相,碳素画像成为普通人家的选择。活着时为自己留下一张遗像的做法,让碳素画像的生意很是兴隆,并成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手艺。
我一个本家叔叔就学过这门手艺,只不过当他学会的时候,乡村的小路上出现了走村串巷的照相师傅,他们扛着笨重而神秘的“木盒子”,显得见多识广,很神气。随后,稍稍贵些的黑白照相取代了碳素画像,我那位本家叔叔的手艺还没开张就遭淘汰了,如果说开过张的话,那便是他正儿八经画过一张相,是为自己。他患癌病过早去世,那副碳素画像成为他的遗像。三十年过去了,那张相至今还挂在他家里,偶尔回老家看到,总让我沉默良久。尽管那时黑白照相已经稀松平常,但他拒绝那玩意儿,一辈子没照过一张相片,他留下的唯一影像是自己为自己画的那张遗像。
我最早开始照相,已经是四五年级了。照相师傅隔半年或一年从镇上到村子里来,村子里就炸开了锅,一群小孩子奔走相告,像过年。大人不舍得照,主要给孩子们照,照也只照三两张,所以我小时的照片很少,都是小小的。小孩的半个巴掌大,黑白,如果再加点钱,照相师傅就可以给相片另外涂上一层胭脂,变成“彩照”,照片的下面还写有“曙光照相”、“晨光照相”等字样及年月日。
我很喜欢看我少有的几张孩童时期照的黑白照片,我很珍视它们。尽管时间久远但画面质量都很好,与一批后来照的彩色照片放在一起,其他都退色发黄,它们却如二三十年前一样,清晰有质感。我看它们,便是看过去的我,我的感觉挺奇怪的,看照片上幼稚的表情,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我自己。而看现在的一些照片,我觉得那不是在看我,像在看别人,照片上的我与自己很是陌生,尽管这些色彩鲜艳、篇幅大大的相片就是不久前专业的相机专业的摄影师拍摄的。
或许还是因为当时的照片少而弥足珍贵吧。也或许,还是因为人是一种怀旧的动物吧。
一个人一生到底需要多少张照片?让我们回到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来。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在我看来,一个人一生只需要六张照片,足矣,恰到好处矣,意义重大矣。
这六张照片是:出生时一张,学业完成时一张,结婚时一张,做父母时一张,当爷爷奶奶时一张,去世时一张。这是人的一辈子,这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印记,虽然这些印记会在若干年之后消失,但作为某某人存在过的直接“证据”,聊以供后人回忆和追溯: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爷爷的爷爷……如果我们的后人连前人的六张照片都嫌多了的话——因为在他们眼中活人的照片多得都无法保存,哪还顾得上逝去的人的照片呢?——那么,一个人一生只需一张照片即可,就像我的那位本家叔叔,一辈子一张照片,却在一个家族永远挂存下去。
现在想来,我比较遗憾的是,二十年前我爷爷去世时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他的样子模糊得我都想不起来了,当时要是拍一张照片就好了。不过,我的外婆今天还活着,她已经八十八岁了,老得不能再老了。她每次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儿啊,我什么时候死啊!我说:我不是你儿,我是你外孙。在我记忆中,她好像是这个“照片成灾”的时代唯一没有一张照片的人,无论如何,今年冬天回家,我得当一回摄影师,为她拍下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