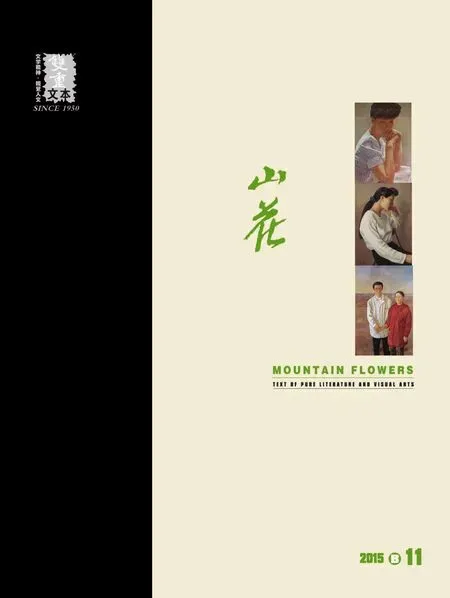家在苗乡
2011-08-15欧秀昌
欧秀昌
我一直想写写我的故乡,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落寞迷茫的时候。
记得在北京读大学时,春节回家,在寨上照了一张相,是在一个小山包上照的,近景是我们寨子,远景是山峦和山沟。山,重重叠叠;沟,狭窄而悠长。时值早春,草木摇落,山寨与山峦一派苍茫。回到学校,同学们见了,大声惊呼:“老欧,这是你的家乡?”他们将“欧”和“乡”拖得足有三拍之长。惊得我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秘密。
那些同学,生在城市,他们的惊呼,意味深长,我不在意。但一声惊呼,让我对故乡有了更深的理解。
毕业后,有了工作,虽说称心了,但我还是念记着我的故乡。
故乡叫做生屯沟,在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镇,为水之源。
那是一条小溪沟,很长,从沟头到沟尾,大约有二十华里,依山傍水坐落着20多个寨子,上千户人家。如果有人有兴趣,从一个叫做铜仁城的地方出发,沿着铜仁锦江的小江走,进入贵阳溪,到一个叫牛郎的地方,两条溪沟,右边的,就是生屯沟。沟里有水,潺潺成溪,沿溪行,弯弯曲曲,弯曲的地方有寨子,像藤上的瓜,一叉一个,铺摆着,直到沟尾。寨子不大,十几家百来户不等,有的排在溪边,有的立在半坡,像天上的星座顺着一条银河有秩序地排列着,星星点点。沟,时宽时窄,狭窄处,相间不足十米,不到午夜时分难见曦月;宽敞处,有河坝,梯田,有山峦,还有满山的油桐林、油茶林、杂木林,形成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寨旁是一些古树,象征着村寨的衰败与兴旺。往里走,到两条小溪汇合处,那个叫中寨的寨子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童年、少年与青年的生活,就在那里。两条小溪是我的生命之河。
生屯沟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我一时还说不清楚,问一些老人,他们也说不知道。这不足为怪,因为沟里的人都是苗族,都说苗话,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他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过去,他们无法记载自己的历史。
生屯沟地名最早见于《铜仁府志》,铜仁知府刘雁题在《石岘平苗纪略》中记载,清朝嘉庆六年,平头司苗族首领白老寅造反,朝庭派兵镇压,兵分四路,其中一路从牛栏场攻新屯。文中所写的牛栏场就是现在的牛郎。牛郎是个集镇,大约上世纪三十年代建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建区,时属铜仁县管辖,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划归松桃,直到现在。新屯就是《府志》所记的新屯沟,也就是生屯沟,现在当地人不改口,仍叫老地名,只不过《铜仁府志》把生屯沟写成了新屯沟,是不是过去汉字记苗音的音误,不知道,只是家乡人一直把它说成是生屯沟,我只是想还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
沟里人自身用文字记录的历史,墓碑上写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这当然是不够的。远的莫说,就说明朝,明嘉靖年间苗族起义领袖龙西波在龙塘起事,而龙塘距生屯沟也就在一山一村之间,那时,生屯沟不可能没有人烟。事实上,龙西波起义失败后,朝庭对苗乡风水龙脉大加斩截,生屯沟的山脉也同样受到蹂躏和斩断。这样说来,墓碑上的时间只是说明这里的人已经接受了汉文化,或者说已经有能力用汉文字为先辈树碑立传。我生长的时候,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已相互交融,也就是说,在苗族文化基因的铺垫下,我拼命地吮吸着汉文化,在苗汉文化生活中成长。两种文化是我的成长之源。
就其苗族文化来说,生屯沟的底蕴是厚重的。听老一辈讲,生屯沟过去因富裕的人家较多,沟里经常举办一些祭祖仪式,这些祭祖仪式最大的是“吃牛”,即“椎牛”(水牛),仪式往往要进行三天三夜或七天七夜,参加的人不论亲疏贵贱,有无贺礼,凡来观看的,一律宴请。听父辈说,那几天,方圆百里的人都来观看,人数众多,热闹非凡,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而每一次仪式,苗族祭司们都要做法事,尽显神通。此外,还有“接龙”、建房、结亲和丧葬仪式等,这些仪式,都是苗族文化的展示与再现。在苗寨中,每一个寨子差不多都有不同的祭司与歌手,他们是苗族的知识分子,知道和懂得苗族的过去与经历,是苗族文化渊博的人。
这些我只是听到老人们说,待我生长的时候,一种新的思想和新的思维已经注入生屯沟,我即在这种新思想中长成。即便这样,由于那里地处偏僻,也有苗族自身的心理意识,除了“吃牛”祭祖无法举行外,其他的祭祀仪式仍然在悄悄地进行和演绎着。即使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后期,我还亲眼看到一些苗族的小型仪式。比如苗族祭司的毕业仪式——“迁阶”。而“迁阶”最后一项就是徒弟要“上刀梯”,用三十六把锋利的刀排列在一根高高的木柱上,竖起,刀刃朝上,徒弟要赤脚攀登上下,不出问题方能毕业;曾亲自聆听过苗族的男女歌手对唱夜歌,一天一夜或者两天两夜,甚至是三天三夜地唱,他(她)们白天休息晚上继续,歌如流水,洋洋洒洒。他们的歌曾让我深深地着迷与感动;也曾在赶场归来的路上和做客时,亲眼见过苗族的少男少女一对一地朗诵动听的“说句子”(那是苗族的抒情诗),对唱动听的酒歌或情歌,抒发内心的情感与爱慕。在他(她)们面前,我曾自卑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苗族文化的文盲或者是一个小学生。
这条沟,说到汉文化,过去很有些惭愧,没有举人,也没有进士,大约是在清朝末年出过几个秀才,立过闱子,据说还是捐的。其实,捐的也行,证明他们已经向往着另一种文明,在向另一种文明攀登。大约他们知道,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不学汉文化是不行的了。在苗族的夜歌中,就有这样的歌词:“读书的人得中举,哪有唱歌成好人?”不管苗歌在对唱中有着怎样极端自谦的表现手法,但歌词已经道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意识在苗族中已成一种燎原之势,那就是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中举,才有功名,才能成为人上之人。事实上,在苗族中,已经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上面所说的“说句子”——苗族的抒情诗,就是苗语与汉语相杂的混合体,因抒情而备受苗族男女青年的喜爱。由于出过几个秀才,他们便在家乡办起了汉文学校,从而推动了生屯沟汉文化的发展。而真正的发展是在解放后,由于这里建立了学校,才有了苗族的知识分子,然后才有了大学生、研究生、作家、艺术家,以及国家的各级干部。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具备着某种文化基因的肥沃土壤,还是挖掘到了储藏基本人才的矿源,抑或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碰撞所产生的灿烂火花!我少有研究,但是,应该说我对这人才的出现是由衷的乐道。
故乡在解放前没有人才可以炫耀,只有三人略可一记,他们分别是曾荣南、曾英才、曾文德。其中一个任过贵州省参议员,一个任过牛郎乡副乡长,再一个任过贵州省主席袁祖铭的秘书,袁祖铭在湖南常德被暗杀后,他失去了依靠,便回了家乡,未谋得一官半职。他们虽然对地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范围也不广。解放后,有一个人值得一书,那就是吴向必。吴向必是长工出生,从一个长工汉到任省委书记、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确实是一个奇迹。更奇的是,一个从没读过书,仅靠参加工作后所学得的知识,晚年患病接近瘫痪,凭着毅力,作画两百余幅,办个人画展,出画册,后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一生充满着传奇。只是他的这一精神未曾引起家乡人的重视,认为任职只不过是得益共产党的领导,而绘画也只是“自成其体,自得其趣”。这难免有失偏颇。其实,对吴向必应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没有上过学校不假,但刻苦学习是真,他的成功是根植在苗族文化之中的,据家乡人说,吴向必当年乃一翩翩少年,能说会道,熟知苗族的古歌与情歌,也曾有过在赶场路上向少女倾吐爱慕的经历,正因为如此,在他任松桃县委书记时,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在演讲时如鱼得水,受到当地干部的广泛赞誉。我以为这完全得力于他的苗族文化的底蕴,以及在大山的挤压下奋起拼搏的毅力,后来吴向必在自叙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应该说,吴向必是一个典型的苗族代表,他的一生蕴藏着许多苗族的基因与密码,有待人们去破译。
苗族人的文化传播,主要靠各种祭祀、节日活动以及各种礼仪的演绎,再就是聚会或火塘边的言说和教授。这些传播在解放后,由于有一部分被认为是迷信而受到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传播。但是,有一个现象值得一说,那就是人民公社化的生产队时期,由于全村人在一起劳动,苗族文化的传播者有了一定的场所,传播者也有了用武之地,他们趁人多在一起的机会,在劳动中传播苗族文化,使得大量的苗歌与民间故事得以传播与传承,特别是所谓非理性文化,也就平常说的“黄色”文化,如“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有了传播的广阔空间。在苗族中,有一个严格的禁忌,即在村寨或家中,是禁止说脏话和带“色”的言语的,否则会被说成是畜生,严重时会被寨老和寨上人赶出村寨。我在家时,我们寨子由于上世纪“粮食关”死了一些人,留下一些孤儿,他们长大后,家里成了光棍汉的天堂,我也参与其中,但从来不说也不敢说带“色”的话。但是,在山上和野外就不一样,只要没有女人在,就可以说,就可以唱。因此,苗族的许多理性和非理性的歌与故事就得以传播,由此,生产队劳动场地倒成了苗族文化传播的一个大学校。我记得我们村的几个小伙子,在这种氛围中,会唱“黄色”苗歌上百余首,成了远近闻名的“黄色”歌手,当然,那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只是说明环境是一种文化传播和生存的基础。在那时,不少人许多非常理性的知识就是在这所学校中所得。
说到故乡,我想应该说说那里的土与田。因为,故乡人的性格与那里的山和水有着极大的渊源。所谓环境造人,当然人也造就了环境。
故乡多是土在高坡,田在水边,应是山高水清。
说到土,就离不开山,土在山上,因为山高,故乡人每天干活,要早早吃饭,包好午饭,上坡干活,待太阳落山才回家,回到家时,天已暗了下来。若要挑担上坡,一次来回要两个多小时,一个强劳力,一天也就走三四趟。直到现在,每每说起,我就想起他们脚穿草鞋,赤膊挑担,一步一步朝着山顶登去。上坡时,两腿青筋暴涨,腿肚鼓涨如纺纱的棉锤,汗水顺着背脊往下流,滴在盘山的路上。后来我看过一幅名为《泰山挑夫》的摄影照片,我想我的故乡人与《泰山挑夫》没有两样,相反,泰山的路要比故乡的山路好走得多,毕竟是风景名胜区,毕竟有石阶,而故乡只是上百年间人们用脚踩出来的山路。由于山陡和干活路远,家乡人往往最懂得生活的艰难,天长日久,也就造就了顽强拼搏的性格。也由于从小登山,练成了一种耐力,有了登山的肌体。我年轻时,到一个叫虎渡口的地方修电站,参加过民兵团举行的登山比赛,在一千多人中,我得了第三名,那些全县的体育尖子都赶不上我。我想,如果国家体育有登山比赛这个项目的话,也许我的家乡人要出全国冠军。这是一句说笑的话,不必当真。
说到田,同样离不开水,田在水边。就其水来说,那是一条温柔的小溪,终日流水潺潺,很美。但是,这条美丽的小溪,春天涨水,一旦咆哮起来也很吓人。我曾见过,那浓浊昏黄的浪,一浪连着一浪,顺着狭窄的山沟奔涌着,那种汹涌澎湃,以至于我后来见到长江黄河时也没有激动过。故乡的田,多在沿溪两岸,且多是围滩砌坎造田,每每遇到三十年或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沿岸的稻田就会全部被洪水冲毁。我们村有过这样一户人家,姓曾,家有近百亩良田,全在河岸边。有一年气候异常,初秋涨大水,黄橙橙的稻谷一夜之间被冲得无影无踪,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就在倾盆大雨的黑夜里,他冒雨站在河边,举着火把,对着闪电雷鸣高叫,直到天亮。当洪水退去,那一片金黄的稻谷与肥沃的良田已是一片沙滩。不用说,这人已经精神失常。过去,这样的人家不在少数。所以,对故乡来说,河边的田,是开了被毁,毁了又开,人们总是在毁灭与创造中生活着,搏斗着。明明知道这田开了会被洪水冲毁,但也还是要开。正像人一样,明知道人老了会死,但还是要生,要生长,要生活。在冲毁的田坝中,随时可以看到层层叠叠的老田泥,一层泥巴夹一层沙,它记录着这里的人们与洪水搏斗的历史。在这里,你说是精神也好,无耐也行,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正因为这样,使他们养成了谦虚做人的心态,也养成了顽强不屈的斗志。
现在说说语言。这里是水之源,很偏僻,沟里的人几乎全说苗语,解放前不与汉族通婚。直到现在,在外面做工作的人,无论职务怎样,回到家中仍说苗语。当然与汉家女子结婚的人,为了与妻儿通话,也说汉语。这里的人,年长一点的说汉话大都带有苗音,说得不大地道。一些妇女还说一些半生不熟的汉语。小时候听说过这么一个笑话,说我们一个苗族妇女赶场去买鞭炮,她不知道鞭炮怎么说,就说:“同志,那个噼噼啪啪咋个买?”而售货员恰巧是个北方的同志,看着苗族妇女比划了半天,也没有明白她要买什么?幸亏有个当地的汉族同志在场,说,她要买的就是鞭炮。这才解决了双方的买卖问题。这样的笑话也不在少数。其实我们对这位妇女的笑话,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就一些深层次的话语,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解决,还不能完全表达其意。其实,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仅靠会说几句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要学透一个伟大民族的精髓,应该说要把握其深刻的内涵。再说,现在中西方文化正在相互渗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作为在历史和地域上边缘化了的故乡,要学的东西就更多,要走的路应更远,好在现在读书的人多了,这样的问题似乎慢慢可以解决,但是大多数人尚不能进行深层次的交流,特别是牵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他们仍然无法用汉语进行充分的表述和评说。当然,我以为,这也只是时日而已。
关于服饰就不多说了,现在只有少部分人在重大节日才穿苗族服饰,就女子来说,平时已经很难再现以往穿戴银饰摇响佩环的场面。我不知道,现在的苗家小伙子与姑娘对银饰的穿戴是怎样的看法,但对我来说,那绝对是一道灿烂的彩虹,是向往着美的生活的再现。其实,服饰的变化也才是一二十年间的事,这固然与社会生活的改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就其变化的速度来说,还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更难以预料的是,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故乡的大多数年轻人以及中老年人都到外地打工,一去几年十几年,去了一代去二代,一代接一代,在家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只有一些老人和儿童在家园守护。人说,没有年轻人的地方是没有希望地方,我不知道这话有几分份量。但我知道,故乡人如我一样,在人文方面正经历一次历史的冶炼与碰撞,不知道这碰撞的结果会怎样。
我知道,这世间的一切都在变,有的变得快一些,有的变得慢一些。有诗为证:“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对于故乡,我想,不管她将来变得怎样,她应是我记忆中的故乡,他们应是我记忆中的故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