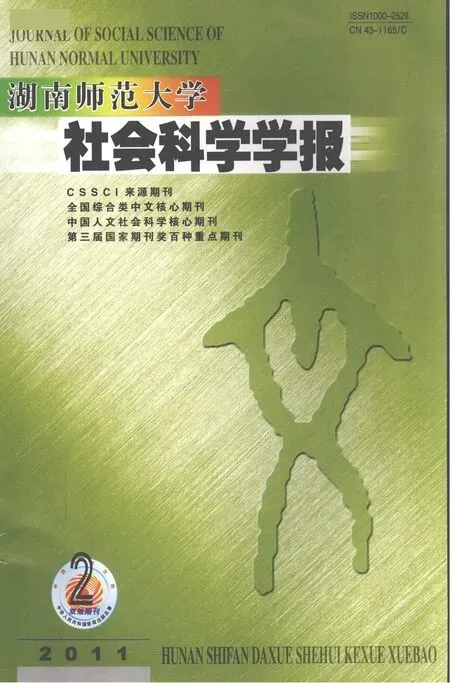从“类型”到“类型的互文性”
2011-04-13王杰文
王杰文
(中国传媒大学 艺 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从“类型”到“类型的互文性”
王杰文
(中国传媒大学 艺 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类型”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围绕着“类型”的争论贯穿于整个民俗学的历史之中。从静态的“类型”研究转向动态的“类型的互文性”研究,不仅是新世纪国际民俗学研究的新动向,也是民俗学与文学、历史学、语言人类学等学科建立对话关系的新基础。
类型;理想类型;分析的种类;民族的类型;类型的互文性
“类型(Genre)”的概念存在于许多学科当中,比如,在文学研究中有“文学类型(Literary Genre)”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有“历史文类”的概念;在民俗研究中则有“民俗类型(Folklore Genre)”的概念。“类型”的概念对于上述三门学科来说都非常重要,然而,至少对民俗学来说,“类型”也是其术语体系中最为模糊与含混的概念之一。
民俗学的“类型”,一般指的是对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谚语、谜语等口头文学的分类。这一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格林兄弟的《儿童及家庭的故事》。他们给搜集来的故事编上号码,拟定一个名称,并对这些故事进行比较。他们认为这些故事之间可以相互区分,而每一个可区分开来的故事都具有多种版本与异文。与格林兄弟同时代的学者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通过把自己记录的故事与格林兄弟记录的故事进行比较,进一步促进了故事类型结构的发展。换言之,在民俗学当中,“类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分类的概念,是划分口头文学材料的工具。在每一种口头文学类型中,依据内容、形式、主题等被进一步细分出许多“亚类型”来。
然而,与历史学从文学领域借用“文学类型(简称‘文类’)”的概念发展出“历史文类”的学术谱系不同,民俗学的“类型”概念(至少“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当中“类型”的概念)则来自植物学。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分类体系的提出被视为任何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面对杂乱无章的材料,科学家们需要依据内容的、形式的、主题的特征来划分材料,在纷繁芜杂的材料中揭示出规律性的程式来。“18世纪瑞典的植物学家卡罗斯·林奈(1707-1778)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式,他的分类模式在植物学界引发了革命,民俗学的学生们借鉴了这一分类形式,希望它也能在传统生活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起到同样的效果”[1](P32)。
可是,众所周知,“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民俗学家们的研究目标是对故事的“主题”与“母题”及其地理传播的轨迹进行历史性地重构,在实践这一研究宗旨的过程中,他们有意地忽略了“类型”之间的差异,那些“异文”间的差异被他们看作是不重要的。结果,“类型”的概念在早期民俗学研究中被当作一个“想当然”的概念,仅仅被看作是对民间叙事进行分类的一个标准。这一做法,客观上为北欧乃至国际民俗档案工作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类体系,却没有给予“类型”以一个明确的界定。
然而,围绕着“类型”的争论却贯穿于整个民俗研究的历史当中,这些争论可以被概括为如下六种相互对应的立场与观点:
一、“理想类型”与“个体讲述”
“理想类型”的概念是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教授提出来的,显然,他借鉴了麦克斯·韦伯的思想。在他看来,“类型”的概念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本,而是指由许多文本组成的一个“群集”。在这些文本当中,某些特点是为所有属于这一类型的文本所共享的,而另一些特点是为个别文本所独有的。换言之,每一个文本都包含有许多特征,其中只有一部分特征使得它的类型属性稳定化,而另一些特征则又使得其类型特征趋于解体。经历一段时间的传播之后,一个特定类型中的一部分文本的类型化特征可能会趋于变异,这种变异将会削弱它作为该类型成员的资格。随着这种变异的加剧,这些文本也许会从所属的类型当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意义上,劳里·航柯教授认为,“类型”是一个“理想型”而不是一个现实的整体。“每一个文本都是由风格、结构、主题、功能、历史因素等组成的特定文本,都只是无限地接近理想型”[2](P53)。换言之,“理想型”仅仅是一个想象当中的分析性的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的文本当中。劳里·航柯教授虽然没有提供与“理想型”相反的另一极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他提供的思想,把“类型”的概念设想为一把“标尺”,“标尺”的一端是“理想型”,另一端是那些仅仅保持了微弱类型特征的“个体讲述”,而大部分可归属于该类型的文本都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
然而,正如丹·本-阿默斯教授所评论的那样,劳里·航柯教授虽然坚持并发展了芬兰学派的“类型”观念,但是,那仍然是一种“分类意义上的类型观”[3](P17)。如果它仅仅是一种分类意义上的“类型观”,那么,“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留给民俗学界的问题就仍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最明显的就是民俗学的“类型”体系常常与被研究对象所固有的“类型”体系 格不入。以民俗学的术语体系分析研究对象,与其说是一种阐释与理解,不如说是一种遮蔽与误解。
二、“分析的种类”与“民族的类型”
美国人类学派民俗学家们很早就发现,早在民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之前,民俗学的类型术语就已经存在了。民俗学家们把这些术语从它们“自然的语言”情境当中剥离出来,作为科学的术语来使用。可是,这些术语在被作为专业术语使用之前,一般都是多义的;而专业术语又要求自身具有清晰的意义与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于是,在“自然的术语”与“科学的术语”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在民俗学家们把“自然的术语”转化为“科学的术语”时,这种模糊性依然存在。
此外,当民俗学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运用民俗学的“科学的术语”来描述不同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在描述非西方社会群体的讲述行为与文本时,这种“科学的术语”的不适应性表现得更加明显。
“比如,鲁丝·本尼迪克特在分析祖尼人的神话时说,那些认为传统故事的‘标准版本’存在于部落社会当中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欧洲民俗学的类型概念来划分祖尼人的故事,那将是误导性的、徒劳无功的。因为,祖尼人的故事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他批评马林诺夫斯基把一个特定族群的神话看作一定是相互一致的观点,在马氏的理论当中,似乎任何一群人都只有一种文化、只有一种结构体系、只有一种相互一致的神话体系。相反,艾德蒙·利奇发现,在卡琴人当中,他们讲述的神话中存在着矛盾与不一致,而这已经超出了故事类型的稳定性与一致性的可能”。[4](P25-26)
“为了避免西方人学术概念对于非西方讲述文本的霸权性的描述与殖民性的误解,同时也为了强调特定文化与社会群体当中讲述的差异性”[5](P198),人类学家采用了“局内的(emic)”与“局外的(etic)”研究视角,创造了“分析的种类”与“民族的类型”两个概念。“前者指的是文学形式的本体,它最终的目标是界定一个文学类型是什么。它应用主题的、形态的、原形的或者功能的术语对文学存在的模式进行描述。类型的‘分析的种类’是在学术语境中提出来的,应当服务于多种多样的研究目标;相反,‘民族的类型’并没有外在的目标,它是一种定性的、主观的秩序体系。其分类背后的潜在逻辑对其群体成员具有意义,在他们的人际交往与仪式行为中具有指导性的作用。”[6](P225)因此,“口头文学的‘民族的类型’是独特的,并不需要与民俗类型的‘分析的种类’相一致”[7](P291)。
三、“永恒的类型”与“多变的意义(功能)”
在民俗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当中,进化论的、功能主义的研究都认为类型是真实的文化整体,是永恒地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口头传统当中的,是民俗学的核心问题。
19世纪英国人类学与民俗学的进化论认为,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它们的民俗形式是持续不变的,只是民俗类型与进化的阶段呈现出一种“反对”关系,即:作为一种永久的类型,民俗类型在迅速变迁的社会中仍然存在,但是,当文化在向前进化时,民俗类型在社会中的位置却是不断被边缘化的。持进化论观点的民俗学家们认为,在文化的早期阶段,民俗类型占据着特定文化的核心位置;然而,在文化进化的后期阶段,民俗类型的形式虽然相同,却只能占据边缘性的位置。在文明的早期阶段,它们的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它们只是传统社会的遗留物。比如,谚语是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当中永久的民俗类型,当人类知识进步时,它们虽然存活下来了,却丧失了原有的重要意义。
功能主义给“永恒的类型”观念增加了一个动态的维度,认为类型不仅仅是文化当中连续存在的口头形式,而且在社会事件中起着某种积极的作用。文化中每一个独立的元素,包括民俗类型,都对社会群体的维持与延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神话表达、加强、修正信仰;保障与强化道德;保证仪式的有效性,并为人们提供指导与实践的准则。因此,神话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是一个随意讲述的故事,而是一种严肃的、积极的力量。传说是通过给予讲述者的祖先以荣耀而满足其野心的叙事,故事则是为了娱乐大众。因此,在他看来,类型最终是为了工具性地满足人们的社会的与精神的需要而存在与继承的。在马氏的理论当中,功能是普遍的,因此它对于人类社会十分重要,故而类型的功能体系应当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可以用于对从世界任何地方搜集而来的材料进行类型分类。
在进化论与功能主义的研究当中,民俗类型的恒久性得到强调,尽管其意义与功能在不同历史时代与空间背景中可能并不相同。
四、“普遍的类型”与“变异的文本”
与进化论、功能主义学派相同,结构主义形态学学派从来没有质疑过“类型”概念在口头传统当中的重要性,事实上,“类型”在口头传统当中的基础性地位是这一学派的工作前提。他们的分析目标是发现每一种类型的独特形态特征,探索各自形式当中的内在关系,试图在口头传统的整体中区分类型。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对俄罗斯幻想故事中“幻想性赠予者”亚类型故事的研究是形态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阿兰·邓迪斯介绍并发展了普罗普的理论,认为类型的特征是普遍的。他不仅认为类型是口头传统的“普遍的特征”,而且肯定了结构形态分析法的优先性地位,认为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其首要任务是对于所有民俗类型进行描述性的结构分析。但是,没过多久,邓迪斯就转向了他的“形态—结构”的类型描述,它不再寻找民俗形式的不同特性,而是去追踪它们的相同范式。在他的分析当中,类型之间变得更加相似而不是不同。他认为,“形态分析可以说明特定的结构模式可以呈现在许多民俗类型当中”[8](P122)。比如,他说,美国印第安民间故事的形态同样呈现在美国儿童的游戏当中。
五、“简单的类型”与“复杂的类型”
结构形态学的方法论认为类型是一种深层的结构,它不具有历史,在民俗的形式当中有一种认知的优先性。相反,作为进化形式的类型观念假定每一种类型的根部都有一个特殊的意义领域。无论是文学类型还是民俗类型,在人类口头表达的形式当中都是从简单走向复杂的。
民俗学家们提出,类型从简单形式走向复杂形式的进化过程,一般要基于如下三个过程:一,在特定的情境下,语言具有把词汇转化成为口头文学的能力;二,围绕着不同的意义领域,词汇被转化成口头文学形式;三,当某种特定的口头文学类型的存在情境转变时,它就会转变为新的口头文学类型,但会在意义方面与此前的类型存在某种关联。随着人类的进步与文明的进化,它们进化为新的复杂的形式,但仍然会保留着相关联的意义。
但是,“简章类型”与“复杂类型”之间的差异往往被简单地赋予相应的价值判断,即“低级的”与“高级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简单类型”与“复杂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口头类型”与“书面类型”或者“民俗类型”与“文学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对应关系往往会被以一种对立的方式对待,即把“民俗类型”视为“低级的”类型。
巴赫金把“类型”区分为“基本的/简单的类型”与“次要的/复杂的类型”,认为通过运用“对话、直接引用、被报告的讲述”等手段,前者被融入后者当中。在被包容进“次要的讲述类型”当中时,“基本的类型”丧失了其关联于现实的方向,变得模糊了。这里,巴赫金的概念与民俗学家的概念虽然相似,却有着不同的理论追求。但是,巴赫金的理论提示我们:重要的问题不是去强调“非文学的讲述类型”与“文学类型”之间的区别,更不是在一种偏见的指导下刻板地强调“非文学的讲述类型”的低级位置,而是要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当一种“非文学的讲述类型”被插入“文学类型”当中时,它从来都不会完全是一种“非文学的类型”。
六、“类型”与“类型的互文性”
至20世纪60年代,民俗学家们基本上都倾向于静态化地处理“类型”的概念,直到“讲述的民族志”开始强调研究“艺术性行为与事件”,“类型”作为讲述事件的构成部分之间的联结点才成为分析讲述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这时,民俗学家才开始重新思考“类型”概念的理论价值。
无独有偶,在文学研究领域,米哈伊尔·巴赫金与晚年的茨维坦·托多洛夫也改变了“类型”研究的方向,把“类型”从“一种分类工具”转化为“一种研究人类讲述行为的方法”。“类型”被视为言说的创造性的组织原则,使得“类型”进一步成为语言人类学当中最重要的概念。
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任何一种讲述的类型都有在“形式、主题、风格”三个维度上获得其形式、变得完整、达到完满的特征。围绕着这三个维度,类型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世界观;一种交流的工具;一种预期的理解框架。
首先,类型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世界观,其中包含着特定的时空观念,偶然性观念,人类动机、伦理与艺术的价值观念。类型是文化知识与可能性的储藏室,它支撑着讲述者的创造活动,指导着听众的理解与阐释它们的方式。对于这些集体性表征的维度——包括时间、空间、行动者、语境、偶然性、动机——以及对于它们的阐释,类型世界的思想指导着一种对“类型”的理解。
其次,所有的讲述类型都是人类的生存工具。人们在特定的语境当中应运类型性的言说,而这种类型性的言说在两种语境当中创造意义,一种是交流的即时的语境,一种是更为宽泛的历史性的语境。在特定的背景当中,讲述者应用类型表演着公开的或者隐秘的主题,陈述着工具性的、道德性的知识,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话语实践。
最后,类型也是讲述者与听众共享的、预期的、多维度性的框架。这一共享的知识让表演者选择与发展其艺术中的元素,让听众理解这些元素。一个文本的类型性的结构是外在于它的,在期待当中,表演者讲述它,听众用它来对表演做出反应,在情节、风格、主题等各个维度上提供规则,调整着听众的想象并随时准备做出反应。
正如上文所说,巴赫金把“类型”区分为“基本的/简单的类型”与“次要的/复杂的类型”,而“次要类型”吸收并消化了“基本类型”,即一个讲述被吸纳进另一个讲述当中,这种生产与阐释的过程即是“类型的互文性”。在消化与吸收其他类型的意义上来说,很少有哪些类型可以说是纯粹的“基本类型”。“类型的互文性”概念所启发的思考是:这种类型之间的消化的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在“类型的互文性”的概念当中,类型间的“形式”关系同时关联着“功能”与“主题”的关系。既然“‘当下的文本’总是与‘已经完成的过去的文本’以及‘预期当中的未来的文本’相关联”[9](P1),那就意味着,“类型”超越了固定的、地方性地发生的讲述事件,作为一个当下的关捩点联结着过去与未来、此地与他处、规则与创造。
虽然“类型的互文性”是强调惯例化的、传统形式的、实践的、主题的话语组织的一种手段,但是,任何一个特定的文本都是受即时的场景性因素影响的。这种即时呈现的指向与类型性指向的框架会产生某种互动,形构着讲述行为的生产与接受。这种互动的过程反过来又会影响类型框架的构成性的特征,意味着“形式、风格、主题”不可避免地也是变动的,这就打开了类型性重构与变化的可能[10](P135)。这样,“类型的互文性”就涉及到了一个文本间差距的问题。“每一个个别的讲述活动都在类型的规则与个体的创造之间进行协调,缩小类型间的差距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支持与维护;相反,扩大类型间的差距则意味着矛盾与不协调,甚至是一种公然的对抗与颠覆。”[11](P85)这样一来,“类型的应用便带有了意识形态的与政治的意味”[12](P132)。
正是通过“类型的互文性”的思想,理查德·鲍曼等人把民俗学的“表演研究”与更大的社会组织、历史过程以及非表演的日常生活关联了起来,极大地提升了民俗学领域“表演研究”的方法在整个社会人文学科领域的适用性。
七、关于“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类型概念的社会功能的核心问题是“恰当性”的问题。何种讲述的形式、主题与风格才是受听众欢迎的呢?既然类型的规则可以被打破,事实上也不能不被打破,那么,如何才是“恰当的”讲述行为呢?
(二)既然类型从来不会以完整的形式呈现,而是一种基于广泛的阅读之后的分析性的建构,那么,正如一些文学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描述类型特征的最好的方法也许是通过个案研究来进行”[13](ppv-xvi)。海登·怀特教授认为,“‘类型’抵制‘理论化’是因为它缺乏本质”[14](P610)。但是,它有一个“历史”。因此,也许处理“类型”问题的最佳方案不是“理论化”而是“历史化”。
(三)在描述与分析任何复杂的对象时,知识总是分布于“信息”与“理解”之间,“信息”越多,“理解”就越少。反之亦然。对于类型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如果想要了解类型的知识,就必须了解关于类型的思想、体系、分类,从而导向“元类型”的理论;如果想要了解任何特定类型的知识,就必须接触大量属于该类型的信息。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研究类型,因为类型被讲述者建构并进入我们分析的对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抵制类型崇拜。类型应当是具体的、易变的,要避免过度的抽象与教条化。
总之,类型本身与类型的理论都是不断变化的。无论是口头文本还是书面文本,其中都充斥着大量的类型混杂的现象。类型分析应该关注类型如何产生与发展,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关联于权力与权威。既然类型是一个“集合”,“类型的互文性”的分析就可以洞察一个类型当中构成成员之间共享特征的本质,也可以分析单个类型成员内部组成要素之间的本质。类型可大可小;可以作为一个构成要素,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可以跨越民族边界,也可以抵制这种跨越行为;可能是来自日常讲述行为,也可能来自书面文本;它们通过结合进某一个特定的类型而被反复重构。
类型的概念已经不再是静态的划分,而是处于转变当中的“互文性”关系。类型成员有增有减,相互竞争;类型或盛或衰,相互植入、移出、吸纳。类型之间是一种对话与竞争的关系,在这里,来自古代的类型与现代的类型比肩,来自文学的类型与日常的讲述类型并存。“类型的互文性”的研究目的是考察类型的互文性的“形式、意义与功能”。
[1]Dan Ben-Amos,The concept of Genre in folklore,Studia Fennica:20,1976a,30-43.
[2]LauriHonko,Genre Analysisin Folkloristicsand Comparative Religion,Temenos:3,1968,48-66.
[3]Dan Ben-Amos,Do We Need Ideal Types (in Folklore)?An Address to Lauri Honko,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Turku.Finland.1992,1-34.
[4]Robert A. Georges.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Tale-Type as Concept and Construct.Western Folklore.XLII:1983.21-28.
[5]Dundes Alan,The Motif-Index and Tale Type Index:A Critique.JournalofFolklore Research,1997,34:195-202.
[6]Dan Ben-Amos,(ed)Folklore genres,Austin,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b.
[7]Dan Ben-Amos,AnalyticalCategoriesand Ethnic Genres.Genres 2-3,1969,275-301.
[8]Dundes Alan,Structural Typology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 Folktales,South-weeste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63,121-130.
[9]Richard Bauman.A World ofOthers’ Word:Cross-CulturalPerspectiveson Intertextuality,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
[10] Briggs,Charles L.and Richard Bautnan,Genre,Intertextuality,and Social Power,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1992,2:131-172.
[11] Richard Bauman,Genre,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Vol.9,No.1-2:1999,84-87.
[12]Richard Bauman,Contextualization,Tradition,and the Dialogue of Genres:Icelandic Legends of the Kraftaskild.In Rethinking Context:Language as an InteractivePhenomenon.Alessandro Durantiand Charles Goodwin,eds.1992,pp.125-1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Ralph Cohen,Introduction:Notes towardaGeneric Reconstitution of Literary Study,New Literary History,Vol.34,No.3,2003,pp.v-xvi
[14]Hayden White,Anomalies of Genre:The Utility of Theory and History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Genres,Vol.34,No.3,2003,pp.597-615.
Abstract:Genre is one of the keywords in Folkloristic field;there are so many discussions about Genre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Folklore.The research,which turn from static genric research to generic intertextual research,is not only the new trend in the world-wide folklore field,but the new basement on which folklore,literature,history and linguistics to have a dialogure.
Keywords:genre;ideal genre;analytical categories;ethnic genres;generic intertextuality
(责任编校:文 一)
From“Genre”to“Generic Intertextuality”
WANG Jie-wen
(Art Research Institute,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Z057
A
1000-2529(2011)02-0105-04
2010-11-20
文化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间文化与大众传播”(07DA02)
王杰文(1975-),男,山西柳林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