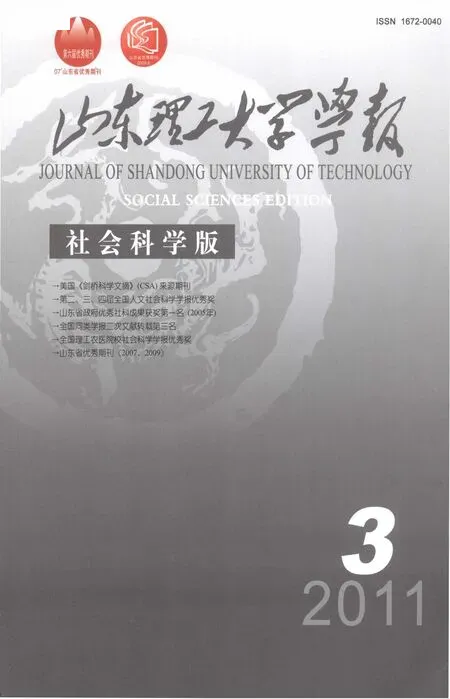意象的经验书写——曹文轩小说叙事方式解读
2011-04-13王来东
王来东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淄博255049)
曹文轩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确非常特殊,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又是很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远远超出儿童的范围,在成人阅读圈子里也广受欢迎。追随永恒、古典唯美是曹文轩对自己的写作定位,而真正给他的作品带来艺术魅力的,又不是单薄的、虚飘的唯美,而是苦难中的唯美,正是人性于苦难中的唯美追求,给他的作品增加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使其沟通了儿童与成人世界的共同的阅读期待。构成其儿童文学作品艺术魅力的要素,主要是江南水乡的特有风物,以油麻地、稻香渡等虚构地点为背景的大河、芦苇荡;少年男女的纯真友情,对两性关系朦胧觉醒时的童贞纯净、少年忧伤、若即若离的怅惘;少年男女承担生活苦难的稚弱与坚强、无奈与义无反顾……这个苦难、美丽、纯净的童年世界的营造,使儿童文学展现出一个新的境界,这里没有廉价的快乐,也没有轻飘的痛苦,更没有做作的艰难,儿童的世界闪现出生存的坚韧、美丽与顽强。在他的小说中,始终对农村,对自然、情感以及女性的经验书写保持着高度的热情,本文从此三方面对曹文轩小说的叙事方式加以解读。
一、自然经验书写
曹文轩出生并生长在苏北的水乡,从小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水。“我家住在一条大河的河边上。这是一个地地道道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橹声中,在渔人噼噼啪啪的跺板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辣泼辣的水声中长大的。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一睁开眼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忆储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有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1]1在《天瓢》中,曹文轩写了二十几种雨(狗牙雨、金丝雨、梨花雨……),借助大自然的神奇来表达情感,雨不仅仅作为小说的幕布,意向化、氛围化地展现主人公的一生,表达了欲望、性爱、激情、爱与憎,表现出巨大的形式感;而且,还把雨作为陪衬,通过雨的强弱变化构成音乐般的美感享受,这是作品最成功的地方。写杜元潮的时候,各种雨倾泄而下,并运用爱、憎近乎残忍的高强度的表现手法,展示了作者对生活观察入微的写作能力。《天瓢》的故事发生在江南水乡的油麻地,“苍茫的天底下,除了一线露出水面的黑色大堤,满眼是水,无边无际的大水”。[2]212在《红瓦》中,也是水网密布垣篱交错的江南水乡油麻地,“油麻地中学四周都是岛,是个孤岛”。[3]41在《草房子》中,“油麻地小学是清一色的草房子”,“油麻地小学四周环水,很独立的样子”。[3]12小学的四周就是桑桑以及小伙伴们游泳的芦苇荡。在《根鸟》中,则描写成是菊花山坡,是开满百合的大峡谷。在《青铜葵花》中,到处是芦苇荡,出门就乘船。对“油麻地”的情结,对“河流”、“芦苇荡”的向往,归根到底是一种对田园、对大自然的渴望。曹文轩把河道纵横的江南平原,把河流、芦苇荡、池塘展现在我们面前。曹文轩说:“我的大多数作品是写田园生活的,形成这种格局的直接原因是我生长在农村,对田园生活格外熟悉,倍感亲切,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对田园生活的价值所作的思考和判断。”[1]6“田园”是文人化的风景。当把田园与文人墨客相提并论,它已不单单是一方田畦或交错的垣篱,而是人的本源所在,或是放飞理想的地方了。田园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小说主人公生活成长的背景。童年的记忆,始终被故乡的水萦绕渗透,于是在作者的笔下,就有了对大雨的描写,特别是在《天瓢》中,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雨景。“天开始下雨了,一种叫‘狗牙’的雨。那雨不是一丝一丝的,而是一点一点的,仿佛这雨早在空中时,就被剪子剪成了一小截一小截。满天空的狗牙。一颗颗,皆很有力,皆很锋利,亮闪闪的。它能穿透薄薄的叶子,砸在人的脸上,让人麻酥酥的。它们一颗撵着一颗,却又十分均匀地落向荒草萋萋的大地”[2]20(狗牙雨)。“太阳晃晃悠悠在天上浮动,雨却下得有声有色。整个天空,像巨大的冰块在融化,阳光普照,那粗细均匀的雨丝,一根根,皆为金色。无一丝风,雨丝垂直而降,就像一道宽阔的大幕,辉煌地高悬在天地之间”[2]78(金丝雨)。描写李长望的倒台,“天又下雨了,一天一天地下,但下得蹊跷:夜里下,白天不下。早晨起来,见着分明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接下来的一天,都是天如青石,日如金盆,空气透明如玻璃,一眼能看到五六里外的烟树与村落。即使到了傍晚,也没有一丝一毫要下雨的迹象,红日西沉,霞光如鸟,飞满天空。甚至是在睡下后,也还闻不见雨来之前的气息,月亮在窗前飘着,轻盈如薄薄的银片。然后是整个村落终于困了,男男女女沉沉睡去时,转眼间,月黑风高,雨的气息从北方随风而来,飘满了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雨下得阴鸷。”[2]68(鬼雨)。李长望倒台,意味着杜源潮的崛起——梨花雨,“雨将一切植物洗得干干净净,绿的,红的,黄的,白的,所有的颜色都比以前鲜亮,那颜色仿佛原先是在睡眠中,而现在都被雨唤醒了,流动着生命的光彩。广阔的田野,在这春天的雨中,蓬蓬勃勃地生长着。每一根草茎,每一片叶子,仿佛都朝天空张着欲望的嘴巴,吮吸着飘落下来的甜丝丝的雨。就在这无比寂静的天空下,却又分明有轰隆轰隆的欲望在喧嚣不宁”。[2]91
二、女性经验书写
曹文轩的小说中,总是有一种女性的情感向往。这些来自“苏州”的陌生女性,总是伴随着主人的成长,而一旦成人,这些女性也就完成了她们的使命如同神秘的女神而消失。在《细米》中,小说一开始,就迎来了“一批从苏州城里来的知青”,这其中就有梅纹。由于梅纹的缘故,平时走路总是又蹦又跳的细米,“走路小心翼翼,仿佛地上是有鸭蛋,怕一不小心踩着了似的”,怪不得妈妈说,“他长这么大,我就没有见过他走路的样子”。《草房子》中的纸月,因为纸月,桑桑变得讲卫生了,在妈妈的眼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也知道要新衣服了”;同时,懦弱的桑桑变得勇敢了,为了救纸月,桑桑居然跟连老师都管不了的刘一水打架,面对死亡,桑桑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根鸟(《根鸟》)离家出走,在那个梦幻大峡谷中出现的紫烟姑娘,冥冥中以神秘的力量深深地吸引着根鸟。艾绒(《天瓢》),一个从苏州城里来插队的知青,曾唤起了杜源潮的爱情。这些女性的出现如同远古社会里的陌生女神,在完成她们的宗教使命后都选择了悄然离开。她们的出现如同原始文化传统中总以陌生人身份出现的生殖女神,她们都具有影响主人公的魔力。艾绒唤起了杜源潮的爱情,二人结婚生子;纸月一直是桑桑的一种憧憬和向往;梅纹则是以一种特有的气质帮助着细米的成长;葵花(《青铜葵花》)在哑巴青铜的眼里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而且少女葵花还能听懂青铜的话语,最终使哑巴青铜开口说话。这些神秘的陌生女性,在人类学著作中就有原型。“塞浦路斯古时的习俗,妇女结婚前必须在女神的圣殿里失身于外乡人。类似的习俗在西亚许多地方都有盛行。无论这种习俗的动机如何,人们显然并不认为这是淫乱放荡行为,而是神圣的宗教义务,是为西亚伟大的母性女神服务”。[4]481当陌生人完成使命,就迅速离开。然而经过几千年的变化,陌生人原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与曹文轩小说中陌生女子与主人公的关系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笔下的陌生女子,尽管不是远古社会中为完成宗教义务而来,但这些陌生的神秘女性,却对主人公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其变得成熟起来。曹文轩的笔下,这些女性有一个共同归宿——“江南故乡”。在她们离开后,读者对她们的命运担忧迷惑时,作者会轻松地看似随意地交代她们的结局,“有人在江南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看到了纸月和已还俗的慧思(《草房子》);“那场大火之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她,有人说她投靠远方的一个亲戚去了,有人说她去了苏州,艾绒给她找了一份打扫剧场的活儿”(《天瓢》)。“江南”让人联想到富庶,“美丽”意味着祥和。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着作者真诚的祝福。作者用祝福调适哀伤,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主张——“哭泣决非一书”。这完全是作者个人的经验和真切的感受。“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只有在依赖他个人经验的前提下,才能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一种确切的感觉”。[5]54
三、情感模式经验书写
在曹文轩的小说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美丽且又结局完美的爱情故事,这本属于浪漫神奇的人世间永恒的话题,在作者的笔下,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一种悲剧,同时也赋予了它一种美丽,生活把爱情从梦幻带到现实,带入一种最为质朴的情感状态——亲情。在表现爱情的模式上,多出现“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或“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关系模式。《天瓢》中,艾绒、采芹与杜元潮。杜元潮与采芹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然而由于家境的差异,他们二人没有走到一起,杜元潮和从苏州来的知青艾绒结了婚。但这婚姻也没有完美的结局,随着孩子的不幸夭折,艾绒毅然决然地回城。杜元潮经过了婚姻,又变成了单身,回到了已成为寡妇的采芹身边。虽然最终二人也没有举行婚礼,但他们一直相守在一起。其实,杜元潮与艾绒的结合,是由于采芹的极力撮合。艾绒对采芹是姐妹般的信赖,采芹对艾绒更是爱怜般的关怀。她们没有因为这一个男人而争风吃醋,而是无条件地满足他的欲望。《红瓦》中的丁黄氏和丁杨氏,是乡绅丁韶广的大小老婆,二人姐妹相称,不厌其烦地伺候在丁韶广的身边,“她们因丁韶广而焕发出女性花一般的美,又因丁韶广的死亡而黯然失色”,她们身上表现出的是对男性的崇拜,在男性面前,她们不是主动地追求爱情,而是被动地等待男人的“爱”,被动地接受男人的“爱”。《天瓢》中的采芹与杜元潮、邱子东,三人从小一起长大,两小无猜的杜元潮和采芹情窦初开,却引起了邱子东的嫉妒。为了采芹,杜元潮和邱子东从未停止过一天的争斗,儿时邱子东对杜元潮的无情折磨,换来了日后杜元潮对邱子东的复仇。仇恨使他们计谋叠出,命运多舛,当邱子东最终在晚年打败杜元潮时,却发现杜元潮的一切都是为了童年的梦想和爱。
综观曹文轩的写作历程,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独具特色的写作姿态,既不在所谓思想理念上追新逐异,也不在技巧上花样翻新,以表面的热闹、轰动赢得读者,而是始终坚持认为文学中感动人的东西是永恒的。如果借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术语,可以说以上分析表现了曹文轩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与原型思想的一致性,而且他在个体无意识层面也有相似的体悟,这就是曹文轩对于文学创作中“重复”这一现象的强调。一般的文学理论强调的是创新,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他人,这几乎成为所有作家的基本信念,但曹文轩认为能够形成一个作家创作特色的恰恰在于对自己的重复,“经历不可重复,但经验可以重复”,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重复“可能是叙述风气上的重复,也可能是在对存在见解上的重复,有可能是美学追求上的重复,而很可能的一个重复,就是经验上的重复。比如由经历而导致的一种忧郁的经验,几乎贯穿了一个小说家的全部写作——忧郁甚至变成了一种作品的总基调”。[5]65“或许是人类社会开始重视个人经验并渐渐有了书写个人经验的风气,或许是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够呈现个人经验的形式——小说,从此小说不可抑制地发达起来”。[6]2
[1] 曹文轩.童年与文学——走进曹文轩的纯美世界[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2] 曹文轩.天瓢[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3] 曹文轩.曹文轩精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4] [英]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5]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6] 曹文轩.小说:书写经验的优越文体[J].小说选刊,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