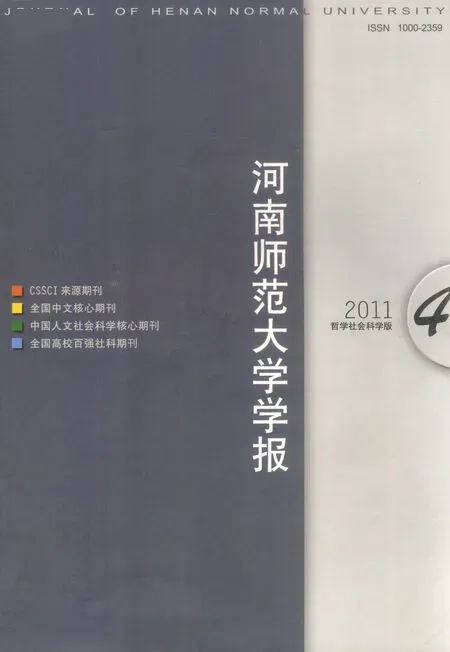试论新加坡组屋政策与国家认同
2011-04-12夏玉清
夏 玉 清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试论新加坡组屋政策与国家认同
夏 玉 清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其外部面临马来西亚等伊斯兰世界的包围和敌视,内有极具离心倾向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族群并存的现实。在此历史背景下,建构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人民行动党政府以实施“居者有其屋”政策为载体,把组屋的分配、管理政策作为建构各族群的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组屋政策的实施打破了殖民地时期各族群集中居住的模式,在空间上形成了各族群平衡分布的居住形态,同时政府在组屋区建立社会控制网络以促进各族群间的整合和凝聚,为新加坡形成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新加坡;组屋政策;国家认同
新加坡作为一个资源缺乏的岛国,经过短短40年的发展,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族群和谐的现代城市国家。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加坡成功地实施了解决社会大众住房问题的“居者有其屋”组屋政策。因此,对新加坡的组屋的考察也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就国内学者现有研究成果而言,有关新加坡组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角度探讨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及其对我国解决住房问题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是侧重于对新加坡的组屋的规划、景观设计及邻里中心等社区管理制度的研究以作为我国住房建设的参考。然而,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的组屋政策,除了具有解决公民基本住房的功能之外,其组屋政策也是基于新加坡特定的历史和政治斗争以及国家建构的背景下实施的。换言之,新加坡政府把组屋政策作为塑造各族群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一、殖民地时期移民的居住形态
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在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新加坡自治政府于1960年撤销殖民地时期解决住房的机构信托局,代之以建屋发展局来解决社会大众的“屋荒”问题。然而殖民地时期政府的发展商业政策和对移民的居住管理对战后的新加坡影响巨大,它不但造成了二战后各族群分割的居住形态和各自的文化认同,而且对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的国家认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殖民地时期移民的居住形态的形成
1822年,莱佛士实行商人至上的市区重建计划。即所有具有商业价值的土地都保留和分配给商人阶级作商业用途,各族群移民的居住区域从属于政府的规划和安排。该计划的实施对新加坡各族群的居住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这一政策,殖民政府市区计划委员会划分了不同族群的聚居区域:欧洲区位于今美芝路一带;武吉士人位于美芝路一带,阿拉伯人居住分布于苏丹王宫西北部,与欧洲人为邻;印度人位于新加坡河下游西岸;华人区位于新加坡河的西南部,介于直落亚逸与珍珠山间,即今牛车水一带[1]。当时莱佛士已经看到华人社会的帮派特色,他特别强调不同方言群应该分开居住以避免发生纠纷。莱佛士在发给市区重建委员会关于华人甘榜的指示中特别指出,“要把华人的甘榜建立在适当的基础上,就必须注意到这个特殊族群的地缘性和其他特性,某一个省份的人比别一省的人较常争吵,而不同省份的人之间,又经常发生不断的争执和争吵”[2]。在他的建议下,华人社区依据不同的方言群,依次再划分为较小的居住地。例如,福建人被分配到直落亚逸与厦门街,潮州人被安置在靠近新加坡河畔,而广府人则奉令住在牛车水一带[3]。殖民地市区重建计划的实施基本奠定了各族群的居住格局。
殖民地时期,伴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各族群也带来了来自各移出地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而形成了各自的文化认同。印度人带来的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等,闽粤移民的妈祖、大伯公以及本土马来人的回教等民间信仰在新加坡并存。正如博物学家华勒斯于1854年游历新加坡时所言:“新加坡有美丽的公共建筑和教堂、回教寺院、佛教寺庙、道教庙宇、欧式的建筑以及中国商场。”[4]各族群形成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相异的生活形态。因此,各移民族群因宗教文化的不同形成了对各自族群的认同感。各族群之间共存但没有交流,而是生活在各自的空间[5]。就华人移民社群内部而言,华人社会内部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6]。华侨社会分为海峡华人和新客移民。海峡华人的观念和行为也迥异于闽粤移民的新客移民,海峡华人于1900年创立了“海峡华人公会”。新客移民内部又分为福建帮、广帮、潮帮、客帮、海南帮五大帮群,各个帮群聚居在彼此邻近界限分明的区域。这种居住形态一直延续到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影响和制约了新加坡建国后国家认同和社会的凝聚,直到建屋发展局实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后,这种居住形态才逐渐得到改变。
(二)改良信托局(SIT)时期解决“屋荒”的尝试
殖民地政府对于移民住房问题关注始于1927年新加坡改良信托局(SIT)的成立。此一时期持续到1960年。殖民地政府关注移民的住房问题主要是由于新加坡移民恶劣的住房状况影响到殖民政府的形象。当时的新加坡被视为“世界上最为拥挤的贫民区之一”。另外,伴随着移民的增加而出现了“屋荒”问题也是改良信托局成立的主要因素。
殖民政府成立改良信托局的目的主要是为低收入的无家可归者建造房屋。但在实践进程中成效不大。截至1960年,改良信托局所建房屋共23019套,其中大部分是两层式组屋、店屋以及政府雇员的宿舍[7]。建设资金缺乏、管理不当等使得信托局对解决“屋荒”问题不了了之。特别是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临近,英国殖民政府不愿把大量资金投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上[8]121。因此,改良信托局时期的移民的住房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各族群仍然居住在殖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里。
二、建屋发展局(HDB)初期解决“屋荒”的背景
1960年,人民行动党政府成立建屋发展局开始解决社会大众的住房问题。建屋局时期以1965年新加坡建国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0年至1965年,即建屋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阶段从1965年至今。第一阶段的组屋建设主要取决于“屋荒”和当时新加坡政党政治斗争的需要。
1960年成立的建屋发展局开始逐步解决民众“屋荒”问题。二战后新加坡面临严峻“屋荒”问题。一方面,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南来移民基本停止,但战后本地人口高出生率(本地人口年增长率直到19世纪50年代一直在4%以上)以及由于战后马来亚内乱,从西马大量的移民导致人口增加[9],使得住房问题凸显。另一方面,1961年的居民区火灾导致大批人员失去家园,政府必须把解决住房问题作为首要的工作。此外,新加坡住房环境亟待改善,1962年,新加坡政府社会福利部的调查结果表明,新加坡73%的家庭居住条件在“贫困线”以下[8]102。
除此之外,人民行动党解决住房也与战后新加坡政治斗争的现实密切关联。1959年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上台伊始就面临行动党内部的挑战。人民行动党就受到内部的亲共派和非共派为争取党内的主导权而较量、外有社会情势的双重压力,因此,人民行动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就必须迎合社会大众民意。而解决“屋荒”问题是当时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之一。而且,在上台执政前,为取得民众选票支持,人民行动党就已承诺解决住房问题。因此住房问题的解决不但能够兑现选举时的承诺以获取民众的支持,而且能够使那些希望得到住房的人成为人民行动党的潜在支持者[8]90。基于以上原因,人民行动党把解决屋荒问题作为首要执政目标之一。
三、独立建国后组屋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塑造
与战后大多东南亚殖民地主动争取国家独立不同,新加坡的独立体现了其独特的方式。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然而,由于理念的分歧以及种族之间的冲突,新加坡终于在1965年8月9日被迫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些国家原本独立,一些国家争取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10]5另外,新加坡是一个由移民发展而来的多元种族社会。就历史发展而言,各族群没有共同认同的历史基础。而民族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和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内涵。对于独立后的新加坡来说,由于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有各自的认同和离心倾向,国家认同的建构不可能以民族主义作为认同的基础。因此,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不能以单一的族群认同为基础,否则各族群的整合必然陷入危机。换言之,新加坡政府是由国家机器为主导,将众多族群认同纠合为一个集体的国家认同,打造一个属于多种族的国族国家。为塑造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新加坡政府把各族群的文化认同置于国家的认同之下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教育与语言、文化政策。除了以上措施之外,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在逐步解决住房问题的同时,围绕组屋出台相关政策及组屋区管理制度,以达致凝聚和塑造各族群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的目的。
(一)通过“居者有其屋”政策塑造国家认同
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实施于1964年。初期由于首付款过高,购买房屋者不多。1968年,为减轻社会大众购买房屋的经济负担,新加坡政府修订了《住房所有权规划》并出台新规定:允许购房者使用个人中央公积金支付住房首付款。该项政策的出台使得大多数人能够买得起政府提供的组屋,新加坡的组屋政策逐渐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
新加坡政府“居者有其屋”制度的实施不但解决公民的住房问题,而且在新加坡建构国家认同的背景下,使政府得以把住房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手段之一,即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实施把个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设想最早体现在1964年李光耀和工会领导人的谈话之中。他认为,解决公民的住房问题不但让人们产生对政府的感激之情,而且是永久的感恩,并且他也察觉到人们潜在的需求:人们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居住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想要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11]。基于这一认识,他产生了让人人拥有住房的观念,如果人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把捍卫国家当作自己的责任,从而形成对新加坡国家的认同并增强人们对国家的凝聚力。正如李光耀所言:“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他们会认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没有奠基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10]111可见,“居者有其屋”的实施以及拥有自己的房屋以培养各族群对新加坡国家认同感是政府考虑的一个因素。事实上,对新加坡的大多数人而言,拥有组屋是其最大的财产,有自己的房屋更能认同新加坡国家。
(二)建立组屋分配制度以打破各族群集中居住的形态
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各族群分割居住以及形成各自的文化认同是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此,要塑造各族群的国家认同,就必须打破各族群的各自分割的居住形态。为达到这一目的,新加坡政府通过严格的组屋分配制度从根本上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居住形态。
政府采取打破族群界限分配组屋的政策始于新加坡马来人对组屋分配特权的要求。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积极推动与马来亚合并,1964年,马来人和华人冲突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巫统交恶,随后,当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分配组屋时,马来亚政府向新加坡提出单独为马来人安排一个享有特权的专有的居住区域的要求,遭到新加坡的断然拒绝,马来亚政府对新加坡政府提出强烈批评。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政府逐渐认识到分配组屋必须打破不同族群的界限对族群和谐的重要性。李光耀说:“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都秉持这个信念。”[10]8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建屋局分配房屋时把打破族群界限分配房屋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固定下来。
按照住房制度规定,建屋局在销售和分配组屋时,同一组屋和邻区由不同比例的族群构成。新加坡政府倡导的多元族群和谐社会也应该体现在组屋分配上,各族群在同一组屋的居住位置不能由自己任意改变。但对于新加坡的不同族群来说,各族群大多倾向于同族群集中居住在一起,因为同一族群集中居住不但能够享有共同生活习惯和风俗以及团结争取获得共同的利益,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骚乱的记忆使得他们认为集中居住能够增强自我保护的力量。然而,从人民行动党国家认同和族群和谐的角度而言,要避免族群冲突就必须首先打破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族群集中居住形态,为各族群交流和融合提供一个在空间上交流的平台。正如李光耀所说:“政府为打破原来的居住模式,我们按照人口比例以抽签的形式把不同的族群家庭均衡地分布在一个单元,这样做能够使我们的社区更加社会化。”[12]294-296换言之,必须把不同的族群按一定的比例分散安置在共同的组屋区。因此,20世纪70年代,在政府的引导下,出于各族群家庭在组屋区均衡分布的目的,新建的小城镇分配组屋时,建屋发展局规定了不同族群在房屋配额上按比例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获得组屋。
然而,20世纪80年代,随着组屋交易数量的增加,一些新建的小镇的组屋又出现了某一族群集中聚居的情况。为达到族群融合的目的,1989年3月,新加坡政府出台了族群融合政策。该政策对各族群的组屋和邻里区的配额严格限制。该政策适用范围包括新组屋、转售组屋、置换组屋和DBSS(私人开发商设计、兴建和销售计划)组屋的购买。
种族融合政策在邻区和大楼的楼层上为所有族群(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与其他族)设置了最大比例。该政策规定:只有属于那个没有超出政策规定的比例的族群成员,才可以在该区域和单元购买、销售和出租。如果某一族群的组屋和邻区限额超出,该族群在该区购买则受到禁止,但买者和卖者属于同一族群则不受此限制[12]。
(三)通过分配资格限制组屋推行国家价值观念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是新加坡国家的价值观之一。这一价值观也借助住屋政策推行和倡导。这主要体现在对组屋购买者的资格的限制方面,组屋的购买者必须是以家庭为单位。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推行以家庭为主的居住模式,新加坡政府就规定以家庭为单位获得组屋。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居者有其屋”政策的顺利实施,新加坡的组屋逐渐成为政府社会规划的精心设计的附属物[13]。此后,政府对申请者限制更为严格:必须是一代以上的家庭。大家庭观念的推行,取得了良好效果。1990年3月,《海峡时报》对603979户的调查发现:一代的家庭占8%,二代家庭居住的户数占77%,二到三代住在一起的占总数的15%。通过该政策的实施,政府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除了推行价值观之外,政府推行家庭居住方式体现了政府的综合考量,即让新加坡公民明晓照顾老人的义务由家庭来承担而非政府的义务。李光耀曾说:“要加强儒家的传统,一个男人应该对家庭、父母、妻子和孩子负责。”[10]121在19世纪70年代,当政府发现年轻人选择居住在远离父母的组屋时,建屋发展局制定措施:父母和结婚的子女的组屋被分在彼此邻近的小区以便于互相照顾。1982年建屋发展局进行的调查显示:这种安排效果明显,老人和子女之间可以互相照顾,在不影响各自家庭隐私的前提下,父母和子女得以和谐相处。而对于少数的非家庭个人,如未婚或终身独身的购房者,政府严格规定禁止购买政府组屋,而只能购买价格昂贵的私人开发的房子。直到1991年,这一严格规定才放松,在家庭成为主要购房者的情况下,政府逐渐对单身购房者放松管制,推行了单身新加坡公民购房计划,允许单身者选购任何一个组屋新镇的转售组屋[14]。
(四)建立国家社会控制网络,加强族群间沟通
为加强各族群对国家的凝聚力,人民行动党政府打破原来各族群的传统社团组织,成立现代化的社区基层组织承担起传统社团的社会功能。1960年7月,法定机构——人民协会成立,现在该协会已发展成为全国社会基层组织的总机构。在人民协会的支持下,政府在各个组屋区设立居民联络所作为其基层组织。2003年,在组屋区共有居民联络所106个。其职能主要是代表人民协会建设和管理民众俱乐部,它主要是组织举办文化、教育、娱乐等公益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加强对社会基层的管理和控制,人民协会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执行地区居民参加社会、文化、教育及体育活动的企画和实践,并借此提高超各族群之利害关系的‘新家坡人’的国民意识。”[15]因此,政府组织的由不同族群参加的活动增进了不同族群的相互了解。
在组屋社区内部,政府设立三个组织机构:居民顾问委员会、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居民顾问委员会地位最高,主要负责整个社区内的公共福利,协调另外两个委员会和其他社区组织工作,根据居民的要求与政府沟通;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负责中心运行并制定从计算机培训到幼儿体育活动的一系列计划,下设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组织;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的重要组织,它主要承担治安、环卫工作,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促进邻里和谐,以增加不同族群之间的认识和了解。管理委员会人员的构成更能体现政府对社会基层组织控制。主要人员不是由选民选出,而是总理公署直接委任。在功能上,“充当政府和人们间的通信渠道,让人们把意见反映给政府,政府向民众解释政策”[16]。民众联络所对于促进社会一体化和国家发展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它们被当成一种重要媒介,以发动群众,支持官方政策。在对旧组屋改造过程中,政府规定,在选举中明确支持人民行动党的组屋选区,政府就优先对组屋升级改造[17]71。
五、结语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塑造各族群对新加坡国家认同是人民行动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各族群集中聚居且相互分割的模式以及由此形成各自的文化认同,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建国后新加坡的国家认同的塑造。新加坡政府出于塑造国家认同的需要,把解决民众急需的住房问题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特别是通过“居者有其屋”以及分配政策,把各族群安排在不同的组屋和邻区,打破了殖民时期各族群集中居住的模式,形成了新的居住形态,从而为族群的凝聚和融合创造了一个活动的空间。同时,新加坡政府也以此为平台在组屋区建立社会控制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族群的交流和融合。当然这一居住形态也存在缺少人性化、传统的人际关系受到影响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政策置于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所面临的历史和国家建构的政治现实背景下,人民行动党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为人所称道。该政策不但解决了人们急需的住房问题,而且引导和塑造了各族群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新加坡历经4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现代城市国家,住房问题的解决以及族群之间的和谐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1]C.Mary Turnbull.A History of Singapore 1918-1975[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15.
[2]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M].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10.
[3]潘玲.海外华人百科全书[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204.
[4]宋哲美.东南亚华人建国史[M].新加坡:立信印刷公司,1976:9.
[5]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4.
[6]曾玲.越洋再建家园[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8.
[7]南洋商报.新加坡一百五十年[M].新加坡:南洋商报,1969:135.
[8]Diang K.Mauzy and R.S.Milne.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M].London:Rortledge Publishing Press,2002.
[9]Yue-man Yeung and D.W.Drakakis Smish.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Public Housing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J].Asian Survey,1974(3).
[10]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下)[M].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
[11]Lee Kuan Yo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1965-2000[M].Times Media Private Ltd,2000:116-118.
[12]Loo Lee Sim.Public Housing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J].Habitat International,2003(2).
[13]Michael Hill and Lian Kwen Fwen.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 Press,1995:118.
[14]新加坡年鉴2000[M].新加坡: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和联合早报,2000:157.
[15]田村庆子.超越国家管理——新加坡[M].吴昆鸿,译.台北:东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1993:78.
[16]游报生,林崇椰.新加坡经济社会25年[C].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1984:233.
[17]Ooi Giok Ling.Housing in Southeast Asian Capital Cities[M].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71.
[责任编辑孙景峰]
K339.6
A
1000-2359(2011)04-0152-05
夏玉清(1970—),男,山东兖州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南亚历史、华人华侨社会文化研究。
201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