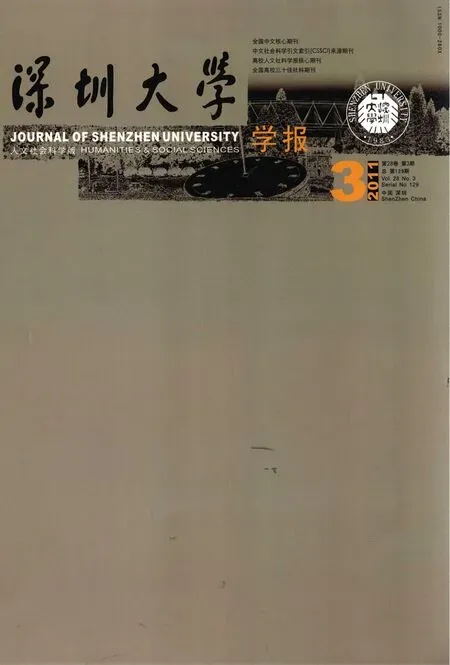儒家德性伦理对社会和谐与生命发展的价值
2011-04-12李忠红
李忠红,王 贺
(东莞理工学院校长办公室,广东 东莞 523808)
儒家德性伦理在二千余年的传承中,产生了持久而强烈的礼治凝聚力与德治感召力,这是其作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也与其有效传播、普及教化的形式要素有密切关联性。随着现代伦理学的中心话语从“人应该做什么”到“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转向,儒家德性伦理掀起了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规范伦理学(以功利和义务概念为中心)的批判性文化思潮,要求重新审视儒家德性在当代人的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研究儒家德性伦理普及教化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其形式要素方面的有效经验,便成了探索适应目前时代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运行机制的必然话题,也是其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和个体生命发展的价值意义之所在。
一、儒家德性的伦理之源
通常意义上,德性伦理也称为美德伦理,“‘美德伦理’(the ethics of virtues),是指以个人内在德性完成或完善为基本价值(善与恶、正当与不当)尺度或评价标准的道德观念体系。”[1]严格说来,儒家德性伦理学说中的“德性”是与“美德”等同的集合概念,从词源追溯,儒家“德性”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地官·师氏》,曰:“敏德以为行本。”在此,“德”即“德行”,东汉郑玄进一步注释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指道德已经转化为人的一种“在心为德”的内在品格。
从孔子开始,“德性”的内涵开始有了“仁”的意蕴。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孔子心目中,“君子”具有完满德性的社会代表人物,“仁”是君子“德性”所具备的必修之德,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时刻不离开“仁”这种德性,哪怕是仓促之间,颠沛流离之际都必须致力于“仁”。这种观点被他的弟子传承了下去。在众多门徒中,孔子对颜渊非常欣赏,因为颜渊的日常生活符合完满的德性标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同时孔子也是“饭素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这种“孔颜之乐”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具有真实德性的人,不论处在何种遭际状态之中,即使是自我独处,也会以“慎独”的态度趋善弃恶来追求“仁”,进而使自己能够具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因此,“仁”不仅具有人生修养的意义,更被赋予了社会责任的价值,“仁”概念也最终成为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所有的德性都围绕着一个“仁”来展开。
在孔子对“德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孟子对“德性”内涵进行了更加深刻地厘析,为“德性”增加了人性“善”的内涵。他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生而有善性,即德性来源于人的先验本性,他进一步阐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孟子·离娄下》)即是说真正道德意义上的人应该是具有“善”德性(察于人伦)之人。
从“德性”修为的角度来说,孟子认为,“德性”如仁义理智是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声色利货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孟子·尽心上》)正是因为“德性”是“求则得”、“舍则失”,所以,孟子认为要想成为有“德性”的人就必须“尚志”,在社会生活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充分发挥人的意志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通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的道德修为方式,“君子”在道德生活的实践中便能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进而“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孟子·离娄下》)即是说人们致力于对道(德)的“深造”,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德性,自得其性之后,便会感到如处于安宅,有深厚的凭借之资,就可以自觉地“尽心”、“思诚”、“居仁由义”,发扬人的善性了。
从孔孟对“德性”的认识与发展的历程中不难理解,儒家德性是以“仁”为核心概念,经过对“仁”之内涵的扩充与外延,最终将作为内在于心的道德精神形态的人性“善”德性,通过道德主体(人)在道德践履过程中外化为现实的德行的伦理过程。因此,有学者说,“由五伦到三纲,即是由自然的人世间的道德进展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宗教意味的礼教。”[2]不过,儒家德性的外化,并非远离现实的生活世界,而是道德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即在“日用常行”中身体力行,从身边的点滴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在“推己及人”的基础上,肯定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成为有德性的“仁”者(君子)。
二、儒家德性伦理的逻辑理路
(一)天理良心:儒家德性伦理的价值尺度
儒家德性伦理是以“仁”为中心的,孔子主张:“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也就是仁者安于仁、以仁为目的就行了,而知者则要以仁为中心,一切行为以利于仁为目的,仁是知的目的。但是,哲学话语体系中的理性是德性的一个内在规定,所以,儒家德性伦理中,“理智从属于德性——仁,以仁为目的”[3],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儒家德性对于价值尺度(价值判断)的观点。
与此同时,考察儒家“德性”伦理的价值尺度,有两个角度,一是“天”的视角,如程颐所说:“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秉受言之谓之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即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德性”源自天赐;二是“人”的视角,即“得天为性”,即是说人得天命而成人性,“德性”得自天,人性源于天,推而广之,不仅人,万物之性也都是得天为性的,正如《周易》中所谓“乾(即天)道变化,人、物各正性命”(《周易·彖传》),这种思维模式奠定了儒家“德性”伦理主体性价值尺度的哲学基础,也为其找到了存在论 (Ontology)依据,当然也是价值的存在论基础。
进一步来看,儒家德性对于价值尺度的观点,是儒家德性“善”内涵的合理扩展。从孟子“性善论”开始,因为人性本善,所以只要循性而行,也就无所不善了;假如人性本恶,那么,循性而行就成了随心所欲地作恶了?因此,孟子“人性本善”思想成了儒家德性伦理的正统。具体来说,儒家德性伦理葆涵的人性之善包括了仁义礼智 “四端”(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是仁之依据,羞恶之心是义之依据,恭敬之心是礼之依据,是非之心是智之依据,最终,“仁、义、礼、智”四德成为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概念。
儒家德性伦理的向善趋势,从孟子那里开始被称之为“良知”或者“良能”,即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进一步“良知”又称之为“良心”,不难理解这种作为德性的“良”是天所赋予的,所以又进而称之为“天良”;到了宋明理学那里,“天”又称为“理”或者“天理”。这种理论上的理解,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价值判断中,可以进一步表述为:人们的伦理生活准则要符合“天理良心”的价值尺度,这是儒家一切正面德性价值的最高尺度,因为人的生存,无非是使善性得以弘扬,“求其放心”、扩充善端是人生存在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进而成圣成仁,所以养善性、陶化美德必须围绕“天理良心”的价值尺度。
(二)修齐治平:儒家德性伦理的终极目标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终极关怀始终是伦理学讨论的热点。那么,儒家德性伦理的终极目标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礼记·大学》中,儒家提出了实现德性的“三纲八目”。“三纲”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如果说“三纲八目”是传统社会个体德性修为的规范,毋宁说这即是体现了儒家德性伦理的终极目标。所谓“明明德”,前一个“明”是动词,意为“明白”,后面两个字“明德”也就是“德性”的意思。所以,“明明德”可以简称为“明德”——即明白自己的德性,或使自己的德性得以昭示于人。那么,如何才能“明德”呢?儒家分为两种途径:一是“自诚明”,二是“自明诚”。“诚”的意思,也就是人的德性之善。《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就是说,“自诚明”就是由“诚”而自然地达到“明”,亦即凭自己本来固有的善性就能明白自己这种善性,“诚则明矣”;“自明诚”则是先由学习而达到“明”,然后再由这种“明”而达到“诚”,亦即通过学习来使自己意识到自己所固有的善性,“明则诚矣”。对大多数人来说,要想“明德”,就得“修身”或者“修道”;而要修道,就须教育,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但是,仅仅“身修”了还是远远不够的。修身不是目的,至少不是终极目的。儒家德性伦理的终极目的,乃是追求一种“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即是“平天下”的境界。总起来说,就是实现一个安乐祥和、丰衣足食的礼仪之邦、道德社会。
儒家这种从自我修身到平治天下的德性修为路线,被后世儒家、尤其是新儒学概括为“内圣外王”(《庄子·天下》)。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内圣”,即通过“格物致知”达到的“正心诚意”;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就是“外王”,即“平天下”。不过显然,虽然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语)、“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语),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人人皆能做到的事情。后来的宋明儒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力图将它改造为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普遍的德性价值实现途径,于是才有了“满皆都是圣人”之说,但实质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典儒家德性伦理的本质”[4]。
三、儒家德性伦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德性伦理是一种与传统社会 (即身份制和等级制)相适应的美德伦理,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境。如果儒家德性伦理仅仅对于传统社会具有意义,那么,本文探讨儒家德性伦理现代价值的努力,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游戏,而没有实践上的意义。实际上,儒家德性伦理普及教化的合理内核,以及其形式要素方面的有效经验对今天促进社会和谐、提升生命质量等方面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促进社会和谐、成就德治社会的思想基础
人的本质不在人的自然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其中,道德是最基本的属性。孟子认为,人与禽兽区别者“几希”,这“几希”者不是别的,就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道德品性。毋庸置疑,现代社会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丰裕的物质生活完全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面貌,“德性”作为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中心性地位丧失带来了种种问题,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道德生活的功利性以及在技术价值的中心性化等,这一定意义上暗合了社会文化传统的 “礼乐崩坏”(孔子语)。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道德元素是社会文化传统中最具稳定性的基因,所以,现代社会的和谐迫切需要“德性”来维护。
随着后现代社会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兴起,以及人们社会道德关系的碎片化和工具性的价值认同,使得德性处于边缘地位。毫无疑义,现代社会的德性由于现代生活形态的改变,已经相当不同于孔孟时代的社会了。因此,完全孔孟式的德性我们不能遵循,但这不是说儒家德性已无价值。在认识论的层面,儒家德性伦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方面,其“仁”思想,可以转化为与人为善,尽己待人,推己及人,人情互动、人际和谐的新型伦理价值观,即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利义”思想,启发我们为人正派、坚持正义,处理义利关系要见利思义、利以义取,不要见利忘义,“以‘义’作为价值向导,做一个具有道德自觉性道德独立精神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被欲望、权势所摆布的‘物役’、‘人役’之人。”[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伦理思想不失为现代社会个人为人处事、正当谋利、团结协作、互惠双赢的社会主义伦理关系的思想基础。从方法论的层面讲,儒家德性伦理不是将某种天赋的法则作为社会有序化的依据,而是立足于主体自身德性的完善,使主体(道德自我)在成其德性的前提下,达到明其规范,成就德性的目的,从而使一切社会生活的有序化真正转变为主体自觉遵从的目标,进而促成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这也是儒家德性伦理“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德治社会理想目标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所在。
(二)完善德性修为、提升生命质量的心理基础
儒家德性伦理以“仁”为核心进行逻辑推理的,“仁”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人性的“善”。儒家认为,人的自然秉赋是“德性”形成的基石,构成“德性”的道德因素有着某种先天的传承,“德性”的培养也是一种符合人的天性的活动。正因为德性源于人性,所以德性的培养与形成过程,也即是人性的完善过程。对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化,利益冲突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同一个家族、一个宗族内部的利益冲突,同时现代社会对个人生活最重要的切割是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的分化,出现了“陌生人”社会,个人德性时常“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黑格尔语),因此,儒家德性“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追求便具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资本的“贪婪攫取性”将传统儒家个人道德由“出世”的纯粹理想境界转向“入世”的世俗化心态,这种“个体德性修养的心理转换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人们道德失范的可能性”[6],现代社会的职业生活、城市生活以及网络生活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改变造成了人类生活中功利与义务的泛滥,但功利与义务不可能替代德性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发挥作用,因为德性并非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心理状态,而是任何一个道德自我的内在品质。
虽然“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当代道德建设固然首先要进行一种基本底线伦理的教育,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但更重要的是,道德作为人生提升的重要方面,作为持久而内在发挥作用的精神机制,却需要社会成员具有一种内在道德精神即对道德原则的信仰、持守和坚持。”[7]但是,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的功利追求改变了人们道德理想的目标,以及对待物质利益的价值态度,也逐渐改变了德性的性质,丰富了德性的内涵,并且对于现代德性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人面对的是远比古人更强大的贪欲和私欲的诱惑,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虚拟世界又使得现代人有着更多作恶的社会可能,这些都对于人的德性提出了远比儒家慎独更高的要求。
所以,儒家德性“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天理良心”的价值尺度,某种程度上可以担负起现代人的道德追求向传统回归、寻求道德价值观念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石。进一步解释来说,可以在儒家“忠、恕、智、勇、孝、悌、温、良、恭、俭、让、宽、信、敏、惠”等德性思想基础之上阐发现代社会的各种美德。儒家德性追求的崇高道德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心系天下、建功立业社会责任,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人类整体生命质量的关注,都可以使个体道德自我获得一定程度的内心的满足。通过对主体内在德性的品质的培养、教化,强调主体在此道德修为过程中,儒家德性伦理使许多人获得一种内在之乐,一种精神的受用,这不仅有其情感的基础,而且也具有了一种终极关怀的意义。当然,儒家德性伦理追求的人生境界不可能完全替代人们内在心理要求的信念(信仰)满足以及对彼岸、来世的期盼,因此,这就需要现代社会的信念伦理在人们生活的一些方面做出补充。不过,现代社会生活仍需要德性伦理,而且需要具有更丰富时代内涵的儒家德性伦理,这也正是它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
[1](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42.
[2]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A].贺麟.文化与人生[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4.
[3]耿有权.儒家教育伦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9.
[4]梁启超.儒家哲学[M].长沙:岳麓书社,2010.127.
[5]霍国栋.孟子“义”德思想析论[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48-52.
[6]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41.
[7]肖群忠,张英.先秦儒家气节观及其现代意义[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41-47.
[8]杨伯峻.论语译注[O].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徐洪兴.孟子[O].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