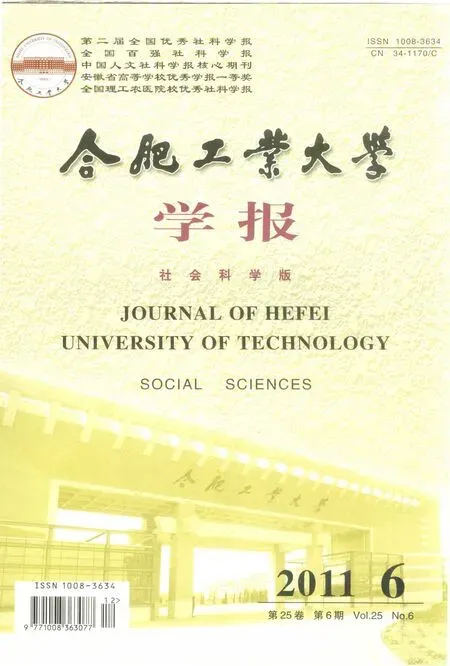道教美术之雅俗两重性
2011-04-07程群
程 群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道教美术之雅俗两重性
程 群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道教美术拥有雅俗双重品格,“雅”是指其符合中国文人的审美需求,蕴涵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是皇室、贵族崇奉道教的见证者,构成皇室艺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文化性、文人性、庙堂性与贵族性之特质;“俗”是指它常常侵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相胶着,充当普通民众的精神安慰剂。它又处于民间庆典祭祀的中心地位,与民众最欢乐、最庄严的时光共在共融,其内容贴近民众的生活,为世俗民众所喜爱,具有民间性、世俗性、大众性以及草根性之特质。道教美术双重品格的形成是由道教及道教美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所决定的。
雅俗;形成原因;道教美术
道教美术是指以道教思想为核心内容或者为道教文化服务的美术,为传播道教作出过重要贡献。道教美术拥有雅与俗双重品格,其形成则是由道教以及道教美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所决定的。
一、道教美术“俗”之品格
道教美术具有“俗”的一面。郑振铎给俗文学之“俗”的界定是:“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1]郑氏对于俗文学之“俗”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于对其他艺术包括道教美术之“俗”的界定。道教美术之“俗”是指它蕴含着民间性、世俗性、大众性或草根性品格。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道教美术融进了普通民众生活与工作的各方面。人们相信,道教塑像与图画所描绘的神灵真实地存在于天上某处,通过特定的宗教仪式,可以招请它们降临人间现世,指引诸多工作的顺利开展、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例如走进皖南黟县乡间任何一个家庭,迎面而来的是贴在门上的彩绘的道教门神,挨着门的地方摆放着土地爷的供桌及塑像,道教天官塑像供奉在院子里,财神爷被置于厅堂或正房里,灶王爷供奉在炉子上面。在危机来临或遇重大事件时,人们在家中还要设置其他神龛或悬挂神像,加以虔诚供奉[2]。当地民众对此解释是:门神保护家宅;土地爷保护全家平安,并且审视家庭成员是否恪守宗教道德和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财神爷则能给家庭带来富裕;灶王爷在年末要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报告该家庭成员一年的行为举止,以决定这个家庭是应该得到奖赏还是受到惩罚。再如,在皖南商业社会中有崇拜行业神的习俗,其中多数为道教尊神,如铁匠崇奉老君、染匠崇奉梅葛仙翁等。在这些行业人家的厅堂中常常要悬挂所崇拜的行业神画像或摆放它们的塑像[3]。当地商人确信,这些道教神灵在冥冥虚空中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举止。人们只要对这些神灵保持虔敬之心,并多行善举,才会得到神灵的佑护,令生意兴隆;反之,如果经营奸诈,那么必将遭到行业神的惩处,令之生意破败。这些神灵为商人们的经营活动提供正义性规范与指导。可以说,神灵绘画或塑像等成为人们随处可遇的家庭宗教文化景观。
在传统节日中,道教神灵画像或塑像的地位尤其显赫,处于节日庆典祭祀的中心地位,与民众欢乐的时光相伴相融。旧时扬州地区每年都要为诸种道教神灵举行生日庆典。二月过土地爷生日,三月过东岳大帝生日,四月过西岳大帝生日……。在神灵生日的当天,人们总是要抬出相应神灵的塑像或悬挂它们的画像,安放于空旷之地,接受人们的膜拜。随后,人们要敲锣击鼓巡游于大街小巷,举行庆典,并且家家户户会在当天设宴,邀集亲友共同为神灵祝寿[4]20。人们相信,通过这种活动,可以赢得诸位神灵对于本地区民众的保佑。有学者认为:“这些塑像或图画多出自民间艺术工匠之手,……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呈现出朴拙粗犷之风貌。”[4]28这些道教美术作品构成庆典活动的中心,整个庆典凭借这些神灵塑像或画像的在场才得以顺利展开。
道教美术中描绘的神仙神灵形象也曾深深浸入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人生在世常常会遭遇种种难题,例如,如何摆脱死亡带来的心理阴影,如何获得丰裕美满的生活,等等。譬如说,生命易逝是人生所遭遇的最大痛苦,人们对“长生久视”的深情呼唤从未停歇,“日月终销毁,天地同枯槁。……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堂,藏身以为宝。”[5]如何克服死亡带来的恐惧,恢复心灵的宁静,成为人们关注的大问题。道教吉祥图画等美术作品往往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这种担忧,充当人们的精神安慰剂。在皖北农村,人们给老人祝寿时,喜爱在家中墙壁上张贴“麻姑献寿图”、“龟鹤齐龄图”等[6]。前者描绘的是道教神仙麻姑在三月三日西王母圣诞时,赴宴向西王母敬献仙桃的情景。后者描绘的是神龟神鹤与道教诸仙共舞的景象。当地民众认为,将这些吉祥图画张贴于家中,不仅可以给整个家庭增添喜庆气氛,更重要的是,只要对画像中的神仙虔诚敬拜,这些神仙就会迅速显灵,赐予家中寿星乃至其他成员更为绵长的寿命。在这里,道教吉祥图画是作为民众的精神安慰剂在场的,它帮助人们削弱“死亡”带来的精神阵痛,将人们的目光引离对死亡的关注,而更多关注于当下欢乐的在世时光。
再譬如物质匮乏会给人带来难言之痛。在民间,人们相信于家中张贴特定的道教吉祥图画,有助于财物丰隆。在陕南乡村,人们过新年都要在大门上张贴“刘海戏金蟾”、“刘海戏金钱”等图画[7](据专家考证,图画中的“刘海”指的是全真派南五祖之一的道教神仙“刘操”)。民众相信,这些道教吉祥图画张贴于大门上,能够形成吸纳金钱的强大磁场,为整个家庭在新的一年里引来丰厚的财富。我们分析,这些吉祥图画为物质匮乏的民众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安慰,这种精神安慰至少包括这样的内容:神仙“刘海”与我们共存于这个世界之中,他终将会降临人间,赐予我们充足的财富,帮助我们抚平物质匮乏带来的心灵创伤。这样,“刘海洒钱”等道教吉祥图画也转化成世俗民众对于美好生活深情呼唤的符号象征。可见,道教美术成为生活中重要的精神安慰剂。
道教美术贴近民众生活,其内容往往又揉合进了一些民众生活的景像,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审美需求。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一些艺术创作者,热衷于创作远离普通民众审美需求之作品,让自己的创作成为超越平庸处境的精神高地,以划清自己与大众之间的精神界限,彰显自身的卓而不群。这样的艺术之作很难满足基层民众的审美之需。举两个例子:南宋画家扬无咎有一幅《四梅图》,仅仅画梅花四枝,有评论家点评:此画“用焦墨渴笔画枝干,用饱蘸浓墨画枝梢,时见飞白。淡墨白描花瓣,浓墨点蕊。笔法清淡野逸。梅花如含山野清气,拂人眉宇。画作体现了作者一意孤行的强烈个性,并让人体会到他以独霜傲雪的野梅自况之意。”[8]这毕竟是学养深厚的文人评价,在普通民众的眼底,作品表现的不过是几茎梅枝而已。再例如,宋朝赵孟坚的《水仙图》,画面构图极简单。有文人评点:“此卷水墨水仙秀而淡雅。布局疏密相间,简繁得体。花与叶的形态先用白描勾出,线条匀停淡约。再用淡墨晕染叶面和花茎,叶子正面着墨,反面留白,层次分明。水仙仪态清贵,栩栩如生。”[8]47
在普通民众特别是缺乏审美素养的民众眼底,画面中只不过是毛笔扫出的几簇墨色水仙而已。与之不同的是道教美术的内容往往通俗易解。例如,在山西洪洞县水神庙明应王殿内有数幅元代道教壁画,其中的《庭院梳妆图》、《卖鱼图》等虽然本质上是道教题材绘画,但是其中融入了大量世俗生活景象,内容很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以《卖鱼图》为例,图中部分内容是对市民生活的精致描绘,图中一人执秤称鱼,前面有一渔翁,后面一张方桌,上置酒罐及杯勺等,桌旁有四人,后面又有栏杆……整幅画面洋溢着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这种贴近世俗生活的道教美术极易为社会大众所理解,能引发他们的共鸣与审美兴趣。
另外,道教美术常常是道教观念的载体,它将道经中记载的神仙事迹转化成感性的图像。这些图像常给人们带来强大的精神震撼,于潜移默化中向人们宣传道教,达到扩大道教影响之意图。例如,道经记载的葛洪携家眷移居罗浮山炼丹成仙事迹,经常被当作道教绘画的题材。五代有黄筌、李昇的《葛洪移居图》,元代有王蒙的《稚川移居图轴》,清代有胡慥的《移居图》等[9]33。这些道教美术作品是以图象语言描绘葛洪的事迹,究其实质,它是在传播道教文化,较之于道经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二、道教美术“雅”之品格
道教美术之“雅”主要是指它蕴涵着文人性、文化性、庙堂性之品格。历史上曾有很多艺术家和文人参与道教美术的创作与评价活动,这使得道教美术的文人性、文化性气息愈发浓郁。有人谈到文人与艺术作品之关系时说:“中国传统文人常常借助于绘画、音乐、文学、书法等等艺术抒发他们或昂扬或落寞、或激奋或忧郁的情感。文艺成为他们精神、情感与意志活动最重要的载体,是中国文人或优美、或崇高、或轻盈、或凝重、或阳刚、或阴柔之诗意文心的符号化形式,成为中国文人诗意文心铺展的方式,体现着他们深邃曲婉之灵心。”[10]同理,由文人和艺术家参与创作的道教美术作品,往往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息,凝结着中国文人的生命意志、情调。道教美术作品与其它文艺一道,共同构筑起中国文人精神的诗意家园。
举两个实例。其一,钟馗是道教神仙谱系中的神灵之一,被人们认为有除恶驱邪之神力。文人创作的“钟馗捉鬼图”往往是要表达出创作者内心对于现实的不满与愤懑之情,暗含着作者希望扫清尘世中的一切乌烟瘴气的高洁理想,彰显出中国文人对理想社会形态及理想现世生活的追求。元初龚开的《中山出游图》很能说明问题。有学者研究,此幅图画是以群鬼喻元兵,以钟馗喻能够重振宋室的猛将,表现作者对于外民族入侵者的刻骨仇恨,传达作者希翼驱除元兵、恢复宋室、还天下太平之梦想。图画之中凝结着作者忧郁、焦虑而又充满渴望的情感[8]55。其二,清代华嵒绘有《钟馗嫁妹图》。有学者认为,作者借助此图,描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类魑魅魍魉,尖锐讽刺和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丑类、丑行,寄托作者对于正义社会形态的深切诉求[9]59。“神仙高道”也是道教美术中常见题材,传统文人常常借助笔下的神仙或高道形象,传达他们对于自由不羁生活的强烈憧憬,抒发他们由黑暗或庸常现实带来的不平之情绪等。例如,画家颜辉创作过很多道教绘画,文人气息与韵味十分厚重。这些神仙、道士形象大都古怪、丑陋,人物背景幽幽忽忽,如仙境、如冥境,令人有神秘莫测之感。创作者精神、意志在画中有非常突出的流露。《铁拐李图轴》是其道教人物画中的杰作,有评论家认为:这幅作品让人感到创作者强烈饱满的情感意绪,作者是运用粗怪不羁的笔墨营造外部世界或人物超凡脱俗的奇形骇貌,来表现和宣泄他身经乱世,内心的不宁和焦躁[11]。归根结底,这些道教美术往往承载着中国文人的深厚情感,成为他们精神自由高蹈的理想家园,流溢着浓烈的文人性、文化性气息。
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是造成艺术之“雅”的重要因素之一,无法想象内容空洞、意蕴浅薄之作能够被视作“雅”艺术。道教美术之作中常常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元素,它往往以道教经典或历史作为其产生的依托。例如,道经中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的事迹是道教绘画中常用题材。绘画史上有多幅《雪山应聘图》,其中分别属于元代、清代的各一幅最著名,描绘了丘处机带领十八位弟子去谒见成吉思汗的路上情景。属于元代的作品现藏于北京白云观,图左下方题有“元人真迹,完颜崇厚识”。属于清代的作品作者为陈鉴,画于道光十二年。因为有道教史迹作为创作背景,使得这样的绘画文化底色异常鲜明,历史意蕴尤为厚重。再如,道经中描绘的神仙之境也是道教绘画常用题材。《三才定位图》为宋代张商英作,是对道经中描绘的诸天景象的刻画:道教仙境的最高层为虚皇十天,其中有天真九皇、虚皇元老、虚皇元尊等崇高诸神,其下为玉清天,居住天宝君……;再次上清天中居灵宝君……;最后泰清天中居神宝君……。此画按照道经的文字描述对道教诸天进行了图像描绘。总的来讲,很多道教美术作品都以道经或道教历史作为其创作的依托。这样,道教美术与道经常常形成相互印证之关系,道教美术也因此积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另外,很多道教美术之作同时融入儒释道的内容,成为多元思想文化凝结之艺术。位于贵州荔波县的积道宫中有一幅明代壁画《仙山论道图》,壁画的内容描绘的是儒释道三家人物端座于松间岩石之上谈玄论道的景象,呈现一派儒释道和合之气。画中一位高士面庞清癯,完全是清净无为的道家人物风姿。一位雅士则是长袖宽袍,头顶方帽,完全是洞穿世事的儒者气度。画中的僧人则慈眉善目,笑意满面。三人背后是飘渺的自然山水。有学者谈到中国绘画中自然山水的意义时说,自然山水一方面昭示出的是世俗人生对闲静生活状态的慕求,以及对闲适心灵状态的渴望。所谓:“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会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荡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山水之本意也。”[12]另一方面,自然山水可以把人的精神引离喧嚣的尘世,作为了悟人生的机缘和寻求心灵解放的手段而令人陶醉,与道家所追求的终极性人生境界和精神境界相契合,成为道家精神境界的符号表征。我们说,儒释道三家人物以及自然山水共存于《仙山论道图》中,说明这幅道教壁画中积淀着大量的儒释道元素,体现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风貌。多种文化元素共融于道教美术之中,使得道教美术蕴涵的文化底蕴格外深厚。
道教美术一方面深深融入于民间的祭祀庆典活动中,另一方面往往又浸淫于上层社会的祭祀庆典之中,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宗教生活相交织,彰显出统治者的崇高威权与宏大气魄,成为皇室文化艺术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道教美术濡染着崇高的庙堂性、贵族性特质。北宋武宗元曾创作《朝元仙仗图》,据学者考证,此图是武宗元为皇室宫观——玉清应昭宫壁画所作样稿。此图长六百厘米,高四十六厘米,描绘的是东华天帝君、南极天帝君率领众仙官侍从,排开仪仗去朝见玄元皇帝的情景,人物众多、场面浩大。每一人物都有题名牌,共八十七名。前有仗剑神开道,末有披甲神王殿后,二位主角比其他人略为高大,头有光轮,非同寻常。众神仙神态不一、动静有别,服饰各按其身份,多姿多彩……。我们看到,这幅绘画幅面极开阔,画中意象极繁富,神仙形象伟岸崇高,神仙出行场面气势恢弘,呈现出辉煌绚烂的宏大气象。可以说这种为皇室宫观所作图画是帝王崇高威权与气魄的符号象征,这样的图画铺陈于皇室宫观的墙壁上,必将呈现出崇高壮观之气势。需要强调的是,存在于皇室宫观中的壁画也融进了帝王的祭祀庆典活动中,成为皇室祭祀庆典活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对皇室祭祀庆典的顺利完成起到推动作用。葛兆光先生曾说,在宏大的皇室祭祀仪式中,“星灯闪烁,烟雾缭绕,道教的法术中,诡秘奇幻,变化莫测,道教的壁画仙姿绰约,瑞气浮升,道教的音乐钟罄齐奏,笙竽和鸣……令人‘临目内思,驰心有诣’,令人‘灵气相感,不由正衿’。置身在这种气氛中的人,怎能不精血沸腾、心动神摇,怎么能不想到昆仑、方丈、瀛州、蓬莱,想到玉皇、老君、玉女、仙人,想到自己上天入地、周游九霄、腾云驾雾,出将入相、入了富贵温柔之乡”[13]!这些道教壁画包括其它道教艺术积极参与和推动皇室祭祀庆典的圆满完成,亦步亦趋的迎合着帝王宏大的政治叙事之需求,充当帝王思想的宣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美术具有庙堂性、贵族性之特质。
三、道教美术“雅俗”两重性的成因
道教美术雅俗双重品格的形成是由道教以及道教美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在道教发展的过程中,道教曾不断地发生着分化,沿着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两个向度发展。道教侵入上层,与贵族以及文人阶层发生密切联系,导致道教文化包括道教美术必然濡染浓厚的文人性、贵族性、庙堂性之气息。例如,葛洪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民间早期道教进行改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伴随着道教在上层社会的传播,贵族阶层参加道教的人也日益增多,这些贵族参加道教以后,必然把他们的观念也带入道教之中。作为道教文化组成部分的道教美术必然会受到贵族阶层思想的影响,从而烙印上贵族阶层、上流社会的审美旨趣。再例如,道教在唐代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崇奉。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等都有浓郁的道教情节,他们毕生都与高道保持密切交往。期间,帝王、贵族的审美观念与情趣必然影响高道,从而影响道教文化包括道教艺术发展的旨趣和路径等[14]180。宋代君主也多崇奉道教,宋徽宗赵佶一贯崇奉道教,曾宠信道士、利用道士编造政治神话。宋徽宗曾宠信刘混康、林灵素等人,与他们有着密切交往[14]210。我们认为道教向着上层社会发展,贵族阶层在受到道教影响的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反过来也会深刻影响包括道教艺术在内的道教文化,作为道教文化组成部分的道教美术必然受到统治阶级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的影响,从而烙印上庙堂性、贵族性之深深印记。
另外,在道教发展史上,高道常常与同时代的文人发生密切联系。文人观念必然经由道士影响着包括道教美术在内的道教文化的面貌,也必然导致包括道教美术在内的道教艺术的文人性、文化性品格之形成。我们试看两个文人与高道交往的例子:李白早年即开始学道,先后居于嵩山、剡溪学道,并和一代道教宗师司马承祯有交往;天宝初他和吴筠同隐会稽,共同修道。李白与道士李含光也有密切交往。李白被朝廷斥逐出京后,求仙访道的活动更进入高峰期,曾于青州紫极宫从北海高天师受道箓,又访道安陵,造真箓[15]206。李商隐和道教也有密切的因缘。他早年曾有过“学仙玉阳东”的经历,曾亲自进入道门,从事养炼实践,后来更和众多道士亲密交往。他毕生研读道经,对神仙传说更是热衷[15]208。可以说,文人与高道之间的交往必然导致文人意识观念渗透于道士的思想世界中,进而影响道教文化。那么,作为道教文化组成部分的道教美术也必然深受文人意识的熏陶,造成其文人性、文化性特色的形成。
我们再分析道教美术“俗”之品格形成的原因。道教理论的渊源是“杂而多端”的,前道教时期的神仙思想和方术、谶纬神学等都曾作为道教滋生的文化土壤而为道教所吸收。而这些思想文化原本就普遍弥漫于前道教时期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人们随处可遇的文化景观,具有民间性、大众性之特征。例如,谶纬神学与秦汉乃至更早时期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秦代时,“谶”已经普遍存在,成为社会大众乃至王公贵族问讯吉凶、生死等最可信赖的方法。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就曾利用“谶语”。“纬”是“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在汉代,谶纬之学普遍流行于朝野上下,成为当时上层与民间知识分子共同热衷的学问。再例如,在前道教时期,神仙思想和方术一直在全社会范围内风行,为社会民众所广泛认可。神仙思想与方术起源也很早,在上古传统中就有关于神仙不死的理想,《山海经》里“不死之国”、“不死之药”等传说的记述可以证明。《庄子》中关于神仙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在秦汉时,神仙思想与方术由当时的方士所携带,四处播撒,导致这种思想遍及整个民间社会。茅盾也曾说:“神仙思想、观念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超自然行为,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对于渴望生命永恒、生活安宁的华夏先民却具有迷人的魅力,这些思想观念广泛充斥于整个民间生活之中,先民们互相传述,信以为真。”[16]我们说,夹带着草根性、民间性与大众性特质的前道教时期的神仙思想、谶纬思想作为道教理论滋长的文化土壤,那些特质很大程度上也会被道教所吸收。这必然导致包括道教美术在内的道教文化在诞生之时就烙印上草根性、民间性、大众性的深刻印记。
另外,道教美术作为中国传统美术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继承了前道教时期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传统美术的内容。而前道教时期以神仙信仰为核心的传统美术具有民间性、大众性之特征,这就决定了与前道教时期美术有着血脉关联的道教美术必定有“俗”之品格。在秦汉乃至更早时期,“信巫鬼,重淫祀”是荆楚之地民众的普遍风气,巫风在整个社会中蔓延流行。荆楚艺术一直与巫文化相互渗透、扭结,弥漫着诡美野性、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呈现出文明与蒙昧、理性与感性相交织之特色,民间性色彩浓郁[17]。也就是说,上古时代的荆楚文化艺术是扎根于民间,从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汲取营养的,从本质上说荆楚文化艺术属于民间或大众文艺。而“上古时代的荆楚文化艺术与道教文化存在着割不断的血脉关联。道教的神仙谱系中的很多神灵就直接来源于荆楚文艺思想体系。”[18]因而深受荆楚文化艺术影响的道教美术,也势必濡染上民间性、大众性之色彩,赋有“俗”之品格。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
[2](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7.
[3]牟钟鉴.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7:39.
[4]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中国俗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李 白.拟古[G]//杨牧.唐诗选集.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93:88.
[6]欧阳发.安徽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89.
[7]张忠国.陕西民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6.
[8]潘公凯.中国绘画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岳仁译.宣和画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10]李素军.艺术与审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57.
[11]王伯敏.中国绘画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80.
[12](宋)郭 熙.林泉高致集[C]//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一)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67.
[13]葛兆光.人生情趣·意象·想象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9.
[14]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15]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6]茅 盾.神话研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35.
[17]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5.
[18]段宝林.中国民间文艺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92.
Elegance and Secularization in Taoist Paintings
CHENG Q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Taoist paintings possess the dual nature of elegance and secularization.Elegance,which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cultures,accords with the aesthetic demand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It is a witness to Taoist beliefs of the imperial and noble houses,and a part of the artistic culture of imperial house,which possesses the unique cultural,aristocratic,intellectual and templelike characteristics.Secularization in Taoist paintings is connected with people's life and gives spiritual comfort to the people.I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folk celebration and takes place in the happiest or the gravest moments in people's life,the content of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and loved by the people.Secularization possesses the unique popular,folklorish,mundane and civilian characteristics.The dual nature of Taoist paintings is determined by the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aoism and Taoist paintings.
elegance and secularization;cause;Taoist painting
B958
A
1008-3634(2011)06-0086-06
2011-04-1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1M500689)
程 群(1972-),男,安徽肥东人,副教授,博士后。
(责任编辑 刘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