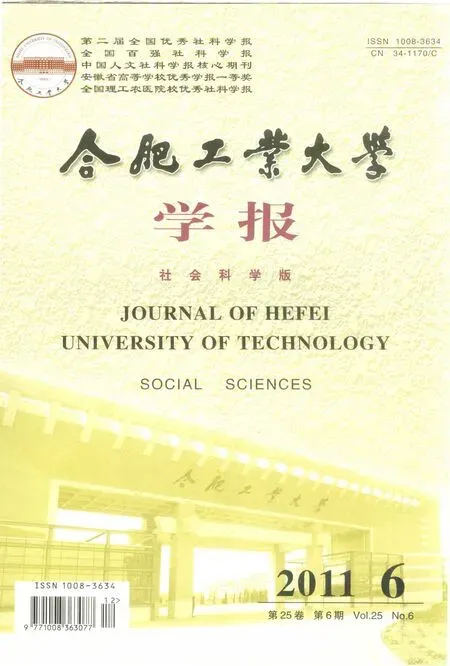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探索
2011-04-07胡兴文巫阿苗束学军
胡兴文, 巫阿苗, 束学军
(1.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 232001;2.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上海 200083;3.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外语教研室,合肥 230031)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探索
胡兴文1,2, 巫阿苗3, 束学军1
(1.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 232001;2.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上海 200083;3.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外语教研室,合肥 230031)
鉴于目前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中存在范围不同、标准不同、名称各异的情况,从宏观的角度以翻译的研究层次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三大流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和阐释学派,语言学派主要由对等派、功能派和认知派构成,而文化学派则涵盖了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综合法,其中翻译研究派又可进一步切分为多元系统理论、规范理论和操纵理论。通过从新的视角进行讨论,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流派划分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文艺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
一、研究缘起
在自古罗马西塞罗(Cicero)以来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史中,译论踵出,名目纷繁,令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有些学者于是尝试着从流派的角度对西方的翻译理论进行分类与考察,如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根据各流派所关注的焦点将当代翻译理论分为四个基本流派: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1];埃德温·根茨勒(Edward Gentzler)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aray Translation Theories)中,根据二战至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态以及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据的理论来源将当代西方译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2]Ⅴ;英国翻译理论学者曼迪(Jeremy Mundy)在其《翻译研究入门:理论与应用》(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中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等效与等值”、“翻译转换法”、“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话语分析与语域分析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的隐形”、“哲学翻译理论”、“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等九大流派[3]1-3。
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如廖七一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借鉴了埃德温·根茨勒的分类方式[4]23。香港学者张南峰、陈德鸿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分为“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和“解构学派”六大学派[5]Ⅲ。潘文国以有无翻译学学科意识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个阶段。他把传统阶段的翻译理论看成是“文艺学派”;把现代阶段看成“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把当代阶段的翻译研究划分为“翻译研究学派”、“解构学派”(或译者中心学派)和“后殖民主义”学派(或政治学派)三类,而翻译研究学派之下又细分为“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和“综合学派”四个亚类[6]。朱健平博士认为从研究层次看,翻译研究可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哲学学派[7]。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把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翻译的文艺学派”、“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的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美国翻译培训学派”和“法国的释意派”七大流派[8]9。刘宓庆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将西方当代翻译思想分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释义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后现代主义与翻译理论”、“心理-认知心理学派”和“新直译论”等七大流派[9]132。李和庆等《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70年代后》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存在八大研究方法:语言学方法、功能方法、系统方法、文化方法、哲学方法、历史方法、机器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10]1-3。谢天振教授除了认为西方翻译研究存在文艺学派外,在《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中他还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语言学派翻译理论”、“阐释学派的翻译理论”、“功能学派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解构学派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和“苏东学派翻译理论”[11]1-2。马会娟、苗菊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中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分为“语言学派”、“功能学派”、“描写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哲学学派”、“认知学派”和“翻译研究的实证研究”七大流派[12]Ⅳ。刘军平在《西方翻译理论通史》中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的文艺学派”、“翻译的哲学学派”、“翻译的功能学派”、“多元系统及规范学派”、“翻译的目的论学派”、“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女性主义翻译观”、“后殖民翻译理论”等九大流派[13]Ⅶ。杨柳在《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中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翻译对等论”、“翻译目的论”、“多元系统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阐释学翻译理论”和“口译理论”等八大流派[14]Ⅶ。
然而,以上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在谈及西方翻译理论时,是应该包括笔译、口译和机器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还是应有所侧重,学者之间理解不同。大多数学者谈论的是笔译理论,少数学者兼顾口笔译理论,个别学者则从笔译、口译和机器翻译理论全面展开论述;其二,由于学者们对西方翻译流派研究在时间跨度上不同,如有的是全景研究、有的是断代研究,导致他们在流派划分涵盖的范围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如研究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就没涉及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即使有些研究当代翻译理论的,对一些新兴理论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没涉及,而且学者们在流派划分中由于目的不同,所采用的标准也是各异,如有的是按研究焦点、有的按研究方法、有的按研究层次、有的按有无学科意识等;其三,在对某一学派名称有共识的情况下,学者之间的认识的也不尽相同,如大家都认为存在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但对两者具体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以上原因,学者们在对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上出现了范围不同、标准不同、名称各异的现象,这给翻译研究者和学习者在带来启发的同时也徒添了困惑。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为方便学术对话与交流,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以翻译的研究层次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笔译翻译理论分为三大学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然后再根据三大流派研究内容的变化将其进一步地切分,希望能展现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
二、翻译研究的文艺学派
潘文国教授认为从古罗马的西赛罗到1959年罗曼·雅可布逊发表他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可以叫做传统的翻译学阶段[6],也即纽马克所称的“语言学前时期”[8]5-6,王宏印教授和奈达所称的“语文学阶段”[8]1-2。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西塞罗、贺拉斯(Horace)的“灵活翻译”、昆体良(Quintilianus)的“与原作搏斗、竞赛”、哲罗姆(St.Jerome)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所指”“能指”与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波伊提乌(Manlius Boethius)的“内容与风格”及“逐词翻译”、阿尔弗列德国王(King Alfred)的“明白易懂”、但丁(Dante)的“诗歌不可译”、阿雷蒂诺(Aretino)的“可译论”、路德(Martin Luther)的翻译七原则、多雷(Etienne Dolet)的翻译五原则、17世纪法国翻译界的“古今之争”、德莱顿(John Dryden)的翻译三分法(metaphrase,paraphrase,imitation)、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翻译三原则、赫尔德(Herder)的译者的任务是“解释”、歌德(Goethe)的翻译三分类(informative translation,adaption,interlinear translation)、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两种翻译途径和洪堡(Humboldt)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元语言观[15]17-32,还是20世纪的克罗齐(Croce)的翻译是艺术美的再创造、萨瓦里(Savory)的“翻译是一门艺术”、列维(Levy)的“翻译是一个选择过程”、庞德(Pound)的“创造性阐释”、卡什金和加切奇拉泽的“现实主义翻译”以及斯坦纳的“理解就是翻译”等翻译思想[8]11-55,除了奥古斯丁、荷尔德林、施莱尔马赫、洪堡少数几位之外,这其中的大多数翻译研究者只对如何翻译经典文献和文学作品感兴趣,立论则多出自自身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关注的焦点是“怎么译”,他们一直讨论的是“忠实”与“自由”、“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内容”还是“形式”这样一些与翻译行为直接有关的具体问题。由于他们在翻译中注重语义的结构、内容的选择和组织的方式,强调分析、权衡和比较修辞手法和价值,符合传统“语文学”的特征,我们把这种翻译思想称之为“语文学派”。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不满传统“语文学”对原作的“亦步亦趋”和缺乏创造性,主张从阐释学(Hermeneutics)的角度研究翻译。1813年施莱尔马赫从阐释学的角度论述了翻译与理解的密切关系,探讨了翻译的原则和途径,指出翻译有两个途径,要么让“译者不打扰原作者,带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使作者靠近读者”;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则从哲学和阐释学的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翻译即解释,解释即翻译”,“翻译”不只是字面的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译者应以本意在先,审视词语的源流,展现被遮蔽的思想,其关键是表达词语后难以真正把握的“道说”;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则在哲学阐释学中指出理解的普遍性、历史性和创造性对翻译理解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对“合法的偏见”、“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的精辟论述,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本质;乔治·斯坦纳则以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为基础,提出“理解就是翻译”的观点,而且他认为阐释翻译的步骤就是“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11]101-103。
这些不同的阐释视角对翻译研究都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我们没有像有些学者那样把它们单独列为“阐释学派”。我们认为虽然它们从阐释学的视角对翻译的理解进行了哲学思辨,从本质上来讲仍旧是关于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理解和阐释,所以仍旧属于文艺学翻译思想范畴,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刘军平教授的思想一致。
综上所述,无论是传统的“语文学派”,还是具有哲学思辨的“阐释学派”,讨论的翻译现象大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都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有着天赋文学才华的译者在翻译中要讲究译文的风格和文学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有人把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称之为“文艺学派”,我们也赞成此观点,这也是谭载喜教授所说的“从泰伦斯等古代戏剧家一直延伸到现代翻译理论家(如捷克的列维、前苏联的加切奇拉泽、英国的斯坦纳)的文艺翻译线”[16]9。
三、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
西方历来存在着两条翻译传统,除了文艺翻译理论路线之外,另一条线就是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潘文国教授称之为“现代的翻译学阶段”[6],王宏印称之为“结构主义阶段”[8]5-6,纽马克所称的“语言学时期”[8],奈达所称的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其实也都属于这一时期。1959年雅科布逊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翻译的重要性以及翻译中存在的一般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理论方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还首次把翻译分为三种类型,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这一分类准确概括了翻译的本质,在译学界影响深远。尤金·奈达则是语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他在语言学的基础上,把信息论应用于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即交际,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翻译原则,并进而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翻译原则,对西方当代翻译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奈达的理论过于注重内容而忽视了形式,英国学者皮特·纽马克针对他的不足提出了“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和“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两种方法,前者致力于重新组织译文的语言结构,使译文语句明白流畅,符合译文规范,突出信息产生的效果;后者则强调译文要接近原文的形式。此外,另一位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特(J.C.Catford)运用韩礼德的理论对翻译的不同层次进行了描写研究,提出了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并指出“对等”是翻译研究和实践的中心问题,这些观点在译学界也影响很大[11]1-3。从以上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从源语转换为目的语过程中的变化规律,而“对等”是他们理论共同点和契合点。虽然此时的翻译研究有了朦胧的学科意识,进入了“科学”的理论层面,但过分强调“对等”,使翻译沦为语言学的附庸,而不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也令越来越多的译者感到不满。
针对翻译研究中“对等”理论的薄弱环节,德国的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贾斯塔·霍茨-曼塔里(Justa Holz-Manttari)、克里斯丁娜·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开始借鉴交际理论、行动理论、信息论、语篇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思想,将研究的视线从源语文本转向目标文本,成为在国际译界很有影响力的流派。1971年莱斯在她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在概念性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方面与原文对等,并把这样的翻译称之为综合性交际翻译(integral 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然而在实践中,她又意识到等值并非如人们所期望的,因此更应该优先考虑原文与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莱斯的学生弗米尔则试图弥合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断层,他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和有结果的行为,这一行为必须通过协商来完成;翻译必须遵循一系列法则,其中目的法则居于首位,即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
此外,翻译还应该遵循“语内连贯法则”(intratextual coherence rule)和“语际连贯法则”(intertextual coherence rule),前者指译文内部的连贯性,后者指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连贯性,有时也被称做“忠实法则”(fidelity rule)。这些法则呈等级排列,这样原文中心的地位就被瓦解,将翻译研究从原文中心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对等”不再是评判翻译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译本实现预期目标的充分性(adequacy)。在目的论的基础上,执教于芬兰的德国学者曼塔里借鉴了交际和行动理论,提出了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这一理论将翻译视作受目的驱使的、以翻译结果为导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翻译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它不仅包括文本、图片、声音、肢体、语言等复合信息的传递(message-transmitter compounds)和不同文化之间的迁移,还包括改编、编译、编辑和资料查询这些行为,大大拓宽了人们对翻译的理解。诺德则首次用英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功能学派的各种学术思想,并针对功能理论中偏激的倾向给译者提出了“功能加忠诚”(Functionality plus Loyalty)的指导原则,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对译入语文化接受者起作用的目的”,而忠诚属道德范畴,关注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译者应当把翻译交际行为所有的参与方的意图和期望都加以考虑”[11]135-138。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语转向推翻了原文的权威地位,使译者摆脱了“对等论”的羁绊,在翻译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很多学者将“功能派”作为一个独立的翻译流派加以论述,这有其合理成分,但我们认为“功能派”虽然和“对等派”有所不同,但它从根源上讲还是属于语言学中的莱比锡学派,本质上运用的还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故我们如李文革教授一样从宏观的角度把它归于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一个次类别。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翻译过程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他们综合利用现代认知科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知识来研究译者大脑在翻译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试图揭示翻译研究中“黑箱”的奥秘。例如沃夫冈·罗斯切(wolfgang Lorscher)提出“有声思维法”(Think-aloud protocols,TAPs),译者采用边想边说边解析的翻译教学模式来记录翻译过程;特肯伦·康迪特(Tirkkonen-Condit)提出“即时回顾法”(Immediate Retrospections,IRs),即译者在完成翻译任务之后即时报告翻译过程的研究方法。
虽然这些研究有口语方面和研究者干预的缺陷,但是它们帮助我们对于翻译过程中心理和语言机制有了更好的了解[12]336。格特(Ernst-August Gutt)则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关联理论者认为话语都有一个“心理语境”(psychological context),也就是某种“认知语境”(cognitive environment),贮存人的知识、价值、信念等等,翻译加工的过程就是受话者将原文话语或文本投入本人的“认知环境”,使之产生足够的“心理上下文效应”(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9]282。翻译过程中对思维过程的重视也反映了翻译研究视角的转移,从对翻译结果的描述上转移到对翻译过程的观察与解释上,这一变化为认知技巧和翻译研究教学法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303。有些学者如刘宓庆、马会娟等把这部分翻译理论单独列出分别称之为“心理-认知心理学派”与“认知学派”,但是我们认为虽然这部分学者运用了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心理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因此我们把这部分翻译思想仍旧归属于翻译研究语言学范畴。
总之,无论翻译研究的“对等”、“功能”还是“认知”都是对翻译研究文艺学派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理论的反拨,它们运用语言学中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认知理论等现代语言学知识使翻译研究深入到对翻译过程、功能、认知的深层探究,通过微观的分析来考察语言之间的转换,较为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翻译研究中的种种问题。这些研究不但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和语篇的层面,也关注到翻译研究的功能和认知,使翻译研究进入了理论的层面。由于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所以我们统称这一时期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这一时期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第一次质的突破和飞跃。
四、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
从1972年霍尔姆斯发表里程碑性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开始至今,可以叫做当代的翻译学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描述性的范式从文化层面来进行翻译研究,如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翻译研究综合法等,我们把这部分翻译思想称之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这些翻译理论竭力想打破文学翻译研究中的禁锢,试图以有别于大多数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的方法,探索在综合理论(comprehensive theory)和不断发展的对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这些理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文学翻译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诠释。
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他不但提出采用“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还对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作出了详细的描述与展望。他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Pure Translation Studies)和应用翻译研究(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理论研究(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翻译辅助手段(Translation Aids)和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三大研究领域,这一翻译研究理论框架的提出,为“翻译研究派”的创立树立了丰碑。
以下的各种理论都是以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路线图”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的研究范式从文化层面将翻译文学作为译语文化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所以我们把它们称之为“翻译研究派”。在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路线图”基础上,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提出了他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着重探讨了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1976年他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论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一文中更是具体分析了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关系,并提出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体系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的三种条件: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形,即文学的发展尚属“幼嫩”,也就是处于正在建立的阶段;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的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literary vaccum)的阶段,这一思想在学界影响深远。另一位学者图里(Gideon Toury)以佐哈的多元系统为主要理论框架,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试图发现翻译选择中的文化制约规范(norms),通过在翻译研究中引入文化历史因素,他提出了以目的语为中心,来衡量和评价译文的功能和效果,为此他在《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和《描写翻译学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等著作中系统地阐释了翻译的规范理论,这里图里实际上是进一步强调了描写翻译研究的基本立场,从而与此前以过程为基础、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形成了本质区别。进入20世纪80年代,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或各自著书撰文,或携手合作,为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勒菲弗尔针对以色列学者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提出“折射”(reflection)与“改写”(rewriting)理论,认为文学翻译与文学批评一样,是对原作的一种“折射”,翻译总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他更是强调了“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三因素对翻译行为的操纵(manipulation)。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以及他的三因素论成为文化转向后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11]2-5。巴斯奈特也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坚定倡导者,她在20世纪90年代与勒菲弗尔合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和合著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等书中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趋势,提出应该考虑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的确,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全面文化转向,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强调消解传统的翻译忠实观,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强调“存异”而非求同,集中表现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批判、意义的差异与延缓(differance)、意义的撒播和中心的分解。这些研究者们认为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撒播(dissemination)、印迹(trace)、错位(dislocating)、偏离(decentring),原作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作的生命不断得到再生,因此其中一些学者主张在翻译中应更多地采用抵抗式的异化翻译策略,从而使更多的异域文化成分得以进入目的语文化。
还有一些学者借助解构的研究途径探讨翻译中的性别问题和政治权力问题,在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11]315-318。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或菲勒斯中心(phallogocentrism)的社会中,语言是意义斗争的场所。所谓的“Les belles infidels”,即“翻译像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不仅包含了对女性性别的歧视,而且也包含着对译作的歧视[15]43,因此她们提倡采用“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和“劫持”(highjacking)等翻译策略,对文本进行“妇占”(womanhandling),以消除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解构原文,赋予译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11]5。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则认为,文化与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异质性,使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成为空想。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其文化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因此,在权力差异原则的指导下,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的不是翻译对等或等值问题,而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的语文化的颠覆作用,通过探讨译本与历史间的关系,对译本中的变形之处进行福柯式的知识考古或葛兰西式的文化霸权分析,揭示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系[17]。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主要还致力于对不同历史语境下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的研究,其目的是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提倡文化多元,努力把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从“对抗”发展为“对话”。从以上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这些翻译思想发展脉络来看,正如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所指出的,“文化转向”中最核心的概念是权力,它涉及文化变迁、文化差异、文化他者、不同世界观、文化宰制与抵抗,甚至可以说翻译中的“文化转向”就是一种“权力转向”(power turn)[13]559。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翻译研究者试图在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其代表人物就是玛丽·斯奈而-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1988年在《翻译学的综合研究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中,霍恩比认为“语言学派”和“操纵学派”互相排斥,都对自身领域以外的翻译视而不见,而她想做的就是弥补两者的缺陷,因而主张新兴的翻译学科应该是个“综合性”的学科[18]13-25。她的基本主张是,填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之间空隙,将文化作为翻译的背景;文本分析要从宏观的语篇开始到微观的词语,而每个词语又不孤立地去看,要联系它在整篇文章中的地位和功能;翻译不是个静态而是个动态的过程,是译者作为读者把对原文的理解在另一种文化中完整地创造出来,因而文学作品不断需要重译,完美的翻译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翻译就必须是个综合性的跨文化学科,除了语言学和文学之外,作为面向文化的学科,它还必须吸收心理学、人种学和哲学的内容,而又不属于这些学科中的任一种,是个独立的学科[18]1-3。
另一位主张综合观点的学者是玛丽·斯奈而-霍恩比的同胞威尔斯(Wills)。威尔斯原来是语言学派在德国的代表,后来他成了“翻译研究派”的准盟友,1999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证翻译学的综合性,强调综合性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及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的区别,并主张翻译学的综合性体现在它是一个六边形的中心,而环绕它的六条边分别是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脑科学、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8]235。由于“综合法”综合利用各种文化理论,与后来拓展了的“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观点实际上也无很大出入,因此香港学者将她归于文化学派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也赞成此做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以从宏观的角度以翻译的研究层次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分为三大流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文艺学派包括传统的语文学派和阐释学派,语言学派主要由对等派、功能派和认知派构成,而文化学派则涵盖了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综合法,而翻译研究派又可以切分为多元系统理论、规范理论和操纵理论。同时我们还应明确三点:其一,哲学学派不应单独作为一个学派和文化学派并列。首先,我们认为主要由阐释学派和解构学派构成的所谓哲学学派虽然都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但前者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关于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理解和阐释,因而在本质上讲仍旧属于文艺学翻译思想范畴,而后者打破结构的封闭性,消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观念,颠覆二元对立的西方哲学传统,从而也消解了传统翻译忠实关,突出译者中心地位,开启了翻译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研究,是文化转向中重要的理论基石,应该归属在文化学派中;其次,生硬地把二者归类在一起也缺少时间上的连续性,因为二者在发展时间上存在较大的断层;此外,从翻译的研究层次来讲,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从属于文化,而不是与文化形成并列关系。其二,对西方翻译流派的划分,并不是说这些流派的发展是对立的、毫无关联的,其实不同流派的理论,只是所寻求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研究的层面和领域不一样,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探讨的问题更是不乏相通之处,这里不存在一个流派颠覆另一个流派的问题,它们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到后来也不仅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转换层面,而进入到文化研究层面,如奈达,他从功能对等到动态对等,就已经涉及不同文化语境对翻译等值的影响;前面提到文化学派中的综合法也涉及很多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其三,西方翻译理论源远流长,流派众多,我们对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划分方法只是众多视角中的一个,也只是我们的肤浅理解,在此仅为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1]Nida E A.Approaches to Transla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J].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1984,(2):9-15.
[2]Gentzler 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3]Mundy 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6]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2002,(1)-(3).
[7]朱健平.对翻译研究流派的分类考察[J].外语教学,2004,(1):38-46.
[8]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10]李庆和,黄 皓,薄振杰.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70年代以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谢天振.当代外国翻译理论导读[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12]马会娟,苗 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4]杨 柳.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5]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7]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4-8.
[18]Snell-Hornby M.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88.
Research on School Classification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HU Xing-wen1,2, WU A-miao3, SHU Xue-jun1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2.Graduate School,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3.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PLA Academy of Army Officers,Hefei 230031,China)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confusing school names with varying scope by different standards in the present school classification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chools in a macro way by its research level,namely,the literary school,the linguistic school and the cultural school.The literary school includes the traditional philological approach and the hermernutic approach;the linguistic school consists of the equivalence approach,the functional approach and the cognitive approach;the cultural school covers translation studies approach,deconstruction approach,feminism approach,post-colonial approach and the integrated approach,of which translation studies approa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polysystem theory,the norm theory and the manipulation theory.By contributing new thoughts to this discussion,the study aims to reach more consensus among translation studies scholars in this aspect.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school classification;the literary school;the linguistic school;the cultural school
H059
A
1008-3634(2011)06-0142-08
2011-02-25
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0sk196);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专项课题(2011sk145);安徽理工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2008057);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项目(wyky2011-1)
胡兴文(1978-),男,河南光山人,安徽理工大学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 刘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