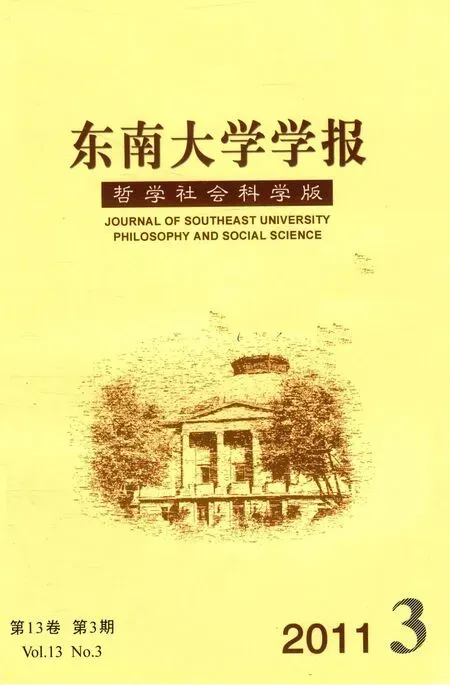文如其人与“修辞立其诚”
2011-04-04王希杰
王希杰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文如其人与“修辞立其诚”
王希杰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修辞立其诚”。周振甫批评《修辞学发凡》抛弃了这一原则。霍四通用有“文不如其人”现象主张修辞可以不“立其诚”。修辞要不要“立其诚”?这是一个问题,需要认真地思考。“修辞立其诚”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翻“修辞立其诚”的传统,需要非常地慎重。
文如其人;修辞立其诚;修辞学
一
周振甫批评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丢弃了诚信原则:
按中国的修辞,《易·乾卦·文言》:“修辞立其诚”。朱熹《周易本义》,“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其诚,则无以居之。”那末“修辞立其诚”,要求“无一言之不实”,这就跟命意谋篇有关,也跟篇章结构有关。《发凡》里讲消极修辞,注意:“一,意义明确;二,伦次通顺;三,词句平匀;四,安排稳秘。”没有注意到作者在修辞上要求“修辞立其诚”,即没有注意到作者根据他所要表达的情意来确立命意谋篇,假如作者违反他的情意,说了假话,即不符合“修辞立其诚”的要求,所以要讲究命意,要使命意真能表达作者的情义,这就是修辞要讲究谋篇的理由。《发凡》里不讲命意谋篇,只要求“意义明确”,那么说了假话,也可以说得命意明确的,就把“修辞立其诚”的要求抛弃了。在这点上,《发凡》似有所不足,《通诠》是有这方面的修辞的。[1]593
周振甫说的《发凡》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通诠》指王易的《修辞学通诠》。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有没有抛弃“修辞立其诚”的要求?第二,抛弃“修辞立其诚”对不对?能不能够批评?第三,修辞要不要“立其诚”?
霍四通博士在《民国修辞著作中的学术腐败和几本书的评价问题》中说:“周振甫于古典文学知识普及厥功甚伟,但从他所写的几本修辞学书来说,他于现代修辞学史上的几个体系确乎缺乏基本了解,于现代语言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上引论述就反映出他没有搞懂《通诠》《发凡》两书的体系,胡乱对应,张冠李戴。”[2]321周振甫是否懂得现代修辞学体系与现代语言学,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霍四通博士反驳说:
修辞学一定要“立其诚”吗?中国古人立论常常暗合“风格即人”的命题。如清代的薛雪就将诗歌的风格和诗人的个性对应起来:
鬯快人诗必潇洒,敦厚人诗必飘逸,疏爽人诗必流丽,寒涩人诗必枯瘠,丰腴人诗必华赡,拂郁人诗必凄怨,磊磊人诗必悲壮,豪迈人必不羁,清修人诗必峻结,谨敕人诗萎靡:此天之所赋,气之所秉,非学之所至也。(薛雪《一瓢诗话》一八一)
但实际情况远远非如此简单对应。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就谈了这个现象。周振甫一生服膺的钱钟书在《谈艺录》四八则“文如其人”详细征引了诸家论述,例如魏叔子《日录》卷二谓:文章“自魏晋迄于今,不与世运递降。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观人。”堪与遗山诗相发明。可见,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既明此,周何必要用这顶大帽子来批评《修辞学发凡》?[2]321
霍四通博士没有就第一个问题回击周振甫。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霍四通博士没有正面回答,所以就断定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就正如周振甫所批评的那样是抛弃了“修辞立其诚”。我以前只是说《修辞学发凡》忽视了“修辞立其诚”,因为陈望道自己并没有公开反对“修辞立其诚”。《发凡》第一句就是“修辞立其诚”,但是立足点在“辞”字,没有顾及“修辞立其诚”的“诚”字。
霍四通博士认为,抛弃“立其诚”没有错儿,周振甫的批评是错的。霍四通博士明确提出:“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这是霍四通博士的观点,不能代表陈望道的。
“修辞要不要‘立其诚’?”这可是一个重大问题,值得也需要认真研究,不是哪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我们不赞同霍四通博士的这个论点。我们来讨论一下霍四通博士的这段论述,抛砖引玉。
二
霍四通博士所用的薛雪《一瓢诗话》一八一中的这段话,其实这并不是薛雪的创新之见。这话是有所本的。《周易》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燥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系辞下》)周振甫《周易译注》中翻译为:“将要背叛的他的话有内愧,中心怀疑的他的话枝蔓,善良的人话少,急躁的人话多,污蔑善人的人他的话游移不定,失掉操守的人他的话屈服。”[3]273郑奠、谭全基编辑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首选的是《周易》,其中就有这一条。《毛诗序》中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3]68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看法。薛雪的这段话可以说就是对《周易》和《毛诗序》的继承与扩展。其实,中国老百姓也相信“修辞立其诚”的。“什么人说什么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等就是这个意思。民间谚语中也有这种观念的影子。
霍四通博士引用元好问(公元1190—1257年)的诗来反驳这种观念。霍四通博士用来论证修辞学可以不立其诚的是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是这样注释三四两句的:“高情二句——《晋书 ·潘岳传》:‘字安仁,……岳性清燥,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既仕官不达,乃作《闲居赋》。’都穆《南濠诗话》:‘扬子云曰:言,心声也;字,心画也。盖谓观言与书,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似不足以观人者。……元遗山之论固如此。’”[4]453元好问举潘岳为例,感叹不能仅仅依凭人的言语文章或者书法绘画来评定其人品人格。其实,生活中“言不及义、言不由衷、言过其实、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是有的,“口如蜜,腹如剑。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口里甜甜,心里锯锯镰。口边甜如蜜,心内毒如蛇。口似莲花心似刀”的人也是有的。甚至是多多的,这是一个常识。对此一无所知甚至全然否定者,很难生活下去的。但是,这未必就能够否定“文如其人”,更不能作为修辞不需要立其诚的论据。元好问这首绝句对此社会现象感慨叹息,提出根据话语和书法来判断一个人,不容易,很难准确,问题很复杂。元好问反对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简单化做法,是行不通的。但是,并未完全否定文如其人说,更没有因此主张写诗不需要立其诚的意思。
郭绍虞等编者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后面的说明中说:
第五,主张真诚,反对伪饰:
元氏从诗歌艺术角度,分析其正伪清浊以外,特别重视作诗的根本关键。他感慨“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伪饰。而对陶诗的肯定,恰正是因为它“真淳”。正面主张“心声只要传心了”,出于真诚才是好诗。元氏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说:“何谓本?诚是本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心口别为二物。”正是这诗的最好注脚。[4]462
这就是说,元好问看到了有文与人的脱节、分离现象的,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文如其人。事实是元好问所否定的正是这种人与文的脱节、分离的现象。元好问更没有因为这种脱节、分离现象而反对诚信原则。正好相反,针对这种脱节、分离现象元好问主张“由心而诚,由诚而言,心口别为二物”。
我们不得不很遗憾地说:霍四通博士用来证明他的论点的论据其实同他的论点恰恰相反。
三
霍四通博士引用魏叔子的言论来为其修辞不立其诚论辩护:
例如魏叔子《日录》卷二谓:文章“自魏晋迄于今,不与世运递降。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虽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观人。”堪与遗山诗相发明。可见,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
魏叔子所说的“日夕揣摩,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语”当然是一种超常行为,而且是负超常。在我们看来,元好问也好,魏叔子也好,他们看到了跟文如其人相反的现象,但是绝没有肯定这种现象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把文如其人当作常规,文与人的脱节与分离现象是一种超常行为。或者说,文如其人是零度现象,文与人的脱节与分离是一种负偏离现象。
关键是,面对这一种负超常现象,魏叔子因此就主张作文就不要立其诚么?未必。我们在中国文论史权威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里看到:
孔子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于《易》曰:“修辞立其诚。”立诚可为质,修之质而后言可甘文。圣人之于文,盖惓惓矣。(魏禧《甘健斋轴园稿序》)
文章之道,必先立本,本丰则末茂。……文章之本,必先正性情,治行谊,使吾之身不背于忠孝信义,则发之言者,必笃实而可传。[5]311-312
郭绍虞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代宗师,霍四通博士应当是熟悉郭绍虞的观点的。因为中国古代修辞学是附属于文论的,跟文论是密切相关联的,研究中国传统修辞学必须结合中国古代文论。
霍四通博士说魏禧魏叔子的言论,“堪与遗山诗相发明。可见,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在我们看来魏叔子是“堪与遗山诗相发明”的。但是却并不因此“可见,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事实是元好问和魏叔子都是主张并坚持立其诚的。
霍四通博士说:“周振甫一生服膺的钱钟书在《谈艺录》四八则‘文如其人’详细征引了诸家论述,……可见,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既明此,周何必要用这顶大帽子来批评《修辞学发凡》?”因为周振甫一生服膺钱钟书,所以霍四通博士拿钱钟书来反驳周振甫。一则,周振甫没有弄懂钱钟书,二来,钱钟书当然比周振甫更权威,钱钟书当然不会错,那错的就是周振甫了。因此周振甫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批评就是错了的。
钱钟书批评说:“故遗山、冰叔之论,只道着一半。”[6]164钱钟书对所谓的言行不符现象,深入地分析说:“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时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唯言哉,性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伪乎。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随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身心言动,可为表里两层,如胡桃泥笋,去壳乃能得肉。”[6]163—164钱钟书看到了文如其人现象的复杂性。他的分析深入而细腻,非常精彩,是前人所没有说过的,即使是现在也并非人人都已经把握了精髓的。重要的是,钱钟书并没有否定文如其人,而是在肯定文如其人。霍四通博士用钱钟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恐怕是很难成功的。因为钱钟书的观点同霍四通博士的看法是刚好相反的。
事实上,中国古代提倡“文如其人”者并没有把文与人完全等同起来。如果文章同人(作者)完全等同,那么提倡“做人需老实,为文要放荡”是什么意思嘛?钱钟书阐述说:“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之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6]163钱钟书在这里明确区分出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思想内容;一个是语言表达及其特征,(言语表达的区别性的)特征的总和就是言语风格(格调)。钱钟书非常高明地指出:文如其人指的是语言表达的特征,而不是话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话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可以伪装,但是用来表达思想内容的表达形式是很难伪装的,千方百计进行伪装的人往往会露出马脚来的。在我看来,钱钟书明确地区别开“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同“文如其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是非常高明的。拿钱钟书来教训周振甫的霍四通博士似乎忽视了钱钟书的这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这里,钱钟书明明是肯定文如其人的,也并没有反对立其诚。霍四通博士用钱钟书来反驳周振甫,我看是很难说服周振甫的。一生服膺钱钟书的周振甫不但没有歪曲曲解钱钟书,更没有对抗钱钟书。事实是,钱钟书和钱钟书所引诸家的言论都不能用来证明修辞不要立其诚。“文如其人”绝不是说文就等于人。主张为人需老实而为文可以放荡的古人显然是看到为人与为文的区别的,并没有混为一谈。
四
修辞要不要立其诚?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修辞立其诚”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翻“修辞立其诚”的传统,需要非常地慎重。
霍四通博士这段话很难说服人。是不能推翻“修辞立其诚”的原则的。弃绝了“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学是什么样子的呢?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余吾金在《警惕文化生活中的“修辞学转向”》(《文汇报》2002年12月19日)中说:“在当今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那就是自我包装、自我夸耀和自我炒作的倾向。借用‘修辞学转向’来指称这种倾向,其含义是:没有事实,只要修辞。”[7]505“当一个人、一个单位或团体在大众传媒或其他场合陈述自己的情况时,人们经常看到或听到的是这样的词语,如‘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等。听起来华丽动人,读起来,琅琅上口,但它不过是一场‘修辞上的“革命”而已’。”[7]505“‘修辞学转向’的要害是用大话、空话和套话来取代实际行动,用修辞学上的手法来取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但降低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使虚假、浮夸的风气到处蔓延,从而加剧文化的泡沫化。”[7]505余吾金教授所反对的修辞学,绝不是“修辞学立其诚”的修辞学,他所批评抨击的东西同“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学毫无共同之点。余吾金教授所攻击的乃是弃绝了“修辞立其诚”的那种修辞学!这是值得主张修辞不要“立其诚”的学者深思的。这种“不立其诚”修辞学的社会——也许还包括其危害!——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修辞学家对这种抛弃了“立其诚”的原则之后的修辞学的负面结果要不要负一定责任?
在我们看来,正因为存在这言行不符的现象,就更应当提出“修辞立其诚”。2010年4月20日南京的《现代快报》封21版上的通栏大字标题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爱说真话?》!在今天,伪劣假冒言行比较盛行的时候,我们尤其应当坚持“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因为归根到底,修辞活动是一种社会心理文化行为。修辞学有其应用学科的特色,应当服务于社会。如果因为存在着言行不符的现象就主张修辞不需要立其诚,那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利于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与进步,不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台湾修辞学家徐芹庭在《修辞学发微》中说:“语言学家巴利(Charbs Bally)尝言:‘吾等说话即战斗,因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多不能完全吻合,此人所重,旁人未必轻之。故两人接触时,即不能不开始语辞之战斗,运用语辞之战术,或辛辣,或委婉,或激动,或和平,或谦恭愁诉,甚至有伪善之气息。如此,方能攻倒对方,传达自己之意志,引起对方之行动,而说话之目的,方能如愿达到。’”(见巴利所著《语言活动与生活》)[8]14-15巴利这番话不能代表整个西方修辞学。并不是所有西方人、西方学者都把言谈当作为一场战斗的。巴利这里所说的战斗,乃比喻也,并非敌我矛盾,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即使排除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依然不赞同巴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和合为核心。言谈是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安定的手段。言谈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言谈即战斗的修辞观念指导之下的交际活动,交际双方都太累,太苦了。在和合修辞观念指导下的交际活动,宽松轻松,欢欢喜喜,快快活活,得人缘,朋友遍天下,健康长寿。李鸿章回答曾国藩如何同洋人打交道这个问题的时候,用他家乡的土话,其意思是耍滑头,曾国藩很不高兴,李鸿章虚心请教,曾国藩的答案是一个“诚”字。这就是说,甚至是对敌斗争,也还需要诚信的。
周恩来总理可以作为“修辞立其诚”的典范。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官员谈判,面对的是敌对人士,在针锋相对的对敌斗争中,依然坚持“修辞立其诚”,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赞扬。我们可以编辑周恩来言谈实录,研究周恩来的修辞实践,总结周恩来“修辞立其诚”的宝贵经验。这是周恩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里的重要财富。
五
“修辞立其诚”这话绝不是对骗子说的,其对象是君子。孔子的修辞学是贵族的修辞学,不是奴隶的修辞学。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西塞罗的修辞学,都是奴隶主的修辞学,贵族的修辞学。因为是贵族的修辞学,所以首先需要确定修辞人的资格。非贵族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甚至,连贵族也并不全部是修辞学的服务对象。只有“可与言”者才是修辞学的对象。“不可与言者”必须排除在外!
智者乃贵族之中的精英人物。智者不失人,积极跟贵族中的精英交流。智者不可失言,不能跟非贵族,不跟贵族之中不可与言者,去罗嗦什么的!既然连言谈都免了,那就根本没有这部分的修辞与修辞学了。所以,孔子的修辞学乃贵族中的精英的修辞学。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也是如此的,研究对象是贵族的精英的言谈,其服务对象乃贵族。中国古代,古希腊罗马,谈论修辞学,首先确定对象与范围,或者说是明确“修辞人”的资格。
需要认真思索的是,难道能够因为世上有人不讲道理我们就提倡反对讲道理吗?当然不能。而且正因为有人不讲道理,我们就更加要强调讲道理。同理,我们不能因为有文不如其人的现象的存在,因为有人说谎骗人,就因此而反对诚信原则,就主张修辞不需要立其诚。不,绝不能这样的。
正好相反。人们之所以要提出、要坚持诚信原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上,生活中,有不诚信,还有虚伪,有言不由衷,有文不如其人,有言是而行非,有谣言谎言等现象的存在!如果没有非诚信现象之存在,如果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回回都非常诚信,心口如一,不诚信者半个也没有,那还有什么必要提倡诚信原则呢?凭空倡导这个诚信原则做什么?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事实上,之所以提出“理解万岁!”的口号,就因为理解难,真正的理解尤其难,很少很难几乎没有。没有不理解的现象,何必提倡“理解万岁!”的口号?难道因为社会上存在着相互不能理解的现象就应当反对或者批判“理解万岁!”的口号吗?就可以因此提倡“不理解万岁”?
我们必须看到,所有的欺骗行为,在欺骗者那边,都必须打着诚信的幌子。我在一个雨天,亲耳听到一个撑着雨伞的教师对对方说:“主任,我这话绝对不是恭维你,我这个人是从来不恭维人的人!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世界上所有的骗子都千方百计地强调自己绝不是骗子,而是谦谦君子,一片真诚。而且想方设法让对方相信自己是遵守诚信原则的,绝无半点虚假!只有这样,骗子才能得逞。也只有在对方相信骗子不是骗子的情况下,骗子的欺骗活动才能得逞。因此,在我们看来,骗子的存在,不但不能推翻诚信原则,反而从反面证实诚信原则乃人类生存之道。
这个道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逐步深信不疑。2009年,复旦大学霍四通博士公开明确地提倡修辞不需要立其诚,我们很震惊。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值得大家深思。我这里,抛砖引玉而已。这绝非客套话,因为如此之重大问题,绝非任何个人能够完全彻底解决的。
[1] 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 霍四通.民国修辞著作中的学术腐败和几本书的评价问题[M]//复旦大学.语言研究集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3]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8] 徐芹庭.修辞学发微[M].台北:台湾“行政院新闻局”, 1984.
H15
A
1671-511X(2011)03-0092-05
2010-12-25
王希杰(1940—),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汉语修辞学,语法学,词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