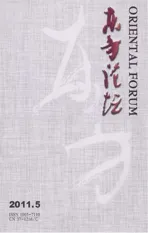理解“制作历史”
——《他者的历史》解读
2011-04-02徐晶
徐 晶
(上海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上海 200444)
理解“制作历史”
——《他者的历史》解读
徐 晶
(上海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上海 200444)
《他者的历史》一书所提出的“制作历史”概念,代表了20世纪末人类学致力于“历史化”尝试的进程。人类学在经历了封闭的、静止的社会分析后,开始逐步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动态的文化研究实践。因此,在人类学者走入田野或社区时,必须审查“过往的历史”,对不同社会记忆过去和思考历史的模式加以辨析和反思。
他者的历史;历史人类学;制作历史;写历史
《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是一本会议论文集,源自科英布拉(Coimbra)举行的一场以“历史的制作”(the making of history)为议题的人类学研讨会。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沿袭了人类学的一贯传统,通过关注欧洲“边缘”社会的文化及其历史,显示出20世纪90年代欧洲人类学者致力将学科历史化的尝试。几位作者通过发挥人类学个案研究的特长,从底层与微观的角度透视了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并且对欧洲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模式进行了批判。本书特别注意历史学之于人类学的作用和意义,文化和历史两种视角在书中的相互考量、相互碰撞,带给读者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是笔者阅读《他者的历史》后,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对“制作历史”加以辨别和分析的初步尝试。
一、本书内容简介
一般来说,传统西方史学认为存在着一种综合的、持续的和线性的社会变迁模型,它假设欧洲的历史经验是最具有典型性的,各个社会的历史进程终将沿着这一模型发展。《他者的历史》一书的编者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在导论中提出:“历史的一致感不仅毋宁是一种哲学推论而非社会实情,而且是高度知识化的产物,欧洲和别处一样拥有众多的历史(克斯汀・海斯翠普,2010,p2)。”在海斯翠普看来,社会人类学应当追寻各式各样的不同于“西方主流意识”的历史故事,而这本论文集的其他作者也出于同样的宗旨,通过人类学研究方法呈现出各个“他者”社会“制作历史”、“思考过去”的模型。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深入体会到发生在欧洲的一些非常另类的历史,它们有别于那种直线的、进步的、扩张的欧洲官方历史版本。
戴维斯在其文章《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中,以也门部落人民与利比亚乌达克村民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想象为例,说明历史学家所擅长的线性的、有情节的“历史”并不是了解过去的唯一方法,因为“思考过去”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除正统“历史”以外,各个社会其实都善于运用“自传”、“先例”和“神话”等另类的记忆方式来解释过去。对于人类学者而言,历史制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历史编撰,而是探索人们如何“思考过去”(以及建构过去)的特殊模式。
托马斯・豪斯查德(Thomas Hauschild)的《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中,描写了一些据信是古老的习俗就在作者眼前任由信徒活生生地窜写、改装和修饰;而当教会试图对某些宗教“传统”进行现代化改革时,信徒们却呈现出保守的一面,以维护信仰为由横加抗拒。作者认为这些信徒的两面性说明,很多表面看似以古典的传统、符号和仪式,事实上与真实的历史毫无关联,而是在后来被“发明”出来的,其原因是由于不同的人群都会企图对集体记忆(特别是宗教的集体记忆)这个象征性财富加以控制和争夺,以期接近话语权的至高点。
若敖・德・裴纳-卡布若(João de Pina-Cabral)的《欧洲文化中的异教遗存问题——异教徒的神祗是魔鬼》描述了葡萄牙北部的基督教社会中,象征古旧和迷信的民间信仰或异教神祗,总是呈现出惊人的弹性和复原力,它从未被彻底消灭,直至今日还在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作者认为西方宗教正史所宣称的理性的、救世的信仰进化史并不是宗教历史的全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有某种重复再现和跨域相似的异教徒实践,正统和异端两股力量之间对于宗教信仰的持续角逐才是历史的常态。
麦可・赫兹飞(Michael Herzfeld)的《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分支与政治》讲述了克里特岛的历史被“制作”的模型:当代的很多不同政治“分支”(segmentation)①根据赫兹飞的解释,“分支”长期以来只被认为是无邦国社会的特征,然而在他所调查的希腊克里特岛社会中,并存着父系分支亲属群(agnatic, segmentary kinship groups)和双边亲属群(bilateral terminology),也并存有同样强烈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因此邦国结构和世系分支是可以并存的。,无论彼此之间竞争如何激烈,却都会对圣徒的传说和祖先的事迹表现出谦卑和信心,这代表了他们愿意承认与敌对派系曾在历史上共享一个超然的团结点。这种对历史忠诚的策略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中依然是首要原则。赫兹飞在文章最后点出了这种政治过程背后的逻辑:追求“再现团结”的历史隐喻其实包藏了现实生活中的分裂事实,事实上不同的派系正是出于对未来利益的算计考量,才会选择追溯过往的历史谱系并去追求那个超然的历史原点。
安・克努森(Anne Kundsen)的文章《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描绘了18、19世纪科西嘉历史自相矛盾的二元性:在当时的科西嘉社会中,一方面拥有欧洲宪政式的“进步”民主文化,另一面人们则又选举出享有绝对权利的专制君主。克努森认为在18、19世纪的科西嘉,一方面是民主文化背后的“司法正义”原则,另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背后的“权力垄断”原则,两者之间界限很不明晰,由此产生了社会结构不断地整合与再整合的从未间断的轮回。这导致科西嘉的历史不断摇摆于民主的“传统稳定性”和专制的“现代扩张性”这两个极端的不同历史空间里,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平衡状态。
最后,在《乌有时代与冰岛的两部历史(1400-1800)》中,克斯汀・海斯翠普介绍了冰岛人“生产历史”、“思考历史”的模型。在冰岛人的经验中,并不存在一种进步、直线或成长的历史,他们生活的世界只有两个:一个是正在亲身经验的历史,它是式微和退化的;另一个是想象的“乌有”时代,意味着永恒和古老。作者认为,前者意指历史思维中的变化感,是冰岛人正在经历的某种社会的具体表现;而后者象征着历史思维中的结构感,是冰岛人处理当下思维和行动的原点。
二、历史人类学与“制作历史”
《他者的历史》代表了20世纪末人类学学科致力于“历史化”探索尝试的进程。人类学在经历了封闭的、静止的社会分析后,开始逐步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动态的文化研究实践。仅仅依靠变迁论或结构功能论等封闭性、共时性的解释框架,无法对不同文化区域的差异做到全面而透彻的理解。随着对历史学的日益了解,人类学者在走入田野或社区时、在以各式理论探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因素之前,首先都会注意加强区域内外体系的共时性(synchronic)联结;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想要了解当下社会的文化结构和事件行动,还必须审查“过往的历史”,即必须结合历时性(diachronic)的研究。人类学对不同社会记忆过去和思考历史的模式也因此有了越来越高的敏感度和关注度。
人类学者开始体会到,“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是相互容受的,正如《他者的历史》编者海斯翠普在导论中提出的:“……‘他者’(otherness)的范围也包括数目庞大的个别历史(separate histories)。”(海斯翠普,2010,p1)这种对于文化的历史背景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899年法国史学家梅特兰(Maitland)的大胆预测:“人类学要么是历史学的,要么什么都不是”[2](P53)。然而,在一百多年的学科发展史中,历史一直被公认为是人类学的一根软肋。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历史人类学”才真正成为人类学界所普遍关注的话题。“历史人类学”基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流和创新而诞生,主旨思想之一就是运用历史阐释文化、运用文化呈现历史。如果我们试图解释某社群是如何会演变成当时当地的面貌,就势必要去了解这群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过去的;而相应的,一个社群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结构,则往往需要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加以表征。
《他者的历史》作为一本历史人类学文集,运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历史资料,将历史融入对社会活动的分析与解释中。为此,本书倡导了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制作历史”(making history)。虽然“制作历史”这一概念并非是《他者的历史》一书首创——事实上早在1851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已使用此概念①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原文是:“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2010,p1-2)。英文原文为:Man makes his own history, but he does not make it out of the whole cloth; he does not make it out of conditions chosen by himself, but out of such as he finds close at hand.[3](P1-2)——但是本书的贡献就是首次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历史人类学”的实践中。关于“制作历史”的具体概念,或许是考虑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原因,又或许是考虑到人类学对概念解释的开放传统,书中并未见到几位作者给出“制作历史”的明确定义。但是从书中各作者的行文之中,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制作历史”的多样而丰富的内涵:如海斯翠普认为,“各个世界有其本身制作历史的模式,以及其本身思考历史的方法,两者是密切交织的……”(海斯翠普,2010,p9);戴维斯指出:“人类学家应该密切注意历史制作(或历史制造者之间)的社会关系”(p16,p29);豪斯查德强调“不可以把学者的论述同实际的社会历史情形混为一谈”(p34);赫兹飞认为,“人类学把历史当作一个可谈判、转让的实体……历史是一条客观的河流,民族学家则可以用各种有创意的方法从中啜饮……历史书写也参与了同样的事实决定过程”(p75,p89)等。几位人类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思路出发,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社群进行“历史制作”的实践过程,同时贡献出他们对于“制作历史”的具体感受和深入理解。
三、历史由谁制作?
“制作历史”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它采取的动宾语式,省略了“制作历史”的主体,未能指明究竟是由人类学研究者来“制作他者的历史”,还是让人类学者去探究“他者如何制作历史”——抑或两个过程皆有。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上面这个疑问时常困扰笔者。如果说“历史制作”试图要揭示的是主流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那么“制作历史”的主体又是谁?安唐・布洛克(Anton Blok)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也对“制作历史”这一概念的主体进行了反思:
“……就算它(过去)只是一种建构(或重构或解构),我们也必须指出它是谁的建构,并且要描绘出其中的权利安排……”(海斯翠普,2010,p134-135)。
对于“制作历史”这个概念,海斯翠普本人或许要强调的是上文所述的第二个过程,即“研究他者如何制作历史”。根据她的理解,历史人类学任务之一就是去研究“当地社会”是如何制作历史、记忆过去的,在海斯翠普这里,制作历史的主体显然与“他者”或“当地社会”有关,而人类学者则应当尽量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
“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生产‘历史’的模式会随着脉络的不同而不同。除了环境、经济和社会组织上的明显差异以外,历史的制作也有一部分取决于当地对于历史的思考方式。”(海斯翠普,2010,p114)
这个“当地社会”强调了人类学一贯秉持的“他者”视野,因而我们可以认为“他者”是海斯翠普所理解的“制作历史”的主要人物。在冰岛历史的研究中,海斯翠普把古冰岛人作为“他者”,视为“制作历史”的主体,而她本人则与这段历史保持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全文也是尽量以客观的语气加以评论。另外,论文集中其他几位作者也都基本采用了类似旁观者的立场。
但是,与海斯翠普的“旁观者”立场不同,第二章的作者托马斯・豪斯查德却是个另类。特别是其文章的标题《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更是带给读者这样一种感受——似乎豪斯查德本人,而不是当地民众,才是历史制作的重要人物。
“我现在已经成为传统的专家和维护者……在被正式宣布为‘专家’之后,我不仅成为敌对两方争夺集体历史的目标,也成为我每一个报导人的私人见证者……于是,田野工作者变成证人和使徒,而意大利南部的农夫则变成语言的理论家。”(海斯翠普,2010,P40,p44)
按照豪斯查德的讲述,一位田野工作者俨然成为了历史制作的主要参与者。当地人极度地看重豪斯查德作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身份,每当当地的人们对历史事实有所争议时,就会请教他的评价和观点,豪斯查德的看法甚至对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和叙述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篇论文的叙事风格和《小泥屋笔记》的幽默戏谑堪称一致[4]。豪斯查德发现,研究者的主体性身份在田野中无处不在。他在意大利南部的经历,事实上是遭遇了教士、信徒,以及作者本身所“制造”的不同历史记忆。这倒正好符合了人类学曾讨论过的田野工作的操作性、合作性问题[5](P25)。如果后现代人类学认为,田野工作中,报导人和人类学家都有参与“制造事实”的潜在可能。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论,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人类学中当然也能成为“制作历史”的主体。
无论我们如何尝试在词义上清晰地分辨,关于制作历史的主体问题,或许根本不可能有明确的标准或限定。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田野经验、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叙事风格等等,都可能影响到研究者、报导人或研究对象的主客观身份。但重要的是,无论是历史是由“他者社会”自己制造的,还是由“研究者”本人制造的(或者是由双方“合谋”制造的),这几种视角都不必过分执着于优劣对错的比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者无需刻板于制作历史的主体类别,而只要尽其所能呈现出“立体的人的历史”①这里,笔者特别强调使用“立体的人”代替“整体的人”。就已足矣。
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社会人类学者选择研究历史的方法策略时,必须考虑哪些“主体”亲自参与、实践和“制作”了这段历史过程,以及“主体”是否能够胜任、担当得起这段历史的“叙述者”——特别是当研究者本人也成为了历史的“制作者”时,这种思辨尤为重要。
四、“制作历史”与“写历史”之辨
与“制作历史”容易混淆的概念是“写历史”(doing history)。“写历史”是由西佛曼和格里弗所提出的另一个与历史人类学相关的概念[6](P16)——所谓“写历史”就是“研究过去”②西弗曼,格里弗的原文为:“我们认识到,如果要继续我们的工作,就必须面对‘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不能只是研究过去,或写历史。”(西弗曼、格里弗,1999,p16)。就某种意义而言,“写历史”同样也属于历史人类学的具体实践方式。那么“写历史”和“制作历史”之间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和区别呢?
海斯翠普的一段评论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写历史”和“制作历史”的区别。她是如下解释的:
“在非常普遍的层次上,历史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纳入社会人类学当中:一是透过对某一特殊历史资料的分析;二是包含在分析社会制度对时间观念的认识当中”(海斯翠普,2010,p136)。
上面所引用的历史人类学的两大取向,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因为每一种方法都很有可能被人类学者所混合使用,只是比重有所不同罢了。不过海斯翠普的分类,确实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学者在考察特定社会如何“思考过去”时,使用的视角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就“过去”这个议题而言,提倡“写历史”的人类学者,通常是要从特定历史资料或文本中探索“真实的、而非想象过去”,它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提倡“制作历史”的人类学者则强调“特定社群对于过去的想法或想象”,往往也包含了人们所想象和虚构的部分——但即使这种想法中有虚构的成分,也有它值得探讨的价值所在。如果说“写历史”强调的是历史“本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制作历史”则强调了历史被“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然,“写历史”和“制作历史”有时会也被混淆起来,因为“历史”即可以意味过去,也可以意味关于过去的故事;即是再现的对象,也是再现本身。本书的作者之一安唐・布洛克也认为:“‘历史’可以意指不同的事物。可以指一个社会在书写或讲述过去时的自我再现(self-representation)过程,也可以代表明确而具体的真实社会的情况、行动和发展。”(海斯翠普,2010,p92)因此,“写历史”和“制作历史”两个概念事实上代表的也正是“历史”概念的这两个不同面向。
五、历史的制作是随心所欲的吗?
在本书最后一章《“制作历史”的反思》中,安唐・布洛克批评了“制作历史”这话带有“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弦外之音(海斯翠普,2010,p134)。它很可能误导人们认为,人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并按自己选择的条件创造历史”③这里是对马克思原话的修改,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原文是:“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2010,p1-2)。的。然而布洛克坚持认为,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互动和依赖是复杂而微妙的,加上诸多意外因素的作用,常常会导致历史上产生看似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戏剧化结局。安唐・布洛克应当会赞成马克思对历史制作的限定:“人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3](P1-2)
从布洛克的质疑中,我们牵涉出一个新的议题来:历史的制作是随心所欲的吗?或者说,历史制作是否要受到某种“因果关系”的制约?
针对上述疑问,海斯翠普是反对那种随心所欲的历史建构论的:“人们必须对文化把他们塑造成的样子负责。”(海斯翠普,2010,p11)约翰・戴维斯①和海斯翠普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各个社会都创造了它们自己的“因果体系”,而且这样的因果系统还会反过来促成事件的走向。而海斯翠普更是特别花费了一节的篇幅论述“时间和因果关系”(海斯翠普,2010,p115),足见其对“因果关系”的重视,从而也否定了历史被“随心所欲”地制作的可能性。
然而戴维斯和海斯翠普也都指出,西方的历史学传统常常以纪年和时序(sequential)来表现历史,采取建立在“时间”面向上的因果关系,而排斥了“空间”的面向的因果经验。不过,“人类学对历史的看法,为历史学家的‘时间因果关系’加上了空间的面向(海斯翠普,2010,p176)。”一个社会建构其历史的方法,也可能是以西方历史学非常不熟悉的方式呈现。例如在赫兹飞和海斯翠普的地中海和冰岛研究中,因果关系就不再是以纪年和时序表达的,而是用荣誉和忠诚的远近谱系来加以表达 。
可以说,安唐・布洛克和海斯翠普分别给历史人类学提出了正反两面的善意提醒:首先,历史的制作确实不能随心所欲,它必然受到文化经验的因果系统的制约;其次,因果体系不仅仅是时间面向的,还可以体现出非时间的特质,人类学需要超越历史学的“时间因果律”。
六、结论
《他者的历史》让读者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时空观,也促使读者对历史记忆进行更深刻的思索,例如不同文化时空的人(即他者)是怎样思考时间和记忆,不同时间概念是怎样塑造空间和文化的,记忆是怎样被文化价值留存或遗忘的,以及文化和记忆最终又是如何定位过去、现在和未来等等。不过归根结底,本书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无疑是它将“制作历史”的概念运用到历史人类学的实践中,并且它对“制作历史”概念的阐释和反思给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带来了更多合作的空间。
总体而言,“制作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包括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对当下的决策,以及对未来的成就,其中这三者可以先后发生的,也可以是同时发生的。其中有几点还需要特别说明:(1)历史是一个场域,各种记忆在此符合、浓缩、冲突,也在此决定它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2)人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人基本上是其自己历史的制造者,但同时也必须对身处的历史负责。(3)历史的制作方式必然会影响到历史本身,而历史本身又限制了历史的制作方式。
[1] 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C].贾士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雅各布・坦纳著.历史人类学导论[M].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卡尔・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奈杰尔﹒巴利著.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M].何颖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保罗・拉比诺著.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高丙中、康敏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
[6] 西弗曼,格里弗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C].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9.
责任编辑:侯德彤
A Discussion about Making History:Response to Other Histories
XU Jing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Making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raised in the book Other Histories. This concept shows the process of anthropologists’ commitment to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 Instead of the closed and static research methods, anthropology is now gradually moving toward a more open and dynamic study of culture. Anthropologists should first examine the past history of a community before stepping into the working field, and also must observe and consider thoroughly the memories and histories of different societies.
other historie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make history; write history
K062
A
1005-7110(2011)05-0013-05
2011-08-06
徐晶(1984-),女,上海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