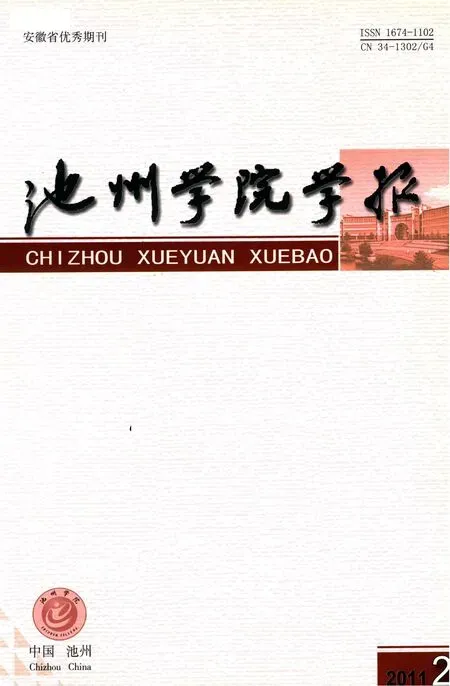艰难生活中的执著追求
——迟子建短篇小说中“怪人”形象评析
2011-04-01程大立
程大立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安徽 桐城 231403)
艰难生活中的执著追求
——迟子建短篇小说中“怪人”形象评析
程大立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安徽 桐城 231403)
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中短篇小说中的“怪人”,以其时清时浊、亦真亦幻的精神面貌和坚贞不移、勇敢执著的情感态度表达了贫困生活中底层人民的精神追求。
迟子建;小说;怪人;生活追求
迟子建中短篇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敢于担当的老潘(《一坛猪油》),宽怀大度的吉喜 (《逝川》),从容赴死的秦山 (《亲亲土豆》),一诺千金的阿尔泰(《草原》),婚外有情又因公殉职的刘良阖(《鬼魅丹青》),报复乡邻又主动改过的马占军夫妇(《白银那》)……还有另外一组令人心酸的人物,如《雪坝下新娘》中的刘曲,《采桨果的人》中的大鲁、二鲁,《雾月牛栏》中的宝坠,《疯人院中的小磨盘》中的李竹板等“傻子”形象,让人们看到了不同年代因疾病等原因 (更多的是社会原因)造成了一个精神失常的群体以及他们或悲苦或温暖的生活境况。
其实,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中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物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怪诞的言行,但又不同于精神失常的“傻子”们。他们基本具备正常人的生活和劳动能力,具有正常人智力和情感;他们大部分的生活是常态化的,但某些行为却又偏离了正常轨道——与他们的年龄、身份、职业等相悖。如年过不惑却迷恋“小儿书”的关全和(《日落碗窑》),坚持为死去的妻子编织草编的陈生 (《青草如歌的正午》),整天钓鱼和醉酒的刘年(《酒鬼的鱼鹰》),以及村中死了人就要玩“失踪”的张无影(《草地上的云朵》)等等,我们把这类介于正常人和傻子之间的人物称为“怪人”。
1 怪人的“怪”
之所以说他们是“怪人”,那是我们以“正常人”的眼光,以人的“正常”言行为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小说中人物的。确实,“怪人”们存在着有悖常理的表现。
《日落碗窑》中的关全和有三“怪”:其一,虽然是三十几岁的汉子,却对“小儿书”情有独钟;其二,对自己的儿子辍学玩丢碗竟然不加阻挡,而对他的年迈父亲尝试烧碗的行为不支持也不加反对;第三,当年选了腿脚有点残疾的女人做了老婆。《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的“怪”首先表现在行为上,妻子已经死去,他却天天在用青草为她编织一些生活用品;最后为了弄清手术刀的模样,竟然闯进了手术室。陈生的“怪”还表现在他的观念上,镇里不惜花大量的钱办滑雪运动会,就是浪费了老百姓治病的钱,他把这归咎为自己老婆“冤”死的直接原因。陈生的“怪”更体现在他奇特的变化上,杀生嗜好和与傻儿亲近,让他近乎于“傻”了。《酒鬼的鱼鹰》中的刘年也说不上有多 “怪”,醉酒是部分男人的常态,天天醉酒也大有人在;而成天以钓鱼为事,无非有游手好闲之嫌。刘年的“怪”在于:他本来是一个本份而又勤劳的人,醉酒钓鱼的生活态度较之以前当然为“怪”了。相比较这前面的三个人,《草地上的云朵》中的张无影确实有点“怪”,结婚多年不敢和妻子同房,怕的是搞出了小孩;每当村庄里死了人,他就要“失踪”几天,然后又完好无损地回来了,每次“失踪”他都要为自己挖一个坑,如此而已。
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迟子建小说中的“怪人”的怪异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儿童心理的滞留。心智与身体发育的进程中,人们逐渐告别童年,摆脱单纯、天真和幼稚。在知识的增量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事物的本真,变得复杂、老成和自信——这就是脱“稚”的过程,也就是平时所说的长大成人的过程。关全和热爱“小儿书”,说明他没能“成熟”,也就是儿童心理的滞留。这种表现如果只是偶发性的,也属正常;但在关全和身上成为一种惯常的嗜好,并且到了痴迷的地步,比如,“儿子关小明犯了错误,关全和欲鞭打他时,他就会像野马一样冲出院子去找小朋友借小人书来讨好父亲,若是借回来了父亲未看过的,父亲便会眉开眼笑的,气也就消了。”“关全和嘻嘻地笑着,与小儿书中的人物会心会意地交谈着,说‘我说你打不过红胡子吧,怎么样,马不是让人给杀了,宝也丢了吧?’”这些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病态了。
第二,人格分裂后的性格偏执。人格分裂症,这是一个医学上的名词,是指性格的多重性,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双重人格。陈生和张无影都具有这种“症状”,而陈生的表现更加鲜明。对与自己曾经有过肌肤之亲如今有病在身的女人有怜惜之情,对死去妻子有怀念之情——为她编一些草编,因为对妻子的爱和忠贞让他拒绝“送”上门来女人的肉体,这些都是正常范围内的人格特征。但是,看别人打牌时一定要“守”着“大王”“、小王”,把妻子的死和滑雪运动会联系在一起,告状失败后爱好杀生,为了编手术刀闯进了手术室等等行为,却是另一种非常态的人格表现。“多单独活动”,“有奇异的信念,或与文化背景不相称的行为”,“奇怪的、反常的或特殊的行为或外貌”,“言语怪异”等人格分裂表现以及偏执性格,是迟子建小说中“怪人”的典型特征。
第三,生活挫折下的精神退避。刘年是一个懦弱的小人物,“麻烦”总是跟着他,不论做什么事都离不开“倒霉”。老婆尽管能干并且孝顺婆婆,开了一家小杂食店倒也衣食无忧。然而,当年刘年是为了洗清“冤情”才娶了这个失过身的女人——这是一件心不甘情不愿的“窝囊”事。到城里儿子那儿寻份事又是麻烦不断,只得回乡以醉酒钓鱼度日。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退避的生活。
第四,恐惧情绪的消解。与刘年、陈生不一样,张无影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但生活并没有多少曲折。妻子是一个“俊俏的小媳妇”,“笑吟吟的”,但“他结婚五年了,就是不跟媳妇同房”,“是怕搞出了小孩子,他说世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人,生了小孩子不等于是送他去死么!”每当伊利库死了人,张无影“就会神秘地失踪一两天,直到死者进了墓地,他才回来。”原来,他每次扛锹出去都是挖坑,也不知挖了多少坑了。从这些描述,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对死亡充满恐怖的人的自我解压方法。他在一次次的恐惧中,一次次地消解着恐惧。
2 怪人并不“怪”
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有着双重性格的人,人们大都戴着一副面纱行走在世间,人们习惯于隐藏着自己真实的一面。如果人们揭去了 “面纱”,也就有了“怪人”一样的表现。因此,从“非常”角度,用本来的面目来还原,“怪人”并不为“怪”。
2.1 关全和:未泯的童心和善良的性格
现实生活中,人的成长和“脱稚”,从积极意义来说,是人们知识、阅历和经验逐渐丰富;但从消极意义上来说,人们也变得复杂,变得世俗,变得功利。这种变化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隔膜,正如鲁迅先生小说《故乡》中“我”和中年闰土就不再有儿时小伙伴之间的纯真和无拘束,这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是极其悲哀的一件事。其实,人的内心是难以完全“蜕”去童心的,只是我们在努力地掩饰着罢了。因此,关全和热爱小儿书的行为,正是人类最可贵的童心依然留存的现象,是一种不惧世俗、敢去功利的高贵行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喜爱阅读的关全和,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只能读一些小儿书,也并不为怪。至于有一定的“痴迷性”,也仅是爱好程度高一点而已,相比较嗜酒好赌之徒,也算是很正常的事。
这样一个从容而又无功利之心的男人,对儿子放弃学业练习丢碗,对老父亲拾掇旧砖窑改烧碗窑,当然不会反对和阻止。在他看来,人的成长和发展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人的爱好和选择都有其合适的理由。对一切合理的东西加以干涉,并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这种观点同样表现在对妻子帮助曾经的“情敌”王张罗上,尽管心中有点不愿甚至不乏嫉妒之心,但还是许可了妻子的行为。关全和,就是一个童心未泯又善良的男人。
2.2 陈生:正义的精神和忠贞的情感
在扑克游戏中,“大王”、“小王”具有最高的身份和能量,能够主宰局势统治局面。陈生看牌守“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权力的一崇拜和向往,也是对自己力量弱小和无法主宰命运的不甘。帮助朋友讨薪,不惜重拳动武,可谓嫉“恶”如仇。这种性格的人,在了解到滑雪运动会“糟蹋”了大量的钱——妻子陈秀正是因为没有钱冶病才死去,而政府却花这么多钱,只是为了让人“玩玩”—— 陈生当然会怒不可遏!事实上,政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来监督它的使用。陈生把自己妻子因贫而死与当地政府 “好大喜功”、对老百姓“不作为”联系起来,可谓有“先见之明”,这是一般人不能认识到的“简单”的问题;陈生是通过“告状”这一神圣而光明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是正义文明的举动。
告状不成杀生泄愤,但陈生并不是逢 “生”必杀。王来喜家的马总是流眼泪,他并没想杀它,而是看出马太累了,告诫王来喜家,不要为了挣钱让游玩的人任意地驱使马。这说明陈生是一个多么“清醒”的人,不仅能“诊”出马的病因,也能“看”出了人的功利之“症”。付玉成家的傻儿子总是哭,谁哄也无效,可陈生一抱,就会眉开眼笑。为什么呢?这一家人总把孩子当傻子,就不会有真爱之心,也不会有和善之言,孩子当然要“反抗”;在陈生的眼里,付大头就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和善的表情和真爱的言行,当然会让“傻儿”也高兴起来。
对妻子执着的爱,让他再也很少去看牌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草编的事上,他在为因贫困导致妻子死去而努力地做着“补偿”;他还利用“告状”的方式为妻子讨回公道。当公道不能伸张,他“补偿”的愿望更加强烈,所以“闯手术室”事件,是正义精神和忠贞情感爆发的极点。
2.3 刘年:归隐与消极中的向往和追求
从本质上说,刘年的“怪”源自他的婚姻。因为买烧饼误入杂食店看到了换衣服时裸体的许春英,他成了“流氓”。不惜与这个曾经失身的女孩结婚,就是为了在婚礼上洗清“冤情”。但这份没有爱的婚姻显然是刘年终生的隐痛。他不断地放大生活中的“麻烦”,最终无奈地消极退避,终日醉酒钓鱼只是借口,而内心还是逃避婚姻。因为醉酒,他可以每天去叫驴子酒店,只有孀居的老板娘寒波把他当“人”;钓鱼意外获得的鱼鹰,成了他们之间的“线人”,于是有了阴雨天里那一次倾心又体贴的共饮。然而,刘年的怯弱让寒波失望,鱼鹰最后被强权者——税务局长占有,意味着刘年的美好情感追求彻底失败。
2.4 张无影:惧死恐生现实与摆脱贫穷期望
人总是要死的,张无影为什么对死那么恐惧?根本原因还在于“穷”。张无影惧生又怕死。他不愿和妻子同房,是恐惧有了孩子却不能给他好的生活,让他在世上受苦受累,最后还是要痛苦地死去;他一次次地 “失踪”,是担心死亡者会拉他作伴同行;为自己挖的一个个坑,就是死亡心理的一次次解脱。在他看来,他已经“死”后重生,一定会平安生活下去,所以他勤奋劳动,把庄稼做得比谁家都好,为的是过好日子。为了摆脱贫穷,他不知爱情的珍贵,更没有享受天伦之乐;为了摆脱贫穷,他抱回了一个炸弹(可能会卖一点钱),最后酿成了血腥的悲剧。
3 怪人形象的意义
3.1 在迟子建小说中作品中的意义
傻子,往往表现为一种“痴态”,即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在迟子建的笔下,傻子与正常人相比或是表现为完全与现实隔离而亲近大自然……但正是这种不正常下却潜藏着生命中最本质、最善良也最纯真的人性。与“傻子”不同,迟子建小说中的“怪人”总是游离于自然和社会之间。一方面,他们渴望融入社会,但社会并不认可也不能完全地接纳他们,他们时常成为人们快乐的材料,甚至是可以利用的工具。陈生告状失败成了人们的笑料,而“付大头”的死,正是付玉成一家“利用”陈生脱离“苦海”的一个阴谋。刘年醉酒连小孩子们也会与他调笑,而他的清白只能以无爱的婚姻来证明。另一方面,“怪人”们又表达对自然世界的无比亲近和热爱。关全和沉浸在与小人书中人物的快乐对话中,充满天真和童趣;张无影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田地的耕种上,全无夫妻生活的愉悦需求;刘年成天看水面的波光,与清风对歌与水草絮语与蛙鸣共吟与细雨共浴;陈生则在青草的清香中享受一个个沉静而亲切的正午。因此,真切地表达人类对自然童真生活的热切追求是迟子建小说中“怪人”形象的首要意义。
第二,迟子建小说中的“怪人”虽然都生活在贫困之中,但他们不失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不失负痛前行的动力。他们没有用破坏社会或自我戕害的方式来报复社会或消极离世,他们在默默前行着。关全和一家节衣缩食也能体味贫困中的温暖生活。他们能消解恐惧,张无影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把全部的精力都种在了庄稼地里,为了过上温饱的日子。他们追寻梦想,刘年心中涌动着对寒波的热流,期盼着拥有一份真实的情感。他们坚守道德底线,陈生在妻子离世后不失善良,还能拒绝女色诱惑。他们在贫困的境地默默地坚守着、艰难地前行着,不放弃自己理想生活和人生境界的追求。
第三,迟子建小说中的“怪人”形象无论是作为主要人物或是作为次要人物,都能以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表现主题并彰显作者的人文思想。作为主要人物的陈生和刘年,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非常压抑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读出了无奈和辛酸,也能看出人世苍凉中的美好亮色;作为次要人物,关全和的潇洒自如,张无影的神秘色彩,恰恰成为钱欲世界的精神追梦者和遥远家园的坚定寻求者。因此我们说,迟子建小说中的“怪人”,是作者对物欲俗众的否定和精神图腾的呈现。
3.2 在当代小说中作品中的意义
在当代小说人物画廊中,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少爷、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以及迟子建小说中的刘曲、大鲁二鲁、宝坠、李竹板等 “傻子”形象,以其强大的功能性和丰富的心理性特征,以其外在的心理表征和内在的精神隐喻,反映了这一特定人群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曲折地表达了作家的生命观念和人格理想,给读者以灵魂的震憾深刻的反思。但是,当我们看到迟子建小说中这一组“怪人”形象时,我们会感到一丝并不轻松的轻松,也会产生一种并不快慰的快慰。
迟子建为我们建立了一组“边缘化”的人物群像,丰富了小说人物画廊。利用“怪人”的视角来叙事,或以“怪人”的形象为观照,在当代小说作品中还不多见。对于迟子建来说这是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探索——尽管这组人物形象的把握还有失分寸,如刘年偏向于正常人而陈生则近乎于傻子——但至少让读者认识到社会人的丰富多元性和复杂多样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迟子建为当代文学构建新的审美意象,拓展和丰富了当代小说人物美学意蕴。
迟子建是一个感丰富的作家,表现人间崇高的爱使她的作品始终流淌着一种灵动而飘逸的美;迟子建也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作家,对人生存价值的揭示和生命意义的关怀使她作品中常流露出一种无常的悲伤和抗争的凄美。因此,“怪人”形象系列是作者对多元人生的深度开掘和生活意义的深切追问,相对于当下众多的情欲化和物欲化的小说人物塑造,迟子建坚守着一个有良知作家的道德底线,坚信着人的那份美好和善良的生活渴望,坚定着自然生活和高尚境界的执著追求。
正如达伦多夫所言,“傻子”作为一个不合社会规范的形象,它本身也构成了对现实的否定力量。“傻子”作为独特的“这一个”,它的力量在于他不受社会等级秩序的限制,他既作为局内人又作为局外人谈论事情。迟子建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塑造的这一组“怪人”形象,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与困惑;并通过他们貌似失常其实却十分清醒、看似荒诞其却离真理最近的言行,提醒当下的“健康者”该如何生活,如何前行。
[1]杨德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案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2]艾娟.论迟子建小说中的孤独意识[D].南昌:南昌大学,2010.
[3]管怀国.论迟子建艺术世界里“傻子”形象的艺术价值[J].理论与创作,2005(5):73-75.
[4]迟子建.日落碗窑[M]//迟子建中篇小说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1—126.
[5]迟子建.青草如歌的正午[M]//迟子建中篇小说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27—178.
[4]迟子建.草地上的云朵[M]//迟子建中篇小说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711—337.
[5]徐艳蕊.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童庆炳.文学理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刘甫田,徐景熙.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I206
A
1674-1102(2011)02-0089-04
2010-10-12
程大立(1966-),男,安徽安庆人,桐城师专人文系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桐城派文化。
[责任编辑:章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