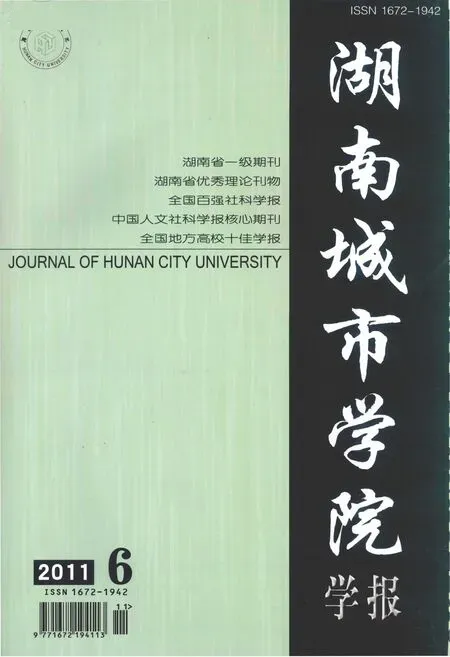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大片的表意策略和叙事风格
2011-04-01刘郁琪
刘郁琪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片异军突起。以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吴宇森的《赤壁》,徐克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陈可辛的《投名状》《武侠》等为代表的中国式大片,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票房奇迹和电影神话。但奇迹和神话的缔造,并非历史的偶然,也非个人的妙手偶得。这背后既有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的时代大背景,又有编导者精确把握东西方市场并将其成功变成表意实践的电影经验的深厚积累。
一
电影与文学不同,它天生就带有商品的胎记,自始至终都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市场与观众。是朝向大众,还是面对精英;是面向本土,还是着眼海外,这种市场态度和观众取向的差异,在根本上决定着一部乃至一个国家和地区影片的叙事风格和表意策略。历史上,中国电影的制作、拍摄、发行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缺少一个明确的海外市场,它作为文化工业的运作始终建立在国内市场自身的循环基础之上。[1]85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除“古装稗史片”等少数大众通俗电影有着初步的抢占东南亚地区电影市场的企图和行动之外,[2]大都以满足国内民众为主。1949年后,大陆电影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其观众被严格限定在新政权下的“全国各族人民”。“文革”结束,所谓第四代导演重新获得生机,在电影的叙事语言和表意方式上比起革命年代已有重大突破,但整个电影的拍摄发行运作体制仍然遵循着严格的计划方式,在观众定位上也仍然是朝向国内。
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中国电影内向化的单一格局开始被打破。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背景,以人性化的个体在各种权力体制中几近无望的挣扎为叙述线索,刻意突显挣扎的失败和个性的压抑,塑造了一个个有关中国专制、落后乃至不可理喻的寓言。[1]8这种寓言化的表意策略和叙事风格与此前的中国电影不同,迎合了西方人有关中国的固有想象,因而在西方的各种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从而成功地打开了中国电影外向化的大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艺谋等人的电影在西方电影节一路凯歌的时候,另一批同样毕业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更为年轻的导演登场了。他们被称为第六代。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在市场取向上主要着眼于国内,以表现新时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情形下一些底层民众或边缘人民的生存状态为主,叙述风格客观冷静。这既与此时张艺谋等人寓言化的外向型电影截然不同,也与此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向型电影模式迥然相异。
张艺谋等人那种外向化的电影制作和第六代导演们的内向化电影制作一起,构成了 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的二元性格局。[1]84-85这种格局对中国新时期电影体制改革和电影产业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这些电影在资金的筹措和发行、放映等环节已不像以往电影那样完全靠国家的计划来行事,而是开始转向市场,开始按市场化的逻辑运行。它们的成功表明,在脱离了严格的计划和国家扶持之后,中国电影仍然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但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市场全面开放开放之后,西方大片特别是好莱坞大片长驱直入,使刚刚走出一条市场化道路的中国电影(无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电影),市场骤然萎缩,一时间几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如何打破西方电影的垄断,创造出中国自己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电影品牌,培育出一种能够弥合内向/外向差异、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新的电影类型以振兴中国民族电影,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电影界的一块心病。
中国电影长期以来的单一性内向化格局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二元性格局的形成,与近现代以来西强中弱的力量对比以及与此相应的民族自卑心态息息相关。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超级大国和超级强国之一。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却由于自身的落后,长期处在西方列强的侵扰和重重包围之中。在西强中弱的实力对比面前,中国人的民族自卑感和文化启蒙的责任感显得异常激越和强烈。如何唤醒国民,如何向西方学习强国之道,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核心主题。在此环境中,电影,作为一种受众更为广泛的艺术形式,被有责任的知识者用作文化救亡和文化启蒙的重要方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既着眼于文化救亡和文化启蒙,中国电影在市场定位上自然就只能是着眼国内民众而非占领西方。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除极少数用于国际交流的电影之外,绝大多数电影的观众定位也都被严格限制在国内,也即新政权下的“各族人民”。这是因为虽然取得了民族独立,但外在西方势力的包围和威胁却始终存在,电影必须成为凝聚内部团结和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文革”后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开始面向西方观众,表现出一种向西方进发的昂扬姿态。这在表面看来似乎是走出了此前那种民族自卑的心态,但事实上正如前所说,其骨子里却透露出迎合西方的自我殖民的意味,所体现的仍然是文化自卑的心理。
历史进入新世纪,中西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有利于中国的微妙变化。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 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不足以改变西强中弱的根本格局,却在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次改变着中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感知。首先,随着综合国力的加强,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人面前的文化自卑,似乎悄然间已为某种不言自明的民族自豪感所替代。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打破西方垄断,与西方平起平坐甚至征服西方的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在各大媒体和网络论坛中像草一样的生长和流行。这种力量对比的改变所引起的感知的变化,自然会带来人们对中国电影的不同期待。人们似乎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影片形式,它既要能体现出国人对于自己的新的想象,又要能有效地征服西方人然后凭此掏空他们的口袋。中西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带给中国电影的另一影响是,不仅大大拓宽了其国内融资的渠道,而且大大降低了其在国外融资的难度,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它的融资能力。
国力增强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提升和融资能力的提高,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为中国式大片的投拍提供了条件。这些条件与中国电影界摆脱西方大片的冲击、振兴民族电影产业的潜在渴望相结合,使得一种能与西方大片抗衡或者说试图与西方大片抗衡、且能弥合中西方市场二元分裂取向的中国式大片的拍摄完全成为可能。于是,一种《英雄》式的面向全球市场的中国式大片应运而生了。这种大片打破了“海内外的界限”,取消了“以往的电影中的外向化/内向化的差异”,“将中国和全球市场作了前所未有的整合。”[1]184
二
中国大片在一种全新的文化处境中叙事并以弥合东西方市场为目标,那就必须同时考虑东西方市场的观影需求。这种东西方市场两面兼顾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式大片的表意策略和叙事风格。
一方面,东方市场的考量,让他不得不注意到中国国内民众的新的自我想象。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充满各种毛病并有待改进的形象。因此,那时第六代导演们的电影,只要采用悲悯眼光和人性关怀来展示新形势下小人物或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和艰难,就足以吸引本土观众的眼光了。但此时,中国在国人的形象中悄然变得强大起来,在西方人面前不再那么自卑了。要满足和平崛起背景下中国观众向西方展示强大中国甚至是征服西方的冲动,中国式大片不得不极力挖掘开发能够代表中国强大和优秀的中国式元素和文化符号,以让国人看到一个与西方不同但却同样强大而优秀的中国,从而满足中国观众征服西方人的愿望或者说新的自我想象。另一方面,要打入西方主流市场,并有所斩获,就必须照顾西方人的胃口。而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落后/专制;二是神奇/神秘。[3]20这也是《红高粱》和《霸王别姬》等中国早期外向性电影,能在西方电影节屡有斩获的原因。虽说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形象在西方有一定改观,但正如中西力量对比的根本改变尚待时日一样,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彻底改变也仍需时间。因此,中国式大片既然以赢取西方大众市场而非小众化的电影节为目标,那就必须向西方展示一个落后而神奇、专制而神秘的中国形象。
要在同一部影片中,既展现出中国人自己的新的强大和优秀的自我期待,又迎合西方人固有的有关中国落后神奇的想象,就必须找到一种与此前的中国电影不同的叙事对象和表意策略。这不仅构成了中国式大片叙事的主要任务,也构成了中国式大片叙事必须超越的主要难题。不过,精明的中国式大片的制作者们通过利用古装宫闱和战争生活、武侠功夫打斗、独特的民俗风物和地理山川景色等中国式元素和文化符号所固有的双重意含以及对它们二元性展示,轻而易举地就跨越了这道难题。
古装宫闱生活和战争题材,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式大片的显著特征之一。这是因为只要调适得当,它能最直接最有效地同时满足中国和西方两个市场的不同要求。如前所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和超级强国,只是到近代以后,才逐渐衰落了。要满足新形势下中国人逐渐高涨的民族自豪感,重树大国形象,自然以古代盛世王朝的展示为最佳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作为激发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方式,其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在此意义上,中国式大片极力表现中国古代王朝的强大和辉煌以及恢宏的战争场面,就是要为中国当下观众重构一个盛世时代和盛世景观,其中寄寓着中西力量对比发生微妙改变的新形势下中国人有关中国已经或者正在不断繁荣和强大的新的想象和期许。其次,古装宫闱生活和战争场面,也是最能满足西方有关中国专制落后神奇神秘的想象的理想载体之一。在被西方叩开国门以前,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的规律和独特道路发展着。这是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不像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那样完全以对西方的认同或者说与西方同质化为目标。这样的中国显然更有吸引力。但这样的中国必须按照西方人的胃口来塑造,才能真正吸引西方观众。因此,中国式大片一方面极力表现盛世王朝和盛世景观,另一方面则极力表现皇宫生活战争场面的神秘、奢华、糜烂、专制,甚至不惜将其奇观化,扭曲化乃至极端化。于是乎,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人心的阴暗歹毒和善于权谋算计,虚假的道德与残酷的杀戮,阴谋叛逆、战争,排场的奇观化的描写,便成为这些影片的基本定式。
武侠打斗,是中国大片整合中西方两个市场的另一重要元素。某种程度上,武侠功夫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部门之一,武侠电影是中国叙事电影中最具民族特色的一个类型,也可以称为特有的样式、体裁,是很有别于外国电影的。[4]最早使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化的电影就是港台电影大师胡金铨所拍的武侠片。而李小龙的功夫片更是让中国功夫享有了世界声誉,并使得中国的武侠功夫无形中就具有了一种引发民族自豪感的奇特魅力。这一切都决定了它可能是最能够激发本土观众的民族热情的中国式文化符号之一。与此同时,武侠打斗也能有效迎合西方人有关中国神奇甚至是非理性的固有想象。弗莱在分析西方文学样式及其演进过程时,按照作品中人物与普通人及环境的关系,将文艺作品分成神话、浪漫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反讽五类。所谓神话和浪漫传奇,便是那些其主人公在本质或程度上优于他人也优于环境的作品。[5]按此观点,中国的武侠电影无疑属于神话传奇的范畴。因为那些武林高手,全是身怀绝技,飞檐走壁的人,他们不但优于一般人,甚至优于自然环境。他们常常随心所欲地违反自然规律,如从地面腾空而起,在竹尖上打斗,在水面上如蜻蜓般飞驰等。中国武侠这种不受自然规律限制的潇洒飘逸的打斗,自然最能满足习惯了科学化理性化思维的西方人有关中国文化神奇、神秘、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想象。而为迎合西方观众的神奇想象,中国式大片对武侠打斗的表现,往往刻意跨大其非理性的一面。如《英雄》中的“意念决斗”,便令人匪夷所思。
与古装皇宫和战争题材的选择、武侠功夫打斗的表现一样,独特的民俗风物和地理山川景色的展示,在中国式大片中也承担着整合东西方市场的双重作用。一直以来,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地大物博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用以激发国人爱国主义热情的重要方式。中国式大片对这些方面的展示,可以激发本土观众的文化亲和力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中国化的民俗风物和地理山川也是突显中国神奇特色的重要手段。而为有效地吸引西方人的眼球,这些大片也不惜将这种民俗风物作极为夸张地奇观化表现。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女人爆乳、千人捣药、遍地菊花,以及《赤壁》中之“回光阵”,均是有违历史真实的故意夸大。
中国大片就这样通过利用中国式元素和文化符号所固有的双重性意含,以及对它们的优秀化和落后化的二元性表现,将同时满足中西方观众需求从而弥合东西方市场的分裂这种看似相悖甚至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三
但经过百余年的西学洗礼之后,中国大片的制作者也清楚知道,强大优秀的东方文化固然能煽动起本土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亲近感,但没有普适性的人性因素的添加,也很难让本土观众看得下去;而纯粹的神奇、落后东方景观固然能调动西方人视觉上的偷窥欲望和满足他们对古老中国的奇观性想象,吸引西方人的眼球并让他们看得下去,但没有西方式人性观念的添加,却撩不动西方人的内心,让他们完全看得懂,看得进去。也就是说,无论是要让东方,还是要让西方人看得进去,都需要添加所谓普适性的人性人道观念这种更为深层的粘合剂。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对普适性的人性欲望的渲染和展现,就成为这些大片不约而同的选择。
在众多普适性的人性欲望中,性爱欲望的铺陈与表现最为突出。这或许是因为性与爱的欲望最没有也最能超越文化差异。为勾起观众超越文化差异的本能欲望,中国式大片常常直接出现性感镜头和性爱场景(也即所谓床戏),并且刻意凸现这些镜头的视觉快感和色情意味。劳拉٠穆尔维指出,“传统电影情境中观看快感的结构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第一个方面,观看癖,是来自通过视觉使另外一个人成为性刺激的对象所获得的快感。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自恋和自我的构成发展起来的,它来自对所看到的影像的认同。……一个暗示着主体的性欲认同和银幕上的对象是分离的(主动的观看癖),另一个则通过观众对于类似于他的人的着魔与确认来要求自我和银幕上的对象认同。第一个是性本能的机能,第二个是自我的利比多(libido)的功能。”[6]在中国式大片的性感镜头和性爱场景中,这两种方式的交叉运用比比皆是。如《赤壁》中周瑜和小乔的一段床戏,就在摄影机的观看(观众直接观看)和周瑜的观看(观众通过周瑜的眼光观看)中来回切换,它所要激起的其实就是观众的窥视癖和性认同。
当然,公开的性感镜头和性爱场面的展示,只是这些影片“人性化”的表层方式。更为深层的表现则是,将爱情的欲望设计成为剧中人物的部分或主要的行为动机。《英雄》的主要目的是要强调和颂扬所谓“天下观念”,但就在其中也独具匠心地添加进了残剑、飞雪、如月三人之间的爱情。《十面埋伏》中卧底与反卧低的曲折离奇构成了故事的主要叙述线索,但其中却巧妙地交织进了两大捕头与小妹的情感纠葛。《无极》主要是想探讨自由命运等宏大的哲学主题,但其中也有皇后与光明、奴隶之间的三角恋情。《赤壁》的目的当然也不是表现爱情,却也被穿插进了所谓性与爱的因素,如曹操征战刘备和孙权的动机,就通过其手下之口说成是“为了一个女人”,周瑜与小乔的爱情似乎纯属多余却硬要表现,这也说明大片对人性欲望的倚重。至于《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人性欲望的追求几乎构成了其主人公们的基本动机。改编自曹禺的话剧《雷雨》的《满城尽带黄金甲》,片中的皇后继承了剧中繁漪因性欲被压抑并且与儿子乱伦的情节,这符合人性的想象。而皇太子元祥也保持了剧中周萍在对旧爱的悔恨和对新爱的渴求的双重煎熬中的人性品格,太医之女蒋蝉也与原剧中的鲁贵之女四凤一样单纯而痴情。
但中国大片最终却以片中人物的悲惨结局,宣告了对性爱和欲望追求的压抑。《英雄》里的残剑与飞雪,最终都牺牲了,连如月都死了。《十面埋伏》中以小妹的死亡,宣布了无论是金捕头还是刘捕头,爱情都是靠不住甚至是不可能的。《夜宴》中的青女、婉儿、甚至为情而弑兄篡位的皇帝,都没能得到各自理想中的爱情。《无极》中的倾城,似乎最后与奴隶昆仑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和自由,但那是以“时空倒转”为前提的。而现实中的每一个观众,都非常清楚,时空不可能到转。所谓时空倒转是一个经常用来表示某物不可能的形容词。因此,即便是倾城的成功,最终也是虚幻的。
人性欲望追求的失败和压抑,展现的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力量。这种权力,可以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种不可动摇的皇权,也可以是《无极》中那种冥冥之中的命运。透过《满城尽带黄金甲》对话剧《雷雨》的改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相比《雷雨》,《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意义与内涵无疑是大大降低了。话剧《雷雨》,作为一部悲剧杰作,不仅是一部社会悲剧,而且也是一部存在悲剧,甚至还有宗教悲剧的意味。[7]但改编成电影后的《黄金甲》,则仅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欲望追求和反抗失败的故事”,变为一个“专制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故事”。[3]20这种设置,在更深的层次上同时满足了东西方市场观众的不同需求:中国人看到了“能者意识”的崛起;[8]而西方人则在一度的激动人心之后,看到了中国专制皇权和压抑性的专制文化的魅影。这样,所谓普适性的人性人欲,不过是一个幌子,其根本目的不在表达其自身,而是其后面的东西,它不过是中国式大片用以整合东西方两个市场的更为深刻也更为隐秘的纽带而已。
总之,人性欲望的追求和压抑构成了中国大片的通用模式。在此模式中,人性欲望就象寓言故事中那把挂在羊头前面的青草,引领着东西方的观众不断往前走,但最后东西方观众吃到的却不是那把青草,而是一路走的过程中通过中国式元素和符号中所激发起的各自心目中早已有之的想象和幻景:中国观众看到了新的强大的自我形象,西方观众则在一度激动人心之后看到了它们脑袋中早已有之的落后与神奇。
[1] 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2] 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65.
[3] 刘郁琪.中国式大片之病[J].电影评介, 2010(9).
[4] 李少白.历史性的考察、记录和分析[M]//中国武侠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1.
[5]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 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45-47.
[6] 劳拉٠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7.
[7]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318-320.
[8] 傅明根, 黄嘉庆.能者意识的崛起——对当下中国大片的一种描述与判断[J].电影文学, 2008(7):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