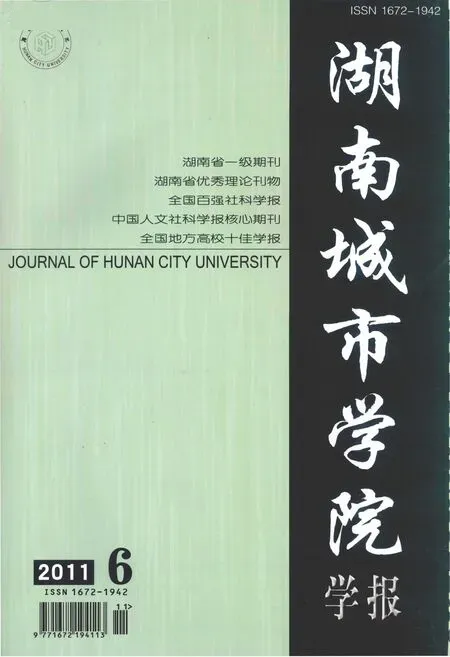民俗学研究的新篇章——读袁文海新著《现代民俗学新论》
2011-04-01万里
万 里
在社会科学中,民俗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s)正式提出了“Folklore”(“民俗学”)这个学术名称,由此奠定了这门学科的基础,1878年成立的英国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则是这一领域的最早研究机构。民俗学传入中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科学和民主观念的引领下,“五四”时期的一代学者开始转变视角,深入挖掘民间文化遗产,重新审视和评估民族文化,民俗学的研究亦随之蓬勃兴起。中国现当代的学者中,周作人、顾颉刚等人都为民俗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则是中国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南北两座重镇。1928年,在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等人的推动下,北京大学发起歌谣征集活动,并创办《歌谣周刊》。除了民间文艺之外,顾颉刚在1925年以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名义发起组织“妙峰山香会调查”,并在《京报周刊》上发表调查报告《妙峰山进香专号》,这是中国民俗学界最早的一次田野作业活动。此后,顾颉刚于1927年在中山大学组织民俗学会(全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丛书和《民间文艺》等刊物,将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新中国建立以后,民俗学研究虽有过短暂的停顿,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大批的新人新作,不但延续了“五四”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传统,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开拓进取,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近年来出版的民俗学著作中,袁文海先生的《现代民俗学新论》是一部颇具新意的作品,值得我们认真一读。
通读袁文海先生的《现代民俗学新论》(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10年12月),我认为,本书立论精辟,语言流畅,纲目清楚,例证充分,基本形成了一家之言。
首先,袁文海的《现代民俗学新论》将“民俗”与“现代”相结合,使民俗学研究贴近当下的时代生活,具有鲜活生动的时代气息,这是本书在理论上卓有建树之处。
在民俗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文化遗留现象。在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研究中,这种意见占据了主流地位。如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的周作人,他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童话和歌谣两个方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周作人认为童话所反映的儿童心理接近于蛮荒时代的原始人类思想。此外,顾颉刚等人的民俗学研究也与其《古史辨》的史学研究取径相一致,目的在于“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可以说,中国早期的民俗学研究从属于史学研究,目标在于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这在胡适1923年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得很明白:“在历史的眼光里,今天民间小儿女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胡适文选》,第322页,亚东图书馆,1930年)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下,民俗学研究很难和当下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而只能成为一种面向过去的学问。钟敬文先生曾特别指出,民俗学要研究要扩大范围,研究“现代生活中的活世态”、“一般民众的生活相”,这一论点的提出是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袁文海先生的《现代民俗学新论》在这方面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除了在书中将“时尚民俗”作为专章进行研究之外,同时提出现代民俗学区别于传统“文献民俗学”之处在于,现代民俗学立足于研究“社会人的生活方式”,不受“残留物”的困扰,不受“过去时”的羁绊,也不再局限于下层社会的“生活事实”,而是以活生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总结概括其演进规律。
其次,《现代民俗学新论》在对“民俗”概念的澄清上也作了进一步的努力。
民俗学研究在中国虽有近百年的历史,但“何为民俗”这一中心问题仍然众说纷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一般以“民风”和“风俗”来指称当时的社会习俗,如《礼记·王制》中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代的《白虎通》中则说:“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古人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所指的都是当时民间社会的礼俗风尚。自“五四”以来,中国民俗学界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民间文艺和历史传说,前者如北京大学收集的民间歌谣,后者如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进行的专题研究。总体来说,中国早期民俗学界的“民俗”概念还囿于“历史遗留物”的层次,着重于其民间性和历史性,同时“民俗”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传统。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认为,民俗包括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事相,无论这些社会事相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是属于历史传承还是时代产物,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都可以归属在“民俗”这一百科全书式的概念之下。在这一点上,《现代民俗学新论》体现了当代民俗学发展的新方向,指出“民俗”不是单纯的历史遗留物,而是涵盖了一切精神性和物质性的社会事相。同时,本书还从行为性、情感性、消受性等方面对“民俗”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分析,指出“民俗”的本质特性是一种生活活动方式,民俗的文化属性是一种特质文化方式。在“民俗”概念定义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民俗现象进行诠释和解读,并提出现代民俗学研究应当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立足于现当代,在全球化、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语境下与时俱进。
最后,《现代民俗学新论》对“民俗学”的学科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
民俗学最初被称为“Folklore”,意为“民众的知识”和“民众的学问”。实际上,“Folklore”一词兼具“民俗”和“民俗学”两层含义,因此,在民俗学建立之初,如何界定“民俗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特定含义就成为了民俗学者的重要任务。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又常常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重叠。在中国的早期民俗学研究历史上,周作人的研究近于文化人类学,顾颉刚的研究则近于历史学。如何划分、确定民俗学的研究范围,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一直是困扰中国当代民俗学界的一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现代民俗学新论》也提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观点。本书认为,现代民俗学的建立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摒弃传统民俗学以“历史遗留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狭隘格局,从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入手,研究活生生的社会事相,并从哲学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在学科关系上,现代民俗学隶属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经济学、美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亲缘关系。在当代社会中,民俗学研究不但要总结历史现象,同时也要深入生活,为当代人提供美好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民俗是人类历史上的古老现象,民俗学则是社会科学中的新兴学科。“五四”时期的学者认为,要认识中国文化的真相,除了文献记载之外,尚有“口传文学”这一传统,在一定意义上,以“口传文学”(歌谣、传说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更为深广的一面。如果说文献记载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那么“口传文学”等民俗文化就是海面下的巨大山体。在这个意义上,民俗学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袁文海先生的新著《现代民俗学新论》为我们带来了民俗学研究的新视野,我们期望类似的著作不断出版,在开辟民俗学研究新领域的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进入新的境界和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