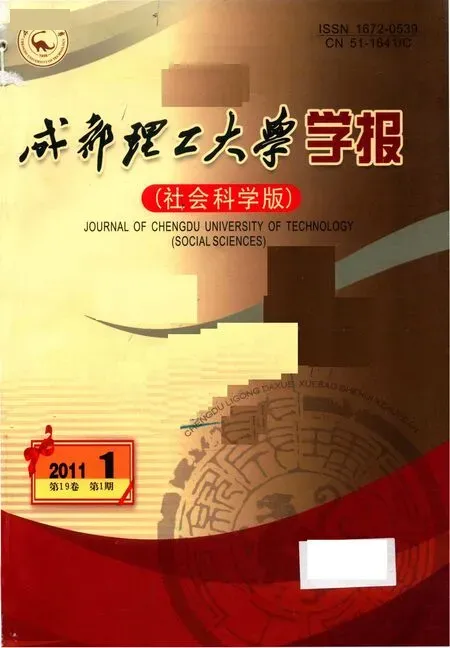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考察
2011-03-31杨金彪
杨金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律系,北京 100038)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考察
杨金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律系,北京 100038)
现行刑法第306条——判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立法根据在于,该罪行具有侵害国家司法作用的高度危险。由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该罪行应当从重处罚。引诱行为的实质内容在于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而不在于引诱的具体行为方式,即使是诱导式询问的某些特别类型也存在构成刑法第306条罪行的余地。刑法第306条与第307条是特别犯与一般犯的关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藏匿、隐避证人的,属于本罪的毁灭证据的行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明知是他人伪造、变造的证据而使用的,应当属于本罪的伪造证据的行为。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1997年新刑法第306条新增加的一个罪名。(1)自本罪名增加以来,就有来自司法理论和实务界的不同声音,既有人对此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也有人对此持反对的意见。当然,相形之下,质疑之声更是鼓噪一时。特别是伴随一系列关于本罪的影响性案件的判决,正反不同意见的交锋就更加激烈,一夜之间本罪成为千夫所指的犯罪,对“306大棒”[1]的声讨之声此起彼伏。有的主张应当在立法论上对本条做出修改,其中主张在立法论上废除第306条的也大有人在。众所周知,正反双方的辩论所折射出的正是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真正交锋,这场战火已经从具体个案中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唇枪舌战,演变为法庭外的博弈。论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第306条的立法根据的质疑,还有本罪客观构成要件的明确性问题,以及由于整个妨害司法罪类型化较差所带来的本罪与第307条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这种论争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这场论争当中。然而,刑法学者不应当盲目地追随所谓主流和时髦,更不应当成为误导舆论的向导,而应当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更加冷静、审慎的态度深入考察上述问题,得出中性无色的结论。
一、新增刑法第306条罪名的立法根据
对于新增刑法第306条罪名的立法根据问题,目前学界既有肯定的,也有质疑声。其中,来自反对说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306条和第307条第1款所规定的两罪的法定刑完全相同,而对于存在着法条竞合关系的两罪来说,刑事立法之所以在普通法条规定普通犯罪之外,还单独规定一个特别法条,另行设立一个特殊的犯罪,是因为这一特别法条所规定之罪的社会危害性已经不能为普通法条所规定之罪的法定刑所涵盖,需要对其加重处罚。这也即是说,特别法条所规定之罪的法定刑应当重于普通法条规定之罪的法定刑,否则,就失去了法条竞合存在的意义。所以,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完全是一种重复的规定。[2]
第二,该罪的设置是立法上对辩护方不公正对待的体现。因为,如果认为律师干扰、破坏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需要将其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单独规定一个罪名的话;那么公、检、法作为参加刑事诉讼的重要一方,其工作人员也可能实施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行为。而且,他们的此类行为无疑具有更为恶劣的影响和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刑法却没有就公、检、法的此类行为专门设置一个罪名。[3]
第三,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均没有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证据犯罪,可以说,我国的这种规定是绝无仅有的。[4]
第四,律师伪证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弊端,导致了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律师更加弱势,并导致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萎缩。[5]57有学者认为,不管从价值取向,还是从实践效果来看,这一条都是失败的立法例。从价值取向上说,这是一种变相的职业歧视,严重影响了律师的活动和职业形象,甚至成了实践中检察机关执法报复的依据。从实践效果来看,据统计,被指控犯有刑法第306条罪行的案件中,90%以上最终被法院判决无罪。很明显,统计数字上表明,这个法条本身的设计是弊大于利。刑法典第306条对律师的行为规范、对律师的权利保护,甚至对整个法治都是不利的。特别是在律师本就不受重视的现实环境下,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立法者可以考虑将这个条文取消,而采用其他的刑法条文规范律师行为。[6]
上述质疑显然难以成立。首先,本罪在罪质上属于危险犯,而不是义务犯。本罪的立法根据并非在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义务违反,即本罪并非仅因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具有特殊的身份而受到处罚,而是因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以及妨害作证的行为导致了国家司法作用受到侵害的危险才受到处罚。
而且,正如反对说所言,刑法除了第306条规定了本罪外,第307条还规定了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307条的犯罪与本罪显然是一般犯和特别犯的关系,即本罪是特别犯。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的确体现了与一般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相比要重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立法目的,而且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的法定刑明显高于第307条第2款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法定刑。尽管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的法定刑与第307条第1款的妨害作证罪的法定刑相同,但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的客观行为方式仅要求威胁、利诱就可以构成本罪,而第307条第1款的妨害作证罪客观的行为方式要求必须使用暴力、威胁或者贿买的方式,显然前罪的成立条件要比后罪的成立条件更加宽松,仍然体现了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重处的立法目的。之所以如此,其实质根据在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诉讼参与人,由于其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决定了要比一般主体妨害作证危害国家的司法作用的危险性更高。
其次,学者们一般认为,第307条的犯罪主体没有限制,而且从第307条第3款关于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从重处罚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条的犯罪主体当然包括了司法工作人员。因此,刑事立法并没有纵容司法工作人员毁灭、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的犯罪行为。对于一般的司法工作人员,只是利用自己抽象的司法职务权限,因为不是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国家司法作用的危险性并不比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高,因此法律规定只要适用第307条的犯罪处罚就可以,没有必要对这类人单独做出规定。而且,尽管如此,刑法第307条第3款仍然规定了司法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原则。
而且,对于作为具体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承办案件的具体职务权限,为了追诉明知是无罪的人,或者为了不追诉明知是有罪的人,而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应认定为徇私枉法罪。[7]基于同样的理由,未具体承办案件和指示、指挥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应认定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具体承办案件和指示、指挥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通过毁灭、伪造证据的方法实施枉法行为的,仍然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论处。2006年7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实际上也做出了同样的理解。[8]9相比较而言,第399条的徇私枉法罪的法定刑远远高于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法定刑,之所以如此,刑事立法实际上正是考虑了作为具体承办案件和指示、指挥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实施上述犯罪行为具有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司法工作人员作为尖锐对立的控辩双方的一方,在这类犯罪上并没有受到更轻的处罚。如果说第306条是高悬在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头上的一根大棒,或者说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9]164那么在司法工作人员的脑袋上不也悬着一把更为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吗?因此,难以得出刑法第306条是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歧视性立法的结论。
再次,对于反对说的第三个理由,姑且不论我国刑法第306条是否世界绝无仅有,即使没有专门规定针对辩护人的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的国家的刑事立法,也并非不处罚辩护人的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司法罪。例如,日本刑法在第104条规定了湮灭证据罪,日本刑法学几乎毫无争议地认为本罪的犯罪主体没有任何限制,即实际上包括辩护人。[10]
况且,我国刑事立法把辩护人作为犯罪主体专门规定也并非世界绝无仅有,俄罗斯刑法典第303条第2款就规定了辩护人等伪造刑事案件证据的犯罪。该条第2款规定:“调查人员、侦查员、检察长或辩护人制造刑事案件伪证的,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3年以下剥夺任何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因此,不能简单地从表面上看外国刑法上没有规定相应的犯罪,就得出我国刑法也不应当做出这种规定的结论。因为,对于相同或相似法益的保护,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完全可能采纳不同的立法体例。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可能非常复杂,每一个国家的刑事立法必然考虑本国的实际国情做出选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认为哪个国家的刑事立法更合理。譬如,关于湮灭证据的犯罪所涉及的范围问题,日本刑法主要规定了针对刑事案件的湮灭证据罪,而俄罗斯刑法典则与我国刑法典大致相似,在第303条规定了制造伪证罪,区别了民事诉讼(含行政诉讼)中的制造伪证和刑事诉讼中的制造伪证,分别规定在该条第1款和第2款中。该条第1款规定:“民事案件参加人或其他代理人制造伪证的,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500倍至800倍或被判刑人5个至8个月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1年以上2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2个月以上4个月以下的拘役。”[11]因此,我国刑法关于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犯罪采取区分不同主体的立法模式,实质上是考虑了不同主体在诉讼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从而其行为对于国家的司法作用的危害程度不同而做出的科学选择。因此,其他国家刑法是否规定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能成为取消我国刑法第306条罪名的理由。
最后,控辩双方处于事实上不平等地位或许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主体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并非由第306条的规定所致,在新刑法制定之前该问题始终就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顽疾。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取消第306条的罪名,在短时间之内也难以改变律师的弱势地位。至于近年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作用的萎缩效果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律师不愿意参加刑事诉讼的辩护还应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把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较为体面的口实。难以断言,只要取消刑法第306条的罪名就会改变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辩护的局面。当然,随着媒体对关于第306条犯罪错案的频繁曝光,让人们隐约可以看到司法机关滥用司法的现象。然而,从司法的滥用不能推断出法律的恶。而且,面对滥用司法更不能用撕毁法律的手段解决。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撕毁法律之害远远大于滥用法律之害。刑法第306条既惩罚危害国家司法作用的犯罪行为,又保障没有危害国家司法作用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不受侵害。该条第2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这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因此,与其说第306条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倒不如说是守护在律师和诉讼代理人之前一手托着天平一手握着利剑的泰美斯之神吧。
二、客观构成要件的明确性
反对说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第306条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多数学者矛头直指妨害作证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例如,有人认为第306条条款规定模糊、笼统,界定不清,可操作性差。律师伪证罪有关“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之类的措辞,极易带来执法的随意性。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这一措辞则以意识领域中的概念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极易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产生个人理解的偏差,并造成操作规则的混乱。[5]56-57有的学者认为,“威胁”和“引诱”是一个技术描述性的词,涉及询问证人的技巧,什么样的询问用语或用词属于引诱并没有标准。因为“威胁”和“引诱”通过“言论”表现,规定威胁、引诱为犯罪,无异于禁止律师的言论。可见,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罪状描述与联合国大会1990年9月7日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12]
上述质疑难以成立。第一,威胁、引诱作为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并非仅为人的意识领域的概念,其本身就是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而且,威胁、引诱显然不能完全与言论等同,尽管威胁、引诱可能通过言辞表达,但是威胁、引诱的行为并不局限于言辞表达。把威胁、引诱等同于言论,进而认为违反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显然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第二,在刑法修正案七之后的刑法典中,有包括本罪在内的10余个罪名近20个条款把威胁作为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要件;即使是引诱一词也有包括本罪在内的8个条款共5个罪名作为客观的行为方式要件。因此,仅仅认为本罪中的“威胁、引诱”的行为方式要件模糊、笼统,难以让人信服。第三,任何用语的核心意义都是清楚的,然而越向概念的边缘部分界限会越来越模糊。但是,不能以此下结论认为概念本身是模糊的。正因如此,刑法才需要进行解释。对于概念边缘部分的界限划分,需要结合条文的规范目的、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等进行解释。第四,在刑事立法中,不同的用语其内涵和外延可能完全相同;相同的用语在不同的条文中也可能具有不同的外延。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认为概念本身不清楚。例如,有些学者分析认为,引诱一词在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引诱吸毒罪、引诱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中的含义大体是相同的。只不过在引诱卖淫罪中诱导的成分大一些,并且在诱导中,须采用金钱、物质利益相吸引。该学者进一步认为,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引诱,不能理解为诱导性询问,也不能按照诱供之引诱来理解,而必须是以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以作伪证为目的,采取金钱、物质或者其他利益的方法,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在此,应当强调引诱必须是采取金钱、物质或者其他利益的方法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因此,这里的引诱决不包括诱导性询问。[9]163学理上尽管对本罪的威胁特别是引诱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尚难以得出本罪的规定不明确而应当予以废止的结论。
关于本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目前学界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以一定的利益加以引诱以及是否包括诱导性询问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如上所述,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一定的利益为诱饵,但是不限于金钱、物质利益,其他利益也可以。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仅限于以金钱、物质利益引诱。[13]443但是,上述论者均没有说明做出这种限制的理由。应当认为,这里的引诱行为没有任何限制,它是与威胁一起构成教唆他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手段行为。首先,引诱的关键在于使他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这才是本条的规范目的。因为只要是故意地使他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都会危害国家的司法作用。换言之,引诱行为无论是采用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还是通过女色等非物质利益的诱惑,乃至通过请求、唆使、欺骗等方式,只要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就足以危害国家的司法作用。所以,没有理由对本罪的手段行为做出任何限制。其次,从条文之间的关系看,证人故意作伪证构成犯罪的,应当以第305条的伪证罪定罪处罚。而第306条的妨害作证以及第307条指使他人作伪证应当属于伪证罪的教唆行为,上述两种犯罪行为实质上是伪证罪教唆行为的实行行为化。然而根据刑法总则关于教唆行为的规定,教唆行为方式没有任何限制。因此,作为独立犯罪化后的妨害作证行为当然不应当有任何限制。再次,从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与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的关系看,既然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是作为特殊主体的犯罪,那么它就应当显示出比第307条重处的倾向。如上所述,这种关系体现在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的处罚范围应当比第307条妨害作证罪的处罚范围更广上。因此,从手段上可以认为,既然第307条包括暴力、威胁行为,那么第306条的威胁也应当包括暴力行为在内,这也是当然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而第307条以和平方式的妨害作证除了贿买行为之外还包括其他行为方式,那么第306条的引诱就更不应当仅限于金钱、物质的利诱,欺骗和诱使行为都应当包括在内。
存在的问题是,这里的引诱行为是否包括所谓的诱导式询问。上述论者认为,引诱行为不包括诱导式询问。然而,一概地把诱导式询问排除在引诱行为之外未必妥当。因为,按照学者的一般理解,诱导式询问具有不同的类型,即包括四种情况:一是虚伪诱导,即暗示证人使其故意作违背其记忆的陈述;二是错误诱导,暗示证人使之产生错觉而进行违背其记忆的陈述;三是记忆诱导,通过暗示使证人恢复对某些事实的回忆;四是诘难诱导,通过提出带有诱导性的问题达到对证人已经提出的相关陈述进行诘难的目的。[14]对于后两种诱导式询问,因为不会导致违背证人记忆的陈述的结果,所以可以认为不属于这里的引诱行为。但是,对于虚伪诱导、错误诱导,因为能够导致违背证人记忆的陈述的结果,所以在证人做出违背其记忆的陈述时,极有可能会导致违背客观事实的陈述。因此,前两种诱导询问存在构成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和作伪证的余地。而且,诱导性询问在英美刑法上主要是庭审中询问证人的方式。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如果仅仅限于在庭审中询问证人时适用诱导性询问,由于在庭审中法官可以依据职权进行引导,而且存在控诉方的反询问,因此一般不会产生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后果。但是,如果像上述论者认为在庭前会见证人的过程中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仍然可以适用诱导性询问的话,那么在虚伪诱导和错误诱导的情况下,则难免有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可能。
本罪中的毁灭、伪造应当与刑法第307条第2款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中的毁灭、伪造具有相同的含义。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这里的毁灭是否包含隐匿的情形,而变造是否属于伪造的情况。对此,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变造证据属于伪造证据。第二种观点认为,隐匿证据的行为属于毁灭证据,但变造证据的行为不属于伪造证据。第三种观点认为,毁灭证据不包括隐匿证据,但伪造证据包括对原证据的部分伪造。如果从实质上解释毁灭与伪造行为,第一种观点应当受到支持。因为,使证据不能被司法机关发现的行为,与使证据从物理上灭失的行为,在性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对真正的证据进行加工从而改变证据价值的行为,也应认定为伪造证据。[8]5
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对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事实改变供述或辩解,或者作虚伪供述或辩解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证人,所以上述行为难以作为刑法第306条妨害作证罪的行为方式。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仍然可以作为本人刑事案件的证据。由于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事实改变以前所做出的供述或者辩解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妨碍了原来符合事实的供述、辩解的证据价值的出现,因此在本质上与毁灭证据没有什么不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06条的毁灭证据的行为。而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伪供述或辩解的行为实质上就是做出本来不存在的证据的行为,与伪造证据的行为没有区别,因此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06条的伪造证据的行为。
三、新增刑法第306条与第307条犯罪的关系
如上所述,在法条的关系上,刑法第306条与第307条是特别法条和一般法条的关系。相应地,第306条的犯罪与第307条的犯罪应当是特别犯与一般犯的关系,即第306条的犯罪是特别犯,第307条的犯罪是一般犯。本来,两罪除了主体方面的要素不同之外,其他的构成要件要素均应当相同。然而,由于两个条文之间在立法技术上的类型化水平较差,在条文表述和规定模式上存在很大不同,从而导致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关于毁灭、伪造证据的犯罪,两个法条之间对行为方式的表述不同。刑法第306条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客观行为方式的表述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另一种是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况。而第307条第2款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客观的行为方式仅表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一种情形。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学者们普遍认为,第306条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的第一种情况系指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自己直接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15]68而刑法第307条第2款中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也应当认为不限于帮助犯意义上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一种情况,当然包括了行为人单独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况。[8]6因此,在行为范围上不应当承认二者具有实质不同。
第二,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藏匿、隐避证人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藏匿、隐避证人的行为具有阻止证人作证的性质,因此,难以包括在刑法第306条的妨害作证的行为中。尽管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妨害作证罪规定了阻止证人作证的情形,但是不能适用第307条第1款的妨害作证罪。否则,就会导致适用法律的不统一,并导致刑法第306条作为特别犯丧失存在意义的结论。因为如果认为上述情形属于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阻止证人作证的情况,那么就会产生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也应当适用刑法第307条第1款的疑问,即没有必要规定刑法第306条中的妨害作证行为。由于藏匿、隐避证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具有防止证据出现的性质,(2)因此应当认定为第306条的毁灭证据的行为。
第三,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明知是他人伪造、变造的证据而使用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日本刑法第104条在规定了隐灭、伪造、变造证据罪后,本条后段又规定了使用伪造、变造的证据罪。[16]那么,能否说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关于处罚使用伪造、变造证据的行为的规定,这种行为在我国不受处罚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首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明知是他人伪造、变造的证据予以使用的行为,即使在我国刑法上其可罚性也已经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一旦把这些伪造、变造的证据向司法机关提供,其所具有的危害国家司法作用的危险性与其他妨害司法的犯罪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那么,究竟应当如何适用法律?应当说,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明知是他人伪造、变造的证据而使用的行为,在实质上无异于自己实施了制作根本不存在的证据或者对已经存在的证据进行改造以改变其证据价值的行为。换言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使用明知是他人伪造、变造的证据的,实际上就等价于自己实施了伪造、变造的行为,因此应当适用刑法第306条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造证据罪的处罚规定。在日本刑法上,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使用伪造、变造的证据不仅限于对搜查机关、法院适用,还包括对作为搜查机关对等的当事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适用的情况。[17]鉴于我国刑事诉讼上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被害人等的作用以及司法机关的职能,因此该罪行规定应当仅限于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适用的情况。当然,对使用明知是他人伪造、变造的证据的主体方面并没有限制,在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之外的其他人使用的情况下,应当适用刑法第307条第2款的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罪。
第四,在具有身份的人与不具有身份的人共同实施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这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唆使或者帮助其他人实施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况;第二种是他人唆使或者帮助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施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况;第三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他人共同实施毁灭、伪造证据的情况。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都只能按照作为身份犯的第306条的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处罚。只不过不同情况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构成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间接正犯,其他人系本罪的帮助犯,其与第307条第2款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想象竞合犯,仍应当以本罪的帮助犯处罚;在第二种情况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构成第306条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正犯,其他人构成本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在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构成本罪的正犯,其他人构成本罪的帮助犯。基于同样的考虑,在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其他人共同协商,由一方伪造、变造证据而另一方使用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均系第306条伪造证据罪的正犯,其他人则系本罪的帮助犯,其与第307条帮助伪造证据罪的正犯的想象竞合犯,即其他人仍应以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造证据罪的帮助犯处罚。只有如此,才能够符合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第五,第306条究竟是概括的一罪还是并合罪的问题。从第306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应当属于概括的一罪的情况,即本罪应当属于选择性罪名。然而,与此相对应的第307条则显然把妨害作证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作为实质上的数罪加以规定。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作为一般主体的行为人既实施妨害作证行为,又实施了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时,依照第307条的规定,应当构成并合罪,即应数罪并罚。然而,作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这一特殊主体的行为人实施上述两种行为时,则依照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只能以概括的一罪处罚。结果在一般犯时由于要数罪并罚,其处罚反而重于作为特别犯的第306条的犯罪,(3)从而难以体现第306条重处特殊主体犯罪的立法目的。立法上的这种缺陷有以下两种方式可以解决:一种是解释论的方法,即把第306条的犯罪理解为并合罪;另一种是立法论的方法,即期待在立法论上对第307条做出修改,像第306条一样把妨害作证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作为概括的一罪规定。然而,第一种方法显然难以成行,因为从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实际情况看,难以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解释为并合罪。而且,如果不改变刑法第307条的规定,当直接办案的司法工作人员为了追诉明知是无罪的人,或者为了不追诉明知是有罪的人,既实施了妨害作证行为,又实施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时,显然形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分别与徇私枉法罪的观念竞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究竟系以一个徇私枉法罪处罚还是以徇私枉法罪的同种数罪处罚?以徇私枉法罪的同种数罪处罚显然不合适,因为徇私枉法的行为毕竟只有一个,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然而,如果作为一个徇私枉法罪处罚,又可能会导致轻于以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数罪并罚的不合理现象。因此,解决第306条与第307条罪数的不协调问题,只能期待立法上对第307条做出修改了。
第六,第306条与第307条的犯罪形态问题。关于这类犯罪的犯罪形态,我国刑法学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这类犯罪是行为犯;[15]72第二种观点认为这类犯罪是结果犯,并强调按照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追究法律责任,认为不能仅在发现有引诱、帮助的行为或仅有伪证的后果而不确定该后果是否是在律师的引诱、帮助下造成的情况下便简单认定律师伪证罪成立;[18]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类犯罪应当属于危险犯,不要求产生已经妨害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的侵害结果,只要求具有妨害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的现实危险。[8]8按照我国刑法学的通说,所谓行为犯是指不需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就可以构成既遂的犯罪形态。[19]那么,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不仅不需要产生对国家司法作用的侵害性结果,而且由于危险犯也是结果犯的一种,[20]则构成本罪也不需要产生对国家司法作用的危险性,将使认定成立这类犯罪的时间过于提前。与此相反,如果按照第二种观点,构成本罪必须要求已经产生妨害国家司法作用的侵害结果,又会使本罪的构成过于迟延。因为根据刑法第306条第1款的规定,产生妨害了国家司法作用的实害后果应当属于本罪的情节加重犯的情形,即因其帮助行为导致案件审理中断、无法进行或者做出了不公正的审理结论等侵害结果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13]446因此,第二种观点显然也不符合立法的实际。构成本罪,既不需要已经产生对国家司法作用的侵害结果,也不能在行为尚未导致侵害国家司法作用的危险性时就认为已经构成本罪。换言之,要求行为已经导致侵害国家司法作用的危险性时才可以构成本罪的第三种观点应当得到支持。
第七,关于第306条、第307条第2款中情节严重的含义问题。质疑第306条的观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关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刑法第306条的规定是一旦构成即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刑法第307条规定必须是“情节严重”的,才构成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而言,构成本款行为如果情节严重的,要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21]然而,上述质疑难以成立,刑法用语具有相对化的可能,相同的用语在不同条文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譬如刑法学对于胁迫的理解就是如此。上述观点把刑法第307条第2款作为基本犯构成情节的情节严重与第306条作为加重情节的情节严重相提并论显然不妥当。
然而,这里是否意味着第307条第2款构成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条件比第306条第1款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成立条件高?其实也难以得出这种结论。尽管第306条的犯罪作为特别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对于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第306条因为具有两个量刑幅度,而第307条第2款只有一个量刑幅度,已经体现了比一般犯罪从重处罚的立法目的。因此,没有必要认为第307条第2款构成犯罪的条件应高于第306条犯罪的成立条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第307条第2款的“情节严重”。该条之所以规定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原因在于本条包含了民事诉讼(包括行政诉讼)中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我国刑法对妨害司法犯罪的规定显然遵从了区别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立法体例,刑法只处罚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不处罚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刑法第307条第2款正是为了限定民事诉讼中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行为的处罚范围,设置了情节严重的条件。然而,对于刑法第307条第2款而言,仍然要区别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情节严重”,即这里的情节严重对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而言其含义仍然具有相对化的可能。对于民事诉讼而言,情节严重可以理解为帮助毁灭、伪造重大案件的证据的、帮助毁灭重要证据的、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等等。对于刑事诉讼而言,完全可以理解为只要达到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毁灭、伪造证据的程度,即只要实施了毁灭、伪造证据行为,产生了对刑事司法作用的危险性结果时,就认为已经符合第307条的情节严重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刑法第307条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构成要件与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的成立条件作相同的理解。
注释:
(1)鉴于本罪的主体事实上主要涉及律师,所以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律师伪证罪。李群主:《论“律师伪证罪”》,《企业技术开发》,2008年第5期第85页。尽管本罪包括了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这种行为应当认为是伪证罪的教唆犯的实行行为化。但是,本罪中还包括了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因此把本罪概括为律师伪证罪并不周延。
(2)在日本刑法学上,没有争议的认为藏匿、隐避证人的行为是隐灭证据的行为。[日]平川宗信:《刑法各论》,有斐阁,1995年版,第543页。[日]藤木英雄:《刑法各论》,有斐阁,1976年版,第82页。
(3)看来,建议删除第306条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得出有利于实施毁灭、伪造证据、妨害作证行为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结果。
[1]秋实.律师无罪——张耀喜妨害作证案辩护纪实[J].中国律师,2000,(9):29.
[2]汪讯.妨害作证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J].法学杂志,2003,(3):73.
[3]左玉慧.“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之质疑[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23.
[4]陈红兵.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司法适用问题[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50.
[5]刘菁.取消律师伪证罪的原因探析[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2):57.
[6]“李庄案”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学术研讨会综述[TB/OL].(2010-01-04)[2010-06-16].http://www.law-thinker.com/new s.php?id=4079.
[7]张明楷.论妨害作证罪[J].人民检察,2007,(8):23.
[8]张明楷.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J].山东审判,2007,(1):9.
[9]陈兴良.辩护人妨害作证之引诱行为的研究——从张耀喜案切入[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5):164.
[10][日]内田文昭.刑法各论[M].第2版.东京:青林书院新社 ,1984 :654.
[11]斯库拉托夫,列别捷夫.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下)[M].黄道秀,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833.
[12]蔡军.律师伪证罪的立法问题解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0.
[13]黄太云,滕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与适用指南[M].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7:443.
[14]张建伟.关于刑事庭审中诱导性询问和证据证明力问题的一点思考[J].法学,1999,(11):33.
[15]田宏杰.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4):68.
[16]日本刑法典[M].张明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5.
[17][日]平川宗信.刑法各论[M].东京:有斐阁,1995:543-544.
[18]余莹莹,赵增田.律师伪证罪的关键词分析[J].法制与社会 ,2008,(23):100.
[19]李文燕,杨忠民.刑法学(修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13.
[20][日]齐藤信宰.刑法讲义总论(第3版)[M].东京:成文堂 ,2001 :96-97.
[21]谢望原,郝兴旺.刑法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56.
Consideration on the Crime of Destroying or Forging Evidence or In terfering with Testimony by Defenders or Law Agen ts
YANG Jin-biao
(Faculty of Law Chinese Peop 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
The essential basison w hich the defenders and law agents are punished in article 306 is that the state judicial action is facing at highly dangerous infringement of such behavio r as destructing o r fo rging the evidenceso r interfering in the testimony of such people.Becauseof the special role of the defendersand law agents in criminal p roceedings,such actions shall be given a heavier punishment.Therefore,there are no essential reasons to abolish such a crime.The substance of the seducing behavior liesat seducing thew itness to changing testimony o r perjuring against facts,but not at the specific way of seducing action,so even the inducing inquiry of some special types can also constitute such a cri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cle 306 and article 307 is special crime or generalone.The article 306 is the special one.The hiding or sheltering behavio rsof the w itnessof the defenderso r law agents belong to the action destructing evidences in article 306,and the emp loying behavio rs of fo rged or altered evidence knowingly of such peop le also belong to the action of forging evidences in the same article.
defenders;law agents;destroying or forging evidence;interfering w ith testimony
DF639
A
1672-0539(2011)01-082-08
2010-07-15
杨金彪(1969-),男,山东临沂人,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