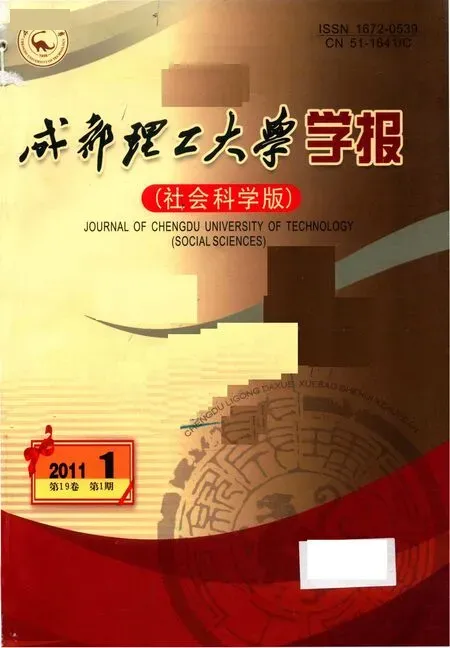《刑事诉讼法》中回避制度规定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2011-03-31丁彩彩
丁彩彩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刑事诉讼法》中回避制度规定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丁彩彩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回避制度的规定存在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实务中也出现异化现象。从立法层面来分析,可通过变更管辖权等方法拓宽回避适用对象的范围,通过明确法律条款的内涵来明确并增加法定回避事由;扩大回避申请权的主体范围,将该权利赋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 ,并将回避“要求”改为“申请”;同时增加回避制度的告知程序和保障条款;构建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以此将回避制度落实到实处。
刑事诉讼法;回避制度;回避对象;回避事由;申请主体;回避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在第28条至第31条当中规定了回避制度。但从条文上来看,仅仅4个条文就将回避这一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规定完毕,必然造成条文内容的抽象性、笼统性和模糊性,导致实务中该制度的实施困难,同时又缺乏对当事人权利的制度保障,使刑事回避制度形同虚设。如此种种,最终导致刑事回避制度设计的初衷——确保司法公正难以真正实现。下面笔者就从法律规定层面对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的立法缺陷做一下简要解析,同时提出进一步修改的建议,以期推动该制度在立法方面的进一步完善。
一、回避适用对象的范围狭窄
《刑事诉讼法》第28条和第31条将回避适用对象限定在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以及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
首先,我们看到,回避制度适用的这六种对象都是个人,而非机关;都是针对个体,而非整体。那么,如果涉及整个办案机关存在回避事由时,该如何处理?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8条有所规定,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对于法院整体回避,我们可以借由变更管辖制度予以解决,既避免了回避制度中所蕴含的对法院整体的不信任感,又不需要浪费司法资源另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设集体回避制度的规定,可谓两全其美。[1]
其次,对于辩护律师和诉讼代理人是否应该适用回避制度的问题,学者颇有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41条规定: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第1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以下简称《检察官法》)第20条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诸如此类的规定同样是回避制度适用的情形。笔者认为,这些本质上是执业限制的法律规定,其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回避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回避制度适用的目的在于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且对案件有处理权或者在案件重大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人排除至诉讼过程之外,而执业限制的对象与本案并无利害关系,对案件也没有处理权,在案件重大问题上也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仅仅是法律服务人员,只享有诉讼权利。第二,程序要求不同。回避制度的适用在程序上要求对方当事人申请,不申请则意味着可以参与案件审理,而执业限制是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参与案件审理,不需要申请等手续,如果违反即应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所经历的过程不同。回避适用的对象是先进入到诉讼过程中来,之后发现存在回避事由,再从诉讼过程之中脱身出去;而执业限制的对象自始至终就没有参与到诉讼进程中来,更谈不上从此进程中脱身了。所以,《律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中关于辩护律师和诉讼代理人执业限制的规定,并非意味着二者适用刑事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
再次,《刑事诉讼法》仅仅将回避制度仅仅适用于六种人,对于其他参与诉讼的人是否可能存在回避情形没有规定。我们注意到,勘验、检查人员在侦查阶段也可能参与到刑事诉讼进程中来,而且勘验、检查笔录是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因此,不具备侦查人员身份的受聘的专业技术人员若与当事人或者本案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也可能会对本案的勘验、检查活动以及后来作为证据的勘验、检查笔录产生不利影响。勘验和检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侦查活动,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勘验的对象是有关场所、物品、尸体,检查的对象是活人的身体,分别形成勘验笔录和检查笔录,因此,勘验人员和检查人员同样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人,不存在包容关系。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刑事诉讼法也应将勘验、检查人员规定于回避适用对象之中。[2]
二、法定回避事由规定得过于片面、模糊
《刑事诉讼法》第28条和第29条规定了5类回避事由,其有两大缺陷:一是规定的事由过少,不能涵盖所有情形;二是事由规定不明确,内涵模糊性太强,留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首先,第28条第一项“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中的“近亲属”与第四项“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中的“其他关系”是被包含与包含关系,为何还要将“亲属关系”单列于外呢?即便立法者内心有将“亲属关系”单列的合理理由,那么“亲属关系”该如何界定呢?《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给予了明确的解释,“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对于“近亲属”的解释是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至此,我们发现,三部基本法中对“近亲属”的规定是不同的,相比之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要小得多。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回避制度若干规定》)第一条对“近亲属”作了扩大解释,指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仅具有司法解释效力。
其次,回避事由中的“利害关系”“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这些法言法语该作何解释,在实务中实质上主要依赖于决定人员的自由心证,于是,决定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在无形中被扩大了。例如,“其他关系”是指哪些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校友关系等是否包括在内?法律并无相应的界定。并且,《回避制度若干规定》将回避事由中的“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限定为“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由此,法律解释对“其他关系”作了限制性解释,其仅仅指利害关系。但是,我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仅用“利害关系”来涵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各种关系是无法保证个案公正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应对这些模糊、抽象的概念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应根据我国的社会传统作出符合法理、道德和人情的解释。
再次,无论是相对于无因回避制度,还是他国的有因回避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回避事由都过于狭窄。我国所规定的回避事由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回避人员与本案相关,二是回避人员与当事人相关。但是,一个诉讼案件并非只有相关人员和当事人,还有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如果相关人员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为了维护司法公正,也应适用回避制度。《回避制度若干规定》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规定“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人员应该回避,但是对于和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有上述关系的情形,该司法解释并未涉及。
三、回避申请权的主体范围狭窄
《刑事诉讼法》第28条将回避申请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规定而言,我国所规定的申请权主体范围非常狭窄,以至于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权利行使的“困境”。在某些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已经死亡,法定代理人也就不存在,那么,由何者行使回避申请权?回避申请权不像被害人最后陈述权那样具有人身依附性,不可由他人代为行使,其作为一项诉讼权利,完全可以由当事人以外的参与人代为行使。因此,为了解决“困境”,我们应扩大回避申请权的主体范围,至少应将该权利赋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提升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力度,为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提供一个平台。
此外,法条中还存在一个立法技术上的不足,即规定有关人员存在回避情形时,除自行回避之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这里用的是“要求”回避,而非“申请”回避。“要求”回避意味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处于优势地位,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一旦提出回避要求,有关机关就应该给予肯定,相关人员就应该予以配合,退出诉讼程序。但是事实上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仅仅享有回避申请权,不享有回避决定权,况且这一申请权在一定程度上也难以获得有效的保障。“要求”回避是一种不规范的说法,不是严谨的法律术语,应当改用“申请”回避。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回避制度的规定中,一律用的是“申请”回避,体现了立法语言的严谨和规范。[3]
四、回避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救济制度尚不完善
回避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制度,理应在法典中作出详细规定,使得制度具体化、程序化,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制度的切实贯彻,达到设定该制度的初衷。然而,我国仅用《刑事诉讼法》第30条一个条文对该基本制度作了所谓的“具体规定”,其抽象性、概括性、片面性可见一斑。由此,我们也可以窥探到实务中回避制度“异化”的原因。
(一)我国缺乏回避制度中的告知程序
当事人并非都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相反,大部分人对回避制度一知半解,而我国对当事人了解回避相关信息的渠道没有任何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当事人缺乏对回避事由相关信息的了解渠道。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无论针对哪种情况申请回避,申请人都应当提出明确的理由,否则法庭当庭予以驳回,并且不得申请复议。而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9条之规定提出回避申请的,除了说明理由外,还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因此,在申请回避时,证明有关人员存在回避事由的举证责任是由申请人一方承担的。但是,在实务中,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相关人员是否存在回避事由没有有效的获知渠道,难以承担举证责任,回避申请权的行使几乎寸步难行。第二,申请人缺乏对于回避制度本身的了解渠道。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28条规定,审判长应该告知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审判过程中享有申请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回避的权利。试想一下,申请人此时方获知自己享有回避申请权,但是鉴于审判程序即将进行,已没有时间去查证该事由是否存在,那么申请人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除了申请人自动放弃回避申请权的行使这一消极途径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的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可以延期审理。尽管延期审理给申请人一定的时间去获取证明材料,但其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回避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存在较多不足
回避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存在较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第3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和检察长决定,而院长和检察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决定。那么,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的回避,应该由谁决定?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作任何规定。第二,相关人员的回避都是由所在机关内部作出决定,难免有“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嫌疑,对申请人而言也同样有失公正。第三,第30条规定申请人对于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而司法解释又规定申请复议是“当庭申请复议一次”。由此我们看到,申请复议是向作出决定的原机关申请,这样就再一次重蹈了“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嫌疑,难以保证案件获得公正审理。第四,申请回避之后应该做出决定的期限以及申请复议之后应该做出决定的期限,《刑事诉讼法》都未作具体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条规定,申请人不服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的,有权在收到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书后5日内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一次;而第27条又规定,决定机关对于复议申请,应该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此也作了一致的规定。但是,此处的规定仅仅涉及到复议期限,而对于申请回避时相应机关应在何时作出决定,除当庭驳回的情形之外(《刑事诉讼法解释》第29条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29条所列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5条延期审理。
(三)回避制度缺乏程序保障条款,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匮乏
有保障的权利才是一项真正的权利。《大清律
·刑律·诉讼》中“听讼回避”条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素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若罪有增建者,以故出入人罪论。”这里,对违反回避制度规定的人,法典规定要受笞刑,即违反法律规定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申请回避的权利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应的责任条款予以保障,这也是回避制度贯彻不力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在法典中设定法律责任追究条款,对违反回避制度的机关和人员进行制裁,切实保障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回避的权利,从而将回避制度落实到实处。违反回避制度的机关和人员应承担的制裁可以分为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实体性制裁指违法人员应该承担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等具体的涉及本人人身、财产等合法利益的制裁;而程序性制裁是指违法机关应该承担的在程序上的不利后果,目前在我国尚未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程序性制裁有两种,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二审程序中因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而发回重审的制度。他们同时认为,与规定在实体法中的实体性制裁有所不同,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和司法解释中的程序性制裁并不直接表现为对程序违法行为实施者个人的实体利益进行剥夺,而是表现为通过“剥夺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要求司法机关进行程序重作”等方式来制裁程序违法的。[4]但是,笔者认为,所谓“制裁”,应指对于违法机关和人员合法利益的剥夺,如人身自由、财产利益,等等。对于非法利益的剥夺并不应该被认定为制裁,因为剥夺非法利益之后,违法机关和人员是恢复到未采取违法行为之时的状态即“恢复原状”,其并没有遭受到任何合法利益的“损失”,何来“制裁”之说?因此,“制裁”之谓细细探究有失偏颇。笔者建议,可将“程序性制裁”改为“程序性规制”或者改为其他不会产生歧义的称谓。但是此处程序性制裁所包含的精神我们应该予以借鉴。若相关机关和人员违反了回避制度,除了承担实体责任之外,还应该承担程序上的不利后果。《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0条规定,因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8条或者第29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而回避的检察人员,在回避决定作出以前所取得的证据和进行的诉讼行为是否有效,由检察委员会或者检察长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该条虽涉及“制裁”,但是应该回避人员回避之前所取得的证据和诉讼行为的效力已处于不确定状态,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这对于相关机关和人员也是一种不利的程序后果。对于侦查人员,《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作了一致的规定。对于审判人员违反回避制度,《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未作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不像侦查活动那样具有取证的及时性和不可逆性,将违反回避制度所进行的审判活动归于无效,重新审判并不会对查明案件事实带来不利影响,而且鉴于二审程序中因一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包括违反回避制度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的制度存在,我们可以以此为参考,将一审程序中法院违反回避制度而进行的诉讼行为归于无效,重新审判,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5]
五、对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回避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使得实务中的回避制度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回避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使回避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首先,可通过《刑事诉讼法》中的变更管辖制度解决法院的整体回避问题。对于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整体上的回避,笔者认为,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变更管辖制度来解决,但其前提是完善我国的管辖制度,将立案管辖、侦查管辖以及起诉管辖予以全面的规定,并且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与回避制度相辅相成,解决实务中出现的各种疑难问题。此外,我们看到,《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已经将“勘验人”规定为回避对象。尽管《回避制度若干规定》已经将“勘验人员”纳入回避对象之中,但是,这只是一种司法解释,而不是法律。并且,上述法律和解释均未规定回避制度也适用于检查人员。因此,为了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全面性,《刑事诉讼法》应将勘验、检查人员规定于回避适用对象之中。此外,回避制度在法律中只涉及到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对于执行阶段是否有回避制度的适用余地,没有任何规定。执行是将法院的裁判付诸实施的过程,只有执行顺利完成,前面所有的诉讼行为才有真正的意义。若执行人员与本案或者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有失公正的现象,阻碍判决的完全实现。因此,执行人员也应纳入回避对象之列。[6]
其次,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对“近亲属”一词的具体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将其范围予以适当扩大,这既符合我国人情社会对其内容的理解,又可保证法律适用的严格性和统一性,以达到回避制度适用的初衷。例如,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的做法。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对“亲属关系”直接做了详细的限定,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亲等内之血亲、五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采用亲等计算法,这沿袭了我国历史上的家族、族亲观念,适应了我国是人情社会的历史传统,有利于保障公平之裁判。对于“利害关系”的界定,我们同样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对于亲属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给予了相对明确的规定,如与当事人订有婚约者、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者,等等。至于其《刑事诉讼法》第18条所规定的“足认其执行职务有偏颇之虞者”,是一种抽象性的“兜底”规定,赋予了当事人广泛的申请回避的权利,在接下来的程序中台湾地区更是设定了相应的限制措施,使得该规定在程序中予以具体化,可操作性更强。[7]
此外,对于相关人员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存在“可疑关系”是否应该适用回避制度的问题,笔者持肯定态度。在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刑事案件中,法定代理人几乎可以行使当事人全部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与案件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因此,相关人员与法定代理人存在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在本质上和与当事人存在这种关系并没有太大差异。所以,回避制度的适用应该扩展至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是中立的,没有自己单独的立场,其参与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方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仅仅对案件事实负责,协助相关人员查明事实,解决争议。虽然后者在诉讼中不存在利益倾向,但是若相关人员与上述人员存在“可疑关系”,上述人员就可能具备了同司法工作人员相同的利益倾向,本质上仍可能威胁到司法公正。因此,相关人员与诉讼参与人存在“可疑关系”,同样有必要适用回避制度。
再次,针对回避制度中告知程序的缺乏,笔者建议在诉讼程序中设立公告制度,例如在审判前对相关人员的具体信息予以公布,使得申请人明确从哪些方面去查找回避事由存在的证明材料,进而使回避申请权落到实处。与此同时,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享有的权利少,并且缺乏有效的保障。因此,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回避事由“确实存在”,申请人很难实现。在我国目前无法引进无因回避制度的现实情况下,只能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来实现回避制度的真正贯彻。在申请回避时,申请人只需提供材料证明或者说明“可能存在”回避事由即可,之后相关人员自己提供材料证明自己不存在回避事由,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申请人滥用申请权,另一方面由相关人员承担证明自己不存在回避事由的责任,又可以避免申请人的申请权有名无实,保障回避制度的真正实行。同时,在公诉案件中,我们可以将回避告知程序提前至送达起诉书之时,即在送达起诉书之时就告知申请人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以便在审判前给予申请人足够的时间了解相关信息确定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在自诉案件中,原告人在起诉之时,法院工作人员即应告知其享有回避申请权,而被告人则在接收起诉书时应被告知其也享有回避申请权。鉴于申请人在审判之前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查证工作,即便当事人在审判之时提出回避申请法院决定延期审理也能很快做出裁定,不需要再花费太多时间进行查证,这样即可避免在审判时因当场申请回避需要给予申请人查证时间而导致延期审理,进而造成诉讼过分拖延,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发生。为了保障上述告知义务的履行,必要的问责机制是不可缺少的。在刑事诉讼法中应设定具体的法律制裁条款,规定若相关人员违反回避告知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以法律责任条款确保回避告知义务的履行。
在具体操作程序方面,笔者建议,对于审判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的回避问题,应交由上级法院和检察院分别作出决定。同时,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尚未建立从而无法将回避决定权全部交由中立性法院统一行使的情况下,可暂时将这一决定权移交给本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来行使,虽其仍未摆脱内部行政裁决有可能偏袒己方的嫌疑,但至少由上一级别的机关行使比由本机关行使决定权更有利于摆脱应该回避人员的个人影响,保证案件审理的相对公正,随着我国立法制度的逐步完善,我们再将这一权利交由中立机关统一行使,以保证回避制度的真正贯彻。而对于申请人不服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笔者认为其应该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而非原机关,进而由上级机关对原机关的决定进行审查,作出正确的决定。对于回避决定以及复议决定的做出过程,笔者建议,应该采用听证程序进行。听证程序使得控辩双方均参与到回避程序之中,决定机关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中立地作出决定。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控辩双方对诉讼结果的可接受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上诉和抗诉行为的发生,进而节约司法资源。此外,为了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结和法律的统一适用,我们应该在回避制度中设定统一的期限条款,以防因回避问题迟迟未解决而造成诉讼拖延进而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形发生。
在回避制度的程序保障方面,我们应在法典中设定法律责任追究条款,对违反回避制度的机关和人员进行制裁,尤其是要对违法行为规定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切实保障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回避的权利,从而将回避制度落到实处。
[1]刘加良,聂广亮.关于刑事回避制度的改进探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17(3):66-69.
[2]贾有治,谷志平.论我国刑事回避制度之完善[J].湖北社会科学,2004(5):78-79.
[3]汪吉友,崔康宁.《刑事诉讼法》回避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建议[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0(3):128-132.
[4]李奋飞.失灵——中国刑事程序的当代命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5]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江雁飞、徐彬.刑事回避制度研究——以回避人员为切入点[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4):333-336.
[7]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The Legislative Defectsand Improvements of Challenge System in the Crim inal Procedure Law
D ING Cai-cai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 t p resent,the rules of the Challenge System in ourCrim inal Procedure L aware general and fuzzy to a certain degree,and dissimilation also occurs in the p ractice.From the aspectof legislation,we can broaden the app lication of theobject of Challenge by changing jurisdiction,definitude and increase the legal causesof Challenge by defining the intension of the articlesof law;we should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body of app lication for Challenge,endow the defenders and the litigation rep resentatives w ith this right,and change the“request”to“apply”in the articles;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increase the no tification p rocedure and the p rotection clauses,and construct a law ful responsibility tracing system w ith respect to violating the Challenge System in o rder to carry out the system.
crim inal procedural law;challenge system;object of challenge;cause of challenge;body of app lication;p rocedure of challenge
DF73
A
1672-0539(2011)01-076-06
2010-10-12
丁彩彩(1987-),女,山东青岛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