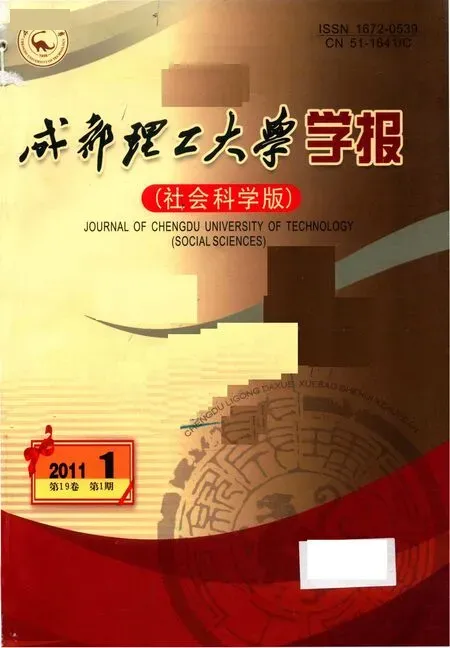宋代民间助学述论
2011-03-31许瑶丽
许瑶丽
(成都理工大学 《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成都 610059)
宋代民间助学述论
许瑶丽
(成都理工大学 《学报(社科版)》编辑部,成都 610059)
宋代教育发达,但其教育投入却相当有限,因此两宋文化的极盛很大程度上实有赖于民间对教育的支持与资助。这种资助既有面向学校的赡学与建学,也有面向举子个人的捐助赴试费用。总体上看,宋代民间助学表现为典型的“官倡民助”模式,且捐助风气南宋浓于北宋,捐助方式以产业捐助为主,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宋代民间助学对今天的启示是民间助学的热情需要官方调动和引导,助学的方式应以产业助学为主,以保证助学的长期、持续性,而且营造良好的民间助学氛围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宋代;民间助学;产业助学;贡士庄;官倡民助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高峰时期,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也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然而要论国力的强盛,宋似不如唐,然而宋朝以“积贫积弱”之国力却能造就如此空前绝后的灿烂文化,其重要原因在于宋历代皆重文治,极其关注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这极大地调动了整个社会对文教的追趋和崇尚。尽管宋朝对教育的投入较前朝有所增加,然而比照其有限的、非持续的教育财政政策与宋代教育文化的巨大成就,笔者认为仅仅把这种成就归功于政府“兴文重士”答案似乎并不完整,故本文拟探讨宋代文教之盛的另一个动因——宋代民间助学。
一、宋代教育规模庞大而教育经费无常制
宋代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兴学始于庆历新政时期,庆历二年下诏各地兴学,建立地方官学,中央除国子监学外,设立太学,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然而由于新政推行不久即告废罢,因此,不但各地方官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中央的太学也常常面临办学金费短缺的问题。赵抃在嘉二年前后所上奏折中提到“:窃见京师太学殆将废弛,在庆历初,朝廷拨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入学充用,是时供生员二百人。后来陈旭判监,赡养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勾已逾三岁,才赡及掌事,谕义孤寒学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以来,一切停罢,令自供给。”(1)此时北宋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主持太学,也不得不面对经费拮据的状况,以太学之地位也仅能提供三二十人公费学习,可见北宋前中期教育投入的非常规性。事实上,地方官学的情况也不乐观,苏轼在元四年所上书状中写道“:本州学见管生员二百余人,及入学参假之流日益不已。盖见朝廷尊用儒术,更定贡举条法,渐复祖宗之旧,人人慕义,学者日众,若学粮不继,使至者无归,稍稍引去,甚非朝廷乐育之意。”(2)州学作为仅次于国子监、太学的大学校,其见管的生员也不过二百余人,还要面临学粮不继的困境。他如滕甫所治之郓地,“郡学生食不给”(3)的情况则是普遍存在的。
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再次兴学,“命诸道各设常产以资永业”,行之十余年后敕命进行教育普查,承担此事的葛胜仲在《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廱札子》中报告的情况为:“总天下二十四路教养大小学生,以人计之凡一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二,学舍以楹计之凡九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学钱以缗计之,岁所入凡三百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二,所用凡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七百八十七;学粮以斛计之,岁所入凡六十四万二百九十一,所用凡三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四;学田以顷计之,凡一十万五千九百九十;房廊以楹计之,凡一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四,既以逐州县离为析数,又以天下合为总数,凡二十有五册,而中都两学之数不与焉。恭惟陛下以有为之资,灼见治本,不爱数百万之费,使隶学士之版者,皆不家食,所以加恵学者至深至厚。”(4)也就是说,按政和年间的情况,全国官学,除京城的国子监与太学之外,共有在校学生167622人(含大小学生),而这些在籍的学生可以享受免费食宿。然而据资料显示,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1],以一亿的人口基数,只有十六万多人在学,其受教育比例约为1.7∶1000,这个比例明显偏低,早在北宋真宗朝,每次参加礼部省试的考生就达数万人,此后大体保持在这种规模上,因此,实际受教育的人群远超葛胜仲所罗列之数,而这些学籍之外的生徒,他们的教育支出显然并不在政府承担范围内。
及至南宋,由于战乱及偏安一隅等原因,教育支出更加艰难,地方官学则主要依赖学田租维持。然而学田租又常常面临诸多贪渎、侵占(5),所以实际情况并不良好。南宋地方学校的真实的情况是有些地方有学无田,如朱熹所说“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有些地方虽有学田租等收入,但却入不敷出,如舒文靖所在的歙中,大抵学校寥落,“学粮无几,日给仅四十辈。岁中又以匮告。”(6)其窘迫之情状令人心酸。而这仅指学校的日常支出而言,如果想要修完校舍,则又更加艰难。南宋地方官学的兴废往往系于地方官是否留意文教,朱熹所言之崇安县学的情况:“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芜废,率常更十数年乃一闻弦诵之声,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这实际代表了南宋地方官学的普遍遭遇,所以南宋欧阳守道有叹曰:“国家能诏郡邑皆立学,不能使为郡邑者皆留意于学”(7)。
通观两宋时期的教育财政,很难找到长期持续执行的政策,一般来说,宋代官方不管以何种形式向学校拨款,大多是一次性或不固定的。只有国子监和太学等中央官学才在学田、房廊等固定资产的收人之外,又享有国家较稳定的年度财政拨款支持,用于养士。除了太学之外,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州郡,也对府州学校提供固定的财政拨款。然而就其稳定性而言,是远不及中央官学的[2]。各级学校常常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这种状况与两宋文化之兴盛发达实难匹配,因此,宋代支撑其庞大教育规模和人才产出的显然并不仅只是朝廷的教育支出,而是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助学力量。
二、宋代民间助学述略
宋代民间助学的情况,笔者拟从两大方面来描述:一是针对学校的资助,一是针对科举考试的资助。
(一)宋代对学校的民间资助
王玉功在其硕士论文《宋朝助学活动研究》中,把宋代民间助学活动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资助学费、提供食宿上的帮助;提供学习用具;提供其它生活资助及供给考试费用四个方面[3]。其中前三点均是宋代民间助学活动中的细小方面,第四点笔者拟在另一部分讨论。实际上,宋代民间助学更重要的一部分活动是对学校的直接资助,包括对其学田的建立扩充和对校舍的修建完缮。
1.对学田的建立和扩充
正如前文所述,中央官学通常能得到较稳定的经费支持,而地方官学则多有赖于守治之人对文教留意与否。范仲淹是宋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相当重视教育,所到之处,往往兴学倡教,此外,他还通过建立义庄的形式,对族人进行赡济,其中就包括了族人的教育资助。由于宋代地方学校学田的划拨与管理并没有一定之规,因此其设立与否及丰欠情况也大相径庭。而这种差异主要根源于地方行政长官对学政是否重视。就笔者所搜集的材料来看,民间对学校的经费资助大多是在地方官员的主持倡导之下展开的。如南宋建安县学的学田就是其地方长官清源留侯毕力经营两年,“得在官之田若干,岁租仅百石,悉举而归之学,于是学之有田,侯实始之。”(8)而东莞县学之所以能在嘉熙年间获得充裕的经费,也是源于温陵许公身先士卒的发动与组织,他不但主持修缮了校舍殿庑,而且将充没之田与金银悉归于学。在他的带动下,“绣衣吴公旗素敬公,慨然弗靳,继粟,益裕以其钱,即直庐而阁其上,轮奂雄峙,博収图籍,庋之万籖森架,士得读所未见。餫使陈公畴亦捐三十万,相厥役又不足,则鸠节用之,赢资其成,成而虞其坏,储十万为后日补饬费”(9)
南宋书院教育发达,除极少数书院如岳鹿书院等能获得政府的经费资助外,大部分书院的经费都来自学生的学费和民间的资助。比如南宋的石峡书院,初为方逢辰讲学之所,“东南之士多裹粮从之,教虽勤,未及于养”,其子捐田二顷有畸,以供学廪,后佥事吴公下令修完书院房舍,于是“士之裕于家者乐以田入,凡若干畝,春秋之祀、廪膳之资、修葺之费,胥此焉出。”(10)在官绅的带动下,士人对民办书院的资助热情不压于对官学的资助。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时,合州少府在祠堂旁边建养心堂,以馆学徒,实则为书院,且“又捐钱千万以广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诸生之廪稍亦云备矣。”(11)合州地方官为养心堂所捐之钱被换购为学田,成为一项可以长期依赖的学校经费来源。此外,在民间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纯慈善性质的书院,如南宋的青云峰书院,这是由一群邹姓士绅自建的一个书院,他们不仅建屋于青云峰下“以为诸子藏修游息之所”,而且“买田其中,收其岁入,专以给游学之书费”(12),这种纯慈善形式的书院相信在宋代为数亦不少。
2.对校舍的修建完缮
宋朝前后三百余年,其间学校岁久或敝,敝又图新,则其修建、完缮校舍殿庑的经费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在宋代教育财政支出里,对地方官学的教学设施的更新完缮全无出处,因此,宋代地方官学的久敝图新往往有赖于地方士绅民众的捐助。北宋吉州州学的建立就是在主事官李宽的主持下进行的,“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庆历四年(1044年)学校建成后,“来学者常三百余人。”[4]这种士民积极出钱出力建学的情况很多,如抚州州学的在庆元二年的修完就是在教官胡元衡的牵头努力下,加上“太守陈侯研首捐千缗,常平使者王君容及后守曽侯楷各助十之三,漕宪继之,总钱又百三十万”(13)才得以完成。广信郡学的重修则是信州长官陶崇叹学舍敝陋,首先捐钱三百万,其后通判陈梦建捐钱六十万,转运使丘寿迈也捐钱十万,“知上饶陶木、知铅山史夏卿及诸生有请于教授,亦各有助。越明年四月,天台陈侯章自毗陵易守,下车首以未毕工为念,复助钱二十万”(14)在上述官员前后相继的捐助之下,广信郡学修完一新。类似的例子还有通泉县(今四川射洪县)重修县学,由资中人杨季穆牵头,并出钱二百万助之,“乡之士民合三百万继之,自大成殿之北为讲堂,一斋庐八,南为大门,一腋门二,文明楼一,东为里贤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绘象凡若干人,西为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吕成公凡七人。”(15)而夔州州学的重建则是一大批士绅历时两年、合力促成,其建筑规模和成效也是众多捐建学校中较为突出的。魏了翁载其事云:“庐陵李侯镇夔之明年,大修学官成,以书抵某,曰:‘夔故有学,自淳煕之季,帅守某侯某尝撤而新之,仅歷三纪,蛊坏弗治,今军器监丁侯黼与转运判官王君观之,尝议更葺,且病其门术弗正也,为审端焉,各捐钱贰千万,市材于恭、涪、黔,市竹于云安、大宁,既赋丈鸠功,会丁侯召去,余实来,乃与王君卒其事,各增钱千万。’始嘉定十六年之六月,讫宝庆元年之五月,礼殿、讲堂、斋馆、门序次第一新,而云章有阁,从祀有象,先贤有祠,文会有所,直宿有舍。学故有李氏五桂楼,今复建于东,偏祠六君子其上以至庖湢管库、黝垩陶甓,率视旧加隆。役成,帅士者修舍菜之礼,余又念堂曰:明伦而无以训迪之也,乃摘六经语孟,切于伦理者凡八条,大书深刻而壁置之。”(16)参与者或捐钱,或助力,对夔州学校的修复可谓不遗余力。
(二)对科举考试的资助
科举取士制度在两宋虽然经历了一些变革和争议,但其持续性和公平性却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学而优则仕”在宋代才真正成为社会通识,学校也多以学生考中进士为荣,诚如周必大所言:“本朝开设学校,复帝王之盛,虽硕儒名卿,布于中外,而士之月书季考,惟在举业。”(17)此言虽意在针砭,但却道出了两宋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多在科举。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科举考试规模可谓空前绝后,据《宋登科记考》统计,宋代科举登科人数为历朝最多,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五倍,元代的近三十倍,明清两代的三至四倍。通常情况下,参加科举省试的人数每次皆达数万人,而这些举子往往来自全国各地,每逢大比之岁,纷纷从家乡赶往京城,往来的盘费高昂,非一般人家所能承担,加上举子往往数举不中,因而反复奔波在赶考路上,所费更是无数。南宋欧阳守道谓:“科举之为士病也,岂不甚哉?盖不惟工文患得之累其心也,文可以得矣,而贫无资者常厄于就试之费。礼部国子监学在京师,四方之士有不远数千里试焉。近且俭者,旅费不下三万,不能俭者不论,远者或倍,或再倍也。士十七八无常产,居家养亲,不给旦夕,而使茫然远行,售文于一试。试礼部得官犹可言也,试国子监学补诸生,释褐未可期,道涂往来滋数矣。有亲在堂,朝夕侍养,子于此时移甘旨之资为已旅费,及坐而食于斋,而白云之日,举目天末,不知我则举匕而亲亦已饭乎否也?”(18)此外,南宋在乡试之外,还可补试太学,一般学子认为在太学就读,有利于了解最新科场讯息,增加考中的机率,所以大多愿意参加太学补生的考试。而这种远赴京城的长途奔走也将产生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不用说参加太学补试前,举子还需到地方长官那里去申请待补公据,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欧阳守道有云:“予尝见士有持据归,计费至万钱”(19),又谓“四方望京师远者数千百里,庐陵非甚远,犹千七百里,每一往返费日盖远两月矣,至而留焉,有应试之费日,有谒报之费日,有游宴之费日,应试强于师者也,谒报游宴强于友者也,三费日之外,澄心静念以亲书巻者无几。”(20)留驻太学期间的各种应试、谒报、游宴之费更是铺天盖地,令一般学子难以承受。而翻检宋代登科人仕履,宋代出身寒微的士人也是空前的多,这一方面有赖于宋代不问家世、公平取士的科举政策,另一方面宋代资助举子赶考的民间慈善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阳达博士对宋代科举义约现象的考察,揭示了义约作为宋代科举考试中为帮助贫寒士子解决应试盘缠而结成的民间经济互助组织,同时兼有切磋举业的作用。然而义约作为临时性的组织,其对举子的资助有限,且不具有长效性。
事实上,在宋代,尤其是南宋,“贡士庄”,亦称“贡士库”更多地承担起了为进京赶考、赴京求学者提供盘缠的责任,而且其存在较为普遍,可以说是宋代贫寒举子得以参加科举省试的主要资助力量。金苏、毛晓阳研究指出,宋代见诸载籍的“贡士庄”有31处之多,而大量同类专设考试经费已经长久地隐没于历史舞台的大幕之后,也就是说在宋代这种专门为举子提供赴试盘缠资助的机构在宋代是大量存在的,尤其是在南宋最为突出。这种半官半私(民间)性质的助学机构实际具备了教育公益基金的基本属性,它们通常由官员利用财政拨款或教育田产、籍没田产以及士绅的捐款来设立,并由学校、官衙或士绅来管理,并有详细的经费管理和发放章程,设置较为完善。[5]如果说宋代的科举取士及封弥誊录制奠立了“取士不问家世”的世风,那么“贡士庄”的存在与运作则是社会对于“取士不问家世”最强有力的认同与支持。进士庄使得部分贫寒士子不误升进,为促进宋代社会阶层的升降变迁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宋代民间助学的特点
(一)“官倡民助”是其主要模式
诚如王玉功硕士所论,宋代参与到民间助学活动中的群体包括了普通民众、出家僧尼、道士、学校教师、私学塾师、社会上层人士(乡绅、富户)等[3],可以说宋代民间对于教育的资助是全民参与的,而且这种全民参与往往具有“官倡民助”的特点,其中民间士绅是资助的中坚力量。北宋末的邹浩在其《衡岳寺大殿记》一文中记载:“余初入湖湘,闻耒阳士李修弟兄勇先甲族,出钱以完学舍,分田以裕学粮,致一邑之士,惟徳行道艺之知,而无他营。”(21)像李修兄弟修学舍、扩充学粮田的义举实是宋代民间助学中士绅积极参与的代表。直至元朝初期,由宋入元的乡国名士唐骏发仍然继承着宋人乐教助教的优良传统,用十年之久的时间为修复学校、完善学校而持续努力(22),显示了宋代民间助学风气的深厚绵长。
宋代这种“官倡民助”的助学模式,不仅有很好的规模效应,而且容易形成全民助学的良好社会风气。例如南安六斋的重建,系由南安守官冯特卿首先“捐钱廿万,继之以粟”,然后永嘉陈公、畏公也别捐钱二十万,三山郑公性之助十万,而徐鹿卿“亦稍出俸廪以佐费”(23),南安六斋的重建正是在地方官的倡导及身体力行之下,士绅鼎力相助而成之。永嘉陈公、畏公在捐助时就称:“此宣风化事也……其可无助?”这些士绅在捐助的时候已清楚地认识到捐资助学良好的社会效应,因此乐于助之。前文所举资助学校的数例也多属于“官倡民助”的类型。朱熹晚年讲学的考亭书院,因为得到理宗的表彰,所以毋逢辰始任地方官便开始修复书院,并“捐田为倡,郭君适自北来,议以克协,诸名贤之冑与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为田五百亩有竒,供祀之余,则以给师弟子之廪膳,名曰‘义学田’。”(24)这种由上至下发起的助学方式既有利于汇聚大笔的助学资金,又能起到“上行下效”、集体响应的效果。
(二)民间助学风气南宋胜于北宋
宋代民间助学,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主要集中在南宋,这与金苏、毛晓阳所论之“目前所见宋代的贡士庄基本都集中在南宋时期,尤其以南宋宁宗、理宗两朝为最多。”[5]情况相似,这一方面是由于南宋后期思想文化的革新与政治环境的清明,为南宋贡士庄的普遍设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南宋建学兴学的传统更盛,南宋欧阳守道在《潭州湘阴县学记》中指出:“今有地百里,无不立学如赵侯之为。”(25)也就是说在南宋方圆百里必定会设立一所学校,而这种立学并不一定是官学,很多可能是民间的自主办学。正是这种学校的普遍设立,使得民间助学有了更浓厚于北宋的氛围。当然,北宋民间助学一则由于时代的原因在机制和形式上还不完善,二则北宋民间助学多临时、个人性质,这可以从诸多文人赠序中看出,对进士考试的资助多为个人临时之举,因此未如南宋贡士庄体制之完善与影响之大。
(三)助学方式多为产业助学。
宋代民间助学形式除直接的捐赠金银外,更多地是采用捐田产等可长期产出助学经费的形式,即使捐金,也多用以买田赡学。前文所举资助学校之例多属此类。诚如南宋一邹姓乡绅,在捐钱捐田助学的时候就谆谆面谕,称“:剏邸宇掠,僦金不若菑畬之安且久”(26)邹侯深刻地认识到,捐助金钱是一次性的,用完即完,而如果捐助的是田产,则可长期、持续地获得地租收入,成为学校的一项长期收入。此外,实现对学校的持续、长效资助,在宋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刻书出版。南宋成都学一度书籍匮乏,正好金州帅节使王公送五百贯赡学,其中的三百贯就用于刻板“,并韩文并行,丰其本息,以给膳养不足之用”(27)。这一做法与苏轼元中奏请赐杭州州学印板的目的是一样的,印板既能给学校提供基本用书,而且还可将印卖书籍所赚的钱用于赡学。
(四)助学风气南方优于北方
通观宋代登科人籍贯不难发现,总体上,南方中举人数多于北方,这一方面由于南宋偏安江南,客观上促成了这一数据,但这种差异实则也反映了宋代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与宋代民间助学的地域差异相类似。
同样是官学,不同地方的官学其境遇是大相径庭的。南宋广信郡学在陶崇的主持扩充下,焕然一新,“规模大略拟国学焉”,而且广信郡学还拥有众多的学田,“乾道三年知州事赵师严拨下乾庄,乾道六年知州事洪遵又以灵溪庄赡学,有翰林学士洪迈记。绍煕五年知州事石画问又以玉山县灵湖、南潭两庄赡学,旧有灵溪、河溪一十四处,岁入钱一千三百余贯文,知州事赵汝谐以其地非通行之地,奏罢之。未几,知州事秀翔续以上饶县东门外官田入学,淳煕五年提刑高公泗以贵溪县桂镐庄入学,有省札石刻。淳煕十二年知州事郑汝谐再拨下新收庄,嘉泰二年知州事何润再拨下青岩太平庄,绍定元年知州事陈章再拨下宴望庄,五年知州事吴旗再拨下黄柏庄,六年知州事王伯大再拨下万祥、板桥两庄,淳三年提刑王瓒以费家田牒学,承买七年,知州事章铸拨下永丰县田及玉虹桥屋业并胡徳权田产入学,为小学庄,并有额在籍贡士庄。”(28)历届官员接连拨下的赡学之田令到这一地区的学子广受惠泽,其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嘉熙乡举、学校之得人最盛,南宫奏名登第者尤多于昔。”人才辈出与学校受重视程度、经费的丰裕程度是紧密相关的。而至于一些偏僻小邑,如分水县学“赡学田仅二十五亩,东北偏池六十亩,岁以莲芡易粒才数石,人日给二缶,养生徒不能十人。”(29)又如安徽歙县县学,舒文靖担任该县学教授时谓“:大抵歙中学校寥落,非吾乡比,学粮无几日给,仅四十辈。岁中又以匮告,乡来处学皆苟二餐而去,荡然不修。”(30)学校不但学粮单乏,而且学风也很差,可以说与上述广信郡学的情况适成对比。
总体上看,宋代民间助学南方盛于北方,就南方地区而言,江浙、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民间助学风气最为浓厚,以“贡士庄”为例,上述四地就占到90%。这一现象充分说明教育的兴盛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参与,即使是在同一政策指导之下,各地重教兴教的差异仍然很大,其关键在于地方官对教育的重视与否。
四、结语:宋代民间助学对于当下的启示
前文对于宋代民间助学情况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略的图景,宋代民间助学风气的浓厚不仅源于朝廷“抑武文”的大政方针,而且与宋代公平的取士环境紧密相关。从宋代有限的教育财政投入来看,两宋文化的极盛实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间对教育的支持与资助。这种资助既有面向学校的赡学与建学,也有面向举子个人的捐助赴试费用。总体上看,宋代民间助学表现为典型的“官倡民助”模式,且南宋风气浓于北宋,捐助方式以产业捐助这主,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宋代民间助学对于今天的启示,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民间助学助教的热情并非自发的,需要政府或官方加以调动和引导,并引入合理的管理模式,以期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第二,民间助学的形式,今人多采用直接捐赠现金的方式。然而,一方面现金管理与运作易出现贪渎的现象;另一方面现金的价值再生能力不强。因此借鉴宋人以产业助学的方式,可以很好的规避上述弊病。
第三,民间助学风气的浓淡其实是社会风气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人才的培养与产出也是大有影响的,因此民间助学的行为与宣传活动应该并行,让捐资助学成为人人羡慕的义举。
注释:
(1)参见赵抃《清献集》卷八《奏状乞给还太学田土房缗 》(七月十一日)。
(2)参见苏轼《东坡全集》巻五十六宋蘇轼撰奏议一十首《乞赐州学书板状》。
(3)参见《东坡全集》巻八十九《故龙图阁学士滕公(甫,元发)墓志铭》。
(4)参见葛胜仲《丹阳集》卷一《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廱札子》。
(5)参见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巻四十六《上傅寺丞论学粮》。
(6)参见舒文靖《舒文靖集》卷上《与王大卿》。
(7)参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七《潭州湘阴县学记》。
(8)参见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十六《建安县(今福建建瓯市)学田记》。
(9)参见李昴英《文溪集》卷一《东莞县学经史阁记》。
(10)参见方逢辰《蛟峰文集》外集卷三《石峡书院增田记》。
(11)参见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十四《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
(12)参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六《青云峰书院记》。
(13)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抚州学记》。
(14)参见赵蕃(1143-1229)《干道稿__章泉稿》卷五《重修广信郡学记》。
(15)参见魏了翁《鹤山集》卷五十《通泉县(今四川射洪县)重修学记》。
(16)参见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十七《夔州重建州学记》。
(17)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广昌县学记》。
(18)参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二《送刘季清赴补序》。
(19)参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请待补公据籍序》。
(20)参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八《送刘雷震入太学序》。
(21)参见邹浩《道乡集》巻二十六《衡岳寺大殿记》。
(22)参见《方逢辰》《蛟峰文集》卷五《常州路重修儒学记》。
(23)参见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重建六斋记》。
(24)参见熊禾《勿轩集》巻二《考亭书院(朱熹晚年讲学之地)记》。
(25)参见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十七《潭州湘阴县学记》。
(26)参见许应龙(嘉定进士)《东涧集》卷十三《学田跋》。
(27)参见李石《方舟集》卷十三《跋王金州送赡学钱书》。
(28)参见赵蕃(1143-1229)《乾道稿__章泉稿》卷五《重修广信郡学记》。
(29)参见何梦桂《潜斋集》卷八《分水县学田记》。
(30)参见舒文靖《舒文靖集》卷上《与王大卿》。
[1]中国各朝人口数量:西汉仅六千万人[EBOL].(2009-03-07)[2010-09-28].http://hi.baidu.com/%BB%B3%C8%CA%CC%C3%D6%F7/blog/item/03623f1040b12a09203f2e78.htm l.
[2]潘天舒.两宋教育财政初探[J].教育与经济.2001,(4):55-59.
[3]王玉功.宋朝助学活动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38-39.
[4][宋]周应和,马光祖.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本:卷之二十八.
[5]金苏,毛晓阳.宋代贡士庄考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14-120.
Summarization and D iscussion about Nongovernmen tal Activity to Assist the Impoverished Schoolsand Students in the Song Dynasty
XU Yao-li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The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flourishing;however the investment to education was rather limited.Thus the culture flourishing in the Song Dynasty depended on the suppo rt from the civil to a great extent.The suppo rts are both to the School and to the individual.In general,nongovernmental activity to assist the impoverished students in the song dynasty had themodel that launched by the officers and the peop le responded.The socialmode to w illing to assist the impoverished studentswasmo re popular in the No rthern Song Dynasty th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Themodeof support to education mainly was estate.The nongovernmental activity to assist the impoverished schools and students in the Song Dynasty reveals that the peop le’s devotion to suppo rt education needs to be inducted,themode of suppo rt should be the estate.
the Song Dynasty;assisting education by estate;bank for the peop leof taking imperial examinations;themode that launch by the officers and the peop le respond
G649.29
A
1672-0539(2011)01-095-06
2010-10-10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西部项目“宋代进士考试与文学综论”(10XJC751007);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宋代民间助学研究”(编号:2008YR19)
许瑶丽(1975-),女,四川简阳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编辑,主要从事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辞赋学研究。
韩冬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