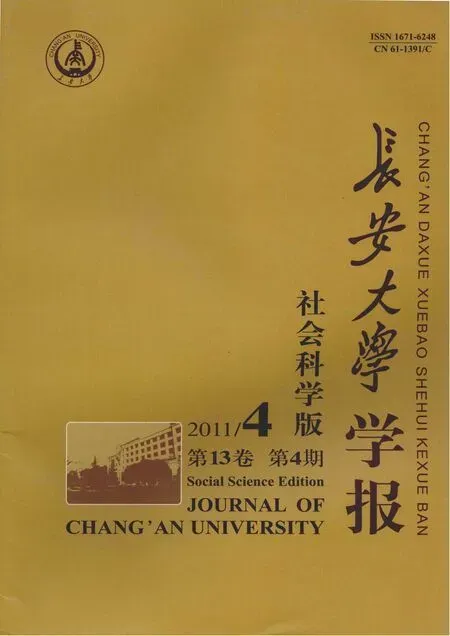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2011-03-31王恩科
王恩科
(1.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重庆 400067;2.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王恩科1,2
(1.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重庆 400067;2.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基于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独特部分,既具有文学经典的基本特质,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从译本的非唯一性、译本的变动性、译本的时代性和译者作用的独特性4个方面分析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以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分析认为,上述4种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译者的参与和文学作品在异域的重生,正是上述4种品格与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翻译文学才经历着经典的建构与重构。
文学经典;翻译文学经典;经典化;独特品格
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一样,也会经历经典的建构与重构。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近年来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然而已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动力因素,很少对翻译文学经典这一研究对象本身予以充分认识。钟玲在分析了部分中国诗歌英译文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诗坛经典化历程之后,认为其经典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把中文诗翻译为优美感人的英文诗章;一些重要的美国文学选集把这些创意英译选入,视之为具有经典地位的英文创作;美国汉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奠定了这些创意英译的文学地位;此外,还有一些美国诗人倡言其成就及影响力。”[1]查明建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之间的关系[2]。王瑾认为:“20世纪外国文学本土的经典化(即翻译文学经典化,作者注)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4个重要阶段”,即“1899年至‘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至1949年”、“1949年至‘文革’结束”、“大致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结束”[3],进而指出:“在以上列举的4个时期当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翻译出来的经典化程度往往会高于第三、第四阶段。”[3]这无疑是说,一个时代的翻译文学比另一个时代的更经典。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区鉷和胡安江分析了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之后,将翻译文学经典化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译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4]。胡安江认为,翻译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体系中要实现经典身份的建构,大致须考虑以下因素:“翻译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译者有意为之的共时性和本土化解读”[5]。上述研究深化了对翻译文学经典化及其动因的认识,但为了更好地认识翻译文学经典及其建构和重构,我们必须对这些研究的基本对象——翻译文学经典本身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只有充分认识了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才能进一步认识一部翻译文学作品是如何凭借着自身的独特品格,在上述动力的推动下完成经典化或实现经典重构的。
翻译文学经典是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因此必然具有后者的基本品格和要素。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6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6]这6个要素中,前2个与文学作品的内在品质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作品的优秀品质是包括翻译文学经典在内的文学经典的基本要素。正因为这样,钟玲在论及中国诗的英译在美国经典化时指出,“史奈德译的寒山诗是创意英译,本身即不容忽视的优美诗歌,所以寒山的作品也成为汉学英译的经典”[1]。而且“中国诗歌创意英译成为美国文学之经典,固然有文化与政治的缘由,但任何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必有其先决条件,即作品本身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1]。翻译文学经典除了自身的优秀品质外,由于译者参与和异域文化环境的介入,翻译文学的经典化便增加了原创文学作品经典化所没有的因素和环节。正是这些因素和环节使得翻译文学经典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品格,主要包括译本的非唯一性、译本的变动性、译本的时代性和译者作用的独特性。
一、译本的非唯一性
译本的非唯一性是翻译文学经典区别于原创文学经典的第一个品格。原创文学经典,如果不考虑版本学上的差异,在作者创作结束后就定型了,无论是经典化之前还是之后,都具有唯一性。《三国演义》自罗贯中写成之后,就像雕刻家刀下完工的艺术品一样,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刻。历代无论如何阐释,无论是刻板还是铅印,《三国演义》还是那本《三国演义》,并不因当权者和读者的好恶而有丝毫改变。在“大话”经典的热潮中,有人曾戏仿《三国演义》,推出了为不少读者叫好的《水煮三国》。如果《水煮三国》有朝一日成为文学经典,那么它或者与《三国演义》并享经典的殊荣,或者将取而代之,但无论如何它始终不会是《三国演义》本身。与原创文学经典这种唯一性不同,翻译文学经典恰恰因为自身的非唯一性,其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与巩固。如果说原创文学经典是在与其他原创作品的对比中脱颖而出的,那么一部翻译文学经典则是在与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其他译本和其他翻译文学经典的对比中确立其经典地位的。很难想象,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只有一种译本,而这本唯一的译本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经典。1935年出版的《简·爱》李霁野译本在1980年祝庆英的译本诞生之前,一直是这本小说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译本。李霁野的译本在那段时间内多次重印,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且茅盾也在1937年《译文》第2卷第5期上《真亚耳(Jane Eyre)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一文中称,居然有伍光建的节译本和李霁野的全译本“那么两种好译本,实是可喜的事”[7]。而且,在解放前的战争环境中“‘《简·爱》的旧译本一直在民间,特别是大、中学生当中流传’,也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连写于1958年的《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一书也承认,自《简·爱》中译本20世纪30年代出版后,‘二十多年来,它一直在我国拥有较多的读者,并且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影响’”[8]。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证明,李霁野的译本并非因为唯一,而是因为是“可喜的”“好译本”才在当时确立了翻译文学经典的地位。然而,李霁野译本的经典地位并非一劳永逸地固定了下来,因为1980年祝庆英的译本出版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
在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的则是由祝庆英新译的译本。……1980年由祝庆英新译的《简·爱》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初印就有二十七万册之多,其后不断重印,至90年代后期其销量竟然超过三百万册,可见受读者青睐的程度[8]。
尽管李霁野的译本在出版后的40多年间拥有大量的读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经典化了,但随着“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祝译本”[8]的诞生,前者的经典地位迅速被后者取而代之,由“当下”的经典变成了“文学史经典”。
与李霁野和祝庆英译本经典化情况不同的是萨克雷的Vanity Fair汉译本的经典化。1932年,著名翻译家伍光建根据赫次堡的节选本将Vanity Fair译成中文,取名《浮华世界》。这本440页的译本在其后的20多年里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著名翻译家杨必的全译本《名利场》自195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学翻译界有口皆碑的经典译作。但是,杨必译本的经典化并没有终结Vanity Fair的汉译,因为在杨必的译本之后,先后出现了其他几种译本,其中主要有贾文浩和贾文渊合译的《名利场》、谢玲翻译的《名利场》、荣如德翻译的《花花世界:一个没有英雄的小说》、彭长江翻译的《名利场》等。在Vanity Fair汉译本的经典化中,虽然早期的译本《浮华世界》已经败下阵去,但是新近的译本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杨必译本的经典地位。
不仅仅是《简·爱》和《名利场》,其他外国著名小说的翻译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译本的非唯一性或多样性为翻译文学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者说,没有译本的非唯一性,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就是一句空话。
二、译本的变动性
所谓译本的变动性,就是指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不同的译者笔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风采。译本的变动性与非唯一性都是就原作与译作之间一对多的关系而言的,但侧重点不同。非唯一性关注的是译本的数量,变动性则着眼于译本的内容。
(1)话说一天,正是个阴郁寒冷的耶稣圣诞节前一天。天上满腾着片片彤云,黑压压的不透一丝天光。地上积雪,足有好几寸厚,好似铺着一条挺大的鹅毛毯子。这时已近黄昏,那一天夜色,却愈腾愈密,愈密愈黑,恰和这满地琼瑶,做了个反比例[9]。
(2)那是一个寒冷而阴暗的圣诞前夕。头顶上那厚实的云层几乎完全遮住了白昼的余光;地上的积雪深达几英寸,而仍在斜斜飘洒的雪花看来在天亮前会使积雪大大增厚[10]。
上述2个段落如果视为创作的话,应该是2位作者对同一雪景的不同观察和描写。然而,它们却是哈代短篇小说Benighted Travellers(后更名为The Honourable Laura)开篇几句的2种译文。它们的差异十分明显:(1)译文长度悬殊:译文1共13句95字,译文2共4句69字;(2)平均句长悬殊,文体风格各异:译文1平均句长7.3字,行文轻快,辞藻华美,译文2平均句长17.3字,语气凝重,书卷气浓厚;(3)叙事风格不同:译文1开篇的“话说”2个字,使读者不禁联想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书场”叙事传统,而这种叙事风格在译文2中踪迹全无。读完这2个译本,读者心目中肯定会出现2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哈代。
同样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不同译者笔下会呈现出不同风采,就是在同一译者笔下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异。张谷若分别于1936年、1957年和1984年三译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不仅用于其中的山东方言在数量和种类上有较大差异,就是其他句子也多有调整更换。张谷若的3个译本之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我们既不能否认它们都是哈代同一部小说的忠实译本,也不能否认3个译本的确是各自独立的翻译文学作品,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教育部给高校中文系推荐的100本必读书目中,外国文学作品中列举的是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1957年版本,而非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的其他版本。
总之,译本的变动性作为翻译文学经典的品格之一,是由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也是文学翻译作为“二度创作”的生动体现。
三、译本的时代性
译本的时代性与译本的变动性密切相连,是翻译文学经典的另一种品格。译本的时代性主要缘于3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译入语的发展变化,导致译本出现文学经典所没有的语言老化现象;二是诗学的变迁;三是不同时代对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进行不同的阐释。这3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导致体现不同时代特征的译本的出现。
译入语发展变化导致的译本语言老化现象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中十分明显。新文化运动前,文言是官场和读书人唯一能接受的书面语言,因此文言就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翻译广泛使用的语言。例如,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使用的是文言,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以下简称《丛刊》)2/3的译文是文言(详见本文第四部分),林纾翻译的小说也都使用文言。如在林纾的笔下,《黑奴吁天录》中的人物张口便“曰”,言谈之中不乏“嗟”、“盖”、“吾”等。如:
嗟夫。人生寿命。盖与时光相逐而俱逝也。汤姆到圣格来家已二年矣。彼虽离去。其亲爱难释之骨肉。而意中犹有余望。意主人将来赎之。故亦不甚忧郁[11]①译文原文的句读全部使用实心的小黑圆点,此处用句号替代。。
这样的译文对清末民初的读者当然亲切,但对现代的读者难免费力、陌生。同样是斯托夫人的这部小说,在一位现代译者的笔下,相同的段落却天壤之别。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日子是一天一天逝去的,对于我们的朋友汤姆也是如此,两年就这样过去了。虽然与亲人分离,虽然怀念远方的故土,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感觉到痛苦,因为人的感情就像一架调得很好的竖琴,除非所有的琴弦都砰然断绝,否则是不可能完全破坏它的和谐的。当我们回顾过去那些似乎是贫困和艰辛的日子时,那些逝去的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唤起了愉悦和慰藉,所以我们尽管并不十分快乐,但也不十分痛苦[12]。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直言,宁愿读林纾的译文,不愿读哈葛德的原文[13],足见林纾的文言译文确实不俗。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白话文成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书面语言后,即使文笔优美的林译也渐渐过时了,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译本。
上述2种译文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叙事手法上也存在差异。叙事手法差异是诗学变迁所导致的主要差异之一。在林纾的译文中,译者将原文作者用竖琴比拟情感的部分省略了,而且“不甚忧郁”的原因也变成了“意主人将来赎之”,与原文相去甚远。上述省略和改动主要缘于清朝末年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中国古典小说由于深受史传和书场传统的影响,情节发展而非人物性格变化往往是小说叙述的动力,这一点在章回小说的常见煞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中国传统小说大都是“情节动力”型的,或者说“中国传统小说正是在对故事的热衷、对情节完整连贯的追逐、对因果逻辑的笃信中形成了叙事结构的情节模式”[14]。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19世纪的英美小说更加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情感的变化,情感和性格的变化往往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正是由于中外小说叙事手法的差异,重情节推移的中国叙事传统让林纾不仅将原文中用竖琴比喻汤姆情感的句子省略了,而且为了情节的连贯,汤姆“不甚忧郁”的原因也被改变了。
语言和诗学的变迁之外,时代精神往往赋予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时代内涵。尤其是经典文学作品,巨大的开放性和阐释潜能,常常会使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历史光芒的照射下呈现出各异的瑰丽色彩。萨克雷的名作Vanity Fair中的句子“Who is 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child,wife,or husband”就是很好的例证[15]。杨必在出版于1957年的《名利场》译本中将其译为:“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16]原文中的“good”意义宽泛,杨必将其分别具体化为“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和“贤良的”(妻子)。应该说,这样的具体化是译者基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这个大背景所做的阐释。那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经历“反右”和“文革”的冲击,传统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影响巨大,因此中国传统伦理规范所默认的家庭成员职责,便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潜意识之中。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a good child”自然应该是“孝顺的”,“a good wife”自然应该是“贤良的”,“a good husband”也自然应该是“尽职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必是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代言人对“good”进行上述具体化处理的。除了“good”一词的具体化,译者还将原文“a good…wife,or husband”中“妻子”和“丈夫”的位置做了调整,译成“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而非“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这种位置上的调整,如果不是译者一时的疏忽,那很可能与传统文化中已经成为潜意识的“男尊女卑”观念不无关系。40年之后,同样的英语句子在彭长江的译本中就成了:“真的是好的基督徒、好父母、好子女、好妻子、好丈夫。”[17]即原文中的“good”译成意义同样模糊宽泛的“好”,而且译者也没有像杨必那样调整“妻子”与“丈夫”的位置。纵观彭长江的译本,可以说它与杨必的译本一样自然流畅,绝少字对字的翻译。因此可以说彭长江译本中的这两处变化,主要不是翻译策略所致,而应该是新的社会环境下译者对家庭伦理观念重新认识和阐释。时代变迁也会使人们对作品中同一个人物形成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在《名利场》中主要人物Rebecca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Bu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ladies held aloof from her,and that their doors were shut to our little adventurer.”[15]这是作者对Rebecca及其丈夫从法国回到伦敦后混迹上流社会初期的一句评论。杨必的译文是:“可是说句实话,所有的太太看她不是正经货,从来不和她打交道。”[16]彭长江的译文是:“但是必须承认,太太们对她敬而远之,把咱们的小冒险家拒之门外。”[17]原文中的“adventurer”是个多义词,可褒可贬。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可知,它既可以指“person who seeks adventures”(冒险家),也可以指“person who is ready to take risks or act dishonestly,immorally,etc.in seeking personal gain”(投机分子)。杨必用“不是正经货”来译“adventurer”,这在视贞操为生命的50年代,无异于宣判了Rebecca的死刑。对于同一个“adventurer”,彭长江却选择了中性的词义“冒险家”,不能不说他对Rebecca有着与杨必不同的态度。这种差异虽有译者个人对Rebecca进行不同阐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是不同时代对同一人物的不同阐释的折射。
四、译者作用的独特性
如果说没有作者便没有文学经典,那么没有外国文学作品和译者便没有翻译文学,也就谈不上翻译文学经典了。虽然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译者在翻译文学经典化中的独特作用很少为学界所关注。无论是原创文学经典还是外国文学经典,作者及其作品自身是构成经典的核心因素,译者从来不会参与其中。然而在翻译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译者的作用却成为核心因素。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一些译者手里无法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译者手里成为经典。正如韦努蒂所言:“经典一经翻译,它作为语言和文学艺术品的内在品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它的价值也在译本生成的异域文化中发生了变化。经过翻译,一部外国作品很可能失去其在源语中作为经典的地位,最后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无人阅读、终止印行。”[18]不同的译者如此,即使同一位译者翻译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如张谷若翻译《德伯家的苔丝》的3个译本,其经典化程度也是不同的。可见,译者在翻译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既是不可或缺的,又是非常复杂和独特的。译者作用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译者的双语能力和文学修养方面,也体现在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上。
有关译者的双语能力和文学修养问题,彦琮早在其“八备”中就有论述。到了近现代,不少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实践或理论上对这2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论证,此处已无赘述必要。
译者卓越的双语能力和文学修养是翻译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很好的例证。“《域外小说集》第l册于己酉(1909)年二月出版,同年六月又出版第2册,本拟第3册、第4册……继续下去,但因销路太差,两册各卖了20本,第3册也就流产了。”[19]
后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1932年l月16日)中谈到:“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鲁迅的译文是用的较艰深的文言,读起来难免诘屈聱牙,而看惯了中国式译文的读者,对于直译的文章一时还看不惯,这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另方面,当时人们还不太习惯于读短篇小说,如鲁迅所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困难极大,此路是行不通的[19]。
郭延礼认为《域外小说集》失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用文言翻译外国小说困难极大,此路是行不通的”,显然是误判,因为鲁迅自己都承认,“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既然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确实很好”,而且能“流行”,可见用文言翻译并非是导致《域外小说集》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域外小说集》选择的大多是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反映人民苦难和争取民族解放的优秀作品,因此很容易在饱受民族存亡煎熬的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而且以周氏兄弟的外语水平和文学修养,他们的译作定能赢得大量读者并步入经典化的轨道,但仅仅二十多本的销量和后续几集的流产,不能不说明《域外小说集》的确“大为失败”。尽管《域外小说集》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那就是周氏兄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出现了较大失误。
同样是短篇小说集,比《域外小说集》晚几年的周瘦鹃翻译的《丛刊》却有着不一样的命运。《丛刊》在1917年出版前呈报教育部审查,担任审查工作的鲁迅和周作人对《丛刊》给予高度评价,称“得此一书,……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9]该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即使在它初版70年后的1987年,岳麓书社仍将它纳入“旧译重刊”丛书予以重印。《丛刊》中“白话译文约占1/3,多数系浅近的文言。一般说,周瘦鹃的译文通畅流美,无诘屈聱牙之弊”[19]。虽然《丛刊》的译文有2/3为浅近的文言,但它依然受到周氏兄弟的高度赞扬和后世的青睐。周瘦鹃曾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因病辍学,因此外语水平和文学修养很难与当时留学日本后来成为一代文豪的周氏兄弟相比,但是《丛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不能不说周瘦鹃在翻译策略上的正确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
《域外小说集》与《丛刊》的不同命运从正反2个方面说明,在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恰当选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难怪钟玲在分析了“一些中国诗歌的英译文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诗坛建立了经典的地位”后指出,“它们的经典化主要由下述力量所推动:最主要的是,有一些英文文字驾驭能力强的美国诗人或译者把中文诗翻译为优美感人的英文诗章;一些重要的美国文学选集把这些创意英译选入,视之为具经典地位的英文创作……”[1]上述2个因素是钟玲所归纳的4个主要“力量”中的前2个,而其中的“优美感人的英文诗章”和“创意英译”都与译者的翻译策略密切相关。无独有偶,胡安江在分析了美国学者华生于1962年翻译出版的《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之后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规范的充分考虑,尤其是对源语文本的细腻考证、‘本土化’翻译策略的确定以及译本加注手段的运用,为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
译者双语能力、文学修养以及翻译策略是社会文化等因素之外制约翻译文学经典化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从来无缘参与原创文学的经典化建构。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翻译文学经典化的进程中,译者的作用是十分独特的。
五、结语
翻译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它的研究既不能忽视诸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外在的动力因素,也不能轻视翻译文学作品自身的品格。本文主要论述了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但并不否认上述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文学经典建构与重构的重要影响,只是希望通过对翻译文学经典内在品格的研究,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翻译文学作品如何凭借着自身的独特品格在外力的推动下进行经典建构和重构的。翻译文学由于译者的参与和文本阐释时空的变迁而与原创文学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使得翻译文学经典与原创文学经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具有了原创文学经典所没有的独特品格。因此对翻译文学经典独特品格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对文学经典化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文学翻译的研究。
[1]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查明建.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J].中国比较文学,2004(2):86-102.
[3]王瑾.文化交流视野中的文学经典[C]//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区鉷,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J].中国翻译,2008(3):20-25.
[5]胡安江.翻译文本的经典建构研究[J].外语学刊,2008(5):93-96.
[6]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C]//童庆炳,陶东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茅盾.真亚耳(Jane Eyre)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J].译文,1937,2(5).
[8]徐菊.经典的嬗变:《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9]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0]哈代.哈代短篇小说选[M].蒋坚松,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11]斯土活.黑奴吁天录[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M].林玉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C]//《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14]谢纳.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结构[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9(1):72-74.
[15]William T.Vanity fair[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16]萨克雷.名利场[M].杨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17]萨克雷.名利场[M].彭长江,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18]Lawrence V.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canon formation[C]//Alexandra L,Vanda Z.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ic:identity as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9]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0]胡安江.美国学者伯顿·华生的寒山诗英译本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32(6):75-80.
Peculiariti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ons
WANG En-ke1,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Sichuan,China)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ons,being part of literary canons and sharing the latter's basic traits,have their own peculiarities because the translators reconstruct the originals and bring theminto a new culture.The author of the paper have found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ons display their peculiarities mainly in the versions'non-exclusiveness,flexibility and time-bound features,as well as in the translators'special roles in the reconstruction,and that the peculiarities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are combined to affect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literary canon;literary translation canon;canonization;peculiarity
H059
A
1671-6248(2011)04-0115-06
2011-07-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40107)
王恩科(1963-),男,陕西岐山人,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