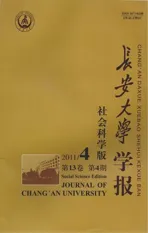“非本色”创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2011-03-31熊海英
熊海英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56)
“非本色”创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熊海英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56)
基于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三次大变革时期关键人物的创作皆具“非本色”特征,对韩愈、苏轼和杨万里“非本色”诗歌创作的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认为:“非本色”创作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在语言变革、审美价值观的突破、“游戏于斯文”的创作态度和重视“意”的自由表达等方面;“非本色”诗人的共同特质是“才、胆、识、力”俱备;文学传统除旧布新的源头活水和巨大动力正是“非本色”创作。
诗歌;非本色;创作特质;诗歌史
诗歌的“本色”概念,与人们对诗歌本质以及诗歌流变历史的认识有关。在不同时代或不同主体的意识中,“本色”的定义有过小幅调整,但相对于漫长持久的古典诗歌系统而言,“本色”的涵义是比较稳定的:它首先是从“尊体”角度来讲的。诗歌创作不仅要符合特定体裁体式的既有要求,还应符合特定的诗学观念,如诗言志、本于情性,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以雅致蕴藉的美学风貌为尚等等。陈师道正是基于“诗文各有体”之观念,提出“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论断[1]。后经明人引申,“本色”也可用来指诗歌驱除浮词虚意,直抒胸臆,得性情之真。“本色”意识积淀成一种深层的心理导向与审美观念,深刻影响和有力支配着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而韩愈、苏轼和杨万里作为诗歌史上三次大变革时期的关键人物,其创作却与“标准”对立,是“非本色”的。导致他们的个体创作发生变异的因素是什么?三者的“非本色”创作有何异同?“非本色”创作对于诗歌发展而言意义何在?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非本色”诗歌创作的核心特征
作为不同时代的重要诗人,韩愈、苏轼、杨万里的诗歌创作都具“非本色”特征,三者的“非本色”创作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诗歌语言的变革
语言是诗歌的载体,语言的变革正是诗歌变革的突破口和表征。捷克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卡罗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质就是具有审美意识地对标准语言进行偏离或扭曲,只有违反标准语言的常规,而且是有系统地进行违反,人们才有可能利用语言写出诗来[2]。韩愈的诗“刊落陈言,横骛别驱”[3];王安石感叹“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4];黄庭坚诗语必生造,意必新奇,张嵲批评他“病在太着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5];刘克庄则云“今人不能道语,被诚斋道尽”[5]。可见,无论是“本色”或是“非本色”诗人,主观上都清楚地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变革对于造就诗歌新貌的重要性,他们的不同之处只是在程度的把握上。韩愈、苏轼与杨万里是其所处时代中诗歌语言突破最明显、最具特点者,而三者变革的方向各自不同。
韩愈不满古今为文遣词用字陈陈相因,认为何异于抄袭,《樊绍述墓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6],他赞美樊氏创作:“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6],这正是他“陈言务去”主张的最佳注脚。基于这一理念,韩愈尝试用险韵、奇字、古句、方言入诗,甚至到了“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程度,而造成“骇人耳目”的效果。其实韩诗语言变态百出,并非只有“奇险眩目、诘曲聱牙”之字句,亦有如《咏月和崔舍人》、《咏雪》等诗,“遣词极工,虽工於试帖者,亦逊其稳丽”(《瓯北诗话》)[7],还有像《落齿》这样平淡家常如口语的诗歌“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总之,韩愈为诗竭力避免蹈袭前人,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尝试,无非希望诗歌语言未经人道,能以其“生”与“新”造成一种陌生感,使读者耳目一新。
苏轼与韩愈不同,他并不回避古人用过的语言,主张“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内涵很广,此处单就诗歌语言而论)。“故”语与“俗”语分别源于典籍与白话,苏轼“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8],语源语料自是丰富无比。时人称道“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9]。最典型的例子是“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以鄙俗之极的“牛矢”入诗,却令诗歌平添真实亲切的情味。其实“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堪称北宋诗人共识,梅尧臣、陈师道、黄庭坚等都曾提及或转述此说。不过陈师道、黄庭坚作诗法讲求“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10],苏轼则以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竹坡诗话》)[1],故参寥谓“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9]。参寥所谓“炉鞲”,或东坡自言“熔化”,皆强调诗人以“意”为主导的熔铸陶冶之功,使语言与诗意的表达浑成融契,这就不同于黄、陈“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宁粗勿弱、宁僻勿俗”的着意选择。从力避陈言而故意以古句方言入诗,以求字面的陌生感,到不避陈言与俚俗,用熟语出新意,苏轼的诗歌语言艺术较之韩愈,无疑又提升了一层境界。
杨万里为诗亦力图语言的新鲜出奇。《诚斋诗话》中既言“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纵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又列举善用经语、文语、法家吏文中语之诗句,欣赏苏轼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僧显万之“探支春色墙头朵,阑入风光竹外梢”,可见亦承元祐“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之风气。他也赞同江西派的用语原则“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11]。但事实上杨万里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未受此前任何原则与界限的约束,尤其表现在以白话、俗语入诗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前人。语言学家认为,宋元以后语法系统已经同现代汉语相差不远,在南宋这个白话语言开始爆炸式发展的时代,新名词以及各种词性的口语极大丰富,这些在“诚斋体”诗中得到了体现。韩愈和苏轼诗歌语言的变化,无论如何仍在文言系统之内,即使使用方言俗语,大多都有出处,哪怕是出于禅籍。而杨万里的诗歌已经贯通白话系统,打破了文白、雅俗之界限,无怪有论诗者称之为“白话诗人”。
(二)审美价值观的突破
被誉为“本色”的诗歌,其审美对象符合传统的美感标准,从属于古典诗歌既定的美学范畴。而韩愈、苏轼和杨万里以其充满个性的审美趣味,从不同方向、不同程度打破传统审美观念与美感标准、开拓了新的审美范畴。
韩愈趣尚“本好为奇崛矞皇”,在诗歌意象的选取和塑造上偏爱奇诡、丑怪者。如《元和圣德诗》叙刘辟举家被戮的血腥场面“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佝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又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写火势:“天跳地踔颠乾坤”,“神焦鬼烂无所逃”,意境令人不安,意象至于丑恶。再如鼾声为人所厌,故鲜有入诗,《嘲鼾睡》却着力刻画鼾声之雄哮咽绝,形容其声之惨如临刑呼冤、韵之苦令人丧魂失魄,本是日常生理现象却写得幽幽然、森森然。再如老态是人情所恶,诗人嗟叹发白云“朝如青丝暮成雪”,意象仍具美感;韩愈却写齿落,曰“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语讹默固好,嚼费软还美”,令人正视老态之丑。就其描写对象而言,这自然是一种观察角度与题材选择的转向,但韩愈在举世皆慕富艳平易之时独标僻重奇特,他“以丑为美”的写作清晰表明其审美观念的深刻变异:美本是令人感到和谐、自然、愉悦的,韩愈却将那些可怕可憎、野蛮混乱的意象纳入诗歌并极力刻画渲染,给读者造成神经上的冲突、紧张、恐惧感,让表现美的诗歌来表现“不美”,造成了一种陌生的“美感”。
苏轼诗歌高雅清旷、自然平淡的美感是符合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标准的。苏轼极为欣赏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歌,将“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视为诗美的至高境界。这与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学观念一致,与宋人尚雅避俗的审美标准又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字面和意象平淡自然,内中却蕴藏新雅的神意,这样的诗歌其实对受众审美能力所达到的精微水平有所要求和期待。总的来看,苏轼的诗歌审美取向与社会主流审美价值观一致,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是苏轼的审美趣味影响引导了时代审美观念的发展趋向,提升了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品味。
杨万里的“诚斋体”诗传递出活泼、新巧、诙谐的美感,这种美感在以前他人的诗中曾偶尔呈现,但没有人谁像杨万里这样专意塑造、表现它,以至于其诗令人觉得聪明有余而难以沁人心脾。这正是因为“诚斋体”诗的创作以“趣”为审美核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情”与“理”为主的传统诗歌的审美范畴。“趣”的性质贯通雅、俗,动、静,令人笑乐,遂使“诚斋体”诗很难用以悲为美、以静为美、以文饰为美、以雅为美的古典诗歌审美标准去衡量和评价,导致数百年来褒贬纷纭,未有定论。
韩愈创造了一种陌生的诗歌美感,它是丑的、不和谐的;苏轼强调一种书卷气的、人文意味的美感,它专属于文人,提升了诗歌审美的品位。杨万里则致力于发掘新的审美范畴,大力表现“谐俗”之美。可以说,韩愈、苏轼和杨万里从不同方向开拓甚至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观念与标准。
(三)“游戏于斯文”的创作态度
韩愈、苏轼和杨万里都曾被批评“以文为戏”。韩愈写过《毛颍传》、《石鼎联句诗序》等文,颇富小说意味。张籍《上韩昌黎书》云:“执事聪明,文章与孟轲、扬雄相若,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为乎!”,“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重与韩退之书》又责备说:“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之说为戏也”[12]。裴度《寄李翱书》亦非议韩愈“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12]。韩愈曲为己辩,《重答张籍书》但云“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6]元祐年间,苏轼在京城与门人好友诗酒唱酬,常常逞才使气、以难相挑,次韵往返有至于八九和者。集会时又往往互相诙嘲、创作谐隐之词以取乐,如《戏和正甫一字诗韵》之类皆是,诗歌“使口吃者读之,必至满堂喷饭,而坡游戏及之,可见风趣涌发,忍俊不禁也”(《瓯北诗话》)[7]。苏轼称羡韩愈“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顷年杨康功使高丽还……次韵答之》),戴复古对苏轼却有微词“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诸公十倍过。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论诗十绝》第二);元好问也认为“杂体愈备,则去风雅愈远”,“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东坡诗雅引》)[13];杨万里亦被刘埙指为“天才宏纵,多欲出奇,亦间有以文为戏者”(《隐居通议》)[14],《宋诗钞》直道“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论者多指责杨诗佻巧、油滑、新奇,可见其诗令人感觉近于游戏文字。
在人类童年时代,艺术与游戏难以迥然区分,它们的功用就是给主体带来愉悦感。后世渐以功利标准衡量文学艺术,诗文已属末事,何况不言志载道,而“以文为戏”,这一创作态度实属不可容忍,且以诗俳谐游戏,也就谈不上出自性情之“真”与“正”,诗人谑笑之际,定“无端人正士高冠正笏气象”,如此一来,诗歌自然“去风雅愈远”,故历代批评者如张籍、裴度、戴复古、元好问等皆指责得理直气壮。但若不执着于教化功用,游戏斯文对诗歌艺术的进步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情绪的放松状态有利于主体创造力的激发和试验创新的大胆进行。张裕钊评价《毛颍传》说:“游戏之文,借以抒其胸中之奇,洸洋自恣,而部勒一丝不乱,后人无从追步。”[6]苏轼的唱和次韵之作,则更因受挑战局面和争胜意识激发,立意翻新出奇,议论澜翻不竭,故人谓“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诗、雪诗,押‘暾字’、‘叉’字;在徐州与乔太博唱和,押‘粲’字数诗,特工”[15]。由此可见,在“以文为戏“的过程中,想象力纵横驰骋,潜力受到激发,才华自由呈现,媒介的种种潜在可能性因此也得到探索和开发。相反,在严肃的、受功利审美标准影响的创作状态下,主体是很难主动逾越前轨、自由发挥的。
(四)首重“意”的自由表达
韩愈、苏轼与杨万里诗歌的共同点是把“意”的自由表达和自我表现放在第一位,形式上的合乎格律、讲求法度等则在其次。
韩愈的诗歌既有驱遣万物的气势,又有寻幽逐微的敏锐,恰可以其诗“鬼神怕嘲咏,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虫鼠诚微物,不堪苦诛求”(《双鸟诗》)来形容。李贺也极称韩愈诗穷情尽变,至云其“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不仅是状物态,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正如欧阳修所言“退之笔力,无施不可……一寓於诗,而曲尽其妙”[1]。苏轼将文字表现力视为作品艺术品质的关键,在《答谢民师书》云:“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16]苏轼自言“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17],以手写心,自由无碍,故赵翼称其“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7],至于杨万里,姜夔形容他是“处处山川怕见君”,因为他的诗笔像快镜头一样将眼前景致全摄入诗中;周必大则称其“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遂谓天生辩才,得大自在”;“笔端有口,句中有眼”(《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钱钟书也认为杨万里以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未描写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18]。
当然,并非仅仅止韩愈、苏轼、杨万里、杜甫和黄庭坚等一流诗人的创作能达到同样高的艺术水准。而本色诗人很难因为表达和表现的需要,而放弃诗歌应遵循的法度、牺牲形式的美感。韩愈时以散文句式入诗,突破格律规定,“波澜横溢,泛入旁韵”,更生造怪奇的心象传达个体特具的情思与趣味。苏轼自言“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诗颂》),将心意的自由表达放在遵循法度之先。正因如此,其创作被批评为“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不觉令人神悚,仔细检点,不无利钝”[4]。杨万里谓善诗者“去词”、“去意”,认为言辞的能指与所指并非“诗”之所在,只有“味”才是诗的真正寄寓之所;基于这样的观念,为了诗歌趣味的传达与表现,甚至冲破了文白、雅俗的界限。虽然“意”的表达与其载体本来互相依存,有时形式即是内容,亦有意味,不过从“形”与“意”未能结合得十分完美的作品中,恰显示出本色诗人与“非本色”诗人各有自己的优先选择:韩愈、苏轼、杨万里的诗多是以意驱驾,不暇形式的锻炼。稍有不同的是韩诗的意味一部分来自于形式。他破坏现成的规则,避熟滑而趋陌生,破齐整而求错落,通过对形式的破坏求得全新的艺术效果。比起苏轼和杨万里,韩愈对形式因素的运用更为重视,苏轼和杨万里则庶几可称“得鱼忘筌”了。
将自我表现和“意”的自由表达作为创作的第一义,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韩愈、苏轼和杨万里的诗歌都不甚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韩愈首倡“不平则鸣”,其诗“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愈穷愈工,但宋人一致评之以“陋于闻道”[19]。苏轼诗多于“讥玩”,黄庭坚则认为“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是失诗之旨”;不赞成诗人“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20],认为此即东坡文章之短处。方回引刘元辉《读东坡诗》云“诗不宗风雅,其诗未足多。气如存笃厚,词岂涉讥呵。饶舌空吾悔,吹毛奈汝何。为言同道者,未许学东坡”[21];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云“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宜时。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13],评论者都因苏轼不约束怨怒情辞而指其诗不能薄古近雅。杨万里的“诚斋体”则疏离了诗歌的风雅传统,其诗不言国事,往往令人大笑,难以沁人心脾,今天人们仍需曲为辩护。而诗之本色则如金石丝竹,看似“寂寞无声”,其实“动则中律”,有国风雅颂那样的优雅从容、敦厚含蓄的风度,衡量之下即知韩、苏、杨三者之诗确非本色。
综上所述,韩愈、苏轼、杨万里诗歌创作的“非本色”主要体现在语言、审美观念、创作态度与诗歌观念诸方面,这样的创作实际意味着对文体界限的突破,即“破体”为诗。韩愈“以文为诗”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古体创作。他不但突破诗歌格律,还借鉴古文章法,布置诗歌意脉的起承转合,又多铺陈描写,加以议论。如《南山诗》排比四时之景,积势蓄气;《月蚀诗仿玉川子作》铺列四方之神,如大赋般豪纵恣肆。五古短篇如《落齿》、《双鸟》,说理层见叠出;诗中还引入古文句法,化骈为散,造成错落之美,如“春与猿鸣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杂诗》连用5个“鸣”字,《赠别元十八》连用4个“何”字,皆在句法上有意出奇,别创一格。苏轼比韩愈更进一步。“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瓯北诗话》)[7],苏轼往往将对事物的形象感受与哲理感悟结合起来,文字如流水行地,滔滔汩汩,在议论和感悟之中呈现主体智性之美。以议论为诗,实即摆脱了以情景交融为标志的传统诗美范式,而以思理为核心,构成一种全新的诗美范式。杨万里与韩愈、苏轼又不同,韩、苏的破体创作毕竟在文言范畴之内,“诚斋体”则以白话为诗,挑战古典诗歌的文言传统和文学的雅俗界限,这种突破就更为彻底了。
韩愈和苏轼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真正被接受是在“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调”凝定成型、成为与主情的唐诗并立的诗美范式之后。但在那些奉唐诗为本色的批评者眼里,韩诗与苏诗仍被批评为“是塾训体,不是诗体”、“是议论体,非诗体”[22]。杨万里的“诚斋体”既非唐音,也不属典型宋调,它不但运用白话,还贯通雅俗,某种程度轶出了古典诗歌美学范畴,无法以既有标准评判,这的确是“非本色”至极了。
二、“非本色”诗歌创作主体的特质:才、胆、识、力俱备
探究诗歌“非本色”创作取向的发生,根源还在于创作主体。韩愈、苏轼和杨万里虽然性情、趣味各异,所处时代和文学环境不同,但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特质。正如叶燮所言,杰出的诗人应该具备“才、胆、识、力”四要素,因为“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23]。在四要素当中,“识”是审美判断力,“才”是审美表现力,“胆”是主体的自信,“力”是作家的艺术功力和气魄。“才”、“胆”、“识”、“力”四者,韩愈、苏轼、杨万里不但俱备,且皆超出常人。
3位诗人皆有通变求新之胆识。韩愈认为“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6],他明确主张以新代陈,以异代常。韩愈于诗别辟奇险之境,赵翼认为“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开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7];叶燮称:“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23]。“向来孟韩息,不有欧苏继”(杨万里《胡英彦得欧阳公二帖……万里用其韵简英彦》),苏轼不沿袭唐诗典型,“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喜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23]。杨万里亦自陈“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问侬佳句如何法,无法无盂也没衣”(《酬阁皂山碧崖道士甘叔怀赠十古风》),可见3位诗人胆识过人。
3位诗人亦皆才华横溢,富有魄力。韩愈的古体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决天地之垠”(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24],许学夷认为韩诗与一般唐诗不同,“唐人之诗,皆由悟入,得于造诣”,“退之五七言古,虽奇险豪纵,快心露骨,实自才力强大得之”[24],故《岁寒堂诗话》谓“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24]。方东树云:“韩公当知其”如潮“处,非但义理层见叠出,其笔势涌出,读之拦不住,望之不可极,测之来去无端涯,不可穷,不可竭。当思其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岳,奇崛战斗鬼神,而又无不文从字顺,各识其职,所谓妥贴力排奡也”[25]。这些评鉴者都看到了韩愈古诗风貌与诗人特有的才力、气魄关系甚巨。苏轼诗境亦壮伟阔大,气象万千。刘克庄云:“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他人无许大气魄力量,恐不可学”[5]。叶寘指出苏轼之魄力较韩愈更胜:“‘天形倚一笠,地势转两轮。五霸之所建,毫端栖一尘。功名半幅纸,儿女浪苦辛’,所见者真超然万有之表。较韩诗‘下视禹九州,一尘集毫端。邀嬉未云几,下已亿万年。闻有夸夺子,万坟压其颠’,此更壮伟矣。又如‘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又‘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此老眼目如许广大,收拾句语中,决非小力量也”[26]。不同于韩愈之横空盘硬语,“坡诗不尚雄杰一派,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瓯北诗话》)[7]。其诗之恢宏气象缘于主体胸襟超旷、智慧高明、识见透澈。
相较于韩、苏2位诗人诗境的阔大雄奇,“诚斋体”诗之境界只能评为小巧新奇,诗人笔触摹写入微,而诗句流畅圆活,诗中鸢飞兔走、蝶舞花开,自然生生不息、流动不滞的生命活力透过诗境传递出来,令读者感同身受,主体精神的充实健旺与韩愈、苏轼是一般无二的。
韩愈、苏轼和杨万里的诗歌又都表现出善于想象和联想的特点,比喻、拟人是他们常用的手法,而且用得既丰富又贴切,使笔下万物无所隐遁,本相毕现,这也正是主体才气的重要表征。
除才识、胆力以外,3位诗人的诗歌风貌形成中亦皆有学力因素。韩愈为诗刊尽陈言、用奇字古句须以熟悉典籍、博览群书为前提;宋人以学问为诗,苏轼和杨万里之博学自不言而喻。《一瓢诗话》云:“苏眉山天才俊逸、潇洒风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因其学力宏赡,无入不得”;周必大曰:“今时士子见诚斋大篇巨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抑未知公由志学至从心,上规赓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可见皆是真积力久,非一日之功。
韩愈、苏轼与杨万里所具备的特质也给其诗带来相应的缺陷,正如钱钟书所言才人容易“困于所长”。如“七言难於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具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石林诗话》)[1],这是以才学、魄力胜者之诗病,气盛、言肆,意便易说得太尽,韩诗的弱点,苏轼、杨万里亦难以避免。正如陆时雍所言“凡好大好高,好雄好辩,皆才为之累也”[27]。
这3位“非本色”创作者气魄雄强,才华横溢,笔力健劲,胆识过人,堪称天才,遂成就典范诗作。诗歌史上杰出的诗人很多,于才、识、胆、力四者间有所长者不少,兼备者却无多。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有通变之胆识,但不具备相当的才力,或是有才力、无胆识,皆难导夫先路,引领风会。韩愈、苏轼、杨万里的难以企及正在于此,他们才识胆力兼备,遂能独辟蹊径,别开生面。
三、“非本色”创作的诗歌史意义
康德说:“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着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又说:“天才的产品是后继者的范例而不是模仿对象(因为这样那作品上的天才和作品里的精神就消失了),它是对于另一天才唤醒他对于自己独创性的感觉,在艺术里从规则的束缚解放出来,以至艺术自身由此获得一新的规则,通过这个,才能表现出自己是可以成为典范的。”[28]康德指出独创性是天才的第一特性,并昭示天才在文学传统革故鼎新过程中的意义:呈现典范之作,并把艺术创作从规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启新的局面。康德所谓的“天才”,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则被称为“豪杰之士”,如王国维所言:“从来豪杰之士,未尝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尝能转风会”,“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29]韩愈、苏轼、杨万里即是以其超凡绝俗、独步一时的“非本色”创作为文学传统注入旺盛的生命力,构成除旧布新的源头活水和巨大动力,使创作得以更新和延续。康德关于“天才”的论断对深入认识杰出诗人及其“非本色”创作的文学史意义极具启发性。
康德还指出天才的创造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其心理结构的特殊性在于想象力与理解力的自由协调。具体到文学创作,我们看到天才的创造性表现在想象、直觉、灵感等潜意识创造心理作用的充分发挥,引领着理性和意识流动,发而为诗时,遂如苏轼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天才为美和艺术树立的典范不是循概念产生,也没有法则可供沿袭。因此后来者只要通过对典范的体悟而唤醒自身的独创性,就能有所成就。如韩孟诗派的诗人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等,皆打破古典抒情诗的和谐优美和种种法度矩式,各自追求一种怪奇之美,自成面目,并不与韩愈诗风相似。而论者评苏轼与黄庭坚的诗法,以禅宗之云门、临济为喻,曰“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跟点地者,百无二三焉;临济棒喝分明,勘辩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门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30],虽有褒贬之意,其实正揭示了天才不立法,无门径可循,不可由“学”而至。至于杨万里,从南宋至明清,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对“诚斋体”诗的妙处心领神会,进而学习它并有所成就的人就更少了,毋庸讳言是因为诗人的创造力早已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与“非本色”创作不同,本色创作较多在认识了规律、掌握了法式之后,意识控制创作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形,虽然也有很多成功之作,但往往因为理性的清晰压抑了主体潜意识,创作因而无法取得并传达出那种不期然而然的自由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韩愈、苏轼、杨万里的“非本色”诗歌创作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表现在语言的变革、审美价值观的突破、“游戏于斯文”的创作态度和重视“意”的自由表达等方面;“非本色”诗人的共同特质则是“才、胆、识、力”俱备。正如苏轼所言“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书吴道子画后》),韩愈、苏轼、杨万里等“豪杰之士”秉持天赋,创体、创格、创意、创调,然后能者立法,余者嗣法。“非本色”创作作为文学传统除旧布新的源头活水和巨大动力,与“本色”创作共同构成诗歌发展的历史。
[1]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穆卡罗夫斯基.标准语言和诗歌语言[C]//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宋祁,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刘克庄,王蓉贵,向以鲜,等.后村先生大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6]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苏轼.东坡诗集注[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9]朱弁,吴可,黄辙.风月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陈长方.步里客谈[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4]湛之.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费衮.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6]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O].文学古籍刊行社.
[17]何薳.春渚纪闻[M].张明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2.
[19]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0]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O].四部丛刊本.
[21]方回.桐江集[M].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1.
[22]程学恂.韩诗臆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23]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24]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5]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6]叶寘.爱日斋丛抄[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8]康德.判断力批判[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9]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0]吴埛.五总志[O].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Non-inherence”cre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history of poetry
XIONG Hai-ying
(Th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Jianghan University,Wuhan 430056,Hubei,China)
In the history of peotry,the key figures in their peom creation during the three revolutions are all characterized by their“non-inherence”.In this paper,the author conducts analysis for the specific cases of“non-inherence”in the peom creation from HAN Yu,SU Shi and YANG Wan-li.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non-inherence”peom creation has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they are:the revolution in language,the breakthroughin aesthetic appreciation,creation attitude in gentleness and the presentation in implication.The peots with“non-inherence”creation all possess the quality of“talent,bravery,understanding and capability.”The source of revolution for the old and creation for the new i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great motivation,surely,come from the“non-inherence”creation.
peotry;non-inherence;features of creation;history of peotry
I052
A
1671-6248(2011)04-0098-07
2011-07-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W051)
熊海英(1972-),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