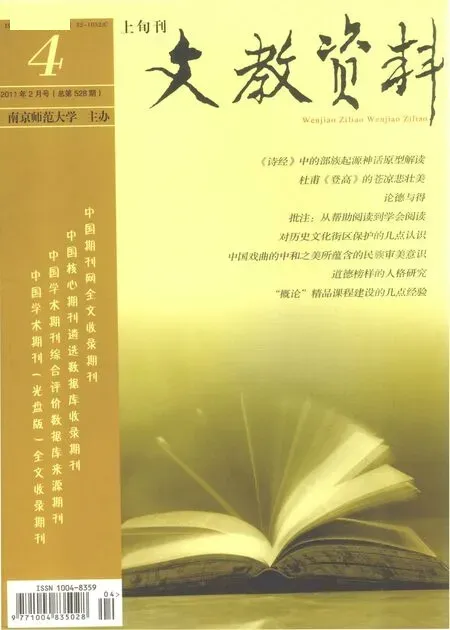中国戏曲的中和之美所蕴含的民族审美意识
2011-03-20常青
常 青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中国戏曲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和人物扮演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艺术,是对众多艺术形式的综合提升,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结晶,凝结着浓厚的民族性格和美学意韵。纵观中国古典戏曲,我们不难发现,中和之美与大团圆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审美意识。这无疑也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以及深层的民族性格。所谓中和之美,是指符合无过无不及的适中原则的和谐美;所谓大团圆,是指戏曲剧目在结尾安排的圆满结局。无论是对中和之美,还是大团圆,当代学者与戏曲创作者不予苟同的大有人在。然而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中华民族特殊的民族性格和传统的审美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正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平和的审美追求、中庸的民族性格造就了传统戏曲的喜剧因素和中和之美。
一、文化渗透进程下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由“中庸之道”融入审美意识转化而成。中和与中庸在意义上是有联系,而且有相通之处的,按照朱熹的解释,中和是就性情而言,中庸是就德行而言。实际上,中庸兼有中和之意。中庸之道的根本含义就是对立双方都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的融洽和谐。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条重要的思想原则。《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把是否遵循中庸之道作为衡量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中庸”、“中和”的观点在儒家的典籍、著作中比比皆是。诸如“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月礼》)。在《荀子·修身》中有:“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另外古代政治家还把“中庸”、“中和”的思想用于政治领域,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制度》篇中这样论述他的限田主张:“使富人足以使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财不匿,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中和之美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而且渗透到封建社会的诸多领域。
中和、中庸思想既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必然会影响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以中庸、中和的标准要求文学艺术的创作。这种要求早在戏曲艺术产生之前就开始了。《国语·周语下》有这么一段话:“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正视听。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这段话指出了音乐只有以和音刺激听众,才能给人以美感,并把这一点看成关系能否施德于民、政通人和的大问题。中庸、中和在中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基础,有广泛的社会心理的土壤,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播散到不同文学艺术作品中,转化为这些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因素,再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在这种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生活的戏曲观众,不可能不受中庸思想、中和思想的影响,在戏曲欣赏中,必然表现出对中和之美的强烈要求。既然中和之美强调的是对立成分的和谐、统一,有悲就要有喜,有离必然有聚,所以“大团圆”的戏剧结尾就是中和之美最方便、最充分的表现。故而在中国戏曲中多为始于悲终于欢、始于离终于和。如果在戏曲结尾冤死者没有伸冤、分离者没有团聚,观众的审美心理就无法消解,他们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就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中国这片独特的土壤孕育出的审美观念,是中国戏曲观众所形成的大众审美需求的强烈表现。
二、情感节制基础上的内在和谐
基于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对中西方的审美差异作简单的对比。西方有戏剧,其中尤为推崇其悲剧性;中国有戏曲,其中多以“大团圆”为主调。西方的人是独立于社会的“公民”,西方的审美主体是个体化的审美主体,而中国的人是“溶解”于社会的“仁人”,中国的审美主体是集体化的审美主体。因此,在西方,“所谓情感,是指忿怒、恐惧、自信、嫉妒、喜悦、友情、憎恨、渴望、好胜心、怜悯心和一般伴随痛苦或欢乐的各种情感”[1]。也就是说,是一种“天性”,一种自然规定,一种永不满足的生命动力。它时时要冲破坚实的理性外壳,喷射出去。它不是情感的自然宣泄,而是外在力量对情感的规范和控制。也正是因此,在西方往往是外在的征服自然、征服生命、征服人生,在中国则往往是内在的享受自然、享受生命、享受人生。
另外,“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观点,它是汉民族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活经历在文化心理深层的积淀。这一古代即已形成的哲学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汉民族的性格和情感,促成汉民族形成了重整合、重中和的人文思想和审美观。这种哲学观在人与天之间划出了界限,将自然世界视为人的对立面。能思想的人,特别指人的理智和灵魂,能认识“思想的对象”。而所谓“思想的对象”即自然界,主要指自然界的本质,而非它的现象。感觉和理智相分离而推崇理智,现象与本质相分离而偏重本质。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同中国人的“观象取类”截然不同。在主观与客观的物象关系上,西方人更多强调的是再现和摹仿,以认清对象的性质意义为最终审美目的,而中国人讲究的是融合和物我两忘,以人与对象的浑然一体为最高审美境界。亚里士多德就主张美学的最高境界便是“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这一观点早就渗透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
综上所述,中国美感意识中深层的情感节制基础上的内在和谐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集中体现,是固有心态平衡的保持。也就是说,中国文学艺术虽然像西方文学艺术一样力求引起读者的心灵震撼,但结果却又不同,西方的艺术是打破旧的心态平衡并建构新的心态平衡,中国的艺术却是重建原有的心态平衡。这在古代戏曲中更为明显,尤其是古典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如同一种标志。它是一种“中和”的美学境界,是中国美感意识追求的一种体现,更蕴含着中国人在情感节制基础上对内在和谐的向往与追求。
三、母性情结泛滥中的柔弱美感
所谓“情结”,是指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簇心理丛。许多心理学家都明确指出:所有的人都是先天是两性同体,即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既具有雄性的一面又有雌性的一面。荣格认为:“假如要使人格得到完美的调节,达到和谐与平衡,那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的女性一面和女性人格的男性一面在意识和行为中显现自身。倘若一个男子仅只表现其男性特征,那么他的女性特征就会依然停留在无意识里。这样一来,这种女性特征依然不会得到发展,依旧会处于原始状态。这将会赋予他无意识一种软弱的特性和敏感性,这就是为什么外表上最有男子气概、行为上最强健有力的男子其内心常常是软弱和柔顺的道理。”[2]因此,由于经历、教养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在个体的深层心态层次上,出现女性情结或男性情结并非咄咄怪事。
就中国而言,母系社会发展得很充分,但由于进入文明社会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父系社会因此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样,在中国美感心态中大量沉淀下来的往往是女性化的原始余绪。这方面的例子毋庸细寻。老子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3]字里行间折射出的正是一种女性的心态和特有的视角,所谓“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而且,这种心态更深深潜沉在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而这种心态在古典美学上的诠释就是中国戏曲观众对女性“柔弱美”的追求。它不仅表现在对戏曲人物的要求方面,而且播散到了对戏曲的叙述方式的要求方面。戏曲叙事的线性结构,就是观众对“柔弱美”追求的表现。中国人何以对线性运动情有独钟?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线给人的感觉是柔和的,团块给人的感觉是强硬。线,让人感到它很容易随着存在环境的变化,可长可短,可直可曲,显得变化自如。团块给人的感觉是不大容易改变,难以随着环境的变化随方就圆。线性的运动如流水,连绵不断,一往无前,很有柔弱的品性。老子把水看作最能体现柔弱性能的东西,“天下莫柔弱于水”。水形成的波状线就更受中国人的欢迎。因此,中国人对线的喜爱,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是对“柔弱美”的喜爱。
戏曲观众对“柔弱美”的偏爱,使中国戏曲中的形象大体以具有“柔弱美”的人物为主导,戏曲的结构、冲突、传达的情感类型也具有“柔弱美”的特点,戏曲从总体上说来显示的是“柔弱美”。当然,这不是说戏曲中不存在刚强、猛烈的成分,只是说它总体的风格是偏重于 “柔弱美”。这种美感意识也正是中国特定文化中母性情结泛滥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国的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传统深厚,在其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喜剧美学体系。尤其是其散发的中和之美更是将华夏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也更能体现中国的文化内涵。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美学意识是在千百年来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节制的结果,更是华夏民族母性情结的依恋所生。它是众多因素的综合体,是中国艺术宝库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1]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9.
[2]霍尔.荣格心理学纲要.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42.
[3]老子.道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