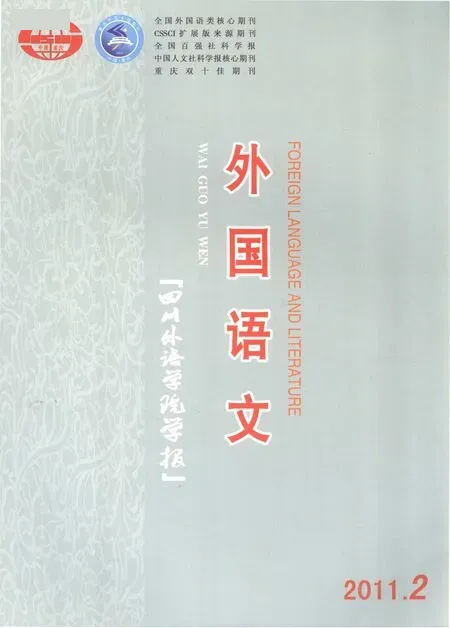《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的认知诗学分析
2011-03-20封宗信
封宗信
(清华大学 外文系,北京 100084)
一、引言
《爱丽丝镜中世界奇遇》(以下简称《镜》) (1872)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的姊妹篇,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数学讲师、逻辑学家、儿童文学作家卡罗尔 (Lewis Carroll,1832-1898)。两书①《境》与《镜》各有单行本,也有合订本。本文简称合订本为《爱丽丝》。同被当作儿童文学,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也使一辈又一辈的成年读者爱不释手。罕有文学批评家对此发生兴趣,但却吸引了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个中原因在于其似乎永远也无法挖掘穷尽的“文学”价值。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922:10)在中国第一部汉译本《境》的“译者序”里把其文学价值与莎士比亚“最正经的书”相提并论,指出其所异“不过又是一派罢了”。
笔者在《新诗神》上发表的论文 (Feng,2009)里总结道,由于《爱丽丝》是写给儿童的滑稽读物,算不上“正统”文学,如果未受学界广泛注意和研究,不足为奇。但它却吸引了各种年龄的读者,风靡全球,被译成近百种文字,两千多个版本,包括港台在内的中文版已有 170多个。至少从受欢迎程度看,其文学价值不比任何经典文学名著逊色。
《爱丽丝》的成功,的确是个奇迹。写给儿童逗趣的娱乐书,按惯例很难归入文学范畴。但《爱丽丝》是个例外。它不是寓言,但不比伊索寓言影响小;它没有暗含任何宗教的、政治的、心理学的寓意,但文学价值丝毫不低;文学批评家对它视而不见,但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却津津乐道。书中涉及的现实与个体身份的判断、错位的时间与空间、颠倒的因果关系、大量的悖论等主题,是包括罗素在内的诸多数学家和哲学家关心的话题。所以笔者曾指出,它是成人写给儿童逗乐的,也是写给成人思考的;它是数学家写给数学家的,也是哲学家写给哲学家的。
《镜》在语言的创造性和逻辑悖论层面,分量超过了《境》。镜中世界里的一切,都与现实世界相反。事物的反向运动,人物的逆向思维,荒谬的推理方式,可笑的争论依据,怪诞的逻辑悖论,都在叙述和话语层面得到凸显,与读者的现实世界知识、语言直觉和认知模式背道而驰。本文拟从认知诗学角度,对《镜》中语言推进故事情节、操纵叙述话语、建构文本世界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价值。
二、“镜中世界”
文学描写的虚构世界是“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与逻辑学中的可能世界有联系但不同,而是一类特定的可能世界。文学文本有自己的模态系统,其中既包括真实世界 (actual worlds)的真实事件也包括可能世界的可能事件。《镜》所描写的真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相反。如第一章中,墙上挂的画是活的;烟囱上的钟表有个小老头的脸庞,还朝着爱丽丝狞笑;棋子一双双在并肩走动,城堡也手挽手在走动。第二章中,爱丽丝总是到不了自己期望的目标。要走近棋盘上的一个目标,只能朝着反方向走;要呆在原地不动,必须不停地跑步,而且要以平时速度的两倍;但接下来要去另一个地方,必须跑得更快才行。王后让爱丽丝再吃块饼干,以确定饼干已经起到解渴作用,让她无言以对。第五章里,爱丽丝在商店买鸡蛋,店主(羊)说,买两个比买一个便宜,但必须都吃掉才行。店主不把鸡蛋递到她手里,而是放在店里另一头的架子上,立起来。爱丽丝要去拿,却发现鸡蛋离她更远。同时发现椅子竟然是一棵树,在长,屋子里还有一条小溪在流淌。王后所讲的准则或方法,令爱丽丝百思不得其解。时间是倒流的,所以人的记忆也是反向的,不能回忆过去,但能回忆未来。爱丽丝坚信自己的记忆是单向度的,不可能回忆尚未发生的事情;而王后的记忆是双向的,不但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而且能回忆起三个星期后要发生的事情 (这里也许不能排除“记”与“忆”的双关)。有关处罚和犯错的先后顺序和实施办法,符合奇幻世界的特有逻辑,对现实世界的读者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熟悉小说惯例的读者不会把文本中的真实世界与自己身处的“真实”世界等同,其原因就在于虚构文本属于他们熟悉的小说语类。Searle(1975: 329)指出,虚构人物并不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承认他们在小说中存在过。《镜》中的真实世界不但与现实的真实世界相反,而且无序。荒诞的规则缺乏逻辑,可以任意变化,前矛后盾。本无生命的东西,在这里是鲜活的;本是静止的物体,在这里是运动的。哲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但镜中世界的物质是反向运动的,而且没有一致的规律。“惩前毖后”之普遍准则,在这里成了“惩后”,是否也能毖前,不得而知。书中的故事情节虽然与哲学家关心的主题难以直接挂钩,但其中叙述话语呈现出的主题,从反面揭示了人类思维方式的本质,对现实世界读者的启示意义,不是该如何思考,而是不该如何思考。
卡罗尔让爱丽丝进入镜中世界,把现实世界的语言带入奇幻世界,成为现实与虚幻的接口,才使镜中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语言层面的纠结和冲突,才使人物话语过程成为叙事过程。镜中世界里的花草都会讲话,但爱丽丝却失去了原本正常的语言能力。与人物角色没法沟通和正常交流时,只好人云亦云,胡言乱语。当她按正常逻辑推理试图找到规律时,总是无章可循,不知下一句话该如何说,下一步该如何走。对荒诞的规则提出疑问时,只能受到呵斥和指责,只好一遍遍俯首听命,任人摆布。刚走出一个困境,又掉入一个意想不到的陷阱,除了困惑还是困惑。语言的诡异功能,使镜中世界的人说一套做另一套。第二章中红桃皇后承诺当爱丽丝走出两码后会给出指令,走出三码后会重复指令(还特别强调怕爱丽丝到时候忘掉),但并没有付诸实施。“言必行,行必果”的规则,在奇幻世界成了“动口不动手”,言而无为,甚至言而无信。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分析哲学家 Austin(1962)、Searle (1969)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有所为,“言即行”。人一旦做出承诺,就是在宣告将付诸实施。语言哲学家发现的言语行为的恰当条件、真诚原则等一系列规约性原则在奇幻世界里并不起作用。镜中世界的荒谬,是故事的主要组成部分,给儿童带来不可思议的乐趣之时,在荒诞大主题下给成人提出了一个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叙事、语言与逻辑艺术
《镜》的叙事顺序和话语结构与读者阅读其他童话过程中的期待没有明显的差别,但镜中世界里故事情节的展开有其独特的逻辑:某个情节之后,会顺理成章发生什么,走入虚构世界的爱丽丝难以预测,身处现实世界的读者也难以预测。
毋庸置疑,认知文体学和认知诗学的文本研究中,最核心的是语言问题。在镜中世界里,语言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使用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来分析,也无法回避语言问题。语言不仅是描述场景和讲述故事的工具,而且是人物角色预测事件、导致事件发生的工具。语言的记录和描写功能,在这里成了规定和导致行为发生的根源。如果第一章中没有爱丽丝朗诵诗歌,那么孪生兄弟、胖矮人、狮子、独角兽就没有主题,无事可做。如果没有爱丽丝的“言”,就没有他们的“行”。也许正因为语言能为所欲为,又可以无所作为,镜中世界才如此新奇。
人物角色的心理活动、说话和做事方式都以爱丽丝为叙事视角和思维模式参照。如爱丽丝看到烟囱上的钟表有 face,叙述者不忘提醒爱丽丝和读者:镜子里只能看到其“背面”。接着,爱丽丝读完镜中诗之后发现很美,但难以理解,叙述者不失时机地提醒读者:爱丽丝从来不喜欢承认自己看不懂。当胖矮人解释有关付工资的情节而爱丽丝不明白时,叙述者又解释道:“爱丽丝不敢斗胆问到底用什么付工资;所以你明白,我是没法告诉你的。”
爱丽丝多次感到困惑,按正常思路提问时,得到的回答是文不对题或南辕北辙。如第六章的一个片断:
Alice felt even more indignant at this suggestion.“Imean,”she said,“that one can’t help growing older.”
“Onecan’t,perhaps,”said Humpty Dumpty,“but two can.W ith proper assistance,you might have left off at seven.”
从表面上看,胖矮人的前半部分回答无懈可击,但后半部分文不对题。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字游戏。爱丽丝的 one是不定人称代词,意思是“谁 (都没法不长大、不变老)”;胖矮人的 one can’t是对爱丽丝的肯定和附和 (“是啊,谁都做不到的”)。但接下来的 but twocan与 one can’t形成反差,貌似在解释理由,却消解了 one的代词性质,移到数词范畴,使原本正常的肯定,瞬间偏离了方向(“一”做不到,但“二”可以)。其中幽默,令读者哭笑不得。这跟《境》中写的树可以用 bark(树皮;犬吠)吓退敌人的情节一样,有据没理。在真实世界里,bark的两个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想和隐喻关系;但在镜中世界里,树有 bark,狗可以 bark,因此树可以像狗一样疯狂地 bark。这些令人捧腹的幽默后面是严肃的逻辑语义层面的语言歧义问题。
寻根求源的问和前矛后盾的答,不但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展开,而且构成了故事本身。在展现这个颠倒黑白、缺少逻辑和准则的荒诞世界过程中,双关语、反讽、戏仿、打油诗、谜题、空话、废话等俯拾皆是。诗文的本质是以最凝练的语言达到最感人的效果,但在卡罗尔笔下,诗与歌没有区别,只有文字组合和堆砌,没有明确意义。爱丽丝的语言与镜中世界里的语言总是难以对应,角色的语言偏离了爱丽丝的语言,也就是偏离了现实世界里读者的语言。词汇意义不确定,说者与听者在语言交流过程中总是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的话语方式与现实世界里人的言语行为准则常常背道而驰,爱丽丝理性的提问得不到期待的回答,毫无逻辑的自言自语有时反而歪打正着。卡罗尔叙事过程中巧妙的语言游戏和富有智慧的逻辑悖论,与常规小说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镜》的核心意义,就在于其无处不在的“无意义”。貌似浅薄的滑稽和童趣,无不显示作者娴熟的叙事艺术、深邃的语言艺术、逻辑艺术和哲学智慧。
四、认知诗学视角分析
认知科学认为图式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有效工具。使用图式,我们就不需要把每一个日常情景作为新信息来处理,便可毫不费力地自动归入已有图式。Stockwell(2002:6)指出,认知诗学不仅仅把文学作为一种语料来分析,而是把批评理论、文学的哲学、认知科学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文学。诗学的“认知转向”不仅仅是对阅读的心理学发生兴趣。他(2002:80)还指出,图式理论的观点在文学语境下指向三类不同的运作领域:世界图式、文本图式、语言图式。世界图式包括与内容有关的各种图式;文本图式代表我们对世界图式的顺序和结构组织展现出来的方式之期待;语言图式包括我们期待一个主题出现时使用的语言排列形式和文体风格。我们对文本结构或文体结构的期待中出现的紊乱 (disruptions),构成了话语偏离 (discourse deviation),才可能让我们刷新图式。
对客观世界的预先知识和图式是人能够理解新话语或新文本的基础。在世界图式层面上,读者会发现一系列的紊乱:活灵活现的图画、狞笑着的钟表、长着树枝的椅子……与现实世界的灵与物、真与假、动与静对立;寻找路径和棋盘上的游戏规则与现实世界的前与后、上与下对立;镜像文字的特点,与现实世界的左与右、正与反相对立;倒流的时光、逆向的思维和记忆、反向的处罚准则,与现实世界的时与空、罪与罚、过去与未来对立。这些颠倒了上下、左右、前后、正反、真假、动静、罪罚等一系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无不在打乱我们理解现实世界事物存在状态、进行过程、事件顺序和物质运动规律的已有知识和图式。正是这种颠倒黑白与读者的世界图式不一致,才使读者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新奇。
镜中世界里的文字与读者的已有知识和语言图式相反。虽然爱丽丝在镜中世界里的镜子里才看到了“可读”诗,但如题目所示,是毫无意义的胡编乱造。作者在多个层面上巧妙地把“可读”与“不可读”的矛盾和逻辑悖论以滑稽嬉闹的方式严肃地呈现出来,给了读者一幅异常复杂的画面。第一,题目(YKCOWREBBAJ)不可读,在镜像中变成了JABBERWOCKY,可读;第二,在镜像中的正文仍不可读(没有意义),但符合读者语言图式中诗歌的形式结构,在可诵的意义上可读;第三,正文虽不可读,但基本上符合爱丽丝语言图式中合格的句法结构 (如第一句 T was brillig,and the slithy toves),因此她至少知道,无意义中有某种意义;第四,正文有一些有意义的词 (如 s word、blade、dead、head),爱丽丝通过语言图式能发现一条断断续续的明确线索。因此她承认虽然不懂该诗在讲什么,但她能总结出一个最简单的句子:som ebodykilledsom ething。这既是 Chomsky(1957)的“核心句”,又是Martinet (1961)指出的“能完美并系统地代表语篇的最小单位”,其中的人物比 Forster(1963:67-68)所描述的“可以用一个句子来表达”的平面人物更简单。
Barthes(1975)指出,“语篇有单位,有规则,也有语法”。叙事理论和小说理论都认为,文本的总体结构可以比拟为一个单句 (Barthes,1975;Fowler,1977)。爱丽丝能把一首不可读的长诗精简到一个可读的叙事语句,说明她的“语言能力”、“文学能力”、“叙事语法”知识共同在起作用。正是这种知识和语言图式,才使她能推测出这首诗是在讲某个事件,内容不外乎有挥刀舞剑者,有利器所至处,便有头落地。
爱丽丝走入镜中世界,这是第一层镜像,也是镜中世界里的“正常”真实世界。她看到的书中文字不可读,以为是某种自己不懂的语言。迷茫了好大一会,突然想起自己身处镜中世界,只有在镜中之镜才可读,这是第二层镜像,应该与现实世界一致,否则爱丽丝仍然看不到可读文字。这给现实世界读者提出的问题是:镜中世界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反面,那么镜中世界里的第二层镜像与现实世界有什么关联,是返璞归真呢还是愈加荒谬?由此可见,卡罗尔想像和描写的不仅仅是乐趣,而是智趣和智慧。
现实世界里的读者知道,正反可读的回文词(palindrome)和逆向词 (anagrams)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回文词如madam可逆读,意义不变,但在镜像里成了mabam,失去意义;lived可逆读为 devil,但在镜像中会成为 bevil,没有意义;互为逆向词的now与won在镜像里仍互为镜射。其奥妙就在于字符是否有对称性。H、I、M、n、O、T、U、V、W、X、Y等是对称字符,在镜像里不会变化,而其余的大多数(C、B、D、E、F、G等)都属非对称字符,在镜像里会变为反向。卡罗尔从自然语言字符绝大多数是非对称图形这一特点,利用印刷材料镜像通常不可读的共识,制造了“由不可读到可读”的艺术性空间穿越和“可读中的不可读”这一逻辑悖论。
读者在这里除了赞叹卡罗尔的幽默智慧,不能不思考字符的视觉特征和语言符号层面之上涉及认知心理学的一些严肃问题。英语字符除了左右对称,还有上下对称 (如 H、I、X)、全方位对称 (如O、X)、互为左右镜像 (如 b与 d,p与 q)、互为颠倒镜像(如M与W,b与 p、d与 q)的性质。如果卡罗尔把爱丽丝放在更为复杂的凹凸镜像系统里,观察到的文字效果将会怎样?这对中文读者的启示是,左右对称的“水”、“火”、“土”、“木”、“林”、“大”、“小”等,上下对称的“王”、“日”、“目”等,全方位对称的“田”、“十”、“口”等,以及互为颠倒的“甲”与“由”、“士”与“干”等字符是否有更神奇的效果?如果中国作家原创或仿写卡罗尔的胡编乱造诗文,在创造无意义中的意义时能否达到甚至超越其艺术效果?如果从“重构”的意义上把《镜》译为中文,译者在发挥语言创造性与忠实于原作之间是否能取得最佳选择以达到功能对等?
在文本层面上,《镜》的叙述与读者的期待差异最大、最多。几乎所有情节都在挑战读者对语言结构和风格的期待。第六章爱丽丝与胖矮人的一段言语互动中,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语言概念的表述和解释层面。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by‘glory,’”Alice said.
Humpty Dumptys miledcontemptuously.“Of course you don’t-till I tell you. I meant‘there’s a nice knock-down argument for you!’”
“But‘glory’doesn’t mean‘a nice knock-down argument,’”Alice objected.
“When I use a word,”Humpty Dumpty said in rather a scornful tone,“itmeans justwhat I choose it to mean-neithermore nor less.”
“The question is,”said Alice,“whether youcan make wordsmean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Thequestion is,” saidHumpty Dumpty,“which is to be master-that’s all.”
爱丽丝的问,符合读者的现实世界逻辑、语言和文本图式。而胖矮人的答,则缺乏逻辑。爱丽丝指出其逻辑错误时,胖矮人强辩道,词的意义是由他自己说了算,他可以随意赋予词汇意义,而且还可以控制意义的强弱、大小、多少。爱丽丝质疑语言词汇是否能担当如此多的重任,胖矮人的回答与爱丽丝的问题既关联,又不关联:他用同样的表达(The question is∗)来反驳爱丽丝的“问题”,但他反驳所提的“问题”与所问的问题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自然而然,爱丽丝迷惑不解,也不知所措。不料一分钟后胖矮人接着说话了:
“They’ve a temper,some of them-particularly verbs,they’re the proudest-adjectives you can do anything with,but not verbs-however,I can manage the whole of them! Impenetrability!That’swhatIsay!”
“Would you tellme,please,”said Alice,“what thatmeans”?
“Now you talk like a reasonable child,”said Humpty Dumpty,looking very much pleased.“I meant by‘ impenetrability’that we’ve had enough of that subject,and it would be just as well if you’d mention what you mean to do next,as I suppose you don’tmean to stop here all the rest of your life.”
胖矮人的逻辑很随意。比如,词汇与人一样,是有脾气的,但不是所有词汇都有。接下来的讲解乱了套,只好用“这就是我要说的!”来草草收场。爱丽丝被胖矮人搞得晕头转向,不得不再接着问,到底是什么意思。面对爱丽丝的穷追不舍,胖矮人不但没有恼怒,反倒高兴了。作者要表现的逻辑混乱,正是胖矮人的正常逻辑——有序中的无序。
与其说是卡罗尔在此创造幽默效果,不如说他从深层上触及了自然语言语义学上的根本问题。胖矮人的话语,在语言行为层面表现了理性话语轮回框架下的缺乏理性和语言符号意义的随意性。卡罗尔借用奇幻世界里人物角色的逻辑混乱和随意行为来展现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曲解和误解,实质上在哲学、逻辑学、符号学和语言学层面提出了很严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卡罗尔间接地触及到了现代语言学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比索绪尔发现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早了将近半个世纪。Saussure(1959/1916)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提到,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代的对象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是任意的。比如一棵树,在不同的语言里有不同的符号来指代,但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就约定俗成,个人不可随意改变。而胖矮人能随意改变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说明镜中世界里的语言符号规约与现实世界无法接合,因此爱丽丝才不知所云。
正是《镜》的语言特点和文本组织模式与读者的期待出现严重的不一致,才使镜中世界的故事能吸引读者,启发读者思考。它们在颠覆爱丽丝的图式,也是在挑战读者的图式。认知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概念是,人在理解话语时会在头脑中建构心智表征,认知诗学称之为“文本世界”。“文本作为世界”这一隐喻最常用于描述“沉浸于”某部小说中的读者感受,即构建其中人物、景色及一步步展开的情节脉络所采用的方式,在复杂与细致程度上与读者真实世界之所见没有差别(Gavins,2003:129)。
文学文本是相对独立的系统,包括了真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统一。认知诗学对文学思考方式的强调,与结构主义诗学中强调的文学阅读方法有一定联系。结构主义诗学家、文学理论家 Culler (1975)指出,使用文学理论,并非一定要去理解一个文本,而是去探究阐释活动。读者之所以把文学文本当作文学来阅读,是因为他们通过阅读获得了有关文学惯例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但可以帮他们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还可以帮助他们积累文学阅读的经验。因此他指出,“细读一部作品,有助于细读另一部”(Culler,1975:305)。这就是说,细读一部文学作品所获得的潜在知识,来源于具体作品,但超越了具体作品,有广而泛之的价值,是一种潜在的也是更高层次的能力,即“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可以说,Culler已经注意到阅读文学的人具有某种类似“文学图式”的机制,只是没有从认知角度明确表达而已,其实质与 Stockwell(2002: 80)的明确解释相吻合,即文学图式不是普通图式,而是“更高层次的概念结构”。我们在文学语境里阅读时,该结构负责组织我们的阅读方式,因此是一个“组建性图式”(constitutive schema)。
虽然奇幻世界里的对话缺乏理性,缺少逻辑,事件发生无章可循,貌似没有艺术价值,但对真实世界正常逻辑指导下的理性交流、事件状态和发生的常规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镜》的文学价值,从认知诗学角度看,不但对读者阅读过程中的深度思考有意义,而且对现代科学家思考基础理论问题也不无参考价值。比如《注释版爱丽丝》(The Annotated A lice,1960)的作者、美国数学家加德纳(Martin Gardner,1914-2001)在他的《科学美国人趣味数学集锦之一》(1988)里写道,镜射映像在生活中很常见,但大多数人解释不了“为什么镜射会把左右翻转却不会把上下颠倒?”的问题。早在柏拉图的《蒂买欧篇》(Tem aeus)里就描述过可以不翻转左右的镜子。加德纳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对称结构。他描述了印刷体字母作为单维度顺序的一连串符号、人的左右之别、诗人的回文 (anagram)音序诗、音符的单维度顺序及音乐镜射和倒播的效果。最后还写到,某些粒子以不对称而著称,所以物理学理论不能回避这一事实:爱丽丝在镜中世界看到牛奶时就在想,这奶能不能喝。由于镜中世界里的物质是反物质 (anti-matter),人们一度认为这奶无法消化,因为人体的消化酶是用来消化左旋分子的,而镜中的奶是右旋分子。现在看来,不仅是能否消化的问题,情况要严重得多。现代物理学宇称结构的实验表明,粒子与反粒子是同一结构的两种镜像形式。如果爱丽丝喝下镜中世界里的奶,必然会导致一场猛烈的爆炸。
五、结语
虚构不等于文学,大多数滑稽作品和笑话是虚构却不是文学 (Searle,1975:319)。但《镜》以虚构的滑稽和笑话著称的同时,其人文和科学价值不可低估。奇幻世界里的怪诞逻辑、语义不通和荒谬可笑之处,恰恰能让我们重新思考所谓“正常”的现实。认知诗学分析方法让我们认识到,文学不是少数人的阳春白雪,只不过是“人类日常经验的一种特殊形式”(Gavins&Steen,2003:1)。与认知诗学同一时期兴起的文学语用学和认知心理学方法对文学的实证研究,把文学当作人类交流活动之一,在“语言作为社会符号”(Halliday,1978)和“文学作为社会话语”(Fowler,1981)的理念下从书面交流的共性来探讨文学交流的本质 (封宗信,1997、2002),也是从共性到特殊性探讨“文学性”这一长期困惑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与认知诗学相得益彰。
《镜》是童话艺术,也是叙事艺术、语言艺术和逻辑艺术。语言作为工具,在呈现文本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超常的叙事功能和话语操纵功能。滑稽模仿诗和胡言乱语的诗学意义,恰恰是其符号本身的毫无意义所表达出的文学语境意义。《镜》的符号学意义在于让我们思考包括语言的任意性和自然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在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认知诗学意义在于让我们通过现实世界与奇幻可能世界之间的联系,思考意义与无意义、文本意义与文学意义、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悖论,从奇幻文学的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寓意出发理解文学的本质,最终触及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的定义问题。
[1]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 ith W ords[M].Oxford: Clarendon,1962.
[2]Barthes,R.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trans.L.Duisit)[J].New Literary History, 1975(6)2:237-272.
[3]Br˚ne,G. and J.Vandaele.Cognitive Poetics.Goals, Gains and Gaps[M].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9.
[4]Chomsky,N.Syntactic Structures[M].The Hague:Mouton,1957.
[5]Culler,J.Structuralist Poetics:Structuralism,L 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M].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75.
[6]Feng,Z.Transl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Wonderland [J].Neohelicon,2009,36(1):237-251.
[7]Forster,E.M.Aspects of the Novel[M].Harmonds worth: Penguin,1963[1927].
[8]Fowler,R. Linguistics and the Novel[M]. London: Methuen,1977.
[9]Fowler,R.Literature as Social D iscourse[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
[10]Gardner,M.Hexaflexagons and O therM athematical D iversions:The First ScientificAm erican Book of Puzzles and Gam es[M].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88.
[11]Gavins,J.“Too much blague?”An Exploration of the TextWorlds of Donald Barthelme’sSnow W hite[C]//J. Gavins and G.Steen.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03:129-144.
[12]Gavins,J. and G.Steen.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C].London:Routledge,2003.
[13]Halliday,M.A.K.Language as Social Sem iotic[M]. London:Edward Arnold,1978.
[14]Herman,D.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C].Stanford,CA:Center for the StudyofLanguage and Information,2003.
[15]Posner,M. I.Cognition:An Introduction[M].Glenview, IL:Scott,Foreman&Co.,1973.
[16]Saussure,F.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C. Bally&A.Sechehaye(eds.).W.Baskin(tr.).New York: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1959;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6.
[17]Searle,J.R.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8]Searle,J.R.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 [J].New Literary History,1975,(6)2:319-332.
[19]Semino,E and J.Culpeper.Cognitive Stylistics: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C].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2.
[20]Stockwell,P. 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M]. London:Routledge,2002.
[21]Tsur,R.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M].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1992.
[22]Tsur,R.Deixis in Literature:What Isn’t Cognitive Poetics?[J].Pragmatics and Cognition,2008,16(1):119-150.
[23]封宗信.语用学、文体学与文学研究 [J].国外文学, 1997(3):24-30.
[24]封宗信.论文学语篇理解的认知心理学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22-28.
[25]熊沐清.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新接面——两本认知诗学著作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40)4:229-305.
[26]赵元任.译者序[C]//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