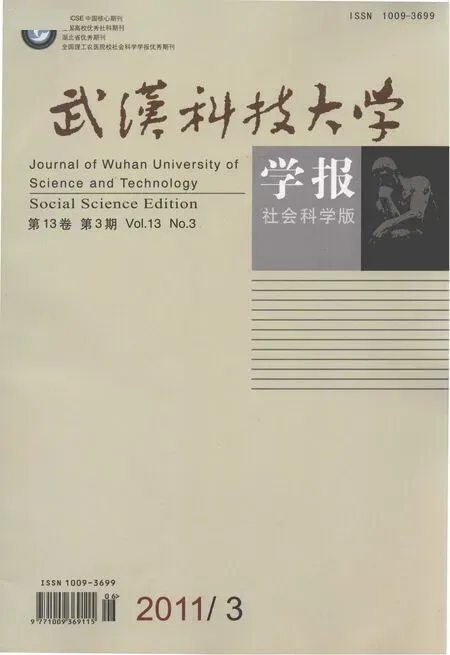试析赫尔德走向历史哲学的契机
2011-03-20陈艳波
陈艳波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作为十八世纪德国重要的思想家,赫尔德对后来在德国兴起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影响非常深刻。就对历史主义的影响来看,赫尔德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的德国人理解历史的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讲求普遍性的理性主义时代,赫尔德强调了一种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待和理解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生。在赫尔德以后,很多德国思想家都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事物和人自身。其次,在强调每个时代和民族有自身独特价值的同时,赫尔德还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的目标和意义,并提出了他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基础之上的“人道”思想。这种从整体来考察人类历史的方式使赫尔德成为“思辨的历史哲学”①英国哲学家沃尔什把历史哲学分为两类:分析的历史哲学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研究人的历史认识何以可能,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则探讨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参见沃尔什著《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的先驱,后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历史哲学的典型体现。这两个方面也成为了赫尔德历史哲学的核心主题。
然而,作为在理性主义时代生长起来的思想家,赫尔德并不是一开始就关注历史哲学问题,他对历史哲学的重视和思考经历了一个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不管是在哥尼斯堡求学期间(1762~1764),还是在里加任牧师期间(1764~1769),早年的赫尔德主要兴趣都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上,而以1774年出版的《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为标志,赫尔德的主要兴趣转向了历史哲学,从那以后,历史哲学成为他思想的核心主题。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赫尔德思想的转变?这其中的思想契机是什么?我们认为促成赫尔德转变的思想契机主要有两方面②这段时期是赫尔德人生境遇和思想状况都比较混乱的时期,不少传记作者都未能梳理出这段时间赫尔德思想的清晰线索。当然本文也不打算对他此期间的生平和思想做详细的描述,只是探讨在这段时间促成赫尔德转向历史哲学的重要思想契机。:一是赫尔德从启蒙运动中学来的“分析的方法”,另一个是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一
二
早年的赫尔德,特别是在里加任牧师期间,其主要兴趣在于文学批评和美学。这从他在此期间发表的著作可以看出。1967年赫尔德公开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关于近代德意志诗歌的断想》,这篇文章主要强调了民歌的意义以及民族语言对于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批判了当时教育中的唯拉丁化倾向。另外几篇文章是赫尔德针对当时美学问题的争论而撰写的,汇集为《批判之林》(1969)。《批判之林》总共有四篇文章,第一篇是赫尔德对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的一些美学观点的质疑;第二篇和第三篇是赫尔德与当时古典美学的捍卫者克劳茨的争论;第四篇中赫尔德比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上的美学观点。虽然《关于近代德意志诗歌的断想》和《批判之林》的前三篇都是匿名发表的,但是还是有人得知了它们是赫尔德的作品,年轻的赫尔德也因此而小有名气。
但是以赫尔德在布克堡时期(1771~1776)发表的《人类最古老的文献》和《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为开始,思想成熟时期的赫尔德对历史哲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对人类历史的思考成为他思想的重要主题,甚至是唯一主题。
赫尔德从文学批判和美学转向历史哲学,这其中的契机首先在于把启蒙理性理解为“分析的方法”。近代启蒙运动对理性作为方法的理解发生了分歧:一方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演绎-综合法”,对理性持这种看法的思想家相信人拥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自明观念和原则,通过它们可以建立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整个人类知识的大厦;另一方是牛顿开创的“归纳-分析法”,认为理性只是一种分析的能力,它只有在经验和现象被给予出来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运用,它分析的程序是把一个给予出来的现象追溯和还原为一些简单的要素,然后再根据这些要素来解释现象。两派围绕着理性的本性展开了争论,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经验主义认识范式和理性主义认识范式①关于把理性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认识范式的内容可参见卡西尔的《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维塞尔的《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贺志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相关章节的讨论。。正是这种把理性理解为“分析的方法”本身蕴含了历史地看待事物的可能,即这种方法的使用使得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因为分析法的实质是认为研究事物就是把事物分解和还原为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或者追根溯源地去了解事物的最初原因,然后再根据这些基本要素或最初原因来理解和解释事物。这种方法运用在人文科学领域必然是历史主义的。因为要理解人文领域的现象就必须去追溯它的原因,找出它的根据,然后根据事物自身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来解释它,显然,这已经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理解事物的方式了。在这场理性作为方法的争论中赫尔德毫不犹豫地跟随他的老师康德选择了“归纳-分析法”作为自己研究哲学的方法②关于康德对由牛顿开创的"分析法"的推崇和采信,请参见康德的《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他在《关于近代德意志诗歌的断想》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看法:“如此哲学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分析的方法……所有真正的哲学概念都被给予(given)给哲学家。”[1]对“分析法”的采信,使得赫尔德不管是研究美学还是从事文学批评,抑或进行古典语言的钻研,都是从一个现象的起因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来进行研究和理解。
因此,早年的赫尔德对于文学和美学的研究方式已经包含了历史主义的因素。赫尔德把从康德那里学来的分析法用来理解语言和文学,他不是从理性的自明原则开始推理,而是从开端和发展过程来理解它们。当他觉得已有的历史知识对于理解一部文学作品来说还不够的话,他就会大量地搜集和了解相关的背景资料,有时甚至是不甚相关的材料在他看来对理解作品也会有帮助。显然,这种看待和理解事物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把赫尔德导向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只是对年轻的他来说,这种对历史的关注只是为他的文学和美学研究提供背景,文学的研究才是他的目的。
分析法这种理解事物的方式,使赫尔德逐渐认识到事物之间是内在地普遍联系在一起的。当赫尔德以分析事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主义方式来研究美学,或者把对诗歌的理解放在具体的文明和时代背景中来考察的时候,他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非常自然的一步,他就可以实现一种转变:把美学和诗歌看作是时代精神和历史的一部分,看成是历史的体现,而不只是用历史来说明美学和诗歌。
赫尔德的思想正是在他对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实现着这种转变。我们可以通过赫尔德对莪相(Ossian)③莪相(Ossian),古代爱尔兰说唱诗人。1762年,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James M acpherson,1736~1796)声称“发现”了莪相的诗,他假托从3世纪凯尔特语的原文翻译了《芬戈尔》和《帖木拉》两部史诗并先后出版,于是这些所谓“莪相”的诗篇便传遍整个欧洲,对早期浪漫主义运动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这些作品虽有部分是根据凯尔特语民谣写成的,但大部分是麦克菲森自己的创作。关于“莪相”诗篇真伪问题一直是批评家研究的一个课题,直到19世纪末,研究证明,麦克菲森制作的不规则的凯尔特语原文只不过是他自己英文作品的不规则的凯尔特语译作。至此,关于莪相的争论才得以解决。学术界一致认为,被浪漫化了的史诗《莪相集》并非真正是莪相的作品,而于16世纪前期整理出版的《莪相民谣集》才是真正的爱尔兰凯尔特语抒情诗和叙事诗。赫尔德当时读到的莪相的诗是麦克菲森的创作。诗歌的研究来说明。赫尔德对于莪相的狂热兴趣来源于他把《圣经》看作先民所创作的真实诗歌,以及他对莎士比亚和克洛卜施托克④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赫尔德很推崇他的诗歌。等人的诗歌研究[2]143,他想在这些民间诗歌中做一些比较。可是由于赫尔德严重缺乏对凯尔特语的背景知识,他不能像对待其他诗人的作品那样也对莪相的诗歌采用历史批判的方法。他狂热地阅读和莪相诗歌相关的一切材料,虽然最后他知道自己阅读的莪相诗歌的版本有可疑之处,但他还是根据已有的关于凯尔特人的知识对莪相的诗歌作出了评价,并谨慎地把莪相的诗歌当作支持他关于凯尔特人一些观点的材料[2]143-159。可见,对于莪相的研究已经使赫尔德注意到诗歌以及整个文学对于理解历史的重要性。文学作品本身是历史的一部分,一旦我们理解了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历史。正是对莪相的研究经历促使赫尔德从把历史当作文学作品的背景来研究转向了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这正如对赫尔德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吉利斯·亚历山大(Gillies A lexander)所指出的:“毫无疑问的是,正是研究莪相所产生的困难促使了赫尔德的思想从文学批判到历史哲学的过渡。”[3]195
启蒙时代的“分析法”使赫尔德从文学批判最终转向了历史哲学的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从事文学批判,必须大量地了解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而文学文本自身是历史的一部分,理解了文学文本反过来也必然加深他对文本所产生的历史时代的理解。这就是赫尔德从文学转向历史哲学的动因和实质。赫尔德在这里遇到的其实是一个“解释学的循环”,部分和整体的循环、单个文学文本和历史整体的循环以及个体作家和时代精神的循环。早年的赫尔德是从部分来理解这个循环,部分是他研究的目的,整体是他实现目的的手段;而转向历史哲学以后他从整体来理解这个循环,作为整体的历史才是目标,而作为部分的文学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促成赫尔德转向的正是他所采信的“分析法”。
从整体来理解“解释学的循环”,那么历史领域最大的整体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这也是运用“分析法”研究事物必然导致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为了充分理解历史上的事情,唯一的道路就是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否则就是在用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事物来解释另外一些我们更不了解的事物。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往前推进。
1769年5月,赫尔德离开里加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他先后去了丹麦、南特、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等许多国家和城市。这次旅行不但使他了解了更多异国历史和文化,也使他进一步思考历史哲学问题。通过这次旅行他明确地表达要把人类历史的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认为,为了理解这个整体,需要了解人类迄今为止所产生的一切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他在旅行途中写的《1769年游记》来说明这一点。在这篇游记中他计划将来写作一部《人类史》、一部《人类史年鉴》和一部《人性的教育纲要》①关于赫尔德《1769年游记》的中文介绍可参见曹卫东的《赫尔德的一七六九之旅》,载于《读书》,2002年第6期。。这篇游记是赫尔德对整个人类历史哲学思考的告白,他在游记中这样呼喊道:“一部关于人类的著作!关于人的精神的著作!关于地球文明的著作!一切空间!时间!民族!力量!混合!形成!亚洲的宗教!……大题目:人类不会消失,直至一切发生!直至大彻大悟的天才布满了地球!世界教育通史!……”[4]32-33这是一部非常宏大的人类历史写作计划,对人的心灵、对人类整个历史的研究成为他这篇游记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德并没有因为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而放弃他的文学批判,他在《1769年游记》中所制定的宏大写作计划也没有完全把文学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只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赫尔德对文学的批判不再只是为了提升德语和德国文学的地位,相反,他是把文学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文学成为他理解人类历史的手段。这一点我们从赫尔德在这段时间出版的专著《关于莪相的书信选》和《论莎士比亚》中就能得到证明。比如在《论莎士比亚》中,赫尔德把莎翁的剧作与索福克勒斯做对比,认为我们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因为他们产生自不同的历史时代。“戏剧产生在希腊,正如它不能产生在北欧一样。北欧的戏剧不可能和当初希腊戏剧的情形一样。所以,北欧戏剧不是也不能是当初希腊戏剧那个样子。所以,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两回事”[5]。另一方面,赫尔德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来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认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吉利斯·亚历山大就曾指出:“他(指赫尔德——引者注)试图通过深入地研究莎士比亚来更好地理解莎翁所生活的时代——这是他心中渴望研究整个人道历史的伟大抱负的一个部分。”[6]
三
当赫尔德把历史不是当作文学批判的背景,而是作为研究目的本身的时候,当他以“分析的方法”,因而也是以起因和发展过程的方式来看待整个历史的时候,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人类的各种文化和艺术都是一个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整体,那么这个整体的意义是什么?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赫尔德在《圣经》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带着这样的问题来看待《圣经》的文本,赫尔德发现了与他在里加时期对《圣经》的解读截然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对《圣经》“创世纪”一章意义的理解。
在里加时期,赫尔德完全是从历史和单纯文学的角度来理解《圣经》“创世纪”的文本。他认为《创世纪》只是早年的希伯来人创作的诗歌,像研究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他从《创世纪》产生的文化、宗教、地理和历史等背景来研究它的产生和特点。在这种理解下,《创世纪》就是先民的民歌。卡岑巴赫对赫尔德早年研究《创世纪》的历史主义特点也进行了说明:“当他(指赫尔德——引者注)离开里加的时候,他的行李里就有一篇题为《东方国家考古学片段》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主张,创世纪并不包含有教义,它无非是一部东方国家的诗歌而已,它的基础就是感性印象,就是对民族信仰的看法,甚至包括民众的完全错误的意见,就是充满了民族感情的想象力的盲目的作品。”[4]55可见,在里加时期的赫尔德对《圣经》的解读完全是建立在“分析法”之上的历史主义的方法。
但是赫尔德在1770年遭遇的一次沉船事件彻底改变了他对《创世纪》的看法。那一次赫尔德打算乘船经过布鲁塞尔前往阿姆斯特丹,然后再乘船去汉堡。可是当船进入荷兰海岸线范围的时候,一场强烈的风暴打翻了他所乘的船。这艘小船在海水中挣扎着,被海风和波浪无情地撕扯着。赫尔德并不确定这艘船是否会被风浪彻底打沉,以致使他葬身于此,他只是在船舱里面呆着,带着午夜惊魂的心情来感受莪相的诗歌中曾经记述的相似的情景。后来,当船上的人都被岸上派出的救援队成功救出以后,这艘船就被海风巨浪撕成了碎片。正如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T Clark)所比喻的那样,这次风暴对于赫尔德来说“几乎是一场极富象征意味的风暴”[2]109。因为这场风暴让赫尔德有机会真实地感受到了启示和信仰的作用,让他深刻地理解了早年希伯来人诗歌中所体现的那种启示和信仰的精神。这一事件升华了他在里加时期单纯从历史和文学角度对《创世纪》的理解。现在他认为《创世纪》是上帝的启示,它作为启示就体现在诗人理解和叙述上帝创世的故事当中,研究《创世纪》就是要去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这种信仰精神,要从启示和信仰的角度去理解诗人的讲述,理解上帝创世故事的真实含义。我们也可以从吉利斯·亚历山大在谈到这次沉船事件对于赫尔德的影响所作的评论来说明:“正如他自己(指赫尔德——引者注)在那个难忘的早晨在微光与寒风中所经历的上帝持续存在的力量那样,他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世纪故事当中所包含的所有生动内涵和鲜活意义。正如哈曼曾经教导的,他在自然中感受到了上帝。在这个他做了一个根本发现的早晨,因此也被认为是创世纪中的那个黎明不断发生的象征。他认识到,上帝必然通过他的造物来显现自己。”[3]198
我们结合赫尔德思想中的另外两个背景来看这次沉船事件对他的影响,那么他转变对《创世纪》的看法就更容易理解了。首先是他幼时从他母亲那里接受的敬虔主义思想。赫尔德所在的教区以及他的父母都信奉敬虔主义,尤其他的母亲更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派信徒。母亲的路德派信仰对赫尔德的影响非常大[4]4-5。虽然赫尔德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但是他始终对神秘主义和宗教体验抱有很同情的理解。成年以后的赫尔德还专门研究过路德和中世纪的神秘主义,深入研究过宗教感情。敬虔主义的真精神在于强调信徒内在的宗教体验,强调在直接的宗教经验中感受《圣经》和上帝的启示,坚信启示只有在信仰中才能获得理解。赫尔德敬虔主义的思想背景无疑对他从宗教的维度来理解沉船事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外是哈曼思想的影响。改宗后的哈曼是一位非常虔诚的路德派信徒,他相信所有的自然事件包括人的语言都是神圣的符号,都是上帝临在的象征,“所有自然的现象都是迷梦,视觉表象和难解之谜,它们都有着隐秘的含义。自然和历史这本书中有的只是密码和暗号,而《圣经》才是解开它们的钥匙”[7]。赫尔德还在哥尼斯堡时就和哈曼相识,并且成为忘年之交,虽然他们之间曾经一度发生过分歧并因此而断了几年的交往①这里主要是指当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这篇论文出版以后,哈曼本着他神秘主义的立场对赫尔德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方法进行了批判,赫尔德觉得他曾经的朋友不再能理解他,所以和哈曼断了交往三年有余。,但赫尔德对哈曼的思想是非常熟悉的。这次沉船事件使他重新来理解哈曼的思想,并且重新走向了哈曼的思想。事实证明,在经历了沉船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布克堡的赫尔德重新恢复了和哈曼的交往,并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哈曼的思想[2]168-171。如果把这两种影响结合起来看,那么沉船事件改变了赫尔德对《圣经》的看法似乎就是必然的了。
经历沉船事件后,赫尔德从宗教的角度来解读《圣经》。现在他在《圣经》中寻找的就不只是早年希伯来的诗歌,而是上帝通过《圣经》的启示。卡岑巴赫也指出了这一点:经历了沉船事件后,“赫尔德知道了上帝是不须让人去认识的,上帝是自己显示,上帝只是用这种显示的历史证据对人的内心体验加以影响”[4]55。不过在赫尔德看来,把圣经既看作希伯来先民创作的诗歌又看作上帝的启示并不矛盾,因为上帝正是通过诗人的诗歌创作来显示他的启示,诗人的灵感和创作的诗歌都是上帝启示的一部分。这样赫尔德就把圣经记录的故事既理解为历史事件又理解为上帝通过这些事件的自我显示,上帝启示诗人对这些事件进行理解和评述,实际是上帝的自我理解和评述。
如此理解下的《圣经》就成为了人类最古老的文献。赫尔德在他的《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一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创世纪》不只是东方民族的诗歌,而且它也是人类最古老的文献,对它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希伯来的历史和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增进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解。它既是历史又是理解历史的钥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哲学家的思辨,因为它展现的是上帝的意图和自我陈述,因此在它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从开端来理解人类历史。跟哈曼一样,赫尔德认为上帝对人的教导是通过隐秘的方式进行的,上帝把他的真实意图隐藏在历史和万物当中,历史事件和万物都是上帝意图的神秘符号,只有通过启示和信仰才能破解。赫尔德因自己的重新发现而激动地写道:“上帝就是这样教导的!用图画!东西!事情!全部本性!”“多么纯粹、崇高的表演方式!没有一句话、一个命令、一个忠告,只有静静的榜样和行动;但是这行动和榜样就是上帝的行动和榜样,它从天上到地上,贯穿于世界和人的全部本性。”[4]56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融合了他历史主义的方法和启示的方法:一方面他接受创世纪故事的史实性,认为确实发生过创世纪所描述的故事;另一方面他把创世纪理解为上帝的启示,是上帝在历史中的显现。
当赫尔德以宗教的方式从启示和信仰的角度来理解《圣经》的时候,他所获得的不只是对《圣经》文本的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还为他以前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基础,他所有的思想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一种综合。当以宗教的方式来看他以前的研究的时候,这些研究都显示了特别的意义。不管是文学批评和语言研究,还是心理学和人性教育的思考,都应该以上帝的启示为依归,所有这些都应理解为上帝的自我显示。如同一个作者拥有不同作品,文学、语言、历史和文化等等都是上帝在不同方面的显现。越是深入地研究这些领域,就越能感受这些领域是彼此相连、不可分割的(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作者上帝的作品),越能体会到上帝实实在在的临在。
赫尔德在这种对《圣经》的理解中找到了历史哲学的基础,他可以这样来回答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人类文化和艺术的意义是什么?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是上帝的显示,通过它们可以理解上帝的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人类历史的目的在上帝创世之初已经决定好了,上帝通过他的方式引导我们不断地走向这个目的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上帝创世的意图和人类历史前进的目标,赫尔德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中,赫尔德认为上帝的意图是不可知的;而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赫尔德认为人类可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来学习和领会上帝的意图。。
对莎士比亚的剧作的研究使赫尔德更加确信上帝的创世和上帝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安排。赫尔德很早就开始关注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莎翁的戏剧。还在哥尼斯堡求学的时候,赫尔德就跟哈曼学习英文,并试图跟哈曼一起翻译《哈姆雷特》。后来莎翁的诗歌和戏剧一直是他感兴趣的主要对象之一,1773年出版的论文《论莎士比亚》就是他长期关注和思考莎翁文学作品的成果。在莎翁的戏剧中赫尔德看到了人类的命运。莎士比亚向他显示所有的事件是如何被命运般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事件是如何被一个绝对的主宰所操控和决定着。从剧作家的角度看,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人们的自由意志和付出的努力之间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都被剧作家的手所指引。只是对于这些事件的实际参与者来说,这种必然的联系是隐秘的。“如果有一个来自天国的天使来权衡人类的情欲,按照他们各自的性格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按照各自自由意志的幻相而行动,这个天使通过自由意志的幻相引导着人类,就像被命运之链拖着走一样——这就是在这部作品(指《奥赛罗》——引者注)中作者如何来设想、勾勒和引导事件发展的方式”[8]300。这有如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每个单子都按照自身对世界的表象在自由运动,但是整个世界却有条不紊地运转,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预先设计好的。在上帝眼中,单子自由的运动其实就是必然。同样,在莎翁的剧中,每个演员实际遵守着作者事先为他们安排好的命运,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以为自己是在按自由意志行动。赫尔德意识到:剧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小的造物主,他拥有上帝造物的一切特点,他安排剧本中每一个人物的命运和每一件事件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也是最大的剧作家,他像莎士比亚一样安排着人类历史中的个人和时间。正如剧作家安排演员的命运一样,上帝也为人类的历史规划了某种目的,只是像剧中的演员不知道他的命运一样,我们也不能领会上帝为人类安排的命运。“根据一些命运的法则,莎士比亚在所有可能的时空组合中选择了那些最有力的、最适合的场景来支配人们行动的激情,在这些场景中那些最意外、最无关的要素也支持着主题;诗人是时代变换的创造者,时代的变换最有力地向我们呼喊道:‘这里有的不是诗人,而是造物主!这就是世界历史!’”[8]301莎翁的剧本使赫尔德明白,我们人类的命运也从一开始就被决定好了,一个最高的造物主创造了我们,同时也使我们迈向确定的方向。《创世纪》表明,我们被上帝所创造,我们的命运也必定已被他决定。“这样,我们发现整个世界就只是这个伟大精神的身体:正如每一种性格和思维方式都是这个精神的特征一样,自然所有的场景都是这个身体的组成部分——我们把这个合起来叫作斯宾诺莎的上帝 :‘Pan!U niversum!’(神 !万物 !——引者注)”[8]303
经历了沉船事件和在莎翁剧作的启示下,赫尔德对基督教神学有了新的理解并使他最终走向了历史哲学。赫尔德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中寻找人类历史的答案,因为不管是沉船事件还是莎翁的剧作都向他表明《圣经》才是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人类历史只有从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才能得到理解。在《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当中,赫尔德表达了以下主题: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神圣的目的,这个目的对于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它只能随着历史的发展才能不断地被理解。上帝临在并活动于自然万物当中,每一个事物都有其被上帝指定的位置和价值,按照自然所赋予的全部力量生活就是最理想的生活。
四
以上分析了赫尔德走向历史哲学的两个思想契机——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分析的方法和基督教神学的思想。分析的方法使赫尔德具有了看待事物的历史主义的眼光,使他能够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来看待事物,这为赫尔德从文学和美学研究转向历史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契机。这种方法上的契机揭示了分析的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赫尔德在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出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重新来定位和思考赫尔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赫尔德站在情感和个体的立场来反对启蒙时代那种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的普遍和抽象的历史观,所以他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和反启蒙运动者。但经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赫尔德对人和事物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启蒙运动自身对于理性的理解,分歧在于启蒙运动自身对理性作为一种方法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如果把理性理解为笛卡尔的“综合-演绎法”,那么赫尔德确实是一位坚决的反理性主义者。但如果是从牛顿的“分析法”来理解理性,那么赫尔德历史主义的方法正是在启蒙理性的孕育下产生,他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其实是启蒙运动的一种自我批判,是启蒙理性对自身理解的深入。这正如卡西尔恰如其分地指出的:“尽管赫尔德尔远远超出了启蒙思想界,他与他的时代的决裂却不是突如其来的。只有沿循启蒙运动的足迹,他的前进和上升才有可能。时代锻造了最终战胜自己的武器,它提供的清晰性和一致性理性确立了赫尔德尔的推论所依据的前提。因此,赫尔德尔对启蒙运动的征服是一种真正的自我征服。启蒙运动的这些失败之一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胜利,而赫尔德尔的成就其实是启蒙哲学最伟大的精神凯歌之一。”[9]
在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赫尔德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它的意义。虽然赫尔德对人类历史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①《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是赫尔德在布克堡时期的著作,而布克堡时期是赫尔德宗教感情最浓郁的时期,他完全是从一种神秘主义的神学观点来看待人类历史,对人类历史的目标和意义充满了不可知论的观点,这在本书中有充分的体现。而在魏玛时期,随着赫尔德对当时科学发现的不断了解,他试图把新的科学发现也纳入到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在这一时期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赫尔德表现出融合当时的自然科学发现和基督教神学观点的努力,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也努力实现这两者的结合。,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始终是赫尔德看待人类历史的重要维度。在他成熟的历史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赫尔德在把整个人类历史看作是上帝的一项隐秘的计划基础上,发展了人类历史是不断走向“人道”的思想。在他看来,“人道”就是人类不断地从尘世走向天国,逐渐地在自己的历史中发现上帝的创世目的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丰富和越来越接近上帝的无限过程。
[1] Robert E No rton.Herder’s aesthetics and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M].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47.
[2] Robert T Clark.Herder:his life and thought[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 rnia Press,1955.
[3] Gillies A lexander.Herder’s app roach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J].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1940,35(2):195.
[4] 卡岑巴赫.赫尔德传[M].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 张玉能.赫尔德与狂飚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6] Gillies A lexander.Herder’s essay on shakespeare:das Herz der Unteruchung[J].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1937,32(2):278.
[7] Frederick C 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M].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21.
[8] Johann Gottfried Herder.Selected w ritings on aesthetics[M].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9] 希尔.启蒙哲学[M].顾伟铭,杨光仲,郑楚宣,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