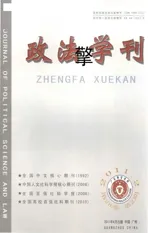公安执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
2011-02-18罗一龙
罗一龙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了严禁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但并未明确规定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效力问题。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文件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79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对治安案件的调查,应当依法进行。严禁刑讯逼供或者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通过这些规定,通常认为“我国已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0年7月1日,两院三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现状
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适用现状有以下问题:
(一)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不明确,导致公安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识不统一
根据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人员采取“刑讯逼供以及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然而,这一界定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界定很不明确。如,何谓刑讯逼供?通说的观点,刑讯逼供主要是指侦查人员采用拷打、肉体折磨的方法获取供述的行为。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侦查人员对嫌疑人采取残酷的精神折磨,诸如“药物催眠”、“车轮战”、“疲劳战”是否属于刑讯逼供?如果是,那么是否该禁止?如果禁止,那对一些司法现象如何认识?如,经常有这样一些报道:“我公安干警不辞辛苦,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经过XX小时的突审,终于XX”,这一方面是对干警工作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否是对“车轮战”、“疲劳战”的默认或者放纵;其二、何谓“威胁”、“引诱”、 “欺骗”?是含混不定的。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并不必然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且威胁、引诱和欺骗往往还是一种侦查讯问手段,在各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手段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也即并没有完全被禁止。其三,非法证据的范围不确定,仅仅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而未合理涵盖通过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和非法羁押等取得的实物证据。这些非法实物证据是否应以排除?其排除是否具有可行性、合理性?其四、未合理区分违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违法程度以及相对人被侵害权利性质上的差异。也即没有区分“证据瑕疵”和“证据违法”。以一份无民警无签名 (或者只有一人签名)的询问笔录为例,依照《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公安机关执法细则》要求,这显然属于程序违法。但侦查人员据此制作的询问笔录是否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在各地法院所作的相关判决对此所持的态度亦不尽一致。
正是因为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不明确,导致公安机关及干警对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很困惑,一些干警对自己取证行为是否违法,往往凭经验、习惯、自身认识去判断,导致“非法证据”界定标准的多元化,从而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统一适用。
(二)非法证据的证明主体不明,证明责任不清楚
公安执法中,一方面,非法取证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较为严重地存在着;而另一方面,这些非法取证行为通常又极难在后续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等程序中被证明。由于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地规定由何人对“非法证据”承担证明责任,因此,实践中的证明责任往往是由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检察机关分担。但这种证明责任的分担不具有合理性。首先,由公安机关自身证明证据的非法性不具有合理性。公安机关作为证据的收集者,如果自身发现收集证据违法情形,总是要想方设法进行修正 (或者说是掩饰),由它来证明自己取证的非法性根本不可能,因此,公安机关不应成为非法证据的证明主体,而是取证合法性的证明主体 (或者说是非法证据的审查对象);其次,由犯罪嫌疑人承担证明责任不具有现实性。实践中往往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公安机关机关取证程序违法的证明责任。而犯罪嫌疑人因大多处于被羁押状态,特别是审讯过程的对外封闭性,通常难以对审讯过程的违法性作有效的证明。因为,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羁押,其人身自由实际上被控制在侦查人员手中,即便在讯问中发生了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也根本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除非刑讯逼供极为明显诸如造成人体残疾等极端情况。况且,通常只有到了法庭审判阶段,才能对刑讯逼供问题要求法庭进行调查,而此时时间已过数月甚至更长。再由被告人承担证明刑讯逼供发生或者“有罪供述”系侦查人员非法取得的责任,显然属于强人所难。如果说对于刑讯逼供的存在,让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属于强人所难的话,那么,对“威胁”、“引诱”、“欺骗”是否存在的问题,让犯罪嫌疑人承担证明责任,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手段基本上是通过言语的方式进行的,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供被告人向法庭提供。即使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帮助,但律师取证手段有限或者不能充分行使,难以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和依据。加之一些律师心存顾虑,不愿得罪侦查机关,参与排除非法证据的积极性不高,律师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再次,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不具有可行性。证据的收集者主要是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检察人员对侦查活动并不直接参与,自然难以履行证明责任。
正是因为证明主体不明,证明责任不清楚,导致公安执法中涉及是否“非法证据”问题时,公安、检察往往互相推诿责任,最后不了了之。
(三)检察院监督的失位和法院裁判中立的缺乏,助长了公安执法中的“非法证据”存在
要排除公安执法中的非法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院监督的是否到位和法院的裁判权能否保持最基本的中立性。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约束公共权力的程序性制裁,非法证据的排除不是对侦查机关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程序性谴责,也不仅仅是为纠正程序性违法行为而存在的,它是实实在在的法律制裁,通常还会导致警察、检察官甚至法院直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程序性制裁的实施还存在放纵“真凶”以至于使国家惩罚权无法实现的可能。如果检察院监督失位和法院不能在审判过程中保持必要的中立性的话,那么程序性制裁的实施只能流于形式。在我国,检察院并不直接参与侦查活动,对公安执法中是否存在“非法取证”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后再去查证,这是一种事后监督、形式监督,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对于法院而言,由于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也很难在审判中保持应有的中立性。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是“互相监督、互相配合”的关系。在这一原则的影响下,指望法院排除通常在证明力问题上并没有太大问题的所谓非法证据,以至于影响对犯罪打击,这无论是不具有现实基础的。从新闻媒体所披露的一些案例来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即使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院通常也会采取规避甚至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拒绝将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纳入法庭裁判的对象。即使个别法院允许被告方提出有关侦查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问题,并给予控、辩双方调查和辩论的机会,但这种调查和辩论并不存在独立的听证形式,而基本上是依附于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并将其作为法庭审判的一个枝节问题而存在。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请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法庭的拒绝。当然,这一拒绝有时是以较为艺术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即法院在其判决书中根本不“谈”非法取证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在不少执法者们看来,建立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有的甚至明确主张,对于那些刑讯逼供获得的“有罪供述”,如果经查证确实“属实”的话,就不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可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适用的对策
(一)在立法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规则”,为公安机关界定非法证据提供统一标准
法律规范由“要求人们去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第一性规则”和“以各种方式决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的“第二性规则”所构成。[1]783学者习惯将前者称为 “实体性规则”,后者中的审判规则称为“实施性规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相关“实体性规则”的立法。其要旨和核心是以法律规定 (或者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非法证据的内涵。这就要求,第一,对刑讯逼供要作明确性规定。尽可能以列举方式对刑讯方法进行描述,如以殴打、捆绑或者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肉刑或变相肉的方法;对“车轮战”、 “疲劳战”是否是刑讯方法要作出说明,可以通过设定每次讯问的时间限定和两次讯问的时间间隔等内容对其规范。第二,威胁、引诱、欺骗问题要作明确界定,区分“非法取证”的威胁、引诱、欺骗与正当侦查手段的威胁、引诱、欺骗的界限。第三,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对一些程序上存在瑕疵的证据,采用可补正的排除,给办案人员补正的机会。第四,界定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对非法言词证据,可采取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可采取相对排除的原则,并以概述式对非法获取实物证据的方法进行规定。
只有通过立法 (包括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规则”作出明确规定,才能为公安机关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提供统一的模式,为其取证行为指明方向。
(二)明确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加重公安机关对取证合法的证明义务
“谁主张,谁举证”的观念认为被告方作为“排除非法证据”这一主张的提出者,当然应承担证明责任,有些甚至要求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这一做法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具有合理性。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应对“非法证据”的证明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一般由控诉方承担,被告方只要提供线索即可启动排除程序,无需承担举证责任。即凡是被提出异议的证据,控方必须证明其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否则,推定为非法证据。这样,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据时负有双重义务,一方面要收集案件证据,另一方面要收集取证行为合法的证据,向检察机关移送案件时,两方面证据都要移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一并审查、采集证明侦查人员取证行为合法的证据,一旦被告方在庭前或庭审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动议,公诉人员当即就能够举出证据,一方面打击了被告人的侥幸和抵抗心理,另一方面也可改变过去那种在庭审中被告方提出证据存在非法问题,公诉人员事先没有准备,而重新进行证据采集和审查工作的状况,保证了指控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第二,证明标准问题,1)应适当的降低被告方程序启动的证明标准,不能要求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被告方只负初步的举证责任,这种初步的举证责任的设置起初步的过滤作用。2)提高控方“实体性”证明标准,公安机关的证明应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程度,应该明确规定禁止使用说明性材料,规范公安机关对取证行为合法的证明方法。
加重公安机关对取证行为合法的证明义务,可以更好地约束公安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如公安机关要证明自己不存在“刑讯逼供”问题,由于其证明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程度,又禁止使用说明性材料,因此,公安机关只能采取讯问时律师在场、全程录音或录像、讯问前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体检等相关配套措施来证明,这对公安机关的取证规范化建设也是一个推动作用。
(三)改变程序工具主义执法理念,树立保障人权和依正当程序控制犯罪的执法理念,使文本形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化为执法主体的理性观念和自觉行为
1.公安机关要确立“程序正当”的执法观念
严格执法应当包括严格执行实体法和严格执行程序法,忽视哪一方面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格执法。在公安执法中,不但要在实体上,而且更要在程序上切实依法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程序的“形式主义”作用,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人治执法现象的发生。尽管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侦查并不能绝对地保证实体结果的客观性,然而,正当程序却能够在人类智识所及的范围内通过诸如保证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等具体的程序性设置力求使定案证据的客观性达致最大化。实体公正最终只能在程序的框架内并通过正当程序得以实现。马克思曾经指出: “程序法是实体法的生命形式”。刑事诉讼是一个由公安、司法人员收集的各种证据回溯案件“事实”的历史证明过程,在客观上此时并“没有任何独立的、参照它即可知道一个确定的结果是否正义的标准。”[2]82因此,实体正义不能游离于程序而独立存在,没有程序也就没有正义。即使在执法者出于破案甚或控制犯罪的高尚动机的情况下,亦不能由此证明其所采取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取证行为的正当性。
2.公安机关要树立“人权保障”的执法指导思想
公安机关对犯罪的追诉活动仅仅是国家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有效行使的手段之一。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违法手段收集证据,其行为自身则是与“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这一刑事诉讼的终极目的直接相悖的。因为“目的不能使手段正当化”[3]250。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追诉过程中“不得克减”涉案公民的核心基本权利。刑事取证工作,要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之规定,保障公民“免受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待遇或刑罚”、“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等权利,即使“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的情况下,国家亦“不得克减”其所承担的保障公民享有此类权利的义务。由此为公安机关的刑事取证行为确立了一条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逾越的底线。即使公安机关在均衡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基于保护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在刑事追诉活动中不得不对涉案公民的自由等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时,亦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明确授权的相关程序规定慎重行事,而不能片面地为了追求破案率置公民的基本权利于不顾。
(四)加强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法院确立公正审判的价值理念,为遏制公安机关的 “非法取证”提供有力保障
人民检察院不是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而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对公安机关的“非法取证”负有监督职责。要求检察院树立“惩罚与保护并重”的司法理念,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察微析疑,严把证据关,并结合工作实际以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第一,建立非法证据的初步认定机制。对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况进行类型化总结,经办人在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初步怀疑时,必须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并向侦查人员调查核实取证的相关细节;第二,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汇报机制。经办人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时,必须向主管领导汇报,并最终决定是否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及要求其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第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监督机制。经办人须就排除非法证据的整个过程建立监督档案,并进行保存,以便对整个过程进行跟踪监督;第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激励机制。在办案干警发现重大非法证据并最终成功加以排除时,对办案干警进行一定的奖励,以有力促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
法院要以公平审判尤其是“过程中心主义”等价值观念为指引。要明白法庭审判过程中一系列程序规则的设计并非单纯是为了确保案件真相得到最大限度的发现,而主要是围绕着如何确保公正审判尤其是审判过程的公正性这一目标而进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来意图显然不应是保证证据的可靠性和相关性,而主要是为了抑制侦查人员的程序性违法,并以此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果法院把自己看作是政府设立的打击犯罪的工具,以至于对追诉犯罪表现出过多的热情,甚至把自己看作是控诉方的伙伴或战友,以至于成为事实上的追诉机构,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不予以排除,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得不到禁止,那么法院事实上就是在纵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因为它使得控方能够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取利益。
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法院的公正审判是排除公安机关“非法证据”的两道屏障,也是两项救济措施。只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消除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侥幸心理,促使他们转变执法观念,有效遏制公安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
[1]陈瑞华.程序正义 [A].陈兴良.法治的使命 [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79.
[2]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3]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洛克.政府论 [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