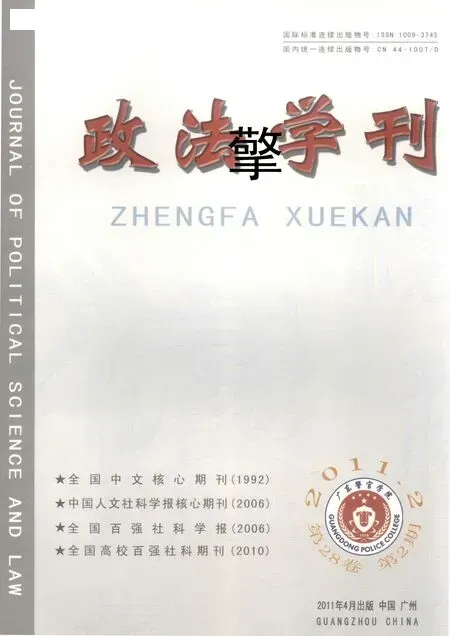矫正技术语境下的行刑个别化
2011-02-18胡配军
胡配军
(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3)
近年来,出于对刑罚执行改革与质量提高的需要,行刑个别化在我国刑罚执行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尤其在监狱领域,一些监狱理论研究者将行刑个别化当作提高罪犯矫正质量的不二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少数监狱已经在为此进行新一轮的矫正技术实践探索,行刑个别化一时成为中国监狱当下话语中的热词。但热词只是表像,热词背后,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监狱当前面对行刑个别化的若干无奈,更要对此进行理性的思考。
一、行刑个别化的含义辩析
何谓行刑个别化,这是一个目前仍有歧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不理清,会严重影响甚至误导着监狱矫正活动的走向。
从源头上看,行刑个别化应当萌发于新派刑罚理论的刑罚个别化思想,而真正的起因当归于刑罚的社会防卫目的与罪犯矫正思想,因为矫正指向每一个犯罪个体的身心,从而必须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矫正措施,才能更好地实现矫正目标,最终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应当说,行刑个别化的源起并没有太多的争议,但行刑个别化究竟是何含义,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个别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可以看作是“个别问题个别处理”,也可以看作是“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别性”。进一步分析个别,就会发现,个别可以是整体中的特殊个别,如我国的个别教育,它不是对每一个罪犯都必然实施个别教育,只对特定罪犯实施特定内容的个别教育。个别也可能被理解为整体中的每一个普通个体,如监狱通过各种心理测试,对每一个罪犯建立的个别化的心理档案。在“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别性”这点上,个别既可以被理解为每一类人之间存在差别,也可以理解为每个人之间存在差别。因此,在行刑个别化的内涵理解上,有人认为,每一个罪犯被定罪处罚本身就包含了量刑的个别化和行刑的个别化,每一个个体被判处的刑罚均是个别化的刑罚,已然的犯罪不同,个体因此受到的处罚也不同。显然这是对行刑个别化乃至刑罚个别化的误解。因为无论是刑罚个别化还是行刑个别化,首先是在刑罚的指向上由犯罪行为转向了犯罪人,只有将犯罪人作为定罪处罚的根据才谈得上刑罚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有人认为,行刑个别化是以个体人格为基础,对罪犯个体进行的个别化行刑,这里的个别被理解为每一个实在的个体,实践中的一人一策、个案矫正当属这一观点。然而,当我们将行刑个别化中的个别理解为就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罪犯时,由于数量众多及相关条件要求的限制,我们很难在现实的生产力条件下实施这样一种矫正活动,显然,这样一种理解并不妥当。一向主张因人施罚的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也视这种行刑个别化为在“美国监狱学者中特别时髦”但“必须避免的极端”。①(注)菲利这里所说的行刑个别化是指美国监狱根据每个犯罪人的情况,进行处罚的制度。而不是指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进行处罚的制度。参见[意]恩得克·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那么到底何为行刑个别化呢?笔者认为,行刑个别化中的个别,不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进行的区分,而是从群体的角度来进行的类别区分。它不是由一个个罪犯个体构成的个别,而是由这些个体经过分化归类,组成若干个类别。行刑个别化强调的是对这一类别的罪犯应当在矫正上有别于其他类别的罪犯矫正,以至形成了行刑个别化。实质上讲,行刑个别化应当是基于类别的行刑个别化。在类别基础上,鉴于行刑即是处遇,行刑的着力点体现为处遇的区别对待,行刑个别化也就是处遇的个别化,不难想像,每个监狱在特定时期,都可以为每类罪犯设定一类处遇层级,或为一类罪犯设定多个处遇层级,但哪个监狱也不可能做到为每个罪犯设定一个有别于所有他犯的处遇层级。
二、行刑个别化的矫正模式与经验应用辩析
不可否认,理论上讲,在罪犯矫正问题上,走行刑个别化之路犹如医生给病人对症下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必将有助于促进罪犯更好的矫正,已有的实践已经给出过这样的答案。但是当下中国关于行刑个别化,不仅理论研究储备并不充足,而且实践探索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且理论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索并没有完全合辙。理论上设计的对每个罪犯个体的个案矫正与实践探索中选定个体进行的矫正本来并不是同一回事。前者试图实施对每一个罪犯一人一策地进行矫正,而后者有可能认同这一设想,也可能是为了积累经验,另作他图。事实上,行刑个别化是有条件的,在现实的生产力条件下,行刑个别化并不允许我们对每一个罪犯都实施基于个体人格差异的个别化矫正,而只能让我们做到从有选择的罪犯个体着手,经过实践探索,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粹取其中精华,抽象成矫正模式,施加于各个类别的罪犯身上。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关于罪犯个体矫正的经验与教训,它不能直接复制粘贴到其他罪犯身上,只能由研究人员经研究处理,变成矫正同类罪犯的矫正模式。这就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虽然一人一方,但又是有归类的的类别化处方,而不是无穷尽的一人一方,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笔者看来,模式可以复制,而经验与教训难以粘贴。这又进一步说明,如果我们要在每一个罪犯个体身上实施个性化的矫正,则不仅矫正活动在技术上被孤立,同时,我们也付不起巨额成本。
三、行刑个别化的依据与价值分析
历史上,刑事法领域的个别化首倡于龙勃罗梭的刑罚主观主义也即行为人主义、完善于德国学者沃尔伯格在1869年提出的刑罚的个别化,[1]169这种个别化的提出,使刑事处罚发生了从回顾已然的犯罪到关注犯罪人的转变。所谓关注犯罪人即是要关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根据这种危险性确定应当判处的刑罚,[1]169也就是通过多长时间的监禁能够使这种危险性得以消除,以此为契机,又有了消除人身危险性从消极等待到主动出击,通过矫正措施的实施使罪犯按照矫正主体的预定目标与方向,发生正向的改变,从而演绎出学者们旨在提高矫正质量的行刑个别化的良心发现,学者们还前赴后继地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理性设
计。[2]167
(一)行刑个别化的依据
行刑个别化源于刑罚个别化,是刑罚个别化在执行领域的个别化,也是刑罚个别化非常重要的方面。行刑个别化的依据包括两个方面:思想依据和实践依据。
1.思想依据
行刑个别化理论离不开对罪犯矫正思想,是对罪犯矫正思想的路径设计。
贝卡利亚认为: “预防犯罪优于惩罚犯罪”,预防犯罪就要矫正罪犯。美国著名政治家本杰明·拉什明确主张分类矫正犯罪人,实行行刑个别化。李斯特认为“罪犯矫正与教育只有通过刑罚个别化方能实现”。[3]428萨雷伊更是直接要求:“法律必须赋予监狱机关足够的主动性与灵活性,以便监狱机关能够随时调节具体的惩罚活动,从而可以满足罪犯教育矫正的实际需要,这就是所谓的行政上的个别化。”[2]174
2.实践依据
在倡导行刑个别化的学者们看来,犯罪人“应被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的轻重不能仅根据犯罪的客观危害事实,而应该以犯罪人的性格、恶性及反社会性的强弱为标准”,“据此实行刑罚的个别化,从而达到社会防卫的目的。”[4]283由此观察,行刑个别化的实践依据根本上在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这种危险性又促成了社会防卫与罪犯矫正思想的产生,为了矫正罪犯实现社会防卫,就必须在罪犯矫正质量上下功夫,显然借鉴医学经验,区别对待,对症下药,对不同的个体施以不同的矫正措施,会取得更理想的矫正效果。
(二)行刑个别化的价值取向
在运作路径上,行刑个别化发端于刑事犯罪的犯罪人,是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着手进行个别化的配刑与行刑。这种人身危险性的考量与分析不仅包括了对犯罪人个体的人格因素的考量与分析,也包括了犯罪人已然的犯罪行为及后果的考量与分析,因此,在价值取向上,行刑个别化既要通过惩罚的个别化以报应正义,[2]176体现法律的公正担当;同时行刑个别化更要通过对犯罪人矫正的个别化,旨在去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实现防卫社会的政治目的。行刑个别化的两重价值既二律背反又二律背合。一方面,报应正义与防卫社会在矫正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报应与防卫互相制约,报应必须兼顾防卫的需要,而防卫不能超越该当的报应。当防卫与报应直接冲突时,防卫必须服从于报应。[2]176另一方面,报应与防卫又是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矫正效果的实现——去除人身危险性,防卫社会。报应通过惩罚,剥夺犯罪人既有权利,警戒犯罪人改过自新,不再危害社会从而起到去除人身危险性、客观矫正犯罪人、实现防卫社会的效果。[2]180没有惩罚就没有矫正;防卫以各种具体的矫正技术,直接着用于犯罪人的身心,去除危险性、促进犯罪人思想与行为的转变。
四、行刑个别化的实践路径辩析
历史上,由于对刑罚个别化的不同理解,就一直存在关于个别化具体操作的分歧。在行刑个别化问题上,这一分歧在我国当下的监狱也客观存在。因为个别化是针对犯罪人,首先要关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在一些学者看来,人身危险性是罪犯人格的体现,要通过人格调查,然后实施个性化的人格改造。一些监狱也试图通过人格调查、心理测试,然后制订出罪犯个案矫正计划,为每个罪犯量身定做具体的矫正实施方案。其中也有些学者从矫正罪犯、去除人身危险性出发,更是主张应当对罪犯实施不定期刑,这样更能突出行刑个别化——即使同样的犯罪,因为个体人身危险性去除时间的长短,从而决定了罪犯个体服刑时间的长短。也有些学者认为,行刑个别化的实践是在罪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类型矫正探索、实施矫正分类、分类处遇、个别教育与矫治。两相比较,虽然前者也并不排斥罪犯分类,但追求的是矫正的个别化包括处遇的个别化,教育的个别化;而后者主要强调是通过分类,根据罪犯个体的具体情况,分成若干类别,使每一类别的处遇与教育显著区别于其他类别,其中也有少量的个别处遇与个别教育,但只是特例,不作为范式。理性地看,虽然每一个罪犯个体人格及其人身危险性存在着差别,但是若干罪犯个体集中于一个监狱时,我们又可以通过分析归类,将罪犯归入某些类别,因而通过分类矫正,类别化处遇与教育,辅助以少量的个别处遇与教育,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当下对行刑个别化的实现路径最现实的设计。对每一个罪犯都实施区别于他犯的个别化矫正不具有可行性,也没有必要。从国际行刑领域的历史演变看,上个世纪曾在西方风靡一时,而今已由喧嚣归于沉寂的正是这样极端的行刑个别化。那种主张实施不定期刑的观点只是考虑矫正与防卫社会的需要,忽略了行刑个别化, “以实现刑罚的报应需要为主”,[2]180更不可行。当然类别基础上的行刑个别化,首先必须选择若干个别典型进行矫正技术探索,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矫正技术应用模式,然后应用于同类别的其他罪犯的矫正活动过程,这一意义上的行刑个别化与过去的分类改造在运作方式上又存在着显著区别。
五、当下我国监狱行刑个别化的实践举措辩析
近年来,在行刑个别化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一些监狱开始了行刑个别化的实践探索,从探索的具体举措来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步骤:一是进行罪犯个体的心理测试与人格调查;二是实施罪犯个体的矫正分类;三是制订矫正个体的矫正方案;四是应用劳动、教育、心理矫治等矫正技术实施矫正。应当说,实施的步骤及相关的举措在理论上都是适宜可行的,但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一)行刑个别化的人格调查问题
从惩罚与矫正犯罪人出发,了解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认清其人格状况,便于矫正措施有的放矢。但人格调查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需要对罪犯个体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罪犯过去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等进行详尽的调查,并作出综合判断与分析,才能弄清罪犯的人格状况。人格调查在量刑时就必须进行,在行刑时需要补充调查。而我国目前的量刑阶段,法院对犯罪人的配刑主要还是侧重于回顾已然的犯罪行为,酌量考虑犯罪时犯罪人的具体情形,除少数可能被处以非监禁刑的刑事案件外,基本上不作人格调查。缺少前置的人格调查,监狱对罪犯进行的人格调查主要是关于心理状态的问卷调查,显然要根据这样的一个简单化的调查得出罪犯个体的人格状态结论是不靠谱的。
(二)行刑个别化的矫正技术问题
行刑个别化无论是出于哪个层面的考虑,都最终依赖于技术支撑,否则个别化没有任何实质意义。那么,行刑个别化的技术到底是什么?有多少人掌握了这些技术?已经应用的效果如何?这些都值得注意。在技术问题上,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人与技术的结合,如对罪犯进行人格调查与评估的监狱民警必须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在当下的监狱,拥有这种知识结构的民警究竟有多少,能否满足进行相关工作的实际需要,这都是问题。由于行刑涉及到国家政治,出于服务政治的大义需要,有些人会不顾实际地将一些未经验证的所谓技术当作矫正罪犯的普世良药,而应用的结果却是并未起到什么实效。这在西方国家行刑个别化的实践历程中已经出现过太多的事例。若干新技术名词名噪一时,但都未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对于我国当下的行刑个别化的技术探索而言,必须要经过大量的个案实证,验证,方可推出某类罪犯的矫正技术,切不可只在纸上谈兵,然后就加以实践应用,不论是否得到验证,又马不停蹄地广泛推进。
(三)行刑个别化的成本问题
行刑个别化需要在矫正方面给予更多的投入,包括人、财、物的投入,这必然加大行刑成本。现有生产力水平下,我国的行刑活动必须要考虑成本。因此,在行刑个别化问题上,行刑资源的成本核算将制约着监狱对行刑个别化的选择。务实地看,由于监狱的警力有限、监狱获得经费保障有限、监狱的矫正设施设备与手段有限,以少量的民警惩罚与改造数倍于自己的罪犯,想实施个别化矫正在精力投入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除非走类别基础上个别化矫正之路,否则难以做到。而有限的经费及各种物质设施的局限也制约了我们对数量众多、人身危险性情况不定的罪犯矫正,很难针对一个个罪犯个体的实际情况,在财与物上按需保障。
(四)行刑个别化中的罪犯需要满足问题
人皆有需要,每个人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服刑期间,由于行刑限制,罪犯的需要受到抑制,但每个罪犯仍有自己的需要,只是有些需要可以满足,有些需要无法满足,即使在普通公民那里是正常的需要,在罪犯这里也无法满足。罪犯个体不同的需要,为行刑个别化提供了实践的着力点与根据,抓住罪犯不同的需要,给予满足与控制,就可以实现个别化的处遇与矫正。但罪犯个体的需要虽然是有差别的,但若干罪犯需要汇集到一起时,根据不同的归类标准,仍可以将这些需要划分成若干类别,从而分类满足需要。有必要指出,尽管在需要问题上,根据罪犯个体需要的不同,实施个别化的满足在理论上最具有可行性,但实质上,监狱能够满足的主要并不是罪犯个体的纯个性化的需要,有些纯个性化的需要由于需要本身的非正当性,或由于不具备满足的条件,本就不可能满足,能够通过激励措施满足罪犯的需要一般只是在刑事奖励、行政奖励、物质奖励、离监探亲、精神奖励等方面,而这些奖励作为满足罪犯需要的具体内容,是多数罪犯都需要的,只是侧重点不同,满足的情形不同。
[1]董淑君.刑罚的要义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翟中东.刑罚个别化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3]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