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税笔记(1990—1996)
2011-01-31李俊平
故事一:“停当”和“董达”的堂客
这里的“停当”和“董达”是我按方言的发音写下的,意思是贤惠和不贤惠的堂客。为了听的原味,就用这四个字代替了。
男人为自家地里的事与另外一家的男劳力发生了纠纷,两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捋袖子、瞪眼睛、在空中挥舞着拳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旁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们。这样的事在农村不说天天有,但时有发生的。而看热闹是人们在地间休闲的最好娱乐了。男劳力的一句话刚好伤了男人的最痛处,男人说:“今天我不废了你,我就不是男人!”男劳力说:“有本事你就来!”男人看看手中的锄头,往地下一扔,飞步就往家赶。回到家,就直奔挂在墙上的长刀。女人刚好在家做饭,拉住男人说:“快把我灶堂(膛)里的火掏了,不然饭就焦了。”男人一甩手,刀就上了另一只手,女人说:“我的饭好了,要打架也要吃了饭去打,有劲也少吃点亏。”男人望着女人,女人说:“来,坐下吃饭,吃完了我们一起去打。”女人在男人犹豫的片刻,就把饭端上了他的手。男人吃完饭,突然觉得不那么气了,而女人的眼睛就一直没离开过男人的脸。男人望着女人的眼睛,心里自我嘀咕着:我刚才干嘛要回来拿刀?他突然对“刀”这个字眼生出一丝恐慌来。一场流血让这个“停当”的女人化解了。
再回过头来说男劳力,他的堂客急急地赶到地里,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让人家欺负,还好意思站在这里。”男劳力站在那越想越气,一挥手中的锄头,就要撵上门去。这一挥倒好,就挥到了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的头上,把人家的头磕开了一口子,鲜血直淋,这一下人家不依了。那“董达”的堂客说:“鬼叫你站在他背后,磕到活该。”这一句话说的,被磕的人不顾疼痛,两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天昏地暗,拉都拉不开。最后闹到派出所,男劳力赔了几百块钱了事。好好的休了场的事件,让这“董达”的堂客搅和成一滩(摊)烂泥。
这个故事,歇户的男主人和我在一个冬夜唠下的,而故事中的“男人”就是他自己。他说,男人这辈子啊,得遇上一个“停当”的女人;如果碰到一个“董达”的堂客,你就有罪受了。
故事二:留下你的麻袋
老彭家是我们税务所收税时落脚的一个点。他家在离我们单位三十公里的地方,因着他妻子的贤惠和老彭自己的热络,只要去了他那个地方,我们都会提前打好招呼,晚上会上他家歇脚。那时交通是极不便利的,骑着自行车下去,一呆就会是几天。老彭家从我到税务上班之前就是(税务局的落脚点)了,接触以后,才知老彭这人真的是没话说。你来一次他热情,你来多次他还是周到,没有一定的心胸,谁会做到呢?何况那时税收一个小店一年也就收百把块钱,你不收他,他也是贴本的买卖。如果我们要是说了,他说:“跟你们打交道,怎么能说生意上的话呢?你们到我家,是看得起我老彭啊。”实际上我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亏着老彭呢。
老彭从改革开放时就开着小店了。按理说他应该早步入先富的行列,可老彭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是很钻营,他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有那样就行了。”有时问起他家的情况,他老婆会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于是我们税务所的老同志就对老彭说:“老彭,你讨着一个好老婆呢。”老彭就“嘿嘿”地笑。
老彭没什么事的时候喜欢喝点酒。如果有哪一家客气的话,留我们吃饭,我们会叫上他。他从不忸怩,他不是忸怩的人,这也是我们能长交的一个原因。在酒席桌上,无论怎么拉,他是不坐一席的,拉急了,他会说:“你们是领导,我怎么能坐一席呢?”他这不是忸怩,是坚持了。在酒席上,几杯酒下去,因着和我们接触得多,他会说上与税有关的话,并且头头是道,结尾还会着重一句:“税务所的同志也辛苦着呢!人家是为谁啊?”常常听得我们竟然激情满怀,你说怪不怪?
我们一起的都是些没结婚的小伙子占多,在枯躁(燥)的乡村,寂寞的夜晚,老彭还真是为我们打发过不少。有时酒过三巡,就要老彭说诨(荤)话。一般是要推辞一番的,但喝过酒就不用了。老彭会打开话闸(匣)子,说他年轻时的乐事,说着说着,会说不说了不说了,我现在不行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了。我们笑着,实际上他已说完。我想着,什么人他都会有故事呢。
那天在老彭家里吃饭,也许是大家白天都跑累了,没有谁提议要玩,就都早早地睡下了。同屋睡的老同志,临睡前在屋角的有陈尿的便桶里尿了一泡,那味道当时差点让我窒息,可又逃离不了,最后用毛衣捂住鼻孔才睡下。老彭在店堂里看店,一个人睡,本来因尿骚味想过去跟他睡,想想还是算了。
老彭睡到半夜,突然地就醒了。借着微弱的光,他发现窗子外有人用长长的铁钩伸进来,在极力地钩他家店铺里的布;第一反应告诉他,有小偷。老彭睁着眼睛想:好大胆的贼,我家可住着税务所的同志,这么些人在,你竟敢来偷我的东西。哼,等会儿老子叫你偷鸡不成蚀把米。老彭睁着眼睛见他用铁钩钩住成捆的布匹,再钩进布头,收钩,用手拉着布头;他一边拉着,里面的布就滚着。老彭又想:狗日的,老子等一下让你装布的麻袋都给我吓留下。老彭准备喊了,又想,等一下再喊,他还没装进。老彭就睁着眼睛心里笑呵呵地想着。

天刚蒙蒙亮,老彭的老婆来收拾店堂,老彭一个激灵爬起来,大声地喊道:“留下你的麻袋!”吓得他老婆一大跳。
吃早饭的时候,老彭边吃边跟我们说他昨夜的事,当时笑得我一口饭就喷出去了。老彭说:“我怎么又睡着了呢?你们说说,我那时候怎么就睡着了呢?”老彭不但没让贼留下麻袋,还白白损失了两卷布,说着的时候,脸上满是不解。他不解他怎么会睡着,却没有懊恼;只有他老婆边盛饭给他边说:“你这个人哪,还想留下人家的麻袋,哪天自己被偷走了都不会知道。”我在想,谁会把老彭偷去呢?
焦大爷
一起下乡收税,到纳税户家是免不了要自我介绍的。比如人家问,同志你贵姓啊?我们都会答,姓胡或者姓张。轮到焦大爷,他会说:“我是焦家老屋的。”听的人就自言自语:哦,姓焦。此时焦大爷则非常的沮丧,他处心积虑的回答,还是让人家说出他最不愿说的两个字。这时我们就忍不住地笑出了声,纳税户被我们笑得一脸的茫然。
焦大爷本名不叫焦大爷。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我们综合他的禀性,说,你今后干脆就叫“焦大爷”得了,免得人家问你,你绕一个圈子还得回到“姓焦”上来。他想了想,也就默认了。因为“姓焦”和“性交”同音,焦大爷忌讳。但叫他焦大爷还是改不了他“姓焦”的本姓。就是一口说焦大爷,有时还是逃不了要“姓焦”的事实。焦大爷是叫出了名,可依然还是改变不了介绍时令人尴尬的局面。同事们下去搞检查都愿意和焦大爷一个组,疲乏的时候,一句“姓焦的”就笑得解乏了。
其实,焦大爷并不大,只是我们因他有忌讳才这么叫他。他和我高中是同学,读书的时候一天到晚腋下夹一副象棋,逢谁有闲就下,棋艺不见长,兴趣倒是越来越浓。我们是高中生,他的模样看起来却像个初中生,个头不高,一双眼睛上下左右,很少停歇。他进教室是火风,出教室像冲锋。高考落榜,因着上辈的关系就到税务所当起了协税员。财校毕业后我刚好也分到了他所在的税务所,这样我们就由同学变成了同事。在一个单位,又常常一起下去,由于对焦大爷叫得久了,对他的真名我们几乎都已忽略了。

焦大爷骑自行车的技术,在税务所是一流的水平。他能够不扶车把和我们骑得一样快。他结婚早,我们还不知另一半在哪的时候,他的孩子就在他肩头了。远远地,如果你见有人骑着自行车,肩头驮个孩子,一只手扶龙头,一手扶孩子,不要问,就是他了。可他收税的水平和骑车的水平就刚好相反,遇上难缠的纳税户,我们戏称他三斧子下去不见效的话,就没戏了;回来后,领导批评他,他赌气丢下一句,这税不是人收的。领导很生气,焦大爷就很难看。他因几次收税的挫折,要回家不干,被他爹又赶了回来。税务所协税员的待遇是非常低的,工作大家还是要一样的做。我劝说过他,我说你这样回家又能干些啥呢?他说,他村里谁谁在外面搞了多少钱,他也要去挣大钱;我说,你算了吧,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那块料。

所里任务逼紧了,焦大爷会找上我陪他跑上一两天,效果明显但收益不大。收税这项工作真的不是字面上理解的意思,不是你一说“法”,对方就交了;而是与你平时同纳税户的交流和多接触密切相关,还有你整个管区的纳税次序、公平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老话说,要钱如割肉呢,不动点脑子还真就不好收。焦大爷收税到哪都是一阵风,和他骑车一样快。上户了,说声,有钱没?把这个季度的税交了。对方说:焦会计啊,我这一天到晚都没生意,哪有钱交税啊?我是真的想交,可就是拿不出来钱啊。焦大爷这时就有点蒙了,不知应对,丢下一句我下次再来就走了。而这样的情况在大部分纳税户身上都会发生。他劳(徒)劳无功的时候就多了。
遇上人多一起下乡检查,焦大爷就显得很兴奋。因为他不用单兵作战,还可以适当地在人后,不用上前。我说,姓焦的,你这样可不行,这是你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你以为是陪你玩啊?焦大爷脸就红,可红过他还是那样,有什么办法?但在酒席桌上喝酒,他还是能应付一下的。同事们送他个外号“焦八盅”,也就是说,他一次酒量八盅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是那种五钱的小盅子。所以每次喝到八盅,同事们就不逼他了。喝多了,就发些奇谈怪论。什么收税不如回家摸鱼,会叫的鸟不如下蛋的鸡,上班是为了不让老爹爹气死等。有人就说,你爹爹不是为你好啊?他说,他是为他自己。很多的谬论,大家也说服不了他,随他去。
老婆第二胎给他生了个儿子,他就嚷嚷:“我还是要回家做生意,不然养不大。”
焦大爷最终还是没有离开,尽管工作中他少不了受训挨骂。他管区的任务,在那时每年一度的大检查中,我们都会集中一段时间,帮他清理了。这样就挨到了九四年,朱总理给他带来了福音。税务机构国地分设,他爹给他买了个商品粮户口,让他一下子就变成了正式的税务干部。像他这样的有着一大批活跃在我们税务战线上。成了正式税干的焦大爷,在工作能力上还是没有一点提高。收税对他来说还是照样的难,唯一的变化是听说他恋上了赌博。虽然分家时他进了国税,但我们还是在一个院子里办公,见到他是常有的。见面了,我说:焦大爷,听说你赌上了?他说:我发现这社会就麻将桌上公平,全凭各自的手气,输赢都痛快。我说,你这是什么混账逻辑,这社会哪点对你不公平了?你从协税员摇身一变为国家干部。你别让人家卖了你,你还帮他数钱。他一脸笃定地说,不可能。
很有些日子不见焦大爷,毕竟不在一个单位,要各忙各的事。有一天听分局的一位老同志说,焦大爷一晚上输了一万一千块钱,说着边摇头:焦大爷啊,焦大爷。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古道热肠。遇见焦大爷的话,我以为他一定会很颓废地懊恼。可真见他,他说,手气真差,钱让老爹给补上了。一副功德圆满的样子。我心想,他那在税务系统退休的爹,总有一天会让这单传的儿子给活活气死。
焦大爷骑摩托车的水平在我们这个地方也称得上一流。一只手骑摩托对大家来说不希(稀)奇,关键他能体现一个“快”字,另一只手遇到紧急情况他还是不拿出来。我说,你玩命呐?他一脸竟然单纯的笑,我还真是不解。他有许多让我不解的行为,比如任务完成不了,他自己就把税票开出来,替纳税户先垫上;再比如纳税户说什么他都相信,还有他一个月不回家,他老婆不吱声,他敢把屠户的女儿带回来睡觉。我说,你真的不愧我们叫你“焦大爷”啊。
焦大爷好像长不大,我们一逮眼就看出年近不惑,他看起来还像个高中生。时常还是能见到他急火火地在乡间收税,还是时常听说他输钱;偶尔碰面,他还说那句老话,这税不是人收的,有朝一日我还是要出去。听了也就听了,我也懒得去反驳,我知道没有人暂时能改变得了他。他在自己的思想里一直很愉快地走着,不上进但也不那么潦倒。他还在认为麻将凭手气,人生无需太努力,他这一路都是这样走来的;他唯一说过的理想就是出去挣大钱,他也就是说说,一直没兑现,但他还没有放弃。有时工作上原因在一起了,我总改不了要说上两句的毛病,我说你不要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国税收入不菲了;你有这样的境遇是你的造化。他听了,进不去。他说,我是吉人自有天相,你们只有一个孩子,我有俩;你在地方部队我还是国军;你读了那么多年书是收税,我读了那么点书也是收税。我说,姓焦的,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接着说,焦大爷,我要写写你。就写焦大爷,猴年生人,现年三十八岁;说话的时候眼睛上下左右,不停歇,有着貌似的单纯。他说,你写就写吧。于是就写了这篇,以为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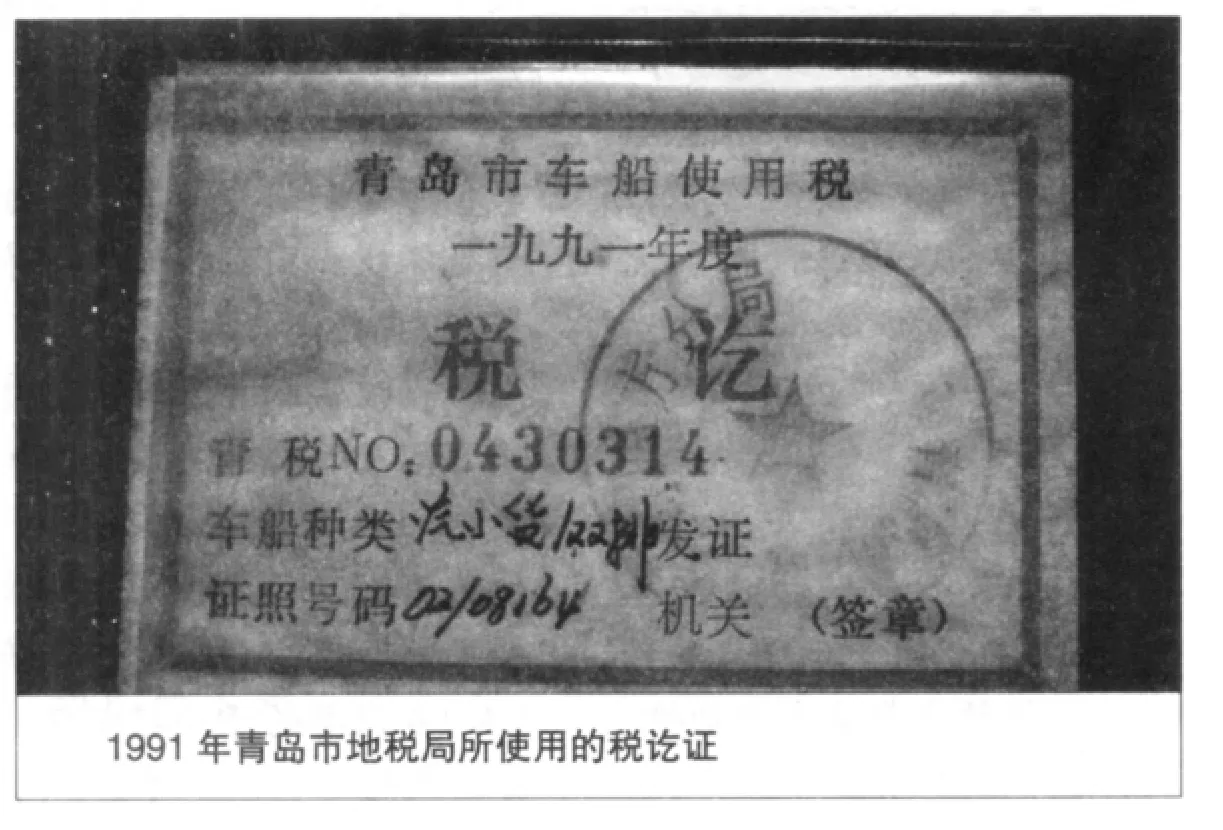
伏击
收税的经历中,曾经有过像打游击战争。埋伏、出击、交手,最后以正义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告终。期间的斗智、斗勇而不赌狠,很是有趣。单兵出击是很危险的,集体性的作战成了必须。尽管这些年的管理在理想的模式里,向征纳之间的“零距离”迈进,但依然不能杜绝这种冲突的真实存在,这样的际遇在每年的国家税事报告里都会有记载;一个领域一旦存在着斗争,就会有牺牲。我们不容忽略,也不能忘记。而在我的收税生涯中,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九十年代初期,对生猪市场的税收实行“三定一分”的管理政策,即集中宰杀、集中检疫、集中交税、分散经营。这项税收政策的出台,无论对税收的管理,还是对老百姓能吃上放心肉,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对交税户——屠商来说,则会由过去的诸项不正规而走向正规。由不正规向正规化的转变,任何领域都缺乏主动性,何况以杀猪为生的屠工,由来已久,都是些泼皮泼赖户,更是变着法子玩花样,想着方子偷逃税。而作为主管机关的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和他们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偷税和反偷税的战斗。而这场战斗的主力军,就由我们一群年轻人组成了。
生猪税收以前的管理模式都是实行核定征收方式,收效甚微。因其经营的特点而注定,散、乱、无固定场所和从业人员众多,征收难度可想而知。实行“三定一分”的政策,屠户不是小学生,能够排队进学校;为了不进点宰杀,同时更为了偷逃税款,无所不用其极。内销白肉我们可以上门查验,也是查不胜偷;尤其是偷杀的生猪大量地运往周边的城市,成为逃避税收的最大漏洞。正常的进点户对此也是怨声载道,心理慢慢失衡,如何堵住这道口子,不仅仅是税收收入的需要,更是“三定一分”政策能否成功实行的首要保证。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偷宰的屠户一般都是深夜出门,用三轮车、农用车、自行车三种交通工具,在午夜过后到天麻麻亮的这段时间里,选择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陆陆续续出县。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有望风的,有打前哨的;还有(人)专门游荡于小镇刺探税务所的行踪。了解到这些,我们及时跟所领导进行了汇报,并做出了周密的伏击计划。偷宰户出县进入周边的城市,只有两条路,而且每条路都只有一个出口;一个出口叫堤湖,另一个叫上闸。上闸近,堤湖远。我们向领导建议,一是制造假象,让不去的同志们在所里打牌给探子看;二是放前哨——骑自行车的,堵大车——农用车。具体到两条线的安排,领导让我们随机应变。在一个下弦月的秋夜,我们一行六个人悄悄出发了。
在路上我说,我们安排两个人在路途较远的堤湖,再从食品部门抽调两人;大兵力我们得用在上闸,也从食品调两人来。有人持反对意见,说,大量的白肉肯定会从堤湖出去;我说他们一定会从上闸走。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也会认为我们要是伏击的话,一定会在堤湖;二是探子会把我们不伏击的消息带回去,他们更会选择从上闸过。
我们一行到达伏击地点已是深夜十一点,附近的住户基本上已睡了,只有不多的几户人家还亮着灯,许是勤快的女人在做着针线活,也可能是在等着夜归的人儿吧。我没事就想象着灯下村妇的模样,是恬淡的引线还是焦灼地蹙眉,或许是农家的辛苦,还在忙碌着吧。我们潜伏引来了几声犬吠,一声即起,众犬应声,给夜平添了几分惊悚。犬声由近即(及)远,及至零落消失在夜的别处。这样一个安静的夜晚,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要发生呢?我们忐忑着,有一丝丝恐慌,夹杂着兴奋。衣服穿得较少的同事在午夜过后,感到了夜的冷。烟还是要抽的,谁知我们的伏击(对象)在哪一个点到来呢?夜把一切都藏着,藏住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提供了便利。
时间在我们静静的等待中流失。因为有等待,感觉时间是那样地缓慢;还是因为有等待,我们竟感觉到夜有了重量,沉沉地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头。指针已指向凌晨两点,来路的方向没有一点动静,只有夜的风拂动着树梢,夜鸟已眠了。蹲点旁的野草,湿透透的。手指如果不小心舞上了巴茅,它细蜜(密)的尖刺就会划你一道长口,绝对有血珠子沁出。
到三点的时候,真的有人要睡了,大家甚至怀疑今夜会是我们一方的坚守。就在这时,听见了自行车的声音,待他骑近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车后挂着的猪肉,闪着些微的白光。大家一下子兴奋了,按原计划,放行。悄悄跟踪他过了出口,见他卸下了白肉,在草丛里藏好,四处望了望,我们在黑暗处大气不敢出。他骑着车又向原路返回了。
烟是早就灭掉了,手电筒攥在手心,生怕不小心按亮了它。后面轰轰烈烈将要到来的是他们的全部。大约过去了十几分钟,又有两人骑着自行车出现了,后面也带着白肉;带队的说,放行,看来今天晚上他们有大量的外运,不然怎么一探再探?我们看着那两人出口向市区方向去了,赶忙搬来农户门口的树段,拦在了出口处。并且整体向他们来的方向推进了一百米,以防他们硬闯。
机器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这样的深夜,听起来感觉像是春雷,有一丝欣喜的惊恐。终于来了,来了就好。我们六人分两边站好,待农用车开近的时候,一起打开手电筒,用突然的光明逼停他们。轰鸣声慢慢地传入耳鼓,前方的路还是黑暗,他们竟然没开灯行驶!我们打开手电的同时,车子突然加快了速度,灯也亮了,射向通往市区的方向;带着灰尘,溅起路边积水的水箭,车子把这一切甩在我们的身上,向前奔去。一百米,我们积蓄了一个晚上的力量,紧跟着飞奔的车,一起到达彼此的终点。
任何不法,一旦人赃俱获,辩白已显多余。狡辩还是有的,但也只有声而无音了。这次伏击,我们共查获二十一头偷宰的生猪;当我们从草丛里把那藏着的猪肉搬上车的时候,骑车的那位,痛苦的表情里夹杂着更多的是不解。

堤湖方向的由于没有亲见,这里只做简单的记录。一辆三轮车在同事们伏击的时候,和我这边一样,强行冲关。由于事先没设障,一同事在追击当中被车子挂倒摔伤,但最后还是成功堵截。
等到我们把截获的白肉押运到食品部门的时候,天已大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