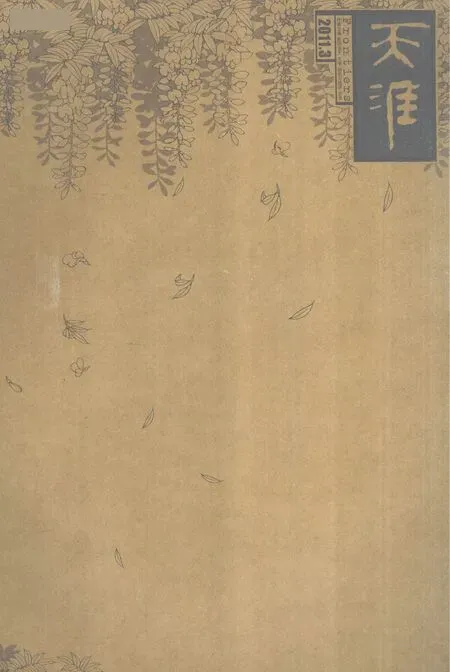当文学遇上音乐,作家也是歌手
2011-01-31李皖
李皖
一股文学雅韵正在当下的民谣界暗涌。钟立风、万晓利、周云蓬……这几位民谣界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人物,衣冠楚楚,神思悠悠,他们唱出的不再是普通的歌词,而是诗。
钟立风歌曲的文艺味越来越浓。
《疯狂的果实》、《她为我编织毛衣》这两张2009年的专辑,把他对文学的钟爱推向了极致。2010年最新EP《那个晚上我把灯光调得比较暗》继续向前。忘掉酒吧里的形象,忘掉在民谣里抚弄琴弦的羞涩男生,这歌里的人不再是人们熟悉的小钟,而是一位诗人,一位现代主义作家。
出版专辑的同时,钟立风也出书。他的书名叫《像艳遇一样忧伤》。三百页的口袋书,几十篇短短的、通常只有一两个页码的文字:随想、闪念、幻想、奇遇、离题、浅睡;奔跑、冲刺、跳跃、撒欢、飞翔、迷路、遗忘;短得像三分钟的凉水澡,洁净、精微、禅意,考验你的智力和趣味……不易读却奇魅隽永,像博尔赫斯一样,闪亮的、发光的、西班牙的,一个迷宫,一副散乱的纸牌,一座小径分叉的花园。理解止于理解的发端,放下书,发呆,思想游走到更远的远方。
是的,博尔赫斯。钟立风的乐队就叫博尔赫斯。任什么也不能取代博尔赫斯对他的吸引力。一个电吉他手,一个沉默、短发、秀美的手风琴女孩,一把贝斯,一套鼓,伴着温厚的、男中音的,像人性一样迷人、像温暖一样忧伤的诗人,定义了民谣的“博尔赫斯”。
钟立风的歌曲里遍布了文学的线索,那是记忆曾经到访双脚却一步也不曾踏去的地方,但是,它比日常生活更实在,更具有感知和体验的要义。看看这些歌名吧,《弄错的车站》、《雷米》、《雕刻时光》、《下午过去了一半》、《告别的聚会》、《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没有了你,会使更多的原野悲伤》……那么熟悉。书名,电影,诗歌中的人物,是的,你曾经去过那里,那些秘密的地点,你与作家、诗人、电影导演曾碰头约会的地方。
钟立风的歌曲,是一些带有幻想和奇遇色彩的故事。民谣中本来就遍布了故事,有一个源远流长、流传了上千年的体裁就叫“叙事曲”,但钟立风和以前的民谣歌手不同,讲的不是他自己的故事,不是他看到的、听说的、经历的,他的熟人之中、他的亲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这些歌曲更像是小说,是像谜题般具有断裂和交叉结构的现代诗,是光线强烈而人影模糊的文艺电影,是他写的或是从别人写的那里偷来的,带着确切却难以看清的情节,形成与生活对望并间离的效果。听这些歌,我们仿佛变成了旅人,走到一个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不可能发生的都发生了,但我们完全地信任它,微微的惊讶,嘴巴何时张开,发出了感叹,却没有声音。心里爆响一颗又一颗惊雷,把人生过上几辈子,把梦想做成一千种可能,与虚幻的人一起生活,生活得更高更远,那是一个比真实还真实的世界。
怀着缓慢的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你让自己陷进一段乐曲/或者诗篇的奇异生命
趟过爱的河流/你吮吸着我的寂寞/我想和你,一起/看电影/吃野草莓(《野草莓》)
钟立风的歌曲有一种特别的叙事之美,更有“幻想般的少女/靠在我身上/想着远方”的那么一种状态,出神入化,比叙事之美更特别。那是文学的状态。而歌者,而我们,就在这种出神的状态中,成了“风中奔跑着的孩子/在歌声里摇摆”。
于是,雷米的故事被我们又经历一遍,去掉了顾城经历中的血迹,变成完全的挚爱与浪漫。弄错的车站一次次发生奇遇,巴吉呀、驿丘呀、索妃呀、罕达呀变成了似曾相识的名字,变成爱人,他们弄错了车站就变成故事,就走进我们心里,变成我们自己。而心变得柔软,柔软得像是要融化,像是要甜美得死去,“她的眼泪慢慢就变成了一朵花”。
他带着谦卑的爱意试探你/你怀着不安而甜蜜的表情别过头去/要命的是此刻叫人想死的音乐又响起/于是你就含着眼泪把嘴和他贴在一起(《他带着谦卑的爱意试探你》)
哦,贴在一起。他和她贴在一起,钟立风和幻想贴在一起,唱片外面的人和唱片里面的人贴在一起。这让人晕眩的疯狂,怎么这么快,怎么会变得可能?原因是音乐,那要命的音乐,它像魔王吹奏的风笛,从天而降,让现实变成了魔幻。故事顺理成章地发生了。感动人的故事,爱情。

当然,绝大多数时候,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人再也唱不出别的,只能唱出爱情。但钟立风的情歌还是跟周围的情歌不一样,他恢复了爱情里的羞涩和幻想,当周围的爱情早没有了羞涩和幻想。那是一种近似于最好的爱情之中最好的一味,像是迷药和迷魂的东西。当眼泪和眼泪、嘴和嘴贴在一起,他们周围还飘动着不真实的空气,和一切都变得可能、变得美好、变得奇妙的神秘浪漫。现实正在变成想象,或者颠倒过来,想象正在变成现实,他们嘴和嘴贴在一起,正在变成想象中的人物。哦,这爱情里幻想的本质,哦,那叫人想死的音乐,有人听见吗?
民谣,正在变成一场文学盛事。和这种文学盛事对等,钟立风的音乐和演唱调子,越来越端庄。它郑重、严谨而又嬉戏着,是一次次的神游、入迷、朝圣。“他的演唱表情隆重”,我曾经这样判断。而阿庆,我的一个朋友,这样发挥说:
“他的演唱表情隆重”,这隆重要我理解就像个朗诵时的样子。今天一提到朗诵很多人要笑了,假把式太多,矫情,酸,很倒胃口,可是听钟立风不会笑出来,情感、文艺调调自有它的庄重之处,不陌生。我们在阅读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在自己想事情的时候经常会进入那种状态,情感主导了自己,人性中的东西撕扯着自己,如此剧烈。那种东西真不是平时好意思说出的,因为隐秘,事关内心,大概比情色笑话还难以启齿。可钟立风就能这么来,隐秘、诗意、出离了现实,别指望他说什么直接的苦与乐,他在文学、艺术的美好意象里穿梭,那把嗓子就是魔毯,哪怕是唱的身边的事情,你感觉也是在小说里。这种东西更接近人心隐秘的一面,唱的是悲伤、情欲、美好,那么迷人,可能在他眼里这世界就是如此。
在小县城上初中,晨读的时候偷偷朗读《简爱》,看到窗帘后的简;或者在学校图书馆读到耀武扬威、装腔作势又纯朴善良可爱敏感的菊千代,菊千代,像个女人名字;或者在吵闹的下班路上第一次听到了老柴的“第一钢协”;这些时刻都发生了什么呢?这些时刻的样子大概跟小钟的歌声有点接近。
万晓利本来是个小城崔健式的人物。1990年代末,他北上北京,唱出他那些现场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词。他的《狐狸》(2002),是民工听了都可能叫好,都可能鼓掌、鼓噪、起哄的歌曲。但是,2007年,《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之后,再不会有民工围观起哄,万晓利的周围围满了文艺青年。2010年,部分文艺青年也变得寡然,《北方的北方》闷得来——,足以闷死一头大象。
发生了什么?文艺青年们面面相觑。万晓利头也不抬,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他低下去,低到地下室去,低沉的声音低到地下室的地板下去,那声音没有听众,它面对的,低吟着的,是一个梦。
《北方的北方》的歌词,就是一部诗集。它也记述了人与事。这人与事或者在童话中,或者身处梦境。诗歌与歌谣碰到了一起,像加拿大的作家歌手伦纳德·科恩那样。所不同的是,科恩是嗓子本身就这么低的唱,万晓利是压低到科恩这么低的唱。
在最繁华的街头/你对她撒下了弥天大谎/现在她说这没什么/是啊 这又有什么呢(《不要问星星有几颗》)
最繁华的。当所有人都扑腾在、欢喜于这最繁华的,万晓利表现的是对这“最繁华的”弃绝和绝望。是啊,这又有什么呢?弥天大谎也没什么,又有什么呢?都到了这个地步!
“民工歌手”是什么时候沉寂下去,变成了诗人,没有人知道。现在,他心里的黑暗足以把太阳吞下去,把周围亲切的笑脸、震天的鞭炮、热闹的除夕和春节也吞下去。大年三十的这种心情是非常不寻常的,只可能发生在现实的黑暗和心境的黑暗渐融为一体的场景中,所有坚实的物体如水面摇晃,变得虚幻和不真实:
羞耻地躺在发了霉的祝福里/梦到世界/被那远古的炮火炸得粉碎,大富大贵的不能醒来
有那么一行清泪瞬间划破了黎明/照亮未来的岁月/那依旧纷飞的战火/说/不要沉睡/快来并肩作战(《除夕》)
万晓利做了一个梦,噩梦,不会醒来的梦;他不理解、不认同的世界,就是这梦,而他就生活在其中。
“你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再摔倒/你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再摔倒/你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再摔倒/你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默默默默默默默默祈祷/她和她的平安/默默默默默默默默祈祷/她和她的平安”(《大坝上的奔跑》)。

万晓利展示的诗歌,是幻想剧、梦境或童话诗,黑色的。诗歌中是这些词汇,草原、牧马人、斧头、柴火、槐树、狐狸、兔子、毒药、袖口、老虎、毒蛇、蜗牛、鳄鱼、油锅、獠牙、火把、树奶奶、春姑娘、小毛驴、袋鼠、精灵……这些词,与当代歌词词汇远离。他的表达是强烈而坚定的,像一个个重复和加强记号,砸下去,再砸下去;而他的歌声,闷下去,捂紧烈火,闷死每一粒火星。这熄灭的、正在熄灭的梦话,低沉得难受,完全不让人透一口气。沉闷,枯燥,不愉悦,这样的审美特性本来是歌曲艺术里没有的,只有严肃文学才会有。歌曲面对着听众,不可避免要带有娱乐属性,但万晓利不管不顾,他坚定而偏执地,把这一属性掐灭。
周云蓬的诗歌历史,也许要长过他做歌手的历史。他本来就是诗人,他的诗是可以在正规诗刊,或者在不正规但是更有诗歌品质的文学民刊上发表的。通常,他的歌手身份和诗人身份是分离的。虽然他的歌中有诗,他的歌就是诗,但听众不一定意会到;他的更著名的身份,一向是民谣歌手。一度,《中国孩子》(2007)的轰动效应,让他成为具有底层人民气质的盲人民歌手。
2008年,周云蓬做了件让人意外的事,他把诗人海子的《九月》演唱了。《九月》是海子的名诗,1999年或者更早,一个叫张慧生的无名琴手把它谱了曲。后来张慧生也死了,跟海子一样死于自杀,所以这首歌就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中,只有很少很少的人,天津和北京的、张慧生当年的一些朋友,听过这首歌。周云蓬却将它重新整理,2008年在《清炒苦瓜》里发表。
这成为一首神作。《九月》的谱曲和演唱,是那么恰如其分,让熟悉并热爱海子的人,再一次受到了震动。它甚至把原诗的境界给拓展了,用音乐做到了诗歌做不到的事。而周云蓬的诗人形象,也就分外地突出出来。
由于周云蓬出名的歌手身份,通常在听歌时,听众会把他先联想成一个歌手,然后把他的作品往诗歌上靠。我们很少联想到,这是一个诗人、作家,拿起吉他唱起了歌。这两种联想方式,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2010年9月,这个事颠倒过来。
周云蓬发表了新专辑《牛羊下山》。《牛羊下山》的大部分,是唐宋及其他朝代的诗歌,周云蓬用古曲或者自度曲把它们演唱了。这张唱片给我的感觉,是地地道道、端端正正一个诗人的感觉。歌手?歌手如何唱出一个诗人?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出就是这个诗人自己?
这件事做得很绝。如果说《九月》让人感觉就是周云蓬自己吟出了这首诗,那么,《牛羊下山》的杜甫、李白就是周云蓬本人,不是他在朗诵古代诗仙诗圣,就是他在吟唱他自己,那些词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词。这种跨时空、跨语言的诗歌效果,之于我的惊讶就像杜甫、李白还魂,不,是杜甫、李白就生活在当下这个世界中,是我熟悉的某个朋友一样。
最后一首歌,《不会说话的爱情》,周云蓬自己写词作曲,当然了,白话现代诗。但这首歌的效果完全是顺接着的,是那个刚唱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人,还是那个人。而专辑一开篇根据《诗经》译出的白话,也是这个人,古人作的诗,完全成了今人说的话。一个潇洒的、洒脱的,诗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歌、古代就是今天、今天也就是古代的人,伙计唉,这可真是神了。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不会说话的爱情》)
远行的人/你在哪片云下歇脚/我们黑白条纹的日夜/飞跑过屋顶/鸡进窝了/炊烟蹲在烟囱上/大黄狗蹲在窗前
牛羊从山上下来/我和它们在一起/想你/想你有衣暖身/有食果腹/有水解渴/有我入你异乡人的梦(《诗经·君子于役》)
当文学遇上音乐,当作家也是歌手,现在遇到的这情形,跟19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中发生的,跟罗大佑、崔健歌词里发生的情形,有点不一样。那个时候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拿诗人的诗词来谱曲;或者,是愤怒青年、抗议歌手,琴弦上琴键上流出的歌声里,出现了诗。现在的这些歌词,歌词的属性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们不听那音符,将它们光光溜溜印到纸面上,就是一点也没走形的诗。而这些歌唱着的歌手,放下吉他,就是品位纯正的诗人、作家。也许,今天,在民谣里,我们正遇上一个从来也没遇上过的风雅时代,比曾经有过的风雅都风雅的时代。
由于篇幅所限,我省略了许多事实。这个场景实际上是极为宽广的,不只是民谣界,也还包括它的边缘,它的外围,以至于摇滚、流行音乐,都在越来越多地出现纯正的文学。仅以近一年多来的专辑举例:
洪启《九棵树》:是歌集,也是诗集,其间流有中亚——西班牙文学、文艺的神秘血缘;
刘冬虹与沙子乐队《一个早已成为童话的世界》:他有时也在歌里写小说,写完全不像歌词的散文和思想粗野的思辩;
苏打绿《春·日光》、《夏/狂热》:歌词彻底变成文学语言,他们想作的是概念专辑,也是组诗,以此写一部人间、人生的新“四季”;
左小祖咒《大事》:以前他写晦涩的歌词,写野蛮的小说,像文学地头的野棉花;这张专辑中,野诗人变得晓畅,其可归入口语诗的诗歌美感,即使传统诗界的人也能够意会;
吴虹飞与幸福大街《再不相爱就老了》:2010年中文摇滚乐中最优秀的诗歌文本,有着近乎极端的生命决绝;歌手本来有些局限的嗓音,调制成了令人心疼的虚弱,配合着毁灭的词,美得肝肠寸断;

张敬《惑》:也许张敬更本色的身份,是画家、诗人、作家、青年哲人,作为早年作品的合集,《惑》并不能代表他,但《童年梦》、《性·感》这两首作品,是“歌坛”不可能的歌曲,那是只有作家才会干的……
当文学遇上音乐,当作家也是歌手,歌曲变得不一样了。在此类人物面前,歌坛不再是听众,而是读者;歌声并非响起在秀场、电视频道、舞台,而是一个人的寂寞开启,心思开始漫游——也许在斗室,也许在路上,也许,在一册册书或一部部电影里,远方的人和事物,幻象一般,翩然而至。
音乐,是我忠贞的妻子。
文学,是我最大的艳遇,它是我骄奢的情人。
两者我都爱,当然爱的方式是不同的——忘记这一切吧,我是个犯了重婚罪的人。
钟立风戏仿伯格曼的这段话,给这一批人画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