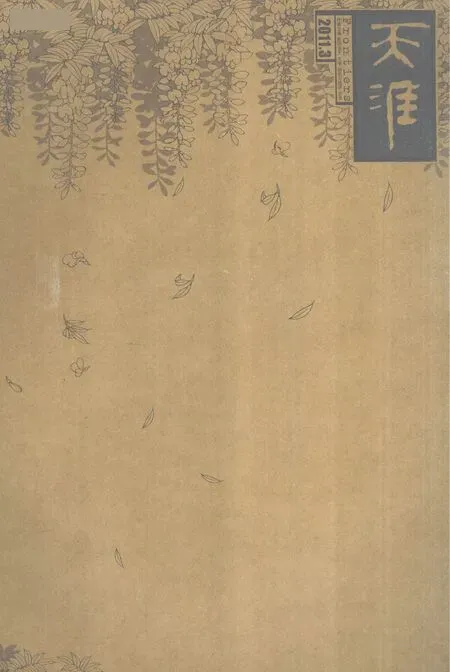天书
2011-01-31陈蔚文
陈蔚文
一
医学院除了教授人体解剖学、诊断学、内科学以及护理学之类,一定还教习了一门书法公共课。不然不会那么多从医者,无论专业资质,字迹都惊人一致!
你凑近医嘱,费力揣测,结果多半徒劳,医生们只使用他们结绳记事的字体。病人怎可腹诽?疾病的确该用另种文字记录:在那暗藏玄机的领域内,医者当然不可轻泄天机!
天书般的医嘱处方,医界同行却可轻易辨认——盖因他们习的是公共书法课,当处方笺递进药房,对方匆匆扫一眼,马上辨出是黄芪而非黄柏,是半边莲而非半枝莲。
“病历,医学小作品,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由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
听上去,病历近似一种新媒体艺术。而从本质来说,它更接近产品维修卡,记录着身体故障的频次与原因,其书写要点是:1、现病史。2、过去史、家庭史。3、此次检查数据。
然而,维修次数与产品寿命并不一定成反比。有些从没维修记录的人,有可能伴着他们的空白病历走向终点:一场意外足以击败所有疾病总和,对人构成致命一击。
还有些病历,寥寥几次记录也并不说明他们质优性牢,经久耐用。
中秋晚,收到Z的祝福短信,回复时顺问她丈夫如何了。
“复发了,走一步看一步。”她回。
头年元月,Z到上海,在当地医院当了多年护士长的她问我肺科医院有无熟人?一问,她丈夫G查出肺癌!特地赶来上海。
他们的婚礼我是伴娘,遥远的阳光稀薄的冬天。削瘦高挑的Z套上两层羊毛裤仍没让婚纱显得充实点,而G高大孔武,皮肤黧黑,说话伴着充足的丹田气流,当时的他是名体育老师,有着完全与一名体育老师匹配的体格。
G会得肺癌?他强壮得连感冒见他似乎都要绕道啊!
Z的口气是医护工作者训练有素的镇定,这镇定中隐含了G病情的不容乐观。G早有些症状,但他不以为然,忙,也出于一个身体倍棒的人对疾病的轻蔑。
Z在所省级三甲医院工作,职工家属每年可免费定期体检,G从不去,觉得浪费时间。他几年前已从体育老师转调至一家行政单位的培训中心,常有饭局应酬。

疾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凌驾一切之上。地位、身份、财富,包括貌似固若金汤的体格。如果遭到蔑视的话,它随时有可能回敬给你更傲慢的蔑视!
有关手术结果,Z未多言。显然非利好消息。
去肺科医院看G。多年未见,没想到再见他竟是如此情状:卧于病榻,神色怅惘。他那么大的个子一旦躺下,比小个子更显虚弱,其健壮程度正好与疾病打击他的力度等同。
他兄妹几个也陪了来沪照顾,只瞒住在家替他们照料女儿的老母亲。病房一角有张新购的轮椅,准备返程时G用的,以免消耗他珍贵的体能。对这位往昔健步如飞的体育教师,步行已成一种奢侈。
然后,便是这则中秋之夜的短信。G化疗后肺癌再次复发!对G夫妇,对亲朋,都知道“复发”意味什么,它意味着Z回复的“走一步看一步”也可解读成“活一天算一天”。
这年的10月3日,兴许是G最后一个中秋。
中秋后,我一直未与Z联系。转眼一年多过去了,有种禁忌横亘在话筒。那头,埋伏着一根随时可能启动的死亡硝引,而拨键这动作也许会立即将其引爆!
我不敢摁下第一个数字,怕一座铁塔瞬间坍塌,震起尘土。
二
假如你有位病史淅沥的亲属,人生显然有所不同,就像长期生活在pH值小于56的酸雨带地区。
从我记事起,母亲身体就不好。生姐姐时她患了“心肌缺血”的毛病,生我时因产房风扇过大,从此埋下关节炎与风湿隐患……
她的人生中,攒下的病历早超过她158CM的身高。这病历高度还在节节攀升,且花色齐全。她喝过的中药,套用那只广告里的奶茶杯子,或者也够绕地球一个可观长度。

这样淅沥的病,母亲反从中淬炼出一种绕指柔的功夫,伴着五花八门的病,损而不毁,还给儿女的日子尽量搭把手。病生着生着,像与人也生出些情分,并非赶尽杀绝的意思。从这角度,病历的绵延或许倒不是坏事,“小病不断,大病不犯”,这句民谚对多疾者是安慰,也是祝福。
药之于母亲,就如化妆品之于某些女人的一生。父亲担任着母亲的服药督导——他以军人的作风,要求她按时定量服药。他认为母亲的病之所以此起彼伏,就是因为没有严格遵循此原则。他相信疾病好转是由量到质的变化,如果药物说明书上写每次服用四至七颗,他必服七颗,他坚信唯七颗才能实现药效的最大化。而母亲,常讨价还价服用四颗,还老忘(我想有时是存心的)。她长年服药,却同时深刻怀疑着药,像一对关系不睦却不得不在一块过的夫妻。这七颗与四颗,足以映衬父母迥然不同的性格:父亲对人生常是无条件信任的(医生最喜欢的病人类型),母亲是无条件怀疑的(医生最不待见这类病人),尽管他俩同为A型血。
母亲除去心脏、胃等老毛病,近年支气管炎常犯。每至秋冬,人咳到像面坏了的鼓,川贝蒸梨、麦芽糖、枇杷糖浆,这些据说可止咳的玩意儿都从坏了的鼓面中漏了出去,然后是漫长的吊针。还有她的类风湿,医生开的激素类药与她的胃病、肝病都牴牾,那些偏方药酒于她的胃也不宜,这使她的治疗矛盾丛生。
父亲以他对万物不疑的信任按位战友提供的讯息,邮购了一期“风湿丸”,据说战友服了颇有效。我上网查后,确认了它的“江湖性”,无非是简陋包装下的过量激素,这激素因无医学监督,简直是个可怕黑洞!天知有多少患者正饮鸩止渴?我让父亲告知战友赶紧把药停了!
受到传统经济发展形式的影响,国内的预算组织机构体系并不健全。就目前来说,能够在专业的预算机构帮助下开展预算决策工作的企业在市场上的数量相对较少[2],同时公司内部的预算组织机构设置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负责预算管理工作的决策单位和具体执行单位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工作过程中的工作效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董事会对企业部门的控制力度相对较弱,导致全面预算管理工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了一定问题。
母亲交往甚少,却有若干病友。常打来电话的有位女病友,比母亲年轻,风湿却更严重,近乎要瘫在床。她来问母亲病情,母亲如起色尚好仿佛对她是阴翳中的微光。这位女病友也四处询医,可收效甚差,莫衷一是的诊疗方案让她乱了套,不知该听谁的。对一个靠长年服药才能维系生活秩序的人来说,病历犹如“人生指南”,可谁又知道,这“指南”有时不是“指北”或“指西”?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命运刻度只能精确地指向某一数值,稍一偏移都可能跌坠深渊。
要感谢命运对母亲的恩惠,她在相互牴牾的药中以一名久病者的韧劲得遇一缕生机(也说不定是某民间疗方显示了不可言说的神秘效力),总之她如今还能爬楼与对付家事,虽然各种病此起彼伏,旧的未去,新的已来。她包里常常携着病历,套用那句陈词,她“不在看病,就在去看病的路上”。作为疾病回声的病历,人生注定的衍生物,它为病者带来“疾病乌托邦的虚幻光明”,是的,它还在被书写,保持着现在进行时,即使病历上的内容语焉不详或不容乐观。
从没病历的人生或许更令人不安。表面的平静有多深,其后潜伏的叵测就有多大!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被挑中,被重奖以“无疾而终”——像彩票般,多数人不出所料的失望托举了极少人的幸运,像家族中的一位女长辈,安然活到九十,某次夜半上完洗手间后,溘然而辞。这是多么理想的离去方式!她最后一句话是叮嘱保姆把卫生纸弄短些,以免费纸。她以毕生的节俭最终没浪费一本病历,包括一份本应具体到分钟的院方死亡记录。

三
这场蹊跷的病,至今未找到渊薮。
是个周末,参加美国马吉·菲利博士(世界级临床女心理学家)的课,“运用本体感觉和能量心理学治疗身体创伤”。活在这世上,从小到大,谁没有些身心创伤?此前也没怎么接触过心理类课程,于是尝试了一下。
课上,有同学在马吉博士的指导练习下,痛哭失声,我不知道马吉博士是否运用了催眠。台上,女子痛泣着,描述她“像陷在一个洞里”,是的,那个黑洞就是她的创伤漩涡。当然,博士同时让她寻找身体的“资源”部分,以期与创伤间寻找新的平衡。
三十多名学员中有些是从事心理工作的,能比较熟练地运用自我身体,而我连“环形呼吸”都很难进入。马吉博士让同学间相互练习,寻找身体舒服与不舒服的地方(其后当然是潜伏的记忆),我开始觉得不适,是身体的明确不适,本来上课前就有些感冒,喉痛。
和我做练习的是位女士,她说她来陈述,我先寻找身体感受。闭眼,有些茫然,不知该如何进入,或者不习惯在陌生人面前这般自我探索,不适感加重。她说,我们先聊聊天好了。她自我介绍台州人,家族做纸巾企业,有两个孩子……
这次课上有几位如她这样的专职主妇,她们对“身心灵整合”的热情让人佩服。这位台州女子,面容平常,目光诚恳,然而不能阻止我不适感的蔓延。我完全进入不了马吉博士所说的“寻找”——心理学上通常建议要正视“创伤”方能清创,以促愈合。对我个人经验却是选择性遗忘,让它在时间之流里沉入无际的黑暗中。
停顿。我没法练习寻找记忆中的失事残骸。
午饭没吃,在走廊玻璃房的阳光下坐了会,难受得发慌,我对返程感到担心。
这段路途,大吐了一次。出租车上,我几次觉得撑不住了,总算到家,一头倒下,拉开架势生病。头痛,晕,从没这么晕眩过,简直怀疑得了美尼尔综合症。
去医院急诊,开始检查之旅,从呼吸科到神经内科再到眼科(青光眼亦会造成头痛呕吐),颈椎,脑电图,脑CT,核磁共振……忍着极度不适,在各楼间挣扎着,全做了遍,没问题。
为何头如此痛晕?昏沉沉地吊针,用了消炎和降颅内压药,仍不能止吐。谷维素、天舒胶囊、散利痛……案头被药堆满,一把把吃下,症状没有缓解。
检查单显示一切正常,病历没能同步阐释肉体症结,像失效的显影液无法作用于胶片。
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有朋友玩笑:“是否那天课上有种潜在气场,而你的‘小宇宙’太弱导致被攻击?”她的意思,这病并非器质性的,而是精神“负能量”的一种变相显现。
母亲甚至担心我头夜因朋友小聚晚归,是否途中或电梯上遇见什么不可言说之物——当我在深夜的空荡电梯摁亮“13”时,也许已有不祥附在身后。
坦白说,朋友和母亲的说法我都信一些。当病得七荤八素时,一个唯物主义者很容易叛变成唯心主义者,况且我本是这二者间摇摆的墙头草。再想,要向“形而上”寻因果的话,这段时日,我一直心神俱疲。有前路重大之事正等我抉择,而我惯性地一再拖延思考,仿效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埋进去的后果就是缺氧晕眩,身心都处于某个临界点,然后,这堂课犹如阿拉伯传说中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算是这场意外之疾的本源吗?
原本,想去见识一下人生创伤如何“运用本体感觉治疗”,却意外实践一场病创。也愈加明白,为何言“身心创伤”——身在前,心在后,那是因一切心的创伤都可假以时间疗愈(或蒙蔽),而身的伤,这种最古老的恐惧,并不随科技发展而稍有减轻,它没有回旋余地,一步可能临渊!
身不在,心何以附存?
身体这列孤独的火车疾驰在黑暗中,司机离席,引擎失控。
按说,人到中年应当越来越强大,财富,见识,社会经验……可所有“强大”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面前都顿失效力。
转而中医。在两位专家间挑了位年龄大的,诊断是胃炎,还不轻。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既然那么多检查都没查出问题,你说是什么?”医生问。
抓回五副治胃炎中药,干姜、焦山楂、柴胡……俱是袪风寒之药,反正吃不坏人,苦就苦吧!得了病哪还有权利挑三捡四,“病急乱投医”是无奈,也是一赌——陷于泥沼中的人辨不清哪一种用力更科学,辨不清深一脚浅一脚的奔逃是朝着正途还是更深的沉陷!
症状缓解在若干天后,应与服药没什么关系。像当初病起时,与检查单上的某样器官没什么干系。
症状稍好,在阳台下望小区花园,感叹人们健身意识日强,瞧!花园中的中老年习剑者队伍明显又壮大了!——后发现是我人为将其数量膨胀了一倍。
视力出现重影(医学上称“复视”)。以为头晕导致眼花,两天后仍是,走在路上能把一个人看出一双。眼科检查正常,既不青光也不闪光。眼科医生说,凡眼部肌肉都由神经支配,眼睛既查不出问题,那转神经内科看,或者是脑神经有状况。
“最好做个核磁共振。”大夫说。
“不才做没多久吗?”
“那是你眼睛出现症状前,不代表你眼睛出问题后的状况。”
“这么快……就有变化?”
大夫本着医学的严谨精神说,别说几天,就一早一晚病情也有变化!
我同意这说法,但仍在拒绝检查的病历上签了字,表示后果自负,绝不连累此大夫。
又去另家知名眼科医院排漫长的专家号,排了近两小时,专家只用了两分钟,说没问题,开了些药(包括眼药水和心血管疏通药)。药一点也没吃,大约一周后,视野回归正常。
像只是场梦魇。从头到尾,没有病历上的结论作为旁证,似在自我臆想中经历了一场病。
病历原来不如想象的洞悉一切。或者说,好比一种化学作用下的隐形书写,谁也不知道显影液藏在哪儿。
普鲁斯特在《斯旺的道路》写道:“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
是否也可以说,“疾病隐藏在医学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
不是所有疾病都服膺于医学。有些疾痼,在更苍茫的辖区内,为沙尘阻隔,就像世上其他人类永远到达不了的区域。
四
收拾抽屉,一包鼓囊囊病历(夹着各种检查治疗单)搁在最下层。扔了?不然留着何用呢,除了说明生每场病的经济成本。至少对我来说,对下场疾病,它并没多少参考价值。会有新一轮检查等着,而既往史,医生只需你言简意赅地描述。
还是没扔,像丢掉有些旧信,像从此丢了段日子——不是那些信,如何证明那段岁月存在过?前阵在父母家抽屉翻到年轻时的信,有几个信尾落款竟是我根本想不起的名字。名字的主人走失了,可他们的确存在过,有信为凭。
病历丢了,也像丢掉某件重要的呈堂供证吧。它记录着我们为身体这架机器正常运转所经受的考验。化验单、输液架、纱布、药棉、手术刀、X光、麻醉剂、羊肠线、各式药片胶囊、让人苦得颤抖的中草药汁……它们,很可能将陪伴我们到最后。
柜子深处,抽屉底部,病历是家庭档案重要的一部分。
保存病历,一切有此习惯的人,是否都对时光和生命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与忧愁?
有位朋友甚至保留着已逝母亲的病历。大牛皮纸袋,封装着他母亲最后几年的生的意志,这其中每步都有他的见证:那些东奔西跑的医院,各项检查诊疗,希望与绝望间的艰难沉浮……
他母亲临终也不知自己的真实病况。
“病变是最与自身血肉相连,却也最不属己的异物。”病历是这句话的最好注释,病人,尤其绝症病人,常出于被保护而不享有知情权。
“我无法充当死神的信使,我无法当面告诉妈妈她的真实病症,因此,我调动自己全部的文学天分和全部医学常识,为妈妈伪造了一份合情合理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直至今天,妈妈深信不疑。可是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刻,比如想到生命意义,我又觉得她有知道病情的权利,有选择最后方式的自由。我是不是太过越俎代庖呢?”
一位女子在母亲肺癌骨转移后的痛苦困惑。
病人体内倒计时的生命秒表——有如警匪片中人质身上的定时炸弹,所有人都听见滴答声,唯病人自己不知。可说真的,我怀疑这是真不知还是佯装不知?作为与身体朝夕相处的主人,它的每点动向与症兆,他如何会不察?也许只是不愿,不敢往最坏处想,对生命抱有最后一星希望。
大卫·科波菲尔有一次在广州接受水均益的访问,水均益告诉他,他的朋友想知道大卫的秘密。水均益得到的答案是:知道魔术的秘密,就像开车看见了车祸。
这世上许多秘密是不宜被洞悉的,比如魔术,比如重疾,因此有了一摞摞在暗中被遮蔽的病历。
那位不敢向母亲坦言病况的女子,母亲却远比她想象的更坦然。从半昏迷状态中蓦然清醒(“回光返照”)时,女儿告之以真实病情,她说:“那还有啥说的。人固有一死,其实也没啥。”——如此从容的一句话,要用多少智慧和心胸来准备?
面对纷纷赶来的亲友,她一直报以微笑。女儿告诉她,为她准备了一小块墓地,上面雕刻着她最喜爱的水仙花。母亲说:“其实用不着。”又说:“我感到我真幸福。”——这是她的最后遗言。
一个能在辞世前说“我感到我真幸福”的人,真是太幸福了!虽然六十八岁在现代寿数中算不得什么,甚至可视作凄惶,可又有多少高寿者能在谢世前吐露“我感到我真幸福”呢?
人类最终极的恐惧在这轻轻一句里,尘归于土。
那让人惴惴难安的病历对有些人其实无须隐瞒的,这世上果真有比死更强大的东西,那就是顺应,这柔软中饱含最亘古的定力。安时处顺,知命乐道,故不忧。这样的沉静,这样的高贵,这样的镇定自恃,在这态度面前,死又是什么?不过是辞君向沧海,烂漫从天涯。
一直觉得与疾病有关的记录是野蛮而悲伤的大雪。这看法,有朝一日它会随岁月改变,它不再发出雪折断枝桠的粗砺啸声,不再抽打一颗因过分脆弱而随时起颤栗的心。那尾随在每个姓氏后的病历更像来自麦田的蝙蝠,或盘旋于头顶的落叶,它何时会落下呢,那要看风的方向与速度……当有一天,它落下并覆盖一个姓氏,并非因怨愤而实施惩罚,只是时辰到了,它伴同一个生命返回他当初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