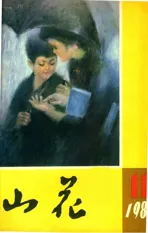老革命周春江
2011-01-18邵丽
邵丽
老革命周春江
邵丽
一、缘起
三月份,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短篇小说研讨会,在会上见到北京大学文学系的的博士生导师陈小明老师。他说,你的王庭柱写得很不错。此前就这篇小说,中国作协的胡平老师,《小说选刊》的杜卫东老师,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表扬过我。激发了我要把这个挂职系列写下去的热情。王庭柱是我另外一篇小说里的人物。其实那篇小说,开始我投给了一个大型文学期刊,某主编打电话给我说,这部作品长得不像个小说,不知道怎么用。这让我相当迷惑,我知道,虽然他没有说出小说应该长成什么模样,但一眼就能看出什么长得不像小说。不过这篇小说另外一个刊物发出来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选载了,好评颇多。
说实话,关于小说的写作,最近一直困扰着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下笔万言,倚马可待;可越写越胆怯,就像一个车手一样,刚开始肆无忌惮,开着开着就胆怯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去了一个县挂职当副县长体验生活。我就是在那里认识“王庭柱”的。
我这次到北京来还有另外一个任务,替老干部周春江申诉。在挂职期间,每个人还要联系一个老干部,据说这是我党珍惜革命财富,充分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过去我知道,老干部退下来之后,还可以到一个专门机构工作,那个机构叫顾问委员会;后来虽然取消了,但老干部还得参政议政,所以现任班子的领导干部,从书记县长到每个副职,都要联系一个老干部,一方面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总之,不要让他们找事,或者他们找事的时候,不能闹事。
我联系的这个老干部周春江,过去是县委副书记。他是1950年初参加革命的,按规定,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的算离休,而那之后的算退休。离休和退休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待遇却差很多。他的情况说起来比较复杂,虽然他错过了1949年10月1日这个期限,但他是在海南岛参加的革命,海南于1950年5月才解放,按规定离休日期可适当延长到解放之日。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他在海南参加革命的时间,算离休;如果按照在家乡参加革命的时间,算退休。他参加革命的过程也挺复杂,他和哥哥去海南岛贩白胡椒,解放海南的仗打起来后,与大陆的交通中断了,他哥俩为了混碗饭吃,一合计就参加了解放军。仗打了一半,他哥被一发炮弹切去了左边的胳膊腿,部队本来想把他送回后方,但他哥眼看生命不保,非要回家埋到自家的祖坟里不可,无论如何不能死在外面。连长做他的工作,他就揣着一颗手榴弹,说如果不让回家,他就自己炸死自己。后来连长批准他把哥哥送回了老家。等他再回海南,海南岛已经解放,成立了海南军政委员会。他参加的那个部队,他既不知道番号,也不知道连长的名字,只知道他叫潘连长。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所以只好回了老家,重新参加革命。
就这个事儿,他退休后与各级组织和信访部门打了不少嘴官司,而且也成为了我县信访工作的一个热点。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和谐社会建设日益提速,各地对信访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严。这次我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帮他到国家信访局讨个说法,免得他到处乱跑给省市县惹乱子。
参加完小说研讨会,我直接去了马家楼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下车一看,万把人挤在那么个小地方,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我吓了一跳。我想过去老北京在新街口斩杀犯人,热闹也不过如此吧。想起这个来,我又记起顾城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这辈子就想做个新街口的杀手,既可以杀人,又可以以国家杀手的名义免除责任。后来这个先锋诗人在新西兰斩杀妻子谢烨,不知是为了圆梦,还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没有地方诉说才出此下策。在马家楼站了一会儿,我打电话找北京的朋友求助。朋友说你别在那里等,还是去国家信访局办公地方吧,在月坛南街,中国造币总公司的隔壁。听完他的介绍,我在车上乐了半天,心想,把这两个单位规划在一起,绝对是决策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你想想看,国家造币总公司是专门制造麻烦的,而国家信访局则是千方百计消除麻烦的,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最近到县里工作后才听有人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靠人民币,其实再往根子上查一查,人民内部矛盾还不都是人民币惹出来的?
二、棋友
这个周春江是个老倔头,之所以把他推给我,一来我是外来的,与他没有过节;二来我是个女同志,他说话再难听也得有所顾忌。分工我联系他后,我往他家打过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他老婆接的,我在电话里给他老婆说明缘由,他老婆说,这不是电话里说的事儿!然后砰一声就挂断了。第二个电话是他接的,他说,你也甭给我讲大道理,这理儿从我哥为新中国捐了胳膊腿儿那阵子我就想通了。你能帮忙你就帮点儿,要是真帮不了你就闪开,我自己来!第三个电话他的口气才有所缓和,说,你每周六下午到锅炉房找我吧,我在那下棋。
按他们的说法,他退下来后忽然变成了两副面孔,一副面孔是对组织的。他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从没给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要说像他这种资格的老干部,早就该提拔上去了,可每一次提拔干部他都是让给人家,说,我这文化不行,让我上去尽是作难。他基本上没怎么读过书,开会做笔记每次都是把一个笔记本用完,每页只写三五个字,都像鸡蛋大小。他退休的时候,光笔记本装了满满两卡车。共产党的会多不多,问问那天去他家收破烂的人就知道了。开会让他念稿子他又不怎么会断句,比如念“我们的工作”,念到“我们——”,他就用指头点住,开始自由发挥讲其它事,从司机不知道节油,讲到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倒台,陈芝麻烂谷子讲了一大堆,然后又回头从“——的工作”开始念。一篇稿子念完,他满头大汗,还要补一句“可算完了!”秘书提醒他说,最后这一句今后不要说了,而且“完了”听着也别扭。他说,你们他妈的别扭个毬!我读个鸡巴稿子明知道也没人听,比杀个国民党都难!可是如果不让他念稿子,光讲具体事,虽然理论上上不去,但讲得头头是道,大家都爱听。
退下来后,他给组织上提的惟一的要求,就是自己的离退休问题,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县委就不得安宁。这样威胁的话语出自他口,让县委书记既非常吃惊又特别不受用。县委书记说,周书记你咋一下去就变脸了?他说我不是周书记,我是周春江,那个副书记是你的,周春江是我自己的。过去是给你干,现在是给周春江干。不该得的我不要,该得的我绝对不让!县委书记说,你的这个离休问题,从情理上说绝对应该解决,但是没有证据嘛!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说,我哥丢在海南岛的胳膊腿儿,算不算证据?

顾铮作品·夜色中的台北老城墙
他的另一副面孔是对平头老百姓的,在大街上不管见到谁,逮谁给谁聊。有时候人家买菜急着回家,他就边走边跟人家说着话,陪着人家过了几条街,话头还没说完,说下次咱们再好好聊聊。有时候人家去他家串门,说不了三两个小时根本走不了人。好不容易出来了,他送人家到门外,站在走廊上还得饶上半个小时。大家都说,老周心态好,能活个大寿限。他说,反正我这命也是拣回来的,那时候说是把我哥背回来了,其实也是把我自己的命背回来了。要留在海南,十有八九回不来。
他让我每个周六去锅炉房找他,是因为他到周六雷打不动地去锅炉房找后勤陈耀金下棋,据说这棋已经下了十几年,也没分个胜负。陈耀金原来是农村户口,接他爹的班上来的。他爹原来跟着周春江当通讯员,1975年,中原地区遇到了一次千年未遇的大洪水,他爹陪当时是公社书记的周春江看守水库大堤,眼看着守不住了,周春江还是不让撤。他爹趁周春江解大便蹲下的时候,一条麻袋套他头上,扔肩膀上把他扛上了山。他们走后半个小时,水库垮坝。后来周春江当了县委副书记,把他爹安排在县委办公室管后勤,说,我不退休你也甭退,县委办的后勤交给谁都没交给你放心,全县没人不知道你的手最干净!他爹说,我要是不干净,耀金还会在农村种地?听了这话,周春江知道他的心病,就让他退休回家,儿子陈耀金接班进城。陈耀金进城之前,本来在农村有个老婆,进城后休了。休这个老婆得到了周春江的赞同,他说,像这种不孝顺父母的东西,留在家也是祸害!陈耀金后来又娶了一个,也是离婚的茬儿。他俩各带了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叫星儿,她老婆的孩子叫马子,然后俩人共同又生了一个叫高台。俩人刚结婚那阵子,好了就好个死,闹了就闹个死。好的时候,下了班,他骑着自行车,前面车杠上坐着星儿和马子,后面车座上坐着老婆,一路小曲儿就去赶夜市了。他在前面一边唱《爱情三十六计》:“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要爱就不要跑。”一边拿着老婆的手,摁在自己的腰上揉搓着。闹的时候,风生水起,不掂着刀撵半条街不算拉倒。俩人大喜大悲地折腾了一年,高台哇哇坠地。按道理这个孩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县里准备处理他,他就去找周副书记。那时候他跟周副书记就是一对儿恩恩怨怨的棋友,有时候周副书记赢不了他,就一推棋盘说,妈拉个逼,看我下次不好好收拾你个孬种!他也没大没小,说,你这老头再胡说,今儿个我把水烧到八百度,明天非开你的追悼会不可!说是这样说,因为他爹的关系,他在周春江这里也跟半个儿子差不多,老周家里的粗重活计,他两口基本承包了。这次事儿他找到周副书记,周副书记正在给俩人说工作,一看他进来,就对那俩人说,你们走吧,我还有事儿,你们明天再来说。接着他们俩就拉开棋盘,战得昏天暗地,他也忘了找周副书记说什么了。过了吃饭时间,他老婆找到周副书记的办公室,在门口喊道,孩他爹,你赶紧吧!你赶紧吧!他说,赶紧啥呀你这个傻逼?他老婆说,家里出大事儿啦!他说,谁在咱家后院埋地雷啦?他老婆说,不是地雷,是地震。你那星儿打我那马子了,把咱那高台吓得要死要活的,你看这咋办!说着说着,她也进办公室了,胖胖的脸蛋激动得通红,一脸的雀斑都淹没在油腻腻的红晕里。周副书记见状,把棋盘一掀,说,你这小子我还正准备找你算账哩,你们闹到我办公室里算啥事嘛?他说,你要想处理我你就处理吧,我天天带仨孩子蹲你门口要饭吃!周副书记说算算算,我也难断你这家务事,你把你的星儿送回你老家,她把她的马子送回她老家,就留下你们俩的高台,我好说话,行了吧孬种?

顾铮作品·永康街冰馆一景
三、去南方
改革开放后刚恢复县政府那阵子,周春江任政府副县长。在此之前,他是县纪检委书记,那时候的纪检委书记是正县级,之所以把他从正县级降到副县级,是因为他当纪检委书记期间,有一次下乡查一个案件,工作结束后他到过去联系的一个农户家去,临走的时候拿了人家几个茄子,一把青菜,还有一罐自酿的蜂蜜。这事儿现在说起来,简直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典型,可在当时不行,这就是白吃白拿老百姓的。要说他对这个联系户非常好,逢年过节都要亲自或委托别人送些吃的用的过去。但党的政策历来是钉是钉铆是铆,对联系户好是应该的,这是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觉悟。拿人家的,再怎么也说不起嘴,而且,违纪。
当了副县长的周春江负责农林水等工作,这是他的强项。他天天蹲在田间地头,按下属的话说,好像一天闻不到大粪味儿,他这个县长就当得不踏实。这让他分管口上的干部苦不堪言。跟着他下乡的局长们如果抱着葫芦不开瓢,他就故意问他们农业生产技术,局长要是说不上来,不管面前有多少人,他会马上抹下脸子,把人家批评得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如果这些局长们对农民指手画脚地瞎指挥,他更是火冒三丈,大骂道,人家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了,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道个毬啊!这还不是最难受的,如果他出差,喊谁谁都推说有事,不愿意跟着他去。他出差有一个规矩,住宾馆拣车站附近最便宜的,吃饭的时候只准点一个菜,如果吃着不错,就再点一个这个菜,吃着不好吃才能再换一个。所以跟着他出差的人,等陪他吃完了,再偷偷出去吃一顿。他退下来之后,有一次去省城看儿子。儿子在省政府一个重要部门当处长,中午给他点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大发雷霆,一口饭没吃站起来就走,说,咱家出你这样的败家子,算是跟监狱挂上钩了!那公家的钱长的都有牙你知不知道?总有一天会咬死你!儿子也不敢给他犟嘴,只好自己掏钱把菜打了包,放到冰箱里吃了一个星期。
有一次,他分管口上的几个局长给他提意见,说,周县长,人家各个单位为了学习先进经验,都到南方去考察,你什么时候也带我们去开开眼界?他说,开啥眼界?还不是为了转一圈旅游啊?我不相信谁种地能种到天上去!后来还是分管的副书记劝他说,老周,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抓工作,是该学习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了,否则我们的农业会越抓越小。这次我们俩带队去南方考察考察,学学人家的先进经验。他勉强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既然去看农业,那就去人家农村,不能到城里去。所以虽然到南方转了十来多天,还是跟在家里差不多,天天蹲在人家地头,像一群流民。考察结束的时候,大家提出来,这辈子没到过广州,回去的时候路过,我们进去看看吧。副书记也说,广州市的城市观光农业搞得也不错,还是去考察考察吧。他们在广州转了一天,没看到人家的观光农业,高楼大厦里姑娘的腿肚子倒是看了不少,这让他窝了一肚子火。晚上安排住宿,房间里冷气开得特别大,他也不知道怎么调。开开门找服务员,走廊里连个鬼也找不到。他想,这他妈连我县委招待所的水平都赶不上,我那招待所,服务员就在门口候着,看见人不喊叔不说话,哪敢擅离职守?他找跟他一起来的人,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把他送回来晚上都跑出去“考察”去了。更可气的是,他床上只有白花花的一床褥子,连个被子都没有。洗了洗澡,又累又困,只好把裤子衬衣搭在身上睡了一宿。第二天起来,他流着眼泪鼻涕,对着办公室主任破口大骂,说他们捉弄他,安排的房间没有被子。办公室主任过他房间看了看,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原来人家宾馆的被子四个角都压在床垫子下,他拉了拉没拉动,也不敢乱动了,只好躺在床罩上睡了一夜。

顾铮作品·永康街的茶人
这还不算,办公室主任结账的时候,他的房间里多出七百多块钱来。仔细查了查账单,他把人家房间小吧台上的商品全部打包了,估计想着是人家宾馆白送的。不过这事儿到现在都没人敢给他说破,如果他知道了,不但得把钱退给公家,估计他们几个挨个十次八次骂也是少不了的。
四、夜宴
2009年是县里最热闹的一年,按照上级要求,因为国家要搞建国六十周年大庆,要各地严密排查各种矛盾,一律把不安定因素化解在基层,不能让那些上访人到北京乱跑,扰乱各项大庆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守土有责,谁出问题拿谁是问。这样一来,县里如临大敌,县委书记县长天天轮流坐在信访接待室里找上访的老百姓谈心。老百姓说,几十年了没见过书记县长这么平易近人,如果这几十年都这样,鬼还去上访啊!
可是上级这样的安排,等于是给那些上访人一个信号,平时不怎么闹事的,也都赶在这个时候来凑热闹。先是一个打官司败诉的上访人,在9月28日这一天,把一家老小上至83岁的老母下至5个半月的婴儿,一共17口人拉到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说,我的事儿你解决不解决?如果不解决,一分钟之后要让全世界震惊,你这县委书记也别干了。县委书记说,你什么事儿啊?他说,你这县委书记是给谁当的?老子打官司输掉了你知不知道?我输掉不打紧,我这一家老小17口人,马上就要被赶到大街上喝西北风。问题是我这官司输得冤枉,输得窝囊。你到底给我解决不解决?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县委书记说,官司胜负书记说了又不算,你让我给你解决什么?他说,官司胜负我也不管了,反正穷人打官司也从来没赢过,我只要你解决钱,官司输掉这15万块钱你给我出了!现在我开始计数了,数到59,我们俩都没有机会了。1、2、3……书记说,你先别这样,我五分钟内给你打过去好不好?那边迟疑了一下,说,好吧。放下电话,书记把电话打给了公安局长,让查查刚才那个号码在哪里,要快。随即公安局长回电说,在北京。书记马上把电话打给了那个人,说,你回来吧,钱的事儿县里从扶贫资金里给你出,算是补助困难群众。那边说,我的电话是按着免提的,一家老少都听着哩,如果你说话不算数,反正北京也没上锁,我说来就来!
这个事情还没按倒,省政府驻京办又来电话,说县里有个叫陈光荣的上访户,在中南海附近溜达被抓住了,要县里一是去领人,二是去领批评。县里派了三个人去,怎么说都领不回来。她是个老上访户,这次排查的时候之所以没把她作为重点,主要是她母亲刚刚去世,想着她不会外出。要说她的事儿也够冤的,过去她是个卖肉的,因为摊位问题,跟一个派出所副所长的亲戚发生了冲突。后来这个派出所副所长就以她的作风问题为由头,把她作为卖淫抓了起来,据说打得不轻。肉摊子没了,老公也带着孩子离她而去。她就从此走上了上访之路,后来上级来查,实在说不过去,就把派出所副所长撤了,又赔她两万块钱,政府还跟她签了合同,要她保证不再闹了。谁知道她回去不久,就又闹起来,尤其是逢年过节,看见人家热热闹闹地过节,她就要闹一场。这次她之所以不回来,要求并不高,去看看长城,然后坐飞机回来,否则免谈。去接她的人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这后面有高人指点,估计也就是趁六十年大庆,想给县里出个难堪。于是就跟她说,连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你要求也太高级了,如果生活有困难,县里补助你几个钱不就得了,你这事儿也犯不着去跟老天爷汇报吧?她说,你们坐没坐过飞机我不管,那书记县长天天云里来雾里去,飞机是他们自己家的?接她的人说,书记县长是工作需要。她说,那好吧,我没有工作,也不需要,可是你们干嘛来接我?书记县长让你们来接我,说明我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工作,对不对?事情汇报到县委书记那里,书记长叹了一声,说,长城,看!飞机,坐!后来又补了一句,日他妈,要不是赶在这节骨眼上,非劳教她个王八蛋不可!
作为挂职副县长,我倒是没有与老百姓打这种交道的麻烦,但一个周春江也够我闹心的。过去他也去过三趟北京,不过都是事先给组织上汇报过,所以大家都觉得他闹事的可能性不大。但县委书记放心不下,专门交代我说,越是轻易疏忽的人,越容易出事,你还是要以防万一。十一放假七天,我陪老公和孩子南巡的计划全泡汤了,只好作废了一张机票。按照县委和书记的布置,我留在县里,对他严防死守,人在阵地在。好在他住在县委大院里,一有风吹草动我就能得到消息,及时出现在他面前。可他是个大活人,总不能二十四小时都盯着他,万一有点疏忽,我就吃不了兜着走。怕鬼处总有鬼,十月二日,我还没起床,秘书的电话就打来了,说周春江六点不到就出去散步,到现在七点半了还没回来。我赶紧穿衣起来,坐上车,然后打电话让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分管的各口领导,抓紧时间去找他。到中午十一点半,仍然没有结果,我只好回县委报告县委书记。书记说,其他人进京,最多是个通报批评,如果他去了,多少闹出一点乱子,估计咱们俩得一锅烩——这个坷垃太大了,能绊倒人。正说着,突然有一个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说,我是周春江,听说你找我了?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只感到脊背发凉,脸上汗立马就下来了。我赶忙说,是这样子,今天本来我想去你家吃饭,结果他们说你出去了,我让找找你。他笑了笑,说,人找人不好找,李县长?这事儿我可干得太多了。今天我出来散步,正好碰见耀金回去看他爹,我就跟着他回农村了。这样吧,晚上回去我请你吃野菜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好!周书记,我等着您,我赶紧说。
真是太好了,好得不得了,我看着县委书记,想痛哭一场的心都有了。
他家就住在县委的后院,晚上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在看着老伴儿炒菜。桌子上已经摆上六七个菜,还有一大堆没有炒。我说,就咱们几个,怎么能吃这么多菜?他说,不,你通知你分管口上的领导,今天他们都挺辛苦的,喊过来一起吃吧。想起来今天找他的事,我脸红了一下,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他说,叫他们都过来吧,过个节也不容易!我只好一个个打电话通知他们。人到齐之后,他说,我也不客套了,今天咱们是陪S县长过节,我先喝为敬!说罢先喝了一大杯酒。酒过一巡,他说,咱们先停住,我说几句再喝,好不好S县长?我心里一紧,赶紧说,你是老书记,让我和这几个局长先敬您老领导一杯好不好?他把手捂在酒壶上,哈哈一笑,说,我知道你是咋想的,怕我胡说是吧?可是你们一人三两杯酒,根本堵不住我的嘴啊!我说,不是不是,你是老领导老前辈,这是礼节。他说,我没几句话,不过也不是胡话。他转过头来问我,李县长,你知不知道党中央在哪里?我说,知道,在北京。他说,北京哪里?这个问题难住我了,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想说在中南海,可是说实话我也吃不准。到北京我曾经问过朋友们,他们说中央领导都在“海里”办公,“海里”就是指中南海吧。至于党中央在哪里,他们也说不清楚,各个部门都不挂牌子。他说,我如果在咱们这里说,我去党中央反应情况,大家肯定都会像你一样说,去北京吧。可是我到了北京,你们没有一个人肯告诉我党中央在哪里!我去了三趟,被糊弄回来三趟。我革命了一辈子,当了二十多年的县领导,你们就让我找不到党中央,人家普通老百姓到哪里去找?我说,如果全国人民都去找党中央,那中央怎么能吃得消?他说,我并不是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如果你们告诉我在哪里,我连门口都不去,这个觉悟我还有!可是连这你们都不敢给我说!其实岂止是党中央,连书记县长在哪里办公,老百姓能知道吗?我们让老百姓跟着我们闹革命,闹到最后连我们在哪里都不敢给百姓说,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交代?他们这样搞,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中央的意思!

顾铮作品·永康街上发飙的老爷子
酒喝到这个程度,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无法再热闹起来了。我再次说,老领导,咱还是边喝边说比较好吧?他说,好好好,我还有两句话,说完咱们痛痛快快地喝。我之所以请大家来到我这里喝酒,知道你们今天找我找得很辛苦,我这也算是谢罪酒。可是你们不管我,我难道会给组织上添乱吗?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喜事,我还没糊涂到那个程度。六十年了,哪个国家有我们这六十年发展得这么好?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怎么庆祝都不过分。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想问问,尤其是李县长,你是大知识分子,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父母是六十年代饿死的,尤其是我哥,在海南国民党没把他炸死,可是在一九六一年给活活饿死了。想起他死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神,我都要痛哭一场;我的很多同事,也是文化大革命那几年被整死的,我们在大庆的时候,能不能想起他们来,也给他们个说法?如果大庆的时候不合适,大庆以后说也行啊,人死了难道就白死了吗?这次我之所以为我的离休闹意见,也只是要个说法。如果对我有错,就要有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给我说一声,周春江,我们搞错了,正式给你道个歉。有了这句话,我要是再放个屁,就他妈的不是人!我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了,我们各级组织把事儿办错了,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把事情糊弄过去,在所不惜!可是一句道歉的话,认错的话,再怎么着也不会说。一句道歉话就那么难吗?难道我们这几十年,就没做错过什么吗?如果错了,怎么一次也没有道过歉?为什么做对了的事情大家都争着站出来说话,而错了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出门你踩人家脚了,也要道个歉吧?我就害怕像我的父母,像我哥,像我的那些同事一样,死了就死了,错了就错了,你能怎么的?我还能活几年啊,想想不寒心吗?
周春江说到这里,突然泪如雨下。大家也都想不起安慰他的话来,一时间有点冷场。过了一会,我说,周书记,我相信你这事儿会有个说法的。但是今天这样的场合,一句话也说不完,把大家请来也不容易,何不痛痛快快喝几杯呢?他说,好吧好吧,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李县长,说实话,你老说对我负责,其实我干了一辈子,能不知道你是对谁负责吗?你是对书记负责,这事儿管不好没法给书记交代。书记是对谁负责?对上级负责,出了事没法给上级交代。这事儿说穿了,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怎么对我负责,也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怎么给我个交代。我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子,人家老百姓的事儿谁会去负责?
那天晚上我回去不久,爱人打来电话,说孩子在上海旅行期间患了感冒,怕感冒治不好影响旅行,一次偷偷吃了十几片退烧药,结果转氨酶升高到4000多,如果不及时治疗,就有可能得换肝,或者会有生命危险。听着电话,我的腿都是软的。电话没说完,我就泣不成声。我通知司机连夜往上海赶,走之前我没有向县委书记请假,这个事儿我想等我到上海把孩子的事情安置停当了再给他说。如果他担心周春江这边会不会出事,我会郑重地告诉他,如果相信我的人格,就要相信周春江不会出事。
五、剪辑错了的故事
年初给老干部体检,周春江查出来有腹主动脉瘤,而且情况也比较严重。后来他家人建议再去省里复查一次,复查的情况更糟,除了有腹主动脉瘤,还有肺癌。要说这事儿不该闹到县委常委会上,可因为是周春江,所以县里很重视,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扩大到卫生局长、财政局长。涉及到周春江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手术到哪里去做?根据专家的意见,这样的手术一般的医院做不了,如果先做肺癌,他的腹主动脉瘤随时可能爆裂,即使在手术台上,出现这样的问题也很麻烦。如果先做腹主动脉瘤,他的肺部被麻醉之后,因为癌症的影响,可能会彻底失去功能,永远再也不会醒来。第二个问题是,费用怎么报销。如果按退休,只能报百分之七十五;如果是离休,就由国家全部包了。

顾铮作品·永远客满的鼎泰丰门口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治疗地点上,我极力主张去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和水平目前在中国是最好的。可县委书记不主张去那里,桌面上的理由是太远,害怕路上出问题,而且家里去护理也不方便。其实我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周春江去北京”,这是一个问题。
争论到最后,形成了一致意见:手术在省人民医院做,由他们去解放军总医院请专家来,所有费用由县里全部报销。这一条意见是县委书记亲自拍板的。我也觉得舍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了。
出门的时候,县委书记跟我说,你一定要给周春江同志带个话儿,把组织对他的关心传达给他。县委这次做了重大突破,可以说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不惜代价。我点了点头,我会告诉周春江同志,这个决定是书记“亲自”作出的。亲自,这里面的分量和压力,相信周春江会明白。
周春江做了手术回来,保住了一条命。据说专家的意见是,如果恢复得好,还可以活个三五年。我去看过他两次,因为在场的人多,也只是说了一些场面上的话就告退了。
很快我的挂职时间到了,由于单位来接我的时候有点突然,我也就来不及给大家一一告别。开完欢送会,我直接坐上车往省城奔去。在高速公路上,我接到了周春江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又加上高速路上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
听说你很快就离开县里了?他说。
我说,是的周书记,我的挂职结束了。
你什么时候走啊?他问。
我……我突然觉得不好回答。短暂的空白之后,我说,周书记,我明天才走。一会儿我去看看你!
在车子回县委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直接去了周春江的家。他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一脸大病初愈的倦容。看见我进来,他没有起身,只是笑了笑,用手指了一下他旁边的凳子。待我坐下后,他说,李县长,我一直想找你好好谈谈。
我说,周书记,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我找你不是谈别的,更不是我自己那破事儿。我那事儿我也想开了,他们不给我解决,是咱们官场的道理;给我解决,是我自己的命。只是我想着,你作为一个作家,要好好把我哥哥写一写,他这一辈子太窝囊了。一直到死,我觉得他有很多话都没说出来,如果我再不说出来,那他就等于白活了一生。
他哥哥在海南炸成那样,怎么能活着回来,这是我心中的疑问。如果他不提及,我还真不好意思问,今天说起来这个话题,我便问他,你是怎么把哥哥活着带回来的?
我给你说实话,这也是我后来一心一意参加革命的原因。哥哥炸成那样,非要回来不可。要说部队正在火线上,哪有时间管这事儿?可是,潘连长把我拽到一边,说,我看你们哥俩也不是打仗的料,我给你们凑点钱,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吧!他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又向其他战士借了一部分塞给我。我说,潘连长,就是为了你,我死活也得回来!他说,你要回来我欢迎,要是不回来,也算你们跟着我生死一场!就为了他这句话,我知道我这辈子就是把命破上,也要参加这样的革命,我觉得这样的革命,只有好人才会参加。我们到了大陆,才知道全国都解放了。那时候你知道,只要说你是共产党、解放军,老百姓就跟看见亲人一样。就靠着我们哥俩这一身军装,到哪里没人照顾?我们几乎没怎么作难就回到了家。
你哥哥没有作为伤残军人对待吗?我问。

顾铮作品·再见台北
没有,他坚决不同意给他报伤残,他说,我连一枪都没放,算是什么军人?别人问起我来,我怎么跟人家讲打仗的事儿?这不尽让别人笑话!回来以后,他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好在我父母身体都好,可以照顾他。1961年的阴历四月初九,是我母亲的生日。我偷偷跑回来给母亲过生日,那时我在另外一个县的县委当干事,由于当时农村形势不好,干部一律不让请假。我回家一看,家里没有一点活气儿,四门大敞。找了半天,才在柴堆里找到哥哥,他已经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我问他,父母呢?他的眼泪流了下来,头歪向了院子里的一个新鲜的土堆。我看看土堆,又看看哥哥血迹斑斑的手,知道父母已经饿死了,是哥哥用一只手把他们埋葬的。我把哥哥抱回床上,他啊啊地喊着,但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拿眼睛狠狠地瞪着我,躺到床上就昏迷了。我在门后找到一把铁锹,在院子里拍死了一只猫。你知道,那时候村子里的人已经饿死得差不多了,成了猫狗和老鼠的世界,它们吃人肉也都挑挑拣拣的,一个个吃得肥光流油,根本不怕人。等我把猫肉汤炖好给哥哥端过去,他已经断了气儿。
说到这儿,周春江好像缺氧似的,不断地作着深呼吸。我站起来给他添上水,示意他停下来。他喝了一口茶,继续很吃力地想说下去。我说,周书记,要不我们改天再说吧,你这身体不能激动。他说,我不是激动,而是愧疚。我好像又看见哥哥躺在我旁边。
我说,像你这么大的手术恢复这么好,还真不多见。我想转移一下话题。
他没接这个茬,继续往下说。你知道我看见哥哥手里拿着什么吗?一颗手榴弹,那颗手榴弹他一直藏在身边。他没死的时候,嗯嗯啊啊地跟我说,估计就是想让我用手榴弹把他炸死,他已经拉不动弦了。他手拿着手榴弹,任我怎么都从他手里拿不下来,眼睛还在狠狠地看着我,不管我站在哪个位置,他都看着我,好像说,既然你是我兄弟,干嘛不帮忙炸死我?他也是饿得受不了了,难道炸死比饿死好受吗?那种眼神,我一想起来就痛不欲生。
眼泪顺着老人的眼角流下来,我递给他几张湿巾。他接过来,但是没去擦。眼泪把一张虚黄的脸洗得明晃晃的。
我说,这事儿你也不用难过,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都无能为力,现在不也是这样?
不!不完全是天灾,大部分是人祸!
人祸?尽管我过去听说过类似的说法,但我还是不怎么相信。
你知道吗?饿死那么多的老百姓,可是我们各级政府的粮仓里,粮食还是满满的。很多老百姓就饿死在粮仓门口,就这也没有一个人去偷、去抢。世界上哪有咱们这么好的老百姓啊!如果连这样的老百姓我们都对不起,怎么给历史交待?
我把他的手拉过来,用两只手捂着。他的手摸起来软绵绵的,冰凉冰凉。我一直努力想暖热它,但坐到很晚,它还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