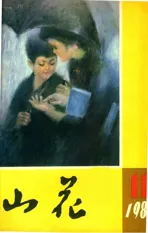青春荡漾
2011-01-18水格
水格
青春荡漾
水格
春天里的一个下午
我的朋友戈蓝是一个聋子。
春天一到,我就站在了火葬厂的高墙外,奶奶在世时对我说人是要从这里去天堂的,眯着眼睛躺在一把竹编的摇椅里的奶奶跟我说,她就要去天堂了。我问奶奶天堂有什么好玩的,奶奶就摸着我的大脑袋说,天堂里有神仙可以治好你的病,让你和你的哥哥一样聪明。
父亲从火葬厂出来后绝望地看着我。
那天下午,从郊外的火葬厂回来之后,我心满意足地躺在我和哥哥的大床上安静地睡去。
醒来的时候,已是黄昏。窗子外面一丝黯淡的光线掠过母亲的头发,有灰尘在跳舞。我恍惚地感觉到肚子在高声尖叫,我就从床上下来,趿拉着鞋子到处找吃的。我的拐杖敲在地板上发出很突兀的声音,像屋檐下的水滴。母亲在父亲的叹息声中忍不住又哭起来。我酡红色的、摇晃的身影一定是逶迤着走到夕阳的温暖里了。
哥哥去了南方
去年夏天的暑假。母亲带着哥哥去了南方。那是哥哥一生中最远的一次旅行。
为了争夺去南方的机会,我们明争暗斗了好长的时间。最后哥哥以胜利者的姿态跟在母亲的身后,提着我家那只年深日久的棕色皮包去火车站的时候,我睁着眼睛哗哗地淌着眼泪。
哥哥看见我的模样捂着嘴巴笑起来,笑得都快折断了腰。母亲转身,冰冷的目光落在哥哥细长单薄的身体上,他的放肆立时收敛,装模作样地往前走去。
我厌恶死他了,他的身体往棕色皮包的一侧微微倾斜,吃力的样子。我就在心里努力地诅咒他被累死。
哥哥去了南方,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
我和哥哥从小就生活在铁路边。在梦里,火车跑过铁轨的声音都会轰隆隆地把我们的梦叫醒,然后再把它们带到远方去。
可是,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从来没有,这是真的。
哥哥得意洋洋地坐上火车和母亲去了南方。这样一次美妙的经历成为他活着时向我炫耀的唯一资本。哥哥去了上海的姨妈家。
哥哥说,在姨妈家的院子里,仰起头就能看见很高很高的楼,有天那么高。我说天那么高是多高。他就很不耐烦地说,就是高到云彩里去啦!我还是有点迷惑,可是我哥哥已经背着手走到其他伙伴面前去炫耀啦!他趾高气扬地问:你们去过上海吗?

李雄伊作品·17
我哥哥到达姨妈家是在傍晚的时候。在此之前,他紧紧地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有气无力地抱怨着。他细长的身体被那只沉重的棕色皮包拉拽成一根面条,母亲的手里攥着一个香烟盒锡纸,上面有姨妈家的地址。
她目光涣散地看着眼前偌大的城市茫然无措。
在上海的街头,他们面色土灰、衣着邋遢,犹如两个来自外星的怪物。有人围了上来,他们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哥哥用袖头蹭着鼻子,然后嘿嘿一笑,带出北方粗糙的味道,同时他努力地竖起耳朵,想听清楚从那些人嘴里吐出来的词语。可是,那些词语就像是从鱼嘴里冒出的水泡,咕嘟嘟地往上跑,然后没有声息的就破碎了,什么也搞不明白。哥哥头上冒了汗,他看着母亲,母亲拿出那张锡纸给围拢的人看。那些人连看都不看就摇着手走开了。
哥哥挠着头皮跟随着母亲在一个又一个弄堂里像是两个勤劳的小贩窜来窜去。一直到黄昏的时候,他们伸长了舌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拍响了一家的木门,讨一口水喝。从里面走出一个穿裙子的小女孩,有漂亮的头发,迷人的眼睛,还有樱红的嘴巴。我哥哥不知道是因为口干舌燥还是色迷心窍,他把粉色的舌头亮出来,在嘴唇四周做运动,同时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女孩子的脸蛋立即变成了漫无边际的红色。小女孩一转身跑回去。不一会,嘈杂的脚步声蔓延到哥哥的脚下,踩在这声音上面威风凛凛的是一个彪悍的女人,她手里端着的不是一大碗水,而是一把剁肉用的刀。我哥哥惊吓得立刻撇下母亲往弄堂口跑去。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女人隔着门突然发出凄厉的嚎啕,母亲不停地抹着眼泪,嘴巴也像水里的鱼一样冒着水泡,听不清楚说些什么东西。
门里的彪悍女人挥舞着手里的菜刀向哥哥招手,菜刀在黄昏的光线里闪耀着金色的光泽。胆小如鼠的哥哥站在弄堂口看着母亲和那个女人一起向他呼喊,快回来,我们到家了。我的哥哥靠在一棵梧桐树下努力地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母亲一定是被那个彪悍的女人胁持了,她一定武功盖世,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我生性暴躁的母亲。破碎的阳光透过厚密的树叶落在他的鞋子上。
我哥哥就这样到了南方的姨妈家,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南方生活。
弄堂里来了一个北方男孩
细长身体的哥哥出现在南方的弄堂。
姨夫是石化公司的工人,穿蓝色的工作服,身上整日散发着油渍的味道,他是那种典型的南方男人,说话办事小心翼翼,埋在灯光下吃饭。席间,只有母亲和姨妈两个人喋喋不休,饭粒说不定从她们俩谁的嘴里飞出来,飞到姨夫或者表妹或者哥哥的碗里。姨夫疑惑地看着两个女人一眼,继续吃饭,要是落到两个孩子的碗里,他们就会叫嚷着,然后在各自母亲的恐吓中安静下来。
哥哥的目光不安地从白色瓷碗的沿儿上看过去,看到桌子对面的表妹面若桃花。她细细的手抓住筷子的下半节努力地在碗里拨动,发出好听的声音,眼睛则小心谨慎地看向别处。

李雄伊作品·18
晚上两个女人仍然忙于说话,她们坐在一起唧唧喳喳,一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一会又抹着眼泪哭哭啼啼的。姨夫看着屋子里仅有的一张床唉声叹气,他收拾好自己的被子对着表妹说,我到单位去睡,你和表哥到阁楼上去睡。他弯下腰,一只大手在表妹的脑袋上抚过,表妹抱着一只布娃娃眨着眼睛说,不,不嘛,我不和表哥在一起睡。
哥哥踩着木楼梯上阁楼的时候,发出了老鼠啃东西似的吱吱声。
哥哥伏在窗口,身体弓成一只虾米,往外望去的时候,满嘴都呼吸着潮湿的空气。这时表妹已经睡了,粉色的被单把她紧紧地裹住,只露着一张可爱的脸蛋。眼睛眯成了月牙。哥哥脱了鞋子,立刻有一股野气窜了出来。表妹睁开了眼睛好奇地问什么味道。哥哥尴尬地提着手里的鞋子说,臭脚丫子的味道,我和妈妈走了一个下午也找不到你们家,把我的脚丫子都走出了水泡,不信,你看看。哥哥说着坐到表妹的身边去,抬起一只脚丫子给表妹看。表妹猫一样从床上窜起来,露出了嫩白的肌肤,小小的乳房朦胧地藏在衣服的里面。她说,我才不要看呢。表妹显然是生气了,但她还是飞快地看了一眼哥哥腿上浓密的汗毛,心里就痒得像爬满了小虫子。哥哥把脚丫子收回去,站在地上。表妹把哥哥的鞋子拎起来,从打开的窗子扔了下去,然后拍拍手说这就好了,她关了窗子神秘地说,开窗子,白色的小鬼半夜的时候会跑进来的。哥哥生气地问她为什么把他的鞋子给扔了。表妹说,我没有扔啊,我只是把它放在外面了,要不然我们俩今天晚上会被熏死的。哥哥生气了,他脱了蓝色的背心,露出狭窄赤裸的上身。表妹突然叫起来。哥哥看看表妹说,在家我连裤衩都不穿的。表妹听了不再说话,只是豁的一下子钻到被单里去,小声地说,别到我的这边来。
哥哥在那个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搂住表妹,他还亲了表妹樱桃一样的小嘴。他醒来的时候太阳还没有爬出来,外面是一片灰蒙蒙的样子,哥哥发现表妹细细的胳膊缠住他的脖子,散乱的头发覆盖住他的眼睛,而他的手正放在表妹的胸上。哥哥同时心惊肉跳地发现自己的裤裆洇湿了一大片,他把手从表妹的身体上轻轻移开。表妹翻了个身,没有醒来。哥哥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丫子踩着木楼梯走到楼下去。姨妈已经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舞弄着菜刀了。哥哥猫着腰从厨房的门前经过,到外面捡回了自己的鞋子,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弄堂里来了一个高挑好看的北方男孩。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曲折潮湿的弄堂里飞翔。于是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多了起来,她们像一群小鸟一样站在表妹家门前唧唧喳喳。表妹一脸的绯红,她让哥哥站在她的身后,并且一条胳膊搭在她的肩上。哥哥就笑嘻嘻地站在表妹的后面。一整个夏天,都是这样。他们两个人乐此不疲。
以下是我对哥哥生前所作所为的猜想:
——他在上海那个弄堂的经历绝对不会这么简单。他一定在某个下午,在一片嘈杂的蝉叫声中爬进某个女孩子的阁楼,然后把她按在床上,那个女孩在半推半就之中绯红着脸查看了哥哥奇异的身体,她的手也许会在哥哥的身体上久久逗留。或者说哥哥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骑在下面。我乐于在哥哥死后进行这些猜测。当然也许哥哥爬进的就是表妹的阁楼。所以在哥哥从那里回来的时候,表妹一直是抽抽搭搭地哭,还不停地给哥哥写信。

李雄伊作品·19
有一天哥哥脸色苍白地问我,你说女孩子怀孕了怎么办啊?
我摇着头表示自己知识的薄浅,哥哥就劈了我一个嘴巴,然后愁眉苦脸地坐在窗子前想了一个下午。
我不知道天性活泼好动的哥哥怎么了。
戈蓝和我
哥哥去了上海。
我说你知道吗?戈蓝,我就要去上海了,那里有很多高楼,还能看见大海,看见长江,看到飞机呢!我摇晃着脑袋,看着她,微笑。即使我很大声地说话,她也不会听到,因为她是一个聋子。——在半年前,她在一家餐馆意外的爆炸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和戈蓝一个夏天都在发挥着我们绚烂的想象力,努力想象上海的美好。我总是把上海想象成一个巨大的冰激凌,而戈蓝总是把上海想象成一个漂亮的开满玫瑰的大花园。我指着在我们眼前跑过的火车说,哥哥就是坐着这样的火车去上海的。戈蓝看着我,她听不见我的声音,但是我还在说,我说戈蓝我们要是能一起坐一次火车该多好啊,你看,要是我们坐火车的话,就不叫火车总是趴在地上跑,我们让它站起来跑,它一定跑得快多了。
我呵呵地笑着,戈蓝看着我的眼睛,她说,我妈妈说,你会死的。
我对戈蓝比划着说,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好好地活着,你也别死,我们都好好地活着,然后我们去坐火车。
戈蓝看着我,眼睛水一样的清澈。
戈蓝说,你要是死了,我一定经常去陪你玩。
我搂过戈蓝,在她的脸蛋上亲了一口,电视上全是这么演的,然后我看见戈蓝的脸上多了一朵小小的玫瑰花。
那一年,我十四岁,戈蓝和我的哥哥同岁,他们都是十六岁。但是我却和戈蓝在一起上学,因为在我们的班级里没有一个人不是残疾。
秋天的一个夜晚
整个秋季,哥哥一直沉浸在对上海之行的美好回忆中。除了偶尔接到从上海邮来的信件让他产生恐惧外,哥哥基本上是兴致勃勃的。走路的时候,他努力地拱起肚皮,两只手交叉放在身后,迈着四方步,一副神气的样子。
父母前往百里之外的外婆家给老人过生日的那个夜晚,只有我和哥哥在家,他把父亲的通化葡萄酒,金士佰啤酒,还有老白干二锅头全都搬出来,像是玩具一样围在我的身边。
他说弟弟,你喜欢哪个就喝哪个。
我看着哥哥呵呵地笑,我想起父亲每顿饭前端着小酒盅神仙的样子,嘴巴里还发出啧啧的声音。
哥哥抽出了一支烟,叼在嘴巴上,点上了火,他闭上眼睛吸了一口,停顿了一会,一股青色的烟雾从他的嘴巴里冲出来,还从他的鼻孔里溜出来,并在我们中间缓慢地升起。我觉得好玩极了,也要了一支,我抽一口烟,喝一口哥哥给我倒好的葡萄酒,甜甜的,像喝了汽水一样。我说哥哥你也喝,他就说,这个算什么,我在上海都喝吐了,我再也不想喝这东西了。哥哥豪气地举起老白干咕咚咕咚地灌了两口。他大大的喉结剧烈地滚动着。
那个秋天的夜晚充满了醉醺醺的味道,黑暗中,门发出“咯吱”的声音,我费力地扭过头去,戈蓝安静地站在门口,她的裙角被风刮过,扬起了一角,露出光滑的小腿。我的大脑袋冲着戈蓝微笑了一下,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在我的面前恍惚起来,哥哥莫名其妙的笑声,戈蓝的影子,还有我看见的斜斜的窗子,都一下子沉到黑暗中去了。——
后来,我在黑暗中醒来,我,我的哥哥,还有戈蓝,我们三个人竟然睡在一张床上。我还发现哥哥正紧紧地搂住戈蓝,他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摇晃着脑袋从床上爬起来,伸手去推戈蓝身体上的哥哥,我哭叫着喊戈蓝的名字。
哥哥生气了,他骂我是大脑袋。我还要拽,哥哥就用他有力的后脚踹了我一下,把我“扑通”一声踹到床下去。等我从地上爬上来的时候,哥哥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像黑夜里的猫头鹰,中间夹杂着戈蓝的呻吟。哥哥一骨碌从戈蓝的身体上滚下来,然后我得到了戈蓝的抚摩,她小声地哭着,求哥哥把我弄到床上来。
那个晚上,我梦到了戈蓝,我梦到她赤裸着身体抱紧我,我们一起躺在水边的沙滩上,把脚丫子放到水里,不断涌过来的水一会涌上我们的肚脐,一会又退到我们的脚趾,那种美妙的感觉不停地袭来,像到了天堂一样。我好想奶奶,我想告诉她我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的了,可是我没有看见奶奶。水不停地涌着,越来越猛烈,一直到水把我们全部淹没。我感觉自己仿佛被融化了,从脚趾一点点蔓延,一直蔓延到我的大脑袋。
哥哥推醒我,我发现自己正抱着他的肩膀。哥哥说,你怎么回事,怎么还尿床?可我闻到的是哥哥身上的味道。哥哥转个身,说,真是的,离我远点,一会又尿到我身上了。
我第二天送戈蓝回家,戈蓝的妈妈正在给花浇水,她问我们说,昨天晚上刮了大风,有没有吓到你们啊?
戈蓝眼睛亮了一下,即刻又被昨天晚上呼呼刮着的大风给熄灭了。我不知道怎么和戈蓝的妈妈说,就什么也没有说。
我的哥哥死了
我的哥哥在春天的时候死了。他死得很安详,他几乎是和父亲同时从家里跑出去的。那天,我呆呆地坐在地板上,吃惊地看着他们。
——事情的起因是戈蓝怀孕了。
他们相互指责和咒骂,使我在恐惧的边缘陷入了陌生,我在他们的争吵声中意外地获得了安宁。他们谁都不在乎我了。甚至我学着哥哥的样子在嘴巴上叼了一支烟屁股,父母都没有对我说什么,他们的目光和语言全部集中在哥哥的身上。哥哥就站在门口,他还没有脱掉冬天的衣服,高挑的身子狠狠地裹在红色毛衣里面,露出一张俊朗的脸,最明亮的是他的眼睛,像两盏小太阳。

李雄伊作品·21
奶奶就曾经对我说,离你的哥哥远点,他的眼睛会灼伤你。
哥哥大大的脚在地上不安地搓来搓去。他不像我们的父母,他们在激动的时候身体都飒飒地颤抖,像风中的庄稼。哥哥就像是一座大山,一动不动,只有他大大的脚表现出了适当的激动。
后来,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这双脚就带着他跑了,跑到了黑色的夜晚里去。
夜凉如水,恣意如火。他在擦肩而过的风声中发出嚎啕的哭声,我坐在家里,隐约听见了哥哥的哭声,那声音仿佛这夜晚里的一道冷光,泛着青瓷的光泽。
我想到了一整个冬天里哥哥在夜晚里的反常行为。他天性的快乐和骄傲无影无踪了。他在濒临死亡的前夜突然抱住我失声痛哭。我大大的脑袋被他弄得濡湿。我就小声地叫他一声“哥”。
我说,戈蓝说,我会死,我真的会死吗?哥哥,我不想死,我想像你那样活着,可以跑,可以打架,可以把戈蓝抱起来。
他说弟弟,你会死,我会看着你死的。
哥哥被父亲拽了一把,他没有被拦腰而来的火车呼啸成一堆烂泥,他只被轧断了两条腿,所以死亡的到来是缓慢的,它乐意看到哥哥细致地完成死亡的仪式。我看到了哥哥湿淋淋的额头上的光洁,有擦不干净的血迹,我想象着那些红色的液体流淌的轨迹。
他睁着恐惧的双眼,我看见欲望的火苗依然在跳动,我想起了去年夏天那个高挑英俊的男孩,他是我的哥哥,为了和我争夺与母亲去上海的机会,他给我的药水里下了泻药。
他诡异地对着我微笑。他经常会一拳将我打哭,有时又拿来棒棒糖换回我的笑容。
我的哥哥,他说我会死掉,而且他会看着我死掉。
第二天的早上,一个春天的早上,我的哥哥他死了,死在一张洁白的床上。医院的人们把他的身体推来推去,最后交给了我的父母。我再一次看见了我的哥哥,他挺安静地躺在床上,额头上的血迹还在,我的母亲给他最后一次梳好头发,看着他甜蜜地睡在白色里。我想着我的哥哥这就要去天堂了,去见我的奶奶。
水格,原名杨学会,生于1981年,现居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