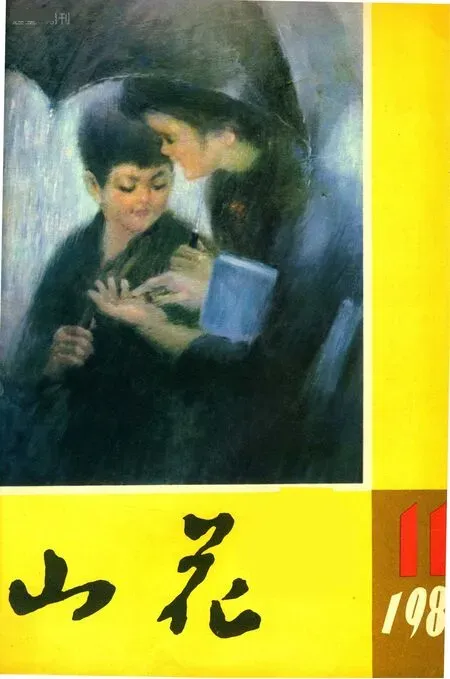纪实摄影与跨区域考察:顾铮、李公明“对台戏”摄影展及论坛纪要
2011-01-18录音整理石代娇曹一帆
录音整理:石代娇、曹一帆
定稿:马琳
纪实摄影与跨区域考察:顾铮、李公明“对台戏”摄影展及论坛纪要
录音整理:石代娇、曹一帆
定稿:马琳
海峡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的开放与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历史时期的重要侧面,在这种交流中产生的在地观察与影像记录将是两岸社会变迁、发展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文本。2010年4月2日,策展人马琳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中心举办了“对台戏:顾铮、李公明摄影展”。结合本展览,学术主持王南溟在99创意中心主持了“纪实摄影与跨区域考察”的论坛。该论坛讨论了以下几个主题:1.在观光摄影与深度性、系列性的纪实摄影之间,影像与社会观察的关系,影像的社会意义问题。2.从该展览看大陆人文学者对台湾社会观察的视角特征、问题关怀。3.台湾学者对大陆学者观察台湾的视角、内涵以及所反映的历史观与现实观的评价。4.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这批作品在当下两岸图像交流方面的意义。5.台湾社会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叙事与图像传播的关系。6.海峡两岸学术界在社会与人文影像方面的交流现状、问题和前景7.对展览作品的摄影性方面的分析。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教授、文化学者如王晓渔、刘擎、许纪霖、李行远、吴亮、张闳、王晓渔、张照堂、陆晔、林路、单世联、赵川、陈映芳、郭力昕、钱永祥、胡懿勋等十多位专家分别进行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及激烈的讨论。以下为论坛发言。
王南溟(独立策展人,批评家):今天上大美院99创意中心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样一个摄影展,摄影在当代艺术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跟当代艺术的转向有关。因为当代艺术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从以前审美的艺术转到面向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使得摄影以镜头为核心的创作方法成为了当代艺术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围绕这样一个内容,我们从美术馆的角度,还有从艺术中心的角度,哪怕是从画廊的角度,整个这样一个机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像我以前经常会说的,以前的美术馆当然包括艺术中心和画廊是一个审美的场所,但是今天由于当代艺术的发展,它不但是一个审美的场所而且也是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这是今天我们当代艺术转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也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99创意中心为李公明和顾铮老师举办了这样一个跟社会相联系的摄影展,同时,也有了这样一个跟社会相联系的社会论坛。今天论坛我们有这么多学生在场,有一点就是:同样是对一个策展人而言,展览只是一部分,展览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以展览来策划论坛,就是当今的展览其实是以论坛为核心而做的展览,这一类展览在当代艺术依然是今天新的一个动向,通过展览来做更好的论坛,通过论坛来讨论社会上的问题,那么围绕着这样一个话题今天的展览又和策展人培训计划合二为一,那么就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么多人的参与,也就是说我们的当代艺术也好、机构也好、艺术家也好在今天通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向。今天这么多专家都来了,我们有两个艺术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一个是顾铮老师、一个是李公明老师,我们先请李公明老师跟大家做一个主题演讲,来谈他是如何在台湾拍摄他的作品。

李雄伊作品·102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谢谢王溟教授。现在大陆的学者赴台的机会已经很多,拍到的照片其实也是很多的,但是我感到这种交流的机会还是少了点。我和顾铮很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向诸位做一个汇报,来听取大家的意见。我是2009年去的台湾,当时个人感觉到无论是情感还是价值关怀,都有一种感情上的激动。我想把我看到的通过摄影的方式呈现出来,我并没有想到我应该是一个摄影家的身份,而是心里确确实实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说句很坦率的话,在台湾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整天找想拍的地方,找想看的书,我们都觉得为什么我们找得那么痛苦,整天都很纠结。这么多的历史,这么多的问题,特别是想到我们在大陆由于很多的信息不畅通、书籍不对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感到非常痛苦。我想把我们长期以来想对台湾了解的欲望,对台湾的想象,包括对我们误解社会的一种看法,有一个更直接的、更快速的手段把它记录下来,表达出来。所以现在我拍了好多照片,但是到最后为什么我选这些东西呢?我很清楚这会给人一种政治化的标签和印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更多次的展览,我们不能说先做一个生活的、小资的展览,再慢慢过渡到等你们适应了我们再做一个政治化的展览,我们没有这种选择。我觉得大陆的民众、学者对于台湾的政治历史,对于很多图像的理解是很不够的。所以我们只能使用任何一次最简单的机会,就把图像摆在这里了,我不关心拍的好不好,因为这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种东西。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几个月的台湾访学,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读书,真的觉得很舒服,而不是一般做学问冰冷冷的感觉,而是有一种个人情感,一种个人经历。不仅仅是学问,还有更多的思考。
吴亮(《上海文化》主编):我先抢先讲一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昨天是愚人节,刚过,今天好像聪明人就蠢蠢欲动,今天聪明人都在开会,我刚刚就是从一个会议跑出来,我觉得这里我要来一下,所以我等不及了,像李公明这样如果要讲台湾历史的话可以讲到晚上。我现在明白了王南溟的意思,这个照片主角是他们,但是曾经试图把它变成一个论坛,当你在组织会议的时候,我觉得话语权是不自觉的转到了你的手里,觉得他们跑偏了,应该由你主持,论坛比展览更重要,说到这个李公明马上抢了过去说,然后说不,我们自己可以解释,那么我们现在明白了,李公明的照片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片后面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从李公明眼中看到很多故事,故事后面还有很多故事。有时间你们可以找李公明谈。那么顾铮是在干什么呢,他还没有说,我和顾铮太熟了,刚刚还看到他,他在被主持的时候,他还拿个相机在偷拍,拍这个拍那个,那么我就觉得想象顾铮这么一个对各种摄影都可以说出一番道理的人,他难道按快门的一瞬间是在思考问题吗?我发现他没有在思考,不可能在思考,因为我看到他到处在拍,就是这种抓拍偷拍,我想可能顾铮在回到家后在选择哪张有意思,因为他在拍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所有的解释都是后面加上的。当然李公明是不一样,他有两种照片,一种是有目标的,当他把相机对准蒋介石背影的时候,对准那个101的时候,对准那个墓地的时候,他是有意图的,但是门口的照片没有意图,那就是在逛街嘛,所以门口走了一圈以后我首先感觉你远远看过去它是台湾吗?它不是台湾,既没有阿里山也没有日月潭,去唯美已经不在审美了。你们的作品绝对不是新闻摄影,因为你们没有什么新闻事件突然发生,你们就闲逛,所以沿途所见,所以这种照片在坐的所有朋友们完全可以拍出来,不是说只有这两位朋友理论多高深。我就不相信,在坐的朋友你们也去转转,你们也可以办个展览,关键是什么呢?正好这个快门是他们按下的,但是你要去拍是没问题的。顾铮也是,既然他说他拍了很多,但是拿出来的很少,我以前听过陆元敏说他拍的就有两万张,那么浩瀚当中,就是选照片了,这里面花的时间要比拍照片多的多,现在基本上是处在成本为零的状态下面,人人都是摄影家,就如安迪·沃霍尔所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资格、有没有这样一种权利让大家在此评论你们的作品。今天马琳在现场介绍的时候,吓我一跳,全是教授,一帮教授吸引了那么多人,人们想知道教授的照片就不一样吗?我斗胆说一句,我经常得罪人,也许人们会说一句,“这种照片没什么意思嘛”,我们要进来听听他们在说什么,说的多重要,所以现在这么多人,比看照片的人还多。

李雄伊作品·107
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我刚刚在展厅看照片的时候其实是有点感触的。民国对于大陆来说就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对于台湾来说民国是个地理概念,所以当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大陆里民国传统是一个非常热的话题,所以想重新走到那个过去时里面。但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照片里面有另外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不可经历的,或者是仅仅只作为一种想象存在着,那这种在知识界里台湾的现在是我们大陆的未来,那么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就要看各种机会了。另外一种将来时,这里面看有一种时空错乱,一会儿过去时,一会儿将来时,一边是顾铮老师的作品,一边是李公明老师的作品。左边的摄影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比如在咖啡吧里面啊,右面里面的就有过去时,比如什么选举啊。那对于右边的场景呢,左边咖啡吧很漂亮的姑娘们就未必有兴趣,尤其对于我们大陆来说,比如28事件、台湾戒严的历史。如果跟台湾更年轻的一代交流,他们是对此不感兴趣的,他们出生在90后,此前怎么样,他们觉得不重要,他们没有想过这些东西。但对我们来说,左右两边我们都感兴趣,这个因为对于右边充分的了解熟悉,我们才能进入左边的生活。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这个“对台戏”看得出有一点差别,就是说顾铮老师他自己收的比较远,旁观的东西多一点。我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人和环境的关系,和空间的关系等细节处理得特别丰富。他有一些主题是不太经意发现的,比如说展览中有一张照片,28广场一个小女孩在卖报纸,她翻出来叫“民主出墙”,这就是藏在里面。然后公明兄呢,有一个理念在那里、一个关切在那里,在寻找着,所以李公明的照片有一点严肃,你看他取的名字,如“历史在这里”,这种在顾铮老师那里是不会有的。这些照片表现李公明有非常多的关怀,比如说那张按摩院下面的猪,那个红颜色的猪对在一起,那种对比戏剧性的张力,在整个感觉里特别强。李公明是带着自己的关怀问题去台湾的,我觉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你的概念,你的关切。顾铮老师的关切呢,肯定是有的,但是比较远,所以我们说照片是一个表征,有一个台北在那里,你们俩给出了不同的呈现。顾铮老师,他当然有自己的关怀和立场,他是尽量的收,尽量的保持着一种距离,以中立一点;而公明兄他是要把这个突显出来,这个主题性非常强,我觉得都非常有意识。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相信李公明和顾铮去台湾的时候,是带有自己的想象的。我看了这个展览后,我在体会你们的想象,因为这十来年我去了台湾八次,自以为台北跑的地方大概比你们多,你们两位看到的难道比我看到的还要多?结果我发现我还是看到了一些我没有注意到的,摄影家还是摄影家,摄影家注意到的东西,是我们凡夫俗子体会不到的。的确,两个人看出的台湾是不一样的,顾铮显然和他眼中的台湾有一种距离感,非常冷峻、不露声色,在他镜头里面看得出那种冷瑟,甚至那种淡漠,在他的照片里面,我觉得情感的东西在很深的地方,但是看不出来。但是李公明呢,刚才我在看的时候,有种霸气外露,就是刚才刘擎说的投射性很强,如同李公明今天的装扮,刻意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当然都是上品的,见仁见智,各有喜好,这里讲一句李公明可能不太想听的话,这两组里面,左和右之间,专业和业余还是看得出来的。但是有时候我倒是比较喜欢那种业余的东西,它没有一种规矩,学院出得了霸气的人吗?出不了的,这种像李公明一样在体制边缘行走的人,一只脚在体制里面,一只脚在体制外面,脑子在体制外面,身子在体制里面的那种。当然你试图通过你的照片去解读台湾的历史,这个有点过了,但是的确很多细节你能注意到。

李雄伊作品·111
李行远(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刚才大家好像把顾铮和李公明分了类,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因为照片呈现出来的,因为在台的那些日子李公明拍了很多照片,在做展览的时候就只能展几十张,就有一种选择上的纠结,昨天我就跟李公明说你死定了,你看顾铮的照片,顾铮的照片有好几张,我就非常喜欢,就一直在看。欣赏艺术品,有些东西我们是试图用语言给学生讲解,但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语言的,因为它本身是视觉的东西,如果能用语言代替的话也不要它。我觉得那个东西本身就是有一些很好看的,那么我觉得他在选择照片的时候我也知道,也经过一些讨论。顾铮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我们也是沉浸在其中的。李公明作品中也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有张照片里面有卷发票的细节,台湾有一种发票的抽奖,政府鼓励人们把发票投到箱子里捐给公众,等到开奖的时候,如果发票中奖的话,这些钱就归到某个基金会或是某个机构,我就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很欣赏台湾生活的很多细节,所以我非常喜欢,当然也有很多不公不正,我们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华人里面民主的社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也可以享受到这些细节。
张宏(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其实每个人初次到台湾去都想拍一大堆照片,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顾铮老师模式的,顾铮老师作品中有一张叫《永康街的茶人》,这个神态特别好。一种是李公明模式的,我也去拍了,有一些我觉得比你们拍的还好一些。你们俩这个模式,公明兄的拍摄有一种霸气的东西,有一种粗糙的东西,甚至不够专业的东西,但是我们讲要面对历史拍的时候,尤其是戒严的历史的时候,你不得不这样,你很难想象象顾铮那样很冷静的人怎样拍这种东西。在这个“对台戏”的展览,我倒是看出来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种关系,历史正在成为由摄影师记录下来,或者是纪念碑、展览馆的记忆,成为日常生活。国家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正在融为一体,给我印象很深,而在我们这里还有巨大的张力,所以在李公明作品中有很多严肃的时刻,而顾铮老师作品更注重日常生活的瞬间。
张照堂(台南艺术大学教授):顾铮的作品摄影感很强,拍得很细腻,也很敏锐,有美感。他把他对台北的感觉全拍出来了。李公明的作品有很多的信息符号,也非常有意思。他们的作品是对于公共空间、社会空间、生活空间的一个报告,不是仅仅限于摄影表面,而是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刚才各位专家都谈了,我就不多说了。
陆晔(复旦大学教授):我看该展的第一感觉跟王小渔很像,就辨认出哪是顾铮的作品,哪是李公明的作品。李公明老师是我很尊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摄影作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在台北层曾做过短暂的停留,我是传播专业的,一直想探讨影像跟都市的关系,即影像是如何建构都市形象的。吴亮老师刚才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好像在艺术界都已经实现了,但我并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我不认为“人人都是摄影家”。这个展览我感觉比较有意思的是无论哪个年代,我们对台湾都有一种想象,这种想像是无法脱离政治文化上的想象。两位艺术家通过摄影作品建构了台北这个城市的影像。这个展览不在于说谁更偏政治,谁更偏文化,谁更霸气外露,谁更细腻。而是在于这两位艺术家在这个地域的概念上给我们观者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丰富了对于一个地区的认识。李公明的作品在两岸政治记忆与社会政治环境角度体现出强烈的思考,重新建构了台北这个地域上的历史概念。顾铮这次的作品与以往不同,他用独特的视角体察日常生活与亚文化群体,像是在暗流涌动,呈现了日常生活的丰富与多元性。

李雄伊作品·112
陈映芳(复旦大学教授):我觉得艺术家拍这些作品并不是很随意的,而是首先是自己被感动了,然后想与大家分享。刚才大家都谈了对他们作品的看法与区别。我们的历史是残缺的,不完整的,我们想去修补。顾铮的作品比较注重感知日常生活。我认为他们的摄影语言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顾铮摄影更专业性些。他们的作品都体现了一种激动性。我不是为他们辩护,我觉得吴亮说的是不对的。他们给自己设定一种风景,自己给自己一种想象,用以表达心中的台湾,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我希望李公明的作品能继续保持他的直白性,顾铮的作品还保持他的专业性。
林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对他们的作品来说,不管是贴标签,还是不贴标签也好,都可以做一个归纳。在这里我不说专业或者业余,到今天可以说专业和业余已经没有什么界限可分,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年代。但是如果真的要给他们的作品贴上一些标签的话,从他们的表现角度来说其实大家已经在前面定了一个基调,我觉得这个基调还是要有的。因为我在看展览的时候就和朋友聊到,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义公明先生的话,那就是“愤青”。如果用一个词来定义顾铮的话,那就是“小资”。这是有明显区别的,这是一个新的标签,但是这个标签和之前也是比较一致的,也是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待,也更从社会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其实如果要选两张照片来代表的话,李公明就是和红色相关的《红色101》。而顾铮老师就是《台北红城》,这个让我特别感动,这是在很暗的光线底下,感光度已经提到1600以上的那种感觉。他们这两个红完全不一样,一个就是“愤青”的红,一个就是“小资”的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不管你贴不贴标签,有时候那些在骨子里的东西还是能够通过他的影像表现出来。其实顾铮也是非常愤青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愤青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你能说他现在不愤青吗?其实不然,当两个人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愤青的感觉仍然存在,但是顾铮更“聪明”一些,他在影像的叙述上把那种愤青的情绪隐藏到深处去了。所以不管怎么说,他把那些愤青的东西给化解了,让人看上去好像很柔情,很世俗化,但是其实他内含着很多批评,很多对社会的一种观察和认识。所以他们两者之间,正如大家所说的,并无高下之分,只是他们选择方式的个性,因为任何图像的呈现都是个人个性的外化,这是勉强不来的。所以从他们的图像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们对台北地域文化的一种解读,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去过台北,但都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对台北的一种感受,那种很独特的视野,确实可以作为一种互补,作为互相之间的融合,可以看到更多样化的台北。所以从他们的视觉语言来说,无论是对社会或是对人生的理解来说,这个展览确实是特别有趣,而且这台“对台戏”也唱得非常的出色。

李雄伊作品·113
单世联(上海交大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教授):刚才有人说到这些作品是从上万张照片中挑选出来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到台湾去拍上万张照片的话,那可以说是什么内容都有的了。现在从上万张照片中选出来这几十张作品一定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展览叫做“对台戏”,既然要演戏,那么就一定会有两个角度,而且一定要对立,不然也就没有戏了。实际上两个人观察到的台北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赞同刚才纪霖兄和李行远所说的,台湾人确实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既有民主和那种自由的精神,也有中国传统的人情。人情在我们这已经被扭曲了,但人情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这一点拿来和香港比,可能更多大陆人或者说一般中国人更喜欢台湾或者香港。从刚才他们两位选择的照片来看,公明可能更关注这方面。我自己想假如下次让我去台湾摄影我可能会选择公明这条路,实际上八十年代台湾和大陆都在不断变化,可能台湾民主已经比较成熟了,而大陆还处在民主建设的进程中,而我们这些年纪的人,特别是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文革前出生的人政治的情结,革命运动、红色、广场这些词总能引起我们激动,我们到一个地方总会去寻找这些,有没有都要把它找出来。实际上在台湾,特别是年轻人对公明表达的这些可能不大了解,就像我们大陆的青年,你和他们说文革,他们一样不知道,都是天方夜谭。这个可能不是大陆人的问题,而是和年代有关,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记忆和经验跟革命的历史、政治的历史、冲突的历史联系的比较紧密。
赵川(上海作家、导演):在过去的将近十年里我去过台北多次,有时还在那里小住,所以看到两位老师的作品有些东西还是很亲切的。那么我的感觉是这些摄影作品还是很直观的,之前也有老师从理论的角度谈到过,从我的感觉来看不管是“愤青”还是“小资”,这些作品都是性情之作。这两位摄影者的性格、价值取向和看待世界的方法在镜头下面也呈现了出来。当然我们这里的生活也有太多不满意的地方,所以台北成为了一个投射,变成一个想象。那台北到底是不是这样,有时重要有时又不那么重要,这样一来又陷入刚才吴亮所说的圈套里面。如果我说这些小青年喜欢漫画文化,他们会想象这个人在一个框子里出现,旁边还带有很多话,那现在这个房间可能已经被框铺满了,所以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王南溟的原意。其实回过头来想象展厅里的作品还是很阳光的,也和现在春天到来的季节十分相符。
胡懿勋(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如果和在座的各位老师比起来,我刚好是中间的中介者。如果从我两地跑的这样一个中介者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展览,我觉得很难去区别两位老师的区别。可能有一个共同点我一定要先提出来,然后才好展开我后面的看法,那就是我觉得两位老师的作品都是知识分子的观点,就是所谓的学者观念。无论他们怎么利用相机拍摄或是他们对哪种题材感兴趣,我觉得最相同的就是学者的观点,也就是知识分子观点。知识分子到了一个城市以后他可能想要印证他的某种研究或者自己的观察,这些影响让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想要印证一些什么,这两位老师是抱着一种相同的态度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比较关心影像本身的表现形式或者是所使用的摄影语言。那些影像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我也可以看到两位老师对台湾的关心到底是放在一个什么角度上面,这些角度和台北本土的知识分子的关心确确实实是有一些差距。比如顾铮老师的一件作品,就是两个穿制服的女孩站在门口,我没有办法揣测这样的影像对他的吸引之处,但是在台北本土学者看来,这样的影像会想到新宿,会想到银座,就认为那是日本传过来的流行文化,他可能不属于台北,那这里面也说明了台北的一种多样性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这里面有个我得到的启示,就是当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我用台北的观点看上海的时候,我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内容。
郭力昕(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我先来说一点我的个人经验,两位老师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很庆幸看到他们两人的创作状态。我在台大附近看见他们两个拿着相机拍摄,有一点搞笑的事情就是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对着东西拍了以后,另一个就马上抢着拍。我就在想你们拍一样的东西有什么意思?那李公明就说那角度不同。那时候我觉得他俩就像两个大男孩,很天真又互相友爱,这让我很感动。刚才听了各位老师说他们之间的异同,我比较赞同的是他们对于政治的关切是十分相像的。李公明也许是在对台湾政治社会的一种直击,一种记录。这些照片并不想有奢侈、悠哉的东西,这和他们作为公众知识分子是一致的,我特别感动的是我知道这些在大陆是很难做到的。而顾铮老师是把政治关切融入到了生活中,体现在细节里,所以与其说是摄影语言的更为复杂,不如说是关切政治话语的角度不同,他们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评论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们是非常认真和努力的。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其实我来参加这个座谈是很没有道理的,我记忆里没有什么看摄影展的经验,所以不能发表什么专业的评论。我今天来看这些作品觉得两位都在呈现台湾,并且是呈现台湾给大陆人看,下面去台湾展览也是让台湾人知道大陆人如何看台湾。这个工作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我每天生活在那里,但是我对很多地方都没有注意到,这就是你们和我这样住在当地人的不同。我觉得你们对台湾的注意力是远远胜于我们的,而你们在注意过后所呈现的东西是很真实的,台北就是有一些很混杂和很小市民的生活景观。刚才各位都是对台湾有很多溢美之词,对台北有很多称赞,我也很高兴听到。不过这几年来我觉得台北有一个问题出现,就是本来台湾人是没有这个自信的,主要是被大陆人称赞让台湾人越来越有自信。我就想说台北有很多地方很好,可是台湾和大陆要做对比的话,我想强调的是两边近代史最大的不同。台湾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社会,跟大陆作为一个胜利者的社会这个文化面向非常不一样。台湾经历过前后二三十年的冲突、磨合,慢慢摸索出这样一条民主化道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历史使得台湾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色,而这些特色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复制,但是我想主要是两边的文化、语言等方面太过接近,太接近的结果就是两边会有一个相融化的作用。最后希望大家多到台湾去,让我们也能多沾沾你们英雄的豪气。
顾铮(复旦大学教授,摄影家):刚才钱老师的发言给我很多触动,大家都把台湾理想化,有自己内心的一种想象在里面,包括我们的摄影语言。其实摄影就是影像的一个操作过程,经过反复的筛选,这一路选下来肯定要思考自己最想留下的是什么,这里面肯定是自己对对象的想象和自己的个人经验,为什么要把这些照片留下来。反过来说这种对台湾社会的反省让我想到我要对这些照片进行反思。我希望我的这些照片成为一种线索,而不是阻碍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台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门板。这些照片就等于是一面墙,我们只是看到了表面的印象,这些都是我看到的,也包括我没看到的。我看到的和没看到的在一个平面显示之后,让观众看不到东西的话那就是我的罪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希望我的这些照片成为满足大家台湾想象的一种东西,而反过来希望能成为一扇窗户,能让大家思考这位摄影者除了这些照片还会有些什么。公明昨天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可能会有出版社会把我们的东西剪辑起来出版,如果出版的话是不是摄影本身还需要一些文字加以补充,或者还可以把对我们因为某些原因主动筛选的东西再补充进去,包括今天的座谈会各位老师跨学科指导和跨海岸的鼓励等等都以某种形式结合起来。当然也更希望这个展览有机会再到台湾去,让台湾的朋友再看一看,通过这样反复的交流过程能够知道看这个东西并非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太多的关卡,我今天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包括比如有两张的有五张的,就是形成一种关系,突破单张照片的限制,更多的照片有一种关系、对话等等。但是这样的努力还是受限制的,所以说摄影还是一种受限制的观看方式,在限制中间怎么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