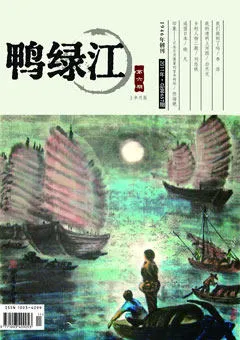乡村人物二题
2011-01-01刘志铁
鸭绿江 2011年6期
刘志铁,男,辽宁凌源人,1987年毕业于朝阳市第二师范学校,曾当过中学教师多年,现供职于凌源市史志办公室。有小说、散文在《鸭绿江》《辽河文学》《经典美文》《华夏散文》《辽宁日报》《辽宁法制报》《教师报》等省市报刊杂志发表。
柳大郎
柳大郎是影匠。柳大郎唱影不是祖传,是半道学的。柳大郎他爷爷是赶驮子的,走口里,一年一个来回。上秋的时候,贩山货去口里,入了冬,再从口里贩布回到口外老家。柳大郎他爷爷四十六岁那年,从口里赶着七八头牲口,满载着各种上好的花布往家走,走到青龙河菠萝树一带遇到了土匪,不但被劫了财物,还差点送了命。柳大郎他爷爷吓破了胆儿,就此罢手,再也不赶驮子了。不但自己不赶驮子了,也不让儿子赶驮子。不让赶驮子,柳大郎他爹就给邻村的“郭记豆腐坊”当了学徒,学做豆腐。三年学成后,柳大郎他爹也开了个豆腐坊,叫“柳记豆腐坊”,打出了自己的旗号。柳记豆腐坊做的豆腐远近闻名,声震半个热河省,连百十里外的满州国县衙里的老爷也打发人到柳记豆腐坊来买豆腐。柳大郎他爹有两个儿子,柳大郎和柳二白。柳大郎他爹原打算让哥俩都学做豆腐,但柳大郎不乐意。不乐意不是嫌恶做豆腐没出息,或是汤汤水水的埋汰,而是闻不了豆腐的腥味儿。柳大郎他爹做了一辈子的豆腐,柳大郎吃他爹做的豆腐不超过三块。就是因为受不了豆腐的腥味儿,柳大郎才跟着一拨下关东的走了。
在辽西一带,关东指的是黑龙江。去黑龙江不说去黑龙江,都说下关东。黑龙江地广人稀,不愁找不到活儿,有活儿干就饿不死人。下关东的人干什么的都有,扛活的,淘金的,伐木的,放山的,拾荒的。柳大郎是奔拾荒去的。拾荒就是捡庄稼。柳大郎在家时听人说,关东耕地多,都是好地,垄头儿也长,站在这边往那边望,一眼望不到头。因为夏短冬长,就多种黄豆,黄豆耐寒。收黄豆不像辽西这疙瘩,小心翼翼的,崩地上一个豆也得捡回来。听说关东人收黄豆用一尺长的弯月大钩镰,像割柴火一样歘歘歘放铺子。黄豆粒子四处开花,满地焦黄,没人管,任人去捡。还听人说,有能捡的,一个秋天下来,能捡多少多少麻袋。柳大郎虽不喜欢吃豆腐,闻到豆腥味儿就晕,但却知道做豆腐用的是黄豆,黄豆值钱,他爹的豆腐坊常因为没本钱买黄豆而关板儿。豆腐坊一关板儿,他爹就闷得慌,就拿追鸡撵鸭打老婆骂孩子解闷儿。
柳大郎下关东就+0kyEkaPJk2kDe+v+1vh5A==是想去拾荒捡黄豆。
柳大郎是偷着跟人走的。临走前一天晚上,柳大郎从他爹黑黢燎光的木头钱匣子里抓了一把铜钱儿。第二天起个大早,趁他爹在套驴磨豆腐,就溜出门蹽杆子了。
下关东路途遥远,道上也不太平。柳大郎他们走了差不多半年,在牡丹江一个叫卧虎山的地方,遇到了土匪,一帮人被冲散了。柳大郎腿快,听到枪响,兔子似的撒腿就跑,翻过几道山梁,穿过了几条沟,才渐渐地收住腿。开始时还为自己腿快庆幸,过后一打量,才知道坏了,自己落单儿了。落单儿倒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是兜里的几枚铜钱也在刚才穿沟越岭时不知颠到哪儿去了,上上下下摸个遍,一枚都没剩下。钱没了也不怕,大不了要着吃,也不至于饿死人,怕的是这里荒无人烟,走了半天的路,听不到一声鸡叫。柳大郎胡摸乱撞地走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天黑,来到一个看场的窝棚里。柳大郎又饥又累,靠着一堆乱谷草,一下子就昏睡过去了。
是一个唱影的影匠班子把柳大郎给救了。影班子的头儿姓周,人称老周,祖籍山西,前清时逃荒过来的,三代影匠。周影匠他们发现柳大郎时,柳大郎正发着烧,嘴里说着胡话。
影班里其他影匠都反对带着柳大郎,说是一个快死的人了,明显是个累赘。还说,死了倒还好了,怕的是不死,不死就得吃饭。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多一张嘴分粥喝不是小事。
老周不以为然。老周说:“好歹是一条人命,看不着也就罢了,看着了假装没看着,心里不落忍。”
又说:“说了归齐,也是个缘分,荒山野岭的,别人没遇着,偏偏就让咱们遇着了,这里面就有个定数。或者是上辈子咱欠了他的,欠了他的咱还他,也就省心了;或者是上辈子咱没欠他,没欠他却救他,算他欠咱们的,那下辈子他再还咱们,都不白搭。”
老周这么一说,别的影匠都不吱声了,七手八脚地把柳大郎抬上了小驴车。
小驴车是雇来的。赶车的老胡伸长脖子看看柳大郎,说有气中,要没气可别拉,晦气。
柳大郎在小驴车上躺了三天,吃了六顿饱饭,身体开始渐渐复元。身体不好时白吃白喝人家的,有情可原;身体好了还赖着不走,就说不过去了。第四天早上,柳大郎给老周磕了个头,告辞想走。
老周说:“人生地不熟的,你往哪走?”
柳大郎说:“去拾荒捡黄豆。”
老周和其他影匠听了都乐了,说:“你小子做梦娶媳妇想得美,哪有那么多黄豆给你留着。这要是真事儿就好了,咱们影也别唱了,都去捡黄豆得了。”
又说:“闯关东是闹着玩的?哪个不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九死一生的,说不定啥时候,小命就丢了。”
又说:“你爹你妈也真舍得你,真格地就放心让你一个孩子闯关东?切。”
话说到这儿,柳大郎眼圈红了,说自己离家时爹妈根本不知道。
老周说:“算了吧,反正多你一张嘴,影班子也困难不到哪儿去,不嫌乎我这庙小,就留下,有我们一口吃的,也饿不着你。等以后有了好路子,你再走你的,咱也不耽误你发财。”
柳大郎又给老周磕了个头,就留在了影班子。
柳大郎跟着老周的影班子流浪关东。柳大郎不会唱影,就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搭台子,拆台子,搬铺盖卷,跑几十里买麻油,给灯添油;哪个影匠拉稀跑肚了,跑药铺抓药,抓回了药再熬药;给老周端过洗脚水,倒过尿盆。柳大郎小时候念过两年私塾,眼跟前的字都认得,所以没事时就看影卷。白天看影卷,晚上拎个麻油筒等着给灯添油。添油不是总添,一晚上也就添个两三回,不添油的时候,就坐在台上听老周他们唱影。柳大郎记性好,白天看的影卷,晚上还记得,所以听影就听得十分明白。不但听得明白,词和人物情节,都记在心里了。白天再跑三十里地去镇上打麻油时,就不寂寞了,把昨晚上听来的,一句一句重复着唱。时间长了,耳濡目染,柳大郎也能有滋有味地哼上几段了。柳大郎喜欢唱大丑,他的嗓音有点沙哑,唱大丑,别有一番味道。
人干啥都讲究一个运气,运气来了,你躲都躲不开。有一次,影班子在高家店一个老财主家唱院影。财主姓高,人称高大户。高大户万贯家财,良田千顷,深宅大院五进数十间。遗憾的是奔五十的人了,却没得一个儿子来接续祖基。高大户十分怄火,小老婆娶了三房,养了一堆丫头,硬是没养出来一个带把儿的。五十一岁那年开春,三姨太肚子里又怀上了。本来高大户并没指望她能生出儿子来,也就没怎么高兴。没承想,入了冬,三姨太还真给他生出个儿子来,乐得高大户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接连蹦了三四个高儿,下令搭敞棚施粥十五天,连唱八台大影。
唱影请的就是老周的影班子。
高大户吩咐:“为感念神明佑我高宅,赐我子嗣,就唱《封神榜》。”
又吩咐:“除管吃管住外,影匠每天每人一块大洋。给我铆足了劲唱,唱好喽,另外还有赏钱。”
头天晚上,高大户让长工宰了一口肥猪,猪肉粉条大锅炖,大盆子上,管够。
也是长时间没见着荤腥了,唱丑的老霍就吃多了。一个影匠,三顿饱两顿饥的,肠子和胃净装那些烂菜帮子野菜团子了,冷不丁一见着油水,就受不了了,先是咕噜咕噜响,然后就开始下坠蹿稀。蹿稀倒也没啥,蹿个一两次,耽误不了唱影,问题是蹿起来没完了。蹿一次刚回来,裤腰带还没系紧,又猫腰撅腚地小跑着往外蹽。不蹿的时候也不行,不敢使劲唱,一使劲下面就往外鼓,像要有东西冒出来。
老周当时就急出一帽头子汗:“人家高大户五十得子,请影谢神,这是小事?这要整砸喽,得了吗?”
情急之下,老周想到了柳大郎。柳大郎不敢上,被老周连推带搡整台上去了。没上台时心突突,大腿肚子哆嗦,上了台,反而镇静了。万事开头难,头三脚踢出去了,剩下的就好说了。柳大郎头三脚踢得不赖。柳大郎学着别的影匠的样子,掐着喉咙,使劲揪着喉结处的那块皮,咧着架子嚎。唱着唱着就入了戏,忘了形,还模仿老霍,接三差五地来两句诨嗑,逗得台下看影的人前仰后合地笑。虽是模仿老霍,却比老霍技高一筹。老霍诨嗑发笨,让人一听就听出假来,一听就知道是老霍自己胡诌的。柳大郎的诨嗑来得巧妙,不露痕迹,能够和戏文浑然一体,让人觉得诨嗑不是柳大郎说的,是戏里的人物说的。
影匠老霍的几泡愣稀,成就了柳大郎。高家店高大户的头台影,柳大郎一炮打响。头天晚上刚一刹台,老周就照柳大郎的屁股踹了一脚,说:“你小子,有尿,几年的饭,没白喂你。”
但老霍蹿稀是吃肉撑的,不是啥大毛病。蹿了一晚上,把东西都蹿出去了,也就好了。老霍好了,唱丑的还是老霍,柳大郎还去管他的老本行,跑几十里去镇上油铺打麻油,给灯添油。第二天第三天就这样过去了。到第四天头上,东家高大户找到老周,说:“咋不让头天晚上那小伙子唱了呢?”
老周说:“那小伙子是跑腿打杂的,头天晚上老霍跑肚,他临时顶缸。”
高大户说:“每天多加两块大洋,你还叫那小伙子唱。”
老周听小道消息说,是高大户三姨太的一个使唤丫头乐意听柳大郎唱。这丫头叫红叶,十六岁,是三姨太从娘家带过来的。红叶不会听影,听影匠们吱吱呀呀地唱,就像听夏天山坡子上呜嘤哇叫,只觉得闹得慌,听不出子丑寅卯。以前唱影,红叶都躲在屋里不出去,这回,因为满大院里一片喜气,热火朝天,就忍不住出来看看,本打算打一绕就回去了,谁承想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柳大郎唱影。按理儿,一个使唤丫头,不至于让高大户巴巴地去找老周,每晚宁可多搭两块大洋,要求换人。其中原委,除了高大户和红叶,别人都不知道。红叶表面上是三姨太的使唤丫头,背地里已经成了高大户的人了。要不是三姨太生了儿子,高大户就收红叶为第四房小老婆了。三姨太生了儿子,事才缓了下来。
这事儿让老周嘬牙花子。换人吧,老霍跟自己这么多年,说功劳有功劳,说苦劳有苦劳,事好办,话不好说;不办吧,东家发话了,顶着不换人,也不是事儿。不是事儿倒不是高大户财大气粗,老周不敢惹,或者是舍不得每晚多加的两块大洋,而是你吃人家喝人家,就得随人家的意,不能逆着东家。老周埋怨老霍,说了归齐,事还赖老霍自己,没成色。他要是不拉肚,就不会有这事儿;拉肚也行,拉就拉个十天八天的,事儿也就过去了,偏偏他拉一天就不拉了。埋怨归埋怨,老周掂量来掂量去,还是去找了老霍,把事儿和老霍说了。
老霍半天没吱声,然后叹口气,说:“中,没事。”
嘴里说没事,心里却别扭着。有毛病让人顶了,不算寒碜;没毛病让人顶了,那就忒寒碜了。单是寒碜,也就算了,寒碜个一天两天,过过火,也就感觉不出寒碜了。问题是这叫让人家给盖帽儿了,栽大跟头了。老霍越想心越窄巴,第二天一早,跟老周说要去打麻油。老周不让他去,说还叫柳大郎去,反正白天也不唱影。老霍笑了笑,说该干啥干啥。老周就让他去了。到了晚上老霍没回来。第二天早上还没回来。老周派人到镇上油铺去问,油铺伙计说根本没看着人儿。老周才知道老霍是磨不开面儿蹽杆子了。
老周跺着脚:“这老霍,心眼咋就这么小呢,针鼻似的。”
过后,老周又后悔没多拿两块大洋给他。
黑天唱影,白天睡觉。影匠们睡觉在东家的偏棚子里。偏棚子实际是牲口棚,五间草房,三间圈牲口,另两间堆草料。有一铺炕,是两间屋的通长大炕,平时喂牲口的住,有走道路过耍杂耍找宿的,也在这铺炕上住。老周他们就睡在这铺炕上。柳大郎白天不睡觉,耽误半宿觉对他来说不算事儿,他在老家时,帮爹磨一宿豆腐,白天也不睡。柳大郎不睡觉,就在牲口棚前面溜达,看红叶在不远处洗尿布,晾尿布。洗完尿布的脏水得倒到牲口棚拐角那儿去,有五十米远。红叶趔趔巴巴地拎着一桶脏水去倒,柳大郎看见了,就赶紧接过红叶手中的脏水桶。
倒完脏水,把木桶递给红叶的时候,红叶说:“把你衣服拿来洗。”
柳大郎就把衣服拿来让红叶洗。
老周悄悄嘱咐柳大郎:“少招惹人家女人,吃四方饭的人,最忌的就是这个,记住了?”
柳大郎点头,说记住了。
八台影唱完,老周的影班子走了,准备沿牡丹江而下,奔依兰和林口。冬天天短,走出四十里地,天就黑下来了,左近没有村落,更无店铺。天又落下雪来。恰好,路边有一个废弃的场窝棚,窝棚边上还有一堆杂乱的谷草。老周他们就把谷草铺在地上,坐在上面躲避风雪。半夜时,听到外面窸窣地响。初时以为是野牲口,等那窸窣声来到窝棚口,才知道是一个人。柳大郎第一个跳起来,他认出那人是红叶,尽管她浑身上下差不多被雪裹住了,但他还是认出来了。红叶显然不知道窝棚里有人。柳大郎跳起来时,红叶妈呀一声,撒腿就跑。柳大郎赶紧喊红叶红叶。红叶听出了柳大郎的声音,停下了。
雪地里,红叶扑到柳大郎怀里,呜呜地哭了。
老周看着雪地里的人影,说:“完了,祸事来了。”
雪一直在下,黑夜里处处放射出一种银白的毫光。
天还没亮,老周带着影班子改道进了吉林境内。
老周的影班沿牡丹江上行到敦化,在敦化唱了二十多天,又来到了安图。在安图停留一个月,又来到了汪清。影班就是在汪清的悬羊镇出的事儿。悬羊镇在悬羊山下,是汪清东北有名的一个大镇,上千户人家。街上店铺一个挨着一个,粮店、饭馆、棉花铺、银饰铺、狗肉铺,烧酒铺,街两边还有不少小商小贩,或挑担子,或推木轮小车,沿街叫卖。油条、烧饼、豆腐脑、馄饨、炒瓜子、冰糖葫芦,样样都有。见这里热闹,老周就决定先不往前走了,在悬羊镇过年。
镇上的几个商家凑份子,请老周的影班唱了三台影,唱的是《五峰会》。头一晚,挺好。第二晚,出事了。影刚开台没一会儿,看影的人群里就有些骚动,好像有人在大声叫嚷。影匠们开始都没在意,以为谁和谁有矛盾,看影时又碰到一起,整起来了。这是常事,不稀罕,走八方卖艺的人什么都见过,不值当奇怪。但接下来老周他们便觉察出了不对劲,叫嚷声好像是冲台上来的:
“什么鸡巴玩意儿,会唱吧?不会唱走人!”
“以为悬羊镇是好糊弄的吗?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相!”
老周和影匠们都吃了一惊:莫非悬羊镇有高人,没拜到挑理儿了?
接下来再一听,又感觉话头不对:
“台上那个妞是干啥的?让妞唱。”
“对,让妞唱,妞唱好听,哈哈哈……”
“谁不乐意听妞唱啊,对不对?细声细气的。谁乐意听大老爷们儿咧咧啊,一张嘴就驴似的,让妞唱!”
……
“妞唱不唱?不唱砸台子,砸!”
台子在晃,灯也跟着晃,柱子和木板嘎吱嘎吱响。老周和影匠们赶紧跳下台子。红叶哆嗦着身子躲在柳大郎身后。
老周抱拳说:“各位爷,小的无知,多有得罪,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人走过来,用手扒拉开老周,走到柳大郎跟前,说:“你叫柳大郎?”
又伸长脖子看看红叶:“这妞不赖,你小子还真有点艳福。我还纳闷呢,一个丫头,还犯得上费这么大操持?嘁,闹半天,是个大美妞。可惜啊,你们缘分浅,到此为止了。”
刀疤脸回头一摆手,轻描淡写地说:“弟兄们,砸折他一条腿。”
一顿拳打脚踢之后,柳大郎折了一条腿,趴在地上起不来。
刀疤脸说:“把妞带着,撤。”
走了几步又回来了,对惊魂未定的老周说:“得罪,你老多担待,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没办法,弟兄们就是吃这碗饭的。”
后来老周才弄明白,这帮人就是牡丹江卧虎山上的土匪。红叶私奔后,高大户窝囊了好长时间,越想越憋气。要是一般的丫头,跑了也就跑了,算不了啥。问题是红叶不是一般的丫头。方圆几十里,高大户动别人的女人可以,但还没有人敢动他高大户的女人。高大户琢磨了好几天,终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叫伙计背上二百块大洋,亲自进卧虎山拜见大当家的许大棒,并答应事成后,再加三百大洋。
伤筋动骨一百天。为给柳大郎治腿,影班就一直在悬羊镇住了下来。第二年开春,柳大郎的腿好了,但留下了残疾,点脚子。影班离开悬羊镇的时候,柳大郎没有跟影班走,独自一人返回牡丹江高家店寻找红叶。路上走了两个半月,到高家店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柳大郎不敢贸然闯进高家,在门口蹲了两天,没见着红叶。去庄里打探消息。一个老妇人告诉他,红叶被抓后,还没等回到高家就死了。老妇人还告诉他,离这儿二十里,有个地方叫鹿儿跳。红叶走到鹿儿跳,假装说去解手,趁人不注意,就从鹿儿跳跳下去了。
柳大郎买了很多烧纸,去了鹿儿跳。鹿儿跳是一面很陡的石崖,高数十丈,一律火红的颜色。崖下是一片乱石滩,并没有树木。柳大郎在崖下烧了纸,纸灰顺着石壁飞起来,一直向崖顶上飞去。柳大郎听老人说过,烧纸时,纸灰飞起来,说明那边的人已经收到了。柳大郎看着飞起来的纸灰,眼里流下泪来,但没有哭出声,脸上的表情也很平静。
柳大郎在牡丹江高家店一带流浪了三年。三年里逢年过节,他都来鹿儿跳给红叶烧纸。其间,他打过短工,当过挑夫,也拾过荒捡过黄豆。
全国解放后,柳大郎回到了辽西老家。回来时,他的爹妈早死了,豆腐坊传给了老二柳二白。柳二白说:“要不咱哥俩合开?”
柳大郎说:“不,我闻不了那味儿。”
柳大郎回来时四十多岁,以后一直未娶。未娶不是说他岁数大了娶不上,或者是眼跟前的女人没有他相中的,而是没有那份心情。柳大郎后来没唱过影。不唱影,但他喜欢抠影人儿。柳大郎抠的影人儿,材料用的是驴皮。一张驴皮,要经过泡皮、刮皮、浆皮、焖皮、雕刻、着色、上油、连缀成型等二十几道程序。柳大郎抠的影人儿越来越精致,县文化馆还来人拜访过他,拿走了一些影人儿,说是要参加什么展览。
传言说,柳大郎有一个最好的影人儿,是他用了一年时间抠成的,但从不示人。有人提起,柳大郎只是一笑,说:“没有的事。”
柳大郎七十五岁死的。死之前,他从褥子底下拿出一个影人儿。影人儿高二尺,黑发盘髻,单凤眼,鼻梁挺直,非常精致,看得出,从选料到制皮到雕刻等诸般工序,柳大郎是下了一番工夫的。柳大郎把影人儿交给二弟柳二白,说:“把她跟我一块堆埋喽。”
谁都不知道,这个影人儿有名字,叫红叶。
马锢漏
锢漏锅子是一种手艺,就是锔锅锔碗锔大缸。庄户人家,过日子仔细,有烧炸了的生铁锅,摔破了的碗,裂了璺的瓷缸,都舍不得丢掉,收拾起来放到一边,等着马锢漏来了锔上,锔完了,照样用。马锢漏是当地有名的锢漏锅子,手艺是祖传的,到他这儿是第四辈儿。马锢漏有名有姓,姓马,名殿举,名字是他爹老锢漏给取的。有一回,老锢漏出门做锢漏活,因为事先没讲好价钱,干完活后,因为钱多钱少跟人犯了口舌,结果让人给打了,锢漏挑子也让人家踹了一脚,断了一根撑。回家后,老锢漏越想越憋气,蒙着破棉被在炕头上闷了三天,最后决定给儿子取大名叫马殿举,进私塾读书,将来弄个一官半职,省得再受这份窝囊气。老锢漏没念过书,但他知道,殿试取进士,乡试考举人,他给儿子取名叫马殿举,意思是希望儿子最好能杀进殿试弄个进士,即使弄不上进士,退而求其次,弄个举人也可以。
马锢漏进学堂那年七岁。先读了《百家姓》,又读了《三字经》。十岁那年,先生开始教他读《论语》。先生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不可不学也。可惜的是,先生说完这话没几天,清政府就倒了台子,成立民国,废了科举,私塾先生也卷铺盖卷儿回了老家。私塾解散了,马锢漏也失学了。老锢漏长叹一口气,说:“人算不如天算,人咋能算也算不过天。算不过,就不算了,还是吃这碗祖上传下来的饭吧,富不了,也饿不着。”
马锢漏跟他爹学了锢漏锅子的手艺,马殿举这个名字也就跟着夭折了。走到哪儿,人家都喊他马锢漏,不叫他马殿举。马锢漏开始还郑重其事地更正过几回,说:“我叫马殿举。”人家听了,恍然大悟似的笑着说:“对对,马殿举,叫马殿举。”可一转身的工夫,又叫他马锢漏。如此再三,马锢漏也就不更正了。马锢漏想明白了,人要是没那命,叫啥名儿都白扯,我就是锢漏的命,叫我马皇上我也还是锢漏,马锢漏就马锢漏吧。
腊月是做锢漏活的旺季。腊月里家家淘米轧面,杀猪宰羊,走油炸丸子。做这些活计之前,都得先把锅碗瓢盆的家什拾掇利索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该锔的锔,该补的补。马锢漏一个腊月闲不着,出东村进西庄,到哪儿都得忙个两三天。
马锢漏有一副锢漏挑子,是跟着锢漏手艺一起由祖上传下来的,一看颜色就知道是有些年头的东西了。原来可能是红色的,但日子久了,又烟熏火燎,就变成黑的了。但木质很好,山梨木做的,一敲当当响。锢漏挑子前头是一只木箱,木箱分上下两部分,下半部分是一只风匣,上半部分是一只带盖的盒子,里面放着小火炉,还有一根铁皮圆筒,是用来连接风匣和小火炉的风道。后头也是一只木箱,但分若干个抽匣,里面分装着各种用具,一个小巧的砧子、一把金刚钻、几只小坩埚、铁丝、铆钉、锔子、小锤子、小剪子,还有不少破破烂烂杂七杂八的小物件。箱子的四角镶嵌着同样材质的四根撑,其中一根中间箍着一截黄灿灿的铜箍,就是他爹挨打让人踹折的那根,是老锢漏化了一块铜接上的。四根撑的上方用横木连接。扁担是桑木的,中间有弧度,两头固定在横木上。扁担和挑子成一体,既方便,又能起到固定的作用,放到哪儿不易倒。扁担前头挂一面小铜锣,一进村,先敲一阵小铜锣,然后扯着嗓子喊一声:“锔锅锔碗锔大缸——”
马锢漏人长得瘦,脖子很细。脖子细,就显得比一般人的长,喊的时候,脖子一伸一伸的,跟公鸡打鸣差不多。走到哪儿,身边都围着一帮看热闹的小孩。他一喊,看热闹的小孩也跟着喊。但小孩喊的不是锔锅锔碗锔大缸,是锔锅锔碗锔尿罐。喊完了,还笑,笑过一气,再接着喊。马锢漏脾气好,不爱说话。但不爱说话的人一旦说话,他一句能顶人家一百句。马锢漏听小孩喊,不生气,拣平整的地方放下挑子,拿出小板凳来坐下,说:“去,家去问问你妈,有破锅破碗破尿罐没?拿来锔,锔完了照样使,保准不漏尿。”村里的女人听见了,就说,这锢漏锅子,看着老实巴交,其实不是啥好人。
不是好人不怕,只要他手艺好,锔完的家什好使就行。马锢漏的手艺不赖,方圆几十里有名。山里的女人都泼辣,不在乎一两句糙拉话,要真惹得她们兴起,撒起泼来,能把那些老爷们吓得落荒而逃。女人眼睛瞅着马锢漏,说:“破盆破碗锔得倒是不错,就是你那嘴总是锔不利索,实在不行,整点锡镴锢漏上得了。”说完,哈哈哈笑一阵,笑完,把在房山墙角厕所旮旯里翻拾出来的破盆破碗往马锢漏跟前一丢,说:“锔吧。”
马锢漏不说话,也不抬头看人,拿起破盆破碗看看,往小板凳上咣咣地磕磕,磕掉上面的泥痂疤,再看看,然后告诉你应该咋整咋整,得多少多少钱,整就整,不整拉倒。然后,把破盆破碗再扔回原处,不多说话。马锢漏吸取了他爹老锢漏的教训。老锢漏临把锢漏挑子交给他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的一句话就是,多少钱,先挑明喽,别等到过后再磨唧,整不好的话,往往在这上面出疵儿。马锢漏坚守着老锢漏的叮嘱,等到人家说整吧,他才又拿起来,拉风匣生火,按着刚说过的方法或是锢漏或是锔。
锢漏和锔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做饭的大铁锅出了窟窿就得锢漏。马锢漏有一只小火炉,一般的时候,火炉里都有余火,用时,放上几块新的焦炭,取铁筒往风匣上一连,几下子就能把火吹旺。没有余火也没关系,打发一个孩子到谁家的灶膛里夹两块火炭儿来,埋在焦炭里,一吹就着。火烧旺了,冒出了蓝莹莹的火苗,马锢漏就从挑子的抽匣里拿出一只坩埚,里面放一小块铁,埋在焦炭里烧。坩埚很小,比过去喝酒的酒盅子大一些。化铁的间歇里,马锢漏用小铲把窟窿眼儿周围的灰垢清理干净,露出新茬儿。铁化好了,马锢漏扣过铁锅,左手抓一把谷糠,从铁锅里面堵住窟窿眼儿,右手持一把铁钳夹起坩埚,对准窟窿眼儿一倒,哧啦一声,冒起一股白烟,窟窿就被堵上了。然后,马锢漏拿小铲吱嘎吱嘎里里外外一顿铲。铲完后,用手一抹,不挡手,面是光的,于是把铁锅一推,拍打着两手,牛哄哄地说:“完活。”
铁锅、缸、碗、大瓷盆裂了璺,就得锔了。在璺的两铡打眼儿,钉一溜锔子。看似简单,实际上技术含量很高。锔完后能盛粥盛泔水腌酸菜,不漏汤,这还算不上高明。高明在锔子要小巧精致,要严丝合缝,打的是补丁,但让人看了觉得它不是补丁,是工艺品。这才是体现锢漏功力的地方。马锢漏功力不浅,也舍得下料。他曾经锔过一只猫食碗,用的是铜锔,金灿灿的。金灿灿的也没啥了不起,了不起的是锔前是猫食碗,锔后就不是猫食碗了,成了小孩的饭碗了;不但成了小孩的饭碗了,两个孩子还为争这只猫食碗打个吱哇乱叫。没办法,孩子他妈拿一只好碗追出二里地撵上马锢漏,夺过马锢漏的小铁锤,一敲,就把一只好碗敲成了破碗,说:“锔上吧。”一只碗,锔之前猫用,锔之后人用;锔之前没人争,锔之后有人争,可见这只碗就已经不是一般的碗了,而是一个好看的艺术品了。
马锢漏有两女一儿。儿子叫马小顺,四十五岁那年得的。马锢漏不想在自己手上封了锢漏挑子,打定主意还要往下传,要收儿子马小顺为徒。马锢漏说:“老祖宗传下来的,咱不能说扔就给扔喽。老人古语,家中再有,不如一技在手,你爷那话儿说得一点不差,富不了,也饿不着人。再说了,当锢漏也不低耷,也有人敬,就说你爹我吧,走到哪儿,都拿咱当人物敬着,老少爷们成百成千,偏偏拿咱当个人物,为啥?还不是因为你爹有这门好手艺,嘁,管说中?不传你传谁?还有传外人的道理?那不是糊涂了吗。”
可马小顺不买马锢漏的账,至死不学锢漏锅子。后来,马小顺考上了省城里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当了老师。马锢漏七十八岁那年,马小顺从省城回到老家,要接马锢漏去城里享福。马锢漏不乐意去,说到城里住楼房住不惯,啥啥都不方便。
马小顺坚持要爹去,说:“爹你年岁大了,一个人在乡下让人不放心。”
马锢漏说:“有你姐管我呢。”
又说:“去也中,那东西我得带着,能行?”
马小顺问:“是啥?”
马锢漏说:“锢漏挑子。你爷爷留给我的,原打算再传给你,你说啥不干,这东西跟了我一辈子了,就跟我的魂儿似的,走到哪都不能丢。”
马小顺没吱声。
马锢漏说:“你同意我也不同意,好几千里地呢,带个锢漏挑子算咋回事。再说,你媳妇也不能干,你当不了你媳妇家。再说,鼓捣去了还得鼓捣回来,是小事?”
马小顺说:“干啥还鼓捣回来啊?”
马锢漏瞅瞅马小顺:“算了,你不懂,说了你也不明白。”
马锢漏这个时候已经不出去做锢漏活了,一是年岁大了,二是人家有个破盆破碗的都随手扔掉直接换新的了,没人再拿去锔了。马锢漏把锢漏挑子放在西屋,一天擦一遍,擦得溜光锃亮,一尘不染。小火炉、砧子、金刚钻、小坩埚、铁丝、铆钉、锔子、小锤子、小剪子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有一回,侍候他的女儿拾掇屋,想把小火炉里的灰倒掉,马锢漏发现了,像被谁挖了祖坟似的呼天抢地劈头盖脸一顿好骂。打那以后,除了马锢漏,没人敢再沾那副锢漏挑子的边儿。
马锢漏八十二岁那年腊月初三,天气好,没风,马锢漏让女儿帮着把锢漏挑子又鼓捣出来了,在村中间老场院的墙根下又摆了一回摊。马锢漏不吆喝了,吆喝不动了,只把那面小铜锣敲得脆脆的响,还能听出当年的那一股子精神头来。过来过去的人像看稀罕一样地看了一回,走了。没走的,跟马锢漏闲打唠:
人说:“老爷子,缺钱儿花?”
马锢漏:“不缺钱儿。”
人说:“不缺钱儿,还出来摆摊?”
马锢漏不吱声,过一会儿,说:“有破盆破碗没?拿来锔。”
人说:“有是有,都甩河套沟子去了,没人锔了,你老歇着吧,锔了一辈子了,还没锔够?”
只有擀毡子的毡匠老霍明白马锢漏的心思。毡匠老霍回家敲瓣了一只小花碗,拿给马锢漏,说:“好好的碗,说打就给打咧,丢了白瞎了,快给锔上。”
马锢漏看了看,说:“两毛钱,锔不锔?不锔拉倒。”
毡匠老霍说:“锔。”
一只碗,锔了两个时辰。不是马锢漏老了,手脚不利索了,而是加了细。不但用了铜锔,还拧出了漂亮的花纹。
毡匠老霍说:“老爷子,这么多年不干了,手艺没忘,还这么好?”
马锢漏抿着嘴乐了,说:“那还忘了喽,忘不了。”
毡匠老霍说:“还两毛?二十年前是两毛,现在还两毛?两毛钱还买不来一个铜锔子呢。”
毡匠老霍掏出一张五十的,说:“别找了,剩下的给你打一瓶酒喝。”
马锢漏摇着手说:“就两毛,你别压我价,我也不能冲你多要。”
毡匠老霍又掏出一块钱钢镴儿给马锢漏。马锢漏找给他八毛。
第二年开春,马锢漏的身体说不好就不好了。
马锢漏是阴历二月死的。马锢漏临闭眼前跟儿女交代说:“别的啥也不用,把锢漏挑子给我带着。”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