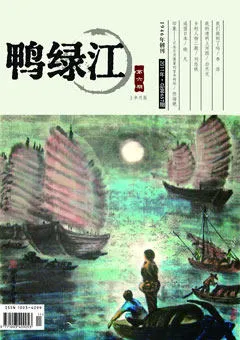一座村庄的几个片段
2011-01-01田鑫
鸭绿江 2011年6期
田鑫,80后,宁夏作协会员,先后在《散文》《青年文学》等多家刊物发表散文作品,有作品被《散文2010精选集》《2010年度散文诗选》等选本收录。
远去的尘土
是的。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尘土了。我要是想尘土了,就回到村庄里去。
这事还得从我刚来这座城市的一些片段说起。
我刚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看见过好几只狗,它们走起路来,头高高地扬着,没有一点看路的意思,似乎在它们眼里,道路是不值一提的。
于是,我开始好奇起这座城市的狗以及它们走路的姿势。我发现,这里的狗,走路的时候从来不低下头去嗅大地。在没有见到它们之前,我固执地以为,城市里的狗,肯定被城市惯坏了,饭来张口的狗已经完全没有了骨气,它们走起路来一定是低头哈腰像个“狗腿子”。可是让我纳闷的是,它们走路的时候,从来不低着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后来在沥青路上跌了一跤,嘴里啃了些尘土之后,我才发现,问题出在这座城市最低处的尘土身上。原来,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所能见到的尘土,大多已经带上了沥青的妩媚,带上了汽油的气味,带上了车轮的圆滑,它们身上的味道,是这座城市所有味道的混合。
难怪这些狗走路的时候不愿意低着头,它们是在与这座城市最低处的尘土保持距离。
城市里的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了,而在我的村庄里,土仍然是土,是小到尘埃大到山峦的土。在村庄里,土的世界也分三六九等:一等土种庄稼,给人以温饱,并养育村庄里所有的生灵;二等土,和稀泥、打院墙、修房子,给人以温暖,并让村庄变得具体;三等土,既种不出庄稼又和不了稀泥,那就只能被当做路了,有了路,人与人之间,房屋与房屋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就被联系起来了。人与人、房屋与房屋,村庄与村庄就不觉得寂寞了。
我一直很喜欢土生土长这个词,觉得它简约、质朴,用四个字就恰当地总结了一个人与某一个具体的地方的关系。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动用这个成语来总结自己与某一个具体地方的关系,要使用这个词,是需要一个特定背景的。
这个特定背景就是村庄。只有在村庄里,一个人才可以说土生土长,因他的出生,是从一拱土炕开始的。当生命以最初的形式完成了在子宫里的旅行之后,随着“哇”的一声,他(她)与这世界见面了。迎接他(她)的,除了父母和亲戚们洋溢着喜悦的笑脸之外,就是土炕和土炕上细小的尘土了。我把村庄里的出生称之为“土生”。这个人生下来之后,吃着土里长出来的粮食,住在土垒起来的房屋里,走在土铺成的大小道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这一辈子,无论活得好与坏、高兴与伤悲,他(她)的生活轨迹都注定离不开土。为了和“土生”对应,我把这注定离不开土的生活叫做“土长”。
哭过、笑过,爱过、恨过,幸福过、悲伤过之后,当他(她)完成了所有生来注定的劫数,闭上眼离开这人世的时候,收留他(她)的,最后也是土。亲人的泪水和悲伤,只能安放一个曾经活过的人的回忆,而土,却能给他们一个不大不小的窝,不管这个人生前是好是坏,在村庄的某个地方,土总会给那个人另一种生活。
这样“土生土长”的生活,就这样在村庄里流转着。是村庄,让“土生土长”这个成语生动起来。但是,当强大的“工业文明”来临之后,一切都变了。
我是随着大流到城里来的。有一次,我正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十字路口踟蹰时,遇到了那些从村庄吹来的尘土。它们在来来往往的车轮和人流中,时而被带起来,时而被踩下去……站在十字路口,看着那些尘土们,我想起了一个词:风尘仆仆。
这个词,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说,“土生土长”恰当地总结了一个人与某一个具体的地方的关系,那么,“风尘仆仆”则简约地概括了一个从村庄里走出来的人的生活状态。
风尘,就是行旅,是辛苦的意思;而“仆仆”就是行路劳累的样子。在城市里,我们多像尘土啊,在有限的空间里苟延残喘着,跋涉着,时不时还要注意着,不要沾染这城市混杂的气味。
其实,你不知道,看着那些尘土,我真想一下子扑到它们怀里。
象征意义的鸡
我之所以写到一只鸡,是因为,从我离开村庄的那一年开始,鸡就用自己的身体,传递和维系着,我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说吧,如果你每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在饭桌上总有一盘香喷喷的鸡肉,当你再次离开村庄的时候,包裹里总有几个热腾腾的鸡蛋,你就会理解我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了。
就是这一盘盘鸡肉和一个个鸡蛋,让我有了给鸡写点文字的想法。
1
鸡崽,是春天我离开的时候,奶奶从鸡贩子那里换来的。半袋子秕麦子,就能换十几个毛茸茸的鸡崽。用爷爷的话说,半袋麦子换十几只鸡,看起来是奶奶赚了,但是细算下来,这些鸡一年得吃掉多少麦子?
不过,奶奶从来不这样算账,因为到了年底,在她的算盘里,这些鸡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2
从我离开的那天起,奶奶就将本应该给我的关爱,相应地分配给每一只鸡崽。于是,它们的吃喝拉撒,就是我的吃喝拉撒。鸡崽们饿了,不等自己叫唤,奶奶就会抱着自己精心配制好的土饲料去喂它们。鸡崽们出门时间久了,奶奶就会踮起她的三寸金莲,倚在院门口,咕咕地召唤。
在这群鸡面前,奶奶的细心和关切,一点也不亚于我小时候对我的照顾。不信你看,当鸡崽们三五成群地回来之后,奶奶就会一遍一遍地清点鸡数,边清点边像奚落我一样,有一句没一句地批评着。这个时候,奶奶看上去很生气,其实她的内心里,全是鸡崽安全回来的欣喜。
一次,有一只鸡病了,奶奶便坐立不安,想着我在外面是不是也病了,于是,一边操心照顾鸡崽,一边让父亲给我打电话确认我是不是一切都好。当父亲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在睡午觉,他问我,你可好?我回答得慢了点,奶奶就着急了,拿过电话,说你没生病吧?
他们娘俩的电话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
3
鸡就这样在村庄里生活着,它们代替着我,在奶奶的眼皮子底下晃悠着。要是有鸡下了第一个蛋或者哪一只鸡突然长肥肉了,奶奶就会高兴好一阵,若是某一只鸡失踪了或者生病了,她就会好几天没精神。
其实,我知道,在奶奶眼里,这群鸡就是她的一群被放出村庄的孙子。而这几只鸡到该吃肉的时候,我们也就一个一个从外面回来了。
4
鸡是我回家之后的那个晚上被奶奶从鸡圈里抱出来的。在被抱出来之前,它已经被绑住双爪单独关了好几天。从我打电话告诉家人我即将回家的那天开始,这只鸡自由自在的生活就结束了,它的厄运也到了。
知道我要回来,奶奶就把最肥最大的一只鸡单独关起来,给它吃平时它们吃不到的食料,让它在短时间内再肥再大点。奶奶说这样的鸡能比鸡圈里的其他鸡多出好多肉。
具体能多出多少肉,我是从来不会注意的,不过我知道,被奶奶单独关起来的鸡,这些年,光我一个人,就吃了不下十只。
5
那只被单独关起来的鸡,从它吃到第一口独食的那一天起,它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于是,它便毫无怨言地在小小的范围内生活,奶奶送吃的东西来,它只顾低头啄食,从不去注意其他鸡羡慕的眼神,也没有了以往的神气。
奶奶把它从鸡圈里抱出来,解开系在它双腿上的绳子,从鸡屁股上揪下一撮羽毛,之后,把鸡交给爷爷。
那些羽毛,将会成为留守在村庄里的孩子们手里的毽子。而将鸡交给爷爷,是因为奶奶不忍心亲手将自己养了一年的鸡杀死。
于是,杀鸡的差事就交给了爷爷。爷爷拿出平时刮胡子用的刀片,用最短的时间,让鸡停止了呼吸。
过程是这样的:爷爷先在鸡的头顶摸了摸,确认血管之后,将鸡的整个头和脖颈部分折叠一下,蹭一下子,刀片划过鸡头的某个位置,就看见血流下来了。
我拿着一只碗,将鸡血收集起来,这些血,性味咸平,补虚活血,一般庄户人都舍不得丢。
在收集鸡血的过程中,我看见鸡,被刀片划开之后,甚至连呻吟的机会也没有,两只爪子在空中徒劳地蹬了几次之后,便安静地躺在了事先准备好的热水盆里。
接下来,它成了我们餐桌上的美食。
6
其实,鸡除了传递着我们一家人的情感,还传递着我们一家和土地神的感情。
在我所生活的村庄,人们只要一遇到大事,就会去村庄西头的土地庙里。不管好事坏事,一进庙门,先烧香磕头,然后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土地庙里的“诸神”,最后以一句“祈求您老人家帮忙让事情顺利,我将以一只低头凤凰(村庄里对鸡的一种美好比喻)还愿”结束。
在随后的日子,不管给“诸神”汇报的事情成与不成,到了年底,曾在土地庙里祈过愿的人们,都会抓一只鸡,到土地庙里还愿。
这只鸡,一般是鸡群里最肥最大的。
7
我亲眼见过爷爷在土地庙里向“诸神”还愿的场景,具体是还什么愿我记不清了,只是那只鸡在“诸神”面前的镇定,牢牢地烙在了我的脑海。
那一次,爷爷从鸡圈里挑出鸡群中最肥最大的那只鸡之后,扫去鸡身上的泥污和粪土,装进一个干净的蛇皮袋子。袋子事先戳几个洞,鸡可以伸出头来喘气。
爷爷让我提了装着鸡的袋子,他装上烧纸用的香火,我们避开人群,去了土地庙。
进土地庙之前,鸡被我们从蛇皮袋子里拿了出来。刚拿出来的时候,鸡因为在袋子里闷得慌,便扇着翅膀乱叫起来,可是一进庙门,它便安静了下来。
爷爷将鸡放在土地庙里的供桌上。不知道是爪子落地的原因,还是鸡看到土地庙的“诸神”神像的缘故,它的双爪缓慢地分开,像个孩子一样,蹲坐在供桌上。
爷爷一边扶着鸡,一边说着一些类似于感谢的话。鸡似乎听得懂,又似乎听不懂,只是安静地蹲坐着,等爷爷将说给神灵的话说完。
烧了纸钱和香火,这只鸡的生命便永远地属于了神灵。
爷爷把鸡抱出庙门,在庙门口的一棵松树下,用之前熟练的方法,终止了这只具有祭祀意义的鸡的呼吸,然后将鸡血留在松树下的土里。
当然,这只给神灵还愿的鸡,后来也成了我的腹中之物。
8
转眼又是春天了,到了离开村庄的时候。
临走之前,奶奶把年前就准备好的秕麦子装进袋子,在鸡贩子那里换回了十只小鸡,说是等我们这些作孙子的回来的时候,这些鸡就长大了。
我看看这些鸡崽,再看看奶奶,眼泪簌簌地就下来了。
奶奶,我不知道,等有一天,您老到无法照顾一群鸡的时候,谁还会从春天开始,为我圈养一窝鸡,把它们当作我一样养着,等我从远方回来。
煤油灯霸占村庄
据说我们村的最后一盏煤油灯,是二懒他们家的。他们家通上电的时候,村子里已经用了好几年电。二懒是两个人的合称,他们是夫妻,男人叫老二,女人叫平子,在村里懒出了名。具体怎么个懒法,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不过村子里有个关于他们的笑话,足以概括和证明他们的懒。说是二懒结婚那晚上,村子里好事的小年轻去听房,几个人伏在墙根听了半晚上,洞房里愣是没动静。后半夜的时候,新娘说了句话,听房的人听得很清楚,是“你去吹灯吧”,很明显,这是一句暗示的话,听房的人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很精彩,可是这话说完很久,洞房里愣是没变化。于是几个人便悻悻地回各自家里了。第二天,有人问老二为什么不吹灯,老二说那天累得人快散架了,到睡觉的点儿头一落枕头就睡着了,没顾上那事。于是,人们便开始说老二懒得连“那事”都顾不上。开始说的时候,老二还辩解几句,说的人多了也就习惯了。
这个笑话出现的年月里,村子里的人家晚上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盏,当时我尚小,不懂得这个故事中暗含的用意。长大后,发现和二懒家一起结婚的几家人,孩子比起二懒家的孩子能大出四五岁的样子。后来,我向村子里的人打听这事,人们告诉我,他们两口子好几年晚上都懒得吹灯睡觉,更不用说干“那事”了,所以他们结婚五年后才有的孩子。
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似乎有些懂,又似乎什么也没听懂,不过我知道了,在新婚之夜,二懒他们两口子懒得吹煤油灯。
之所以说起这个故事,是为了引出煤油灯。这煤油灯,就是二懒新婚之夜没有顾上吹的那盏。那盏灯,一直在村子里亮着,一亮就是好多年。
在没有电灯的年月里,煤油灯就这么霸占着村庄里所有的夜晚。
一小撮棉花,一个废旧的牙膏皮,一个小玻璃药瓶子,用农民朴拙的创意连起来,就是一个夜晚所有的光明。这光明,有时候豆丁般大小,母亲凑近它做针线的时候,墙上却能映出一个巨大的背影;有时候一座屋子大小,一家人围坐在它的周围,有一句没一句的对话,把一个沉默的夜晚填充得满满的。
细细想想,当那根细细的灯芯,从牙膏皮做成的灯引子里穿出来的时候,它独特的造型已经注定了它要执掌这个村庄的所有夜晚。因为从来没有一盏灯,能像煤油灯一样简约、朴素,还给我的童年带来那么多的美好和诗意。
村庄里的夜没有诗歌里说的那么突然,也没有散文里描写的那么恬淡,村庄里的夜晚和其他地方的夜晚一样,一到时间就来临了。当夜晚带来的黑把整个村子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那一盏盏煤油灯就渐次亮起来了,先是从村庄东边开始,接着是村庄中央,然后是村庄西边,那些灯盏亮起来的地方就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要是站在村庄的最高处往下看,就会明白村庄之所以叫村庄的缘故了,白日里看不见的东西晚上在灯的作用下一一出现了。
最后一盏煤油灯被吹灭的时候,一村子的人就都睡下了。于是村庄陷入巨大的惯常的黑暗之中。这个时候,要是有夜鸟要飞过村庄,它们就只能凭借着白日里飞翔的记忆;要是有陌生人要经过村庄,他们就只能靠着时而被云遮住时而被风吹斜的月光。只有狗才可以大摇大摆地在村庄的暗夜里行走自如,因为这是它们的世界,白天人们霸道地呵斥它们,到了夜里,人都睡了,梦里喊几句是影响不了狗的,所以村庄的暗夜是狗的暗夜。
偶尔,那灯盏,也会在半夜里亮起来。有起夜的老人摸索着找夜壶,磕碰了屋子里的物什,老伴便会一边咕哝着一边划一根火柴,点亮头顶某处的煤油灯。也有睡不着觉的,一会把灯点着,一会又吹灭,一会再点着,一会再吹灭,这时候,睡在身边的人或者一个院子里的其他人就会看不下去,暗夜里传出几声怨言,大抵是败家子浪费火柴、浪费煤油云云。
这些灯就这么亮着,有意义无意义地霸占了村庄好几十年的夜晚。终于有那么一天,它们把自己烧灭了……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