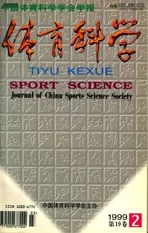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探微
2010-12-29王润斌熊晓正
王润斌,熊晓正,杨 麟
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探微
王润斌1,熊晓正2,杨 麟3
脱胎于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娱乐方式的延展,球类文化在以竞技哲学为核心的古代西方体育文化图景的边缘艰难地演进。简陋的用具设施、松散的组织形式与朴素的思想内涵形成了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结构性特质。强健身心、娱乐休闲、社会教化与军事训练表征了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功能性属性。集体行为与个人主义的悖离、休闲诉求与竞争精神的偏差、欺骗谋略与公平伦理的相左是球类文化难以融入古代西方主流体育文化的深层原因。
古代;西方;球类运动;文化
引言
以宙斯众神为宗教信仰序列,以竞争精神为哲学基础,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伦理导范,以竞技赛会为组织保障,古希腊竞技文化开启并铸就了古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时代丰碑。阿尔菲斯河谷旁的竞技场上,希腊人赤裸着身体奔跑着,奋力将标枪掷向天空,四轮战车掀起的尘土弥漫着整个天空,艳阳下大汗淋漓的观众翘首期盼着惟一的胜利英雄的诞生。雅典郊外的阿卡德穆学园里,里拉琴声悠扬,柏拉图正指挥着共和国未来的士兵们进行摔跤训练。这样的画面并非古代西方体育文化的全部,却占据着古代西方体育文化图景的中心。以田径、重竞技、赛车为核心体系的项目群落在四大冠冕赛会延续千年,哲学家普鲁塔克甚至认为,只有场地跑才是奥运会的嫡系项目[9]。这种缺少了球类运动的综合性竞技赛会和体育教育手段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毕竟“自近一个世纪以来,用球类运动或近似于球类的器材来进行比赛的团体运动比以往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6]。与球类文化的历史实践命运相比,记载描写球类文化的符号表征同样匮乏且凌乱,除了盖伦、马提雅尔等笔下的断纸残篇和希腊花瓶、大理石雕塑上的偶露峥嵘,球类文化仿佛被古代西方体育文艺表征所失落和遗忘。
竞技文化位居中心与球类文化自身边缘化的对比、古代社会中弱势文化地位与现代社会中强势体育文化地位的差异、古代体育文化实践与表征的双重缺失等学理性的议题,促使本研究试图在如下论域取得突破:发掘古典作家与现代学者对球类运动的思想艺术表征,深描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演进的真实轨迹;探寻古代西方球类运动自身的结构体系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球类文化的多元功能;最后,批判性地认识球类文化的自身阈限及其在古代西方体育文化中的弱势边缘地位。
1 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流变
在原始社会,狩猎工具形式的延展和部落儿童娱乐的需要为球类运动的萌芽提供了最初的社会文化养分。公元前4000年前后,西亚北非出现了人类的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及成为古代体育文明的发祥地,人类早期较为模糊的球类文化图景也得以闪现。
在古埃及,宗教和军事性的体育活动占据主流位置,但法老等上层贵族的休闲体育活动也开展的丰富多彩。其中,“古埃及的球类活动影响较大,除了妇女的球戏外,还有一种男子的马上球戏,骑者在马上抛接好几个球,对骑术和技巧要求极高”[1]。除了文字记载外,公元前2000年埃及法老本尼·哈桑墓的壁画中,就出现了用球杂耍的场景(图1)。图中,同时抛接多球的举动与当今杂技表演者的手法不无二致,骑在背上的两名球手也在进行相互抛接球的表演,这样的行为更像是在宫廷贵族面前的娱乐表演而不是体育活动。根据古埃及的风俗和画中球手的装束,可以推断这些球戏的主角多为女性,且为奴隶身份或者职业艺人身份。作为体育实践的参与者,古埃及的法老们更喜欢去非洲草原猎狮或者留在宫廷中下棋。纯粹的观赏球戏,仅仅是社交场合中的消遣、是家庭聚会中的欢娱。

图1 古埃及球戏图
漫长的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时代,斗牛和战车赛成为体育活动的主角,球类活动的踪迹难寻。荷马时代,球类运动穿越千年的历史时空,从法老的宽阔庭院走向城邦贵族的休闲生活。《奥德赛》首次记载了球戏的场面:菲阿西亚国王阿尔基诺奥斯的女儿瑙希卡和侍女们在海边洗衣服,当她们等待衣服晒干时,就开始摘掉头巾玩球,瑙希卡带领她们边玩边唱。当衣服晒干准备拉回王宫时,瑙希卡将球投向一个侍女,结果却没有投中,落入了海滩边的一个大深坑,她们开始尖叫起来。根据上下文叙事,荷马描述的尖叫仅仅是想唤醒在周围沉睡的奥德赛,并没有对这项球戏进行太多的介绍,然而,却被认为是记载古希腊球类文化的始作俑者。除了瑙希卡,历史学家阿森纳乌斯还列举了古希腊其他知名的球手:“迪奥克利迪斯的哥哥德墨忒里斯,哲学家奇安和克瑞丰等。来自乔希斯的哲学家忒修斯擅长玩球,安提戈诺斯国王的朋友们都喜欢脱光了衣服和他一起玩球。斯巴达的提莫克莱特斯还写了一本关于球戏的书”[17]。然而,在竞技文化的光环笼罩下,古希腊的球类文化数百年来只能残存在荷马史诗和少数希腊哲人的只言片语中,无法成为体操馆中的主角,更不要奢谈有朝一日登上奥运会的舞台。
亚历山大大帝开启了马其顿帝国的序幕,也宣告了希腊化时期的来临。亚历山大在年轻的时候是个跑步高手,由于其他参加者都主动让他赢得比赛,他于是放弃了田径项目,改而参加球类运动。他招募了一名来自凯修斯的职业球手阿瑞斯托尼休斯,阿森纳乌斯还曾反对授予他公民资格,然而,有碑文记载,这种荣誉的授予的确发生过。亚历山大大帝是个喜爱被阿谀奉迎的人,而谄媚之徒的最高境界就是模仿皇帝的一举一动,因此,球类运动因亚历山大大帝的喜爱在马其顿广为流传。同时期的希腊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球场(Sphairisterion)一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专门为球戏而修建的场地。
当热衷娱乐和休闲的罗马人登上历史的舞台,球类文化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在罗马时期,球场进一步正式和完善。罗马的球场大多隶属于大型的公共浴场,一些有钱的罗马人也拥有私人的球场。罗马学者小普林尼曾经在信中提到自己在乡村的两处房子都带有球场。在他劳伦狄安别墅旁的球场紧挨海滩,面朝夕阳;在他图斯坎的房子旁,球场紧挨浴室的更衣室而建,规模很大,可以同时容纳好几群人玩球,每种球戏都还有一圈人在围观。罗马时期,贵族们对球戏的热爱和追捧达到了高潮,在西塞罗皇帝62岁的时候,他依旧参加在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举行的球类活动,“这看起来是罗马政治家和律师们习以为常的消遣方式,就像现代社会的高尔夫、网球和壁球一样”[21]。随着受欢迎程度的增加,球类游戏的种类也逐渐齐全和丰富,讽刺诗人马提雅尔将一件斗篷和一首短诗送给一位朋友,诗中写到:“当你热衷于玩令人微微出汗的特拉贡(Trigon),玩灰尘弥漫的哈尔帕斯顿(Harpastum),或者传递用皮毛包裹的佛里斯(Follis)时,这件斗篷将派上用场”[27]。随着球类游戏花样的翻新,罗马思想家对球类文化的认识也达到新的高度,除了马提雅尔对球种类和玩法的详细论述外,生活在公元2世纪左右的名医盖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小球锻炼》,详细阐释了球类游戏的锻炼原则、锻炼方法和锻炼价值,他提出的均衡锻炼效果理论还首次科学地揭示了球类运动的本质和特征。
西罗马后的拜占庭时代,受波斯帝国的影响,球类运动与西亚北欧游牧民族的骑马传统较好地结合起来。公元12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斯纳莫斯在描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打马球时如何跌落马下被马拖行的场景时,顺便提到了马球比赛:年轻人被分为人数相等的两支队伍,他们选择一块开阔和平整的地方作为球场。球用皮革制成,有苹果般大小。当球开始在球场中央滚动时,双方全速冲向它,每队都试图将球打进赛前标志好的对方的球门。比赛充满着危险和事故,因为运动员要始终屈身骑在马鞍中,并扭转身体,急速转向,调整步幅和步伐,以赶上球的运行[21]。这里描述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球杆的出现,拜占庭人在希腊人曾经从事的球类运动中,开创了使用球杆的漫长历史。马球的东传成为体育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桩疑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黑暗的中世纪宣告了高扬肉体旗帜的竞技文化与身体教育的低落,球类文化随之湮灭。
2 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结构
2.1 球、球场的形制
球类文化的最显性层面即为运动的载体和对象——以球为核心的器物层。有学者指出:“球具有不稳定的结构,稍一碰动,就会发生位移。球又是一种非常容易稳定下来的物体,可以在任何位置上变动态为静态,变静态为动态。所以,它是最听从指挥的,把它作为游戏的器具,可谓得天独厚”[4]。球可以使用各种材质,被做成各种规格,但在古代,一般只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像今天的棒球、曲棍球和网球一样的小球,第二类像今天足球那样的大球。马提雅尔根据罗马球类游戏的种类提到了5种球的拉丁名字:皮拉(Pila)、佛里斯(Follis)、帕噶尼卡(Paganica)、特拉贡尼斯(Trigonalis)、哈尔帕斯顿(Harpastum)。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增加了福力库勒斯(Folliculus),伊西多罗斯增加了阿瑞纳塔(Arenata),罗马人还用希腊单词斯费瑞拉(Sphaera)来形容一个球。
盖伦曾经提到过孩子们将猪膀胱或牛膀胱膨胀制成球的过程:“孩子们选用猪膀胱,使之充进气,在火旁用灰烬揉搓,使之温暖,但不能弄破它们。这种游戏常见于艾奥尼亚和周边其他民族中。他们一边揉搓,一边唱着合辙押韵的歌词,这些都是希望膀胱变大的歌词。当它看上去涨的足够大时,他们就再吹气,让它膨胀的更大,然后又揉搓它;他们就这样反复做几次,直到膀胱看上去足够膨胀为止”[15]。动物膀胱做的球太轻、易破,古希腊罗马人为了防止刺破,就在外表包裹上皮革,大小球都如此,而且,还有填充毛发的例子。拜占庭时代的《宫廷诗集》(Anthologia Palatina)借哲人柏拉图之口提到了一个极富韵律感的谜语:我浑身长满毛发,但皮条却包裹了它,防止出现破洞了。柏拉图还透露制做球对孩子们特别有吸引力,而且球的表面往往五颜六色。公元7世纪的拉丁教父伊西多罗斯在他的《辞源》(Tymologiae)援引一位无名的拉丁诗人曾经创作的两行诗,诗歌提到了如何做球的方法:做球时要将急速奔跑的牡鹿的毛发填塞进去,直到重量达到两磅零一盎司。这些球显然是一种大而轻的球。马提雅尔在诗歌中提到了不同球的材质和特点:“这个帕噶尼卡(Paganica)塞满了硬硬的皮毛,比佛里斯(Follis)要坚硬一些,但却比皮拉(Pila)柔软一些”,他还用拟人的手法描写了一种叫做特拉贡尼斯(Trigonalis)的球:“如果你知道如何用敏捷的左手击打我,我将属于你。如果你不能?那不好意思,请放弃比赛吧!”[16]学者王以欣根据哈尔帕斯顿(Harpastum)来自于动词抢夺的词源性和古典学者的描述,认为它是一种用马鬃填充皮革的小球,而且比较硬[8]。
此外,古代西方球场的出现也对深入理解球类文化至关重要。古代的球场往往比较简陋,甚至没有固定的场所,比如瑙希卡在海滩、西塞罗在广场、亚历山大在庭院玩球,球类游戏玩法的简单和自由决定了球场单独呈现的困难。当然,出于城邦国家的公共教育目的以及私人贵族身份等级制的炫耀,球场还是出现在希腊化时期的历史舞台,公元前3~2世纪,在德罗斯和德尔菲发现的碑文证明了球场往往附属在一个体育馆周围,其中,德尔菲的一块碑文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它记载了挖掘、平整球场的成本,而且,记载了球场中还修建了一堵矮墙,另一块碑文比较了用黑色泥土和从体育场借白色沙子做球场表面的成本差异。这样的球场显然不是用石头砌成,而是直接建造在平整的泥土地上。罗马时期,球场进一步正规和宏大,在西西里岛肯特利帕城的一对父子为了纪念他们成为城市的联合执政官,就向城市捐赠了公共的球场,考虑到地中海的气候,这样的球场应该是露天而建的。马提雅尔还在一首诗歌里提到一座附属于公共浴室的球场,人们总是在正式洗浴之前玩一场球赛,然后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诗人斯塔休斯还提到罗马的一个球场有地下供暖设备,以便人们在冬天玩球。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对罗马时期球场的大小、布局、设施了解甚微。
无论如何,球的特质和球场的出现对球类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古代西方人利用简单甚至寒酸的球和球场也能带来不少乐趣,但对发展玩球的高超技艺而言,球的圆整度和弹跳性、球场的规整与舒适都十分重要。遗憾的是,古代工匠并不能保证两者,这也许就是为何古代球类运动没有像今天的球类运动得到如此大发展的原因之一吧。
2.2 游戏、比赛方式
古希腊的球类运动只局限在家庭及社交圈子里面开展,游戏完全没有正式的规则和一贯的传统,荷马史诗中的瑙希卡及其侍女们玩球的形式显得如此松散和自由。经过历史的沉淀,古罗马时期的球类游戏比赛开始逐步正规,不同球戏中球的使用、人员的数量、游戏的规则慢慢清晰和明确起来。古罗马的修辞学家波吕克斯较为完整地梳理了古希腊罗马球类游戏的玩法和比赛规则,为后来人解读西方球类文化提供了依据。这些球戏包括俄皮斯库罗斯(Episkyros)、费尼达(Phaininda)、阿波瑞阿克斯(Aporrhaxis)、欧拉尼亚(Ourania)和俄费德瑞斯莫斯(Ephedrismos)[26]。
俄皮斯库罗斯(Episkyros)亦称青年人的比赛或团体赛,有人数相等、彼此相对的两个球队比赛,中间用碎石片标志出一道界线,成为斯库罗斯(Skuros),球置于线上。每队后方再划出一道底线。得球的球队向对面抛球,对面的运动员则试图抓住抛出的球,并反方向地将球抛回,直至把另一对逼至底线后面为止(图2)。这个游戏也被称为球战(Ball Battle)。虽然他没有提到球的大小和材料,但根据描述用于俄皮斯库罗斯的球应该是大而轻的球,双方的距离应该足够长。

图2 大理石塑像底座刻画的俄皮斯库罗斯图
费尼达(Phaininda)或得名于其发明者费尼斯提奥斯(Phainestios),或得名于球员用的投球假动作(Feinting),因为球手假装把球传给某人,实际上却投给另外一个人,因此欺骗了准备抢球的球手。希腊人玩的费尼达(Phaininda)到了罗马时代就变成了马提雅尔描述的哈尔帕斯顿(Harpaston)的小球比赛,后者同样得名于传球的方式:“一名选手站在两队运动员中间,试图拦截双方投掷的球。显然希腊球戏费尼达的策略——使用假动作——也会在此游戏中使用,一名球手假装往某方向传球,当中间的截击者向那个方向移动时,球手将球投给了另外方向的人。这种策略也被称作 Ephetinda或者 Phennis”[12]。
阿波瑞阿克斯(Aporrhaxis)是一种用力将球弹击地面,并抓住弹起的球然后迅速再弹击地面、再抓住的运动。以成功弹击和抓球的次数来决胜负。
欧拉尼亚(Ourania)。一名选手向后仰起身体,奋力将球掷向天空,其他人在球落地之前上前抢夺球。当他们持球投向一堵墙时,用来计算反弹的次数。失败者被称作驴子,不得不接受任何惩罚。胜利者被称为国王,下令惩罚失败者。
俄费德瑞斯莫斯(Ephedrismos)。在一定距离远处放置一块石头或木板作为目标,然后试图用球击中它。没有击中的运动员必须背起击中的运动员,失败者的眼睛被后者用双手蒙起,失败者继续用球投掷目标,直到成功击打到被称作Dioros的那块石头。图3和图4分别描绘了运动员游戏的场景。
除了上述游戏比赛形式外,古代西方的一些球类游戏或比赛至今无人能对其起源、形式和规则给出准确的阐释,现代人往往根据其表面的形制,充分发挥想象力,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现代某些球类运动的鼻祖。图5是一尊希腊大理石双柄长颈瓶上面的图画,藏于希腊国家博物馆,被证明属于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葬礼用品,图中年轻人的玩球方式和现代足球的颠球惊人的相似,希腊政府曾经在发行的邮票中自豪地将此图片展示的古代球戏和现代足球放在了一起。然而,众多的古典学家对其真实的形制出言谨慎,斯蒂芬·米勒只是推断球为皮革包裹的动物膀胱球,质地轻且弹性好,但认为在没有任何文字描述证据的前提下,断定其为足球言之尚早,哈里斯甚至认为它不过是运动员在竞技训练洗浴后的休闲娱乐活动,主要考量的是人的平衡性。图6为一尊大理石雕像底座上的画面,雕像藏于希腊国家博物馆,被考古学家鉴定为公元前6世纪末期的文物。显然,画面中的球戏同现代曲棍球的场景几乎毫无二致,然而从画面展示的图景看,这显然不是集体项目,而更像是一对一的抢球游戏,输者退出,旁边等待者再加入游戏。图7是一尊希腊细颈长瓶表面的图画,瓶藏于牛津阿什摩尔博物馆,所属时代为公元前6世纪初。老者(训练师)向三组骑背站立的年轻人做投球状,这同样被现代人认为是篮球的古代雏形,显然仍然缺少证据来进一步解释这项神秘的游戏。

图3、图4 瓷器描绘的俄费德瑞斯莫斯图

图5、图6 古代西方“类足球”游戏和“类曲棍球”游戏图

图7 古代西方“类篮球”游戏图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其与兰格合著的《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提出了“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2]的观点。他提醒我们在辨识古代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叙事之间的关系时,应当保留更多的谨慎和清醒,任何主观的臆测只会是缺乏根据的、一厢情愿的“传统发明”。显然这样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上述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游戏样式。
2.3 思想、文化内涵
球类运动,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实用的还是玩耍的,都能够被投掷,也能够被接住,能够在地面或墙面上持续弹起,能够在地面滚动,能够被球拍或身体的某些部分击打以击中目标,也能够被击打或投掷到一定距离,为其他选手的跑位得分赢得时间。球网、球洞、界线等障碍的加入使得球类运动变得更加富有挑战性和魅力。这些特性为理解球类运动的本质提供了外显的表征,而项目特性一定蕴含了球类运动的思想文化内涵,薛岚等研究者进一步将本质的稳定性、内容的延展性、形态的多样性、体验的直观性归结为球类运动的文化特性[10],古代西方球类运动同样呈现这样的文化特性与思想内涵。
无论球的大小、重量、弹性、材质,以球为中心展示人的体能与智能规定了古代西方球类运动的稳定性。从最早的瑙希卡抛球到罗马三人抢球,再到拜占庭贵族的马背球杆击球,古代西方球类运动始终在延展球类游戏的玩乐方式和竞赛方式上迈进,显然这是球戏的延展,也是人类认识球类运动规律的延展。古代西方球类运动的种类繁多,每种球类项目又都有自己的特点、规则和受众。诗人马提雅尔曾经在关于 Follis球的诗篇中,将球进行了拟人化:“离我远点,年轻人,我只适合年老者。一个Follis就是适合儿童和老年人玩的球”[28]。形态的多样性为球类运动搭建了多种文化形式展示的舞台,促进了古代球类运动文化向多元化方向迈进。球类游戏中,球手们通过身体动作表现出的跑、跳、投等人体所需基本技能和展示的球类运动特定的技术、策略,使得运动体验更为即时、生动与直接。公元前4世纪,阿森纳乌斯借德摩克利斯之名写到:“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年正在玩一种球赛。他来自科斯岛,一座似乎出产神明般少年的岛屿。每当他接球或抛球,他的目光触及我们观众时,我们都大声惊呼:太有节奏感了、太优美了、太得体了。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好像是美的奇迹,我从未耳闻目睹如此俊美的人物”[12]。难怪美国学者古姆布莱希特将球类游戏的这种审美形式称之为运动员身体与时空物组合形式的完美展现,为之大加颂扬。
当然,古代西方球类运动的深层思想文化内涵在展示球类游戏独特的样式和规定性的同时,也在同行为主体、社会设置、历史传统的博弈中发挥着源自自身体系的多元功能。
3 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功能
3.1 强健身心
“体育文化的结构和功能都统一于这个核心——人,通过体育锻造出来的身心健全的人”[11]。在身心健康的功能发挥方面,球类运动实现了自身结构体系与主体需求之间的基础性连接,也正因为此,古代西方的球类文化才得以脱胎于史前的蒙昧行为状态,进入体育文化的大系统中。古罗马最著名的医学家盖伦对球类运动的此项本质功能可谓推崇有加。他最初的职业是一名角斗士和医疗师,最后成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御用医生,通过他的作品《用小球锻炼》,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的体操训练师将教学技能进行改进后更加科学化的体育训练方法。
盖伦认为,古代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医生都曾讨论过体操训练和节食带来的良好效果,但是从没有人尝试详细地阐释小球锻炼带来的好处。他认为,小球对人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如果你去考虑和比较其他项目的话,你会发现小球是一项全身运动……当运动员们并排站好,双方相对,尽力不使站在中间的选手抢到球,这是一项相当剧烈的运动,需要人们经常保持仰脖和摔跤姿势,因此,头部和脖子通过仰起而得到锻炼,肩部、胸部和腰腹通过摔跤姿势得到锻炼。这种融合了向前、向后、侧面移动的跑动对腿部的锻炼量较大,也是惟一的促使腿部所有部位得到锻炼的方法,跟腱、肌肉在向前、向后和侧面的移动中都能受益……就像球戏对腿部有好处一样,它对人们的肩部的锻炼效果更佳,因为选手要采用各种姿势救球……如果你了解到选手如果不能正确地用眼睛观察球运行的轨迹,他就无法得到球时,你就会明白球戏对人们的眼睛也是一种锻炼”[24]。除了身体的锻炼,他还认为,运动员们也会通过实施策略来截获球,从而离开中间位置,这对人们的思维判断能力同样不无裨益,更重要的是,这项对人们身体和心灵均有促进作用的运动还会激发蕴含于运动员身上的卓越品质。
通过盖伦的描述,不难发现这里的小球游戏是希腊人爱玩的费尼达和罗马人擅长的哈尔帕斯顿,这类游戏速度快、节奏强、有对抗,适合青少年。一些更大更轻柔的球则对老年人的身体锻炼颇有益处,曾任罗马执政官的小普林尼在他描写罗马社会生活的书信集中提到:“我最近一次拜访了朋友斯普瑞纳,每天下午这位主人都会在阳光下散步之后长时间地玩一种活力无限的球类游戏,他将此当作保持老年人健康的锻炼方法。斯普瑞纳告诉大家,他已经78岁了”[14]。
3.2 娱乐休闲
“按照古希腊人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休闲是生活里的一种常态,与工作是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却可以看作是一致的,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5]。如果连奥林匹克赛会都是娱乐天神的游戏,罗马贵族们的战车赛、罗马平民的浴场生活何尝不是休闲的典范,流转于王公贵族庭院的球类游戏更为主人和看客们的欢愉时光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话题。
除了提及了瑙希卡公主的闲暇球戏,荷马史诗中还提到了另外的球类场景:在菲阿希亚国王阿尔基诺奥斯欢迎奥德赛的午宴结束后,他请全国最出色的舞蹈家哈利奥斯和拉奥达马斯表演。首先,他们拿起了一个紫色的圆球,这球是由心灵手巧的波吕博斯缝制的。二人之中,有一位将球高高抛起,并后仰下腰,另一位则跳了起来,双脚还未着地,已将紫球紧紧地抓在手中。抛接圆球的游戏结束以后,他们就在平坦的舞场上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他们步伐灵巧,迅速变换位置。在旁边观看的年轻人也跺着脚应和,热闹非常。显然,我们还无法从这段描述中找到任何与竞技有关的字眼,反而体味到了无穷的惬意和欢乐。
尽管罗马人对希腊式的竞技不感兴趣,但他们对希腊的球戏却十分热衷,尤其是有钱的罗马贵族,纷纷将球类运动当作休闲娱乐的一种选择。罗马诗人霍瑞斯在旅行日记中提到,当他拜访卡普阿城时,招待他的贵族米希纳斯晚宴后就去玩球了。公元前52年,政治家卡托在议院选举中遭到挫败,但他仍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去马尔斯学园参加球戏。公元1世纪,一个无名的拉丁诗人生动地描绘了罗马皇帝皮梭玩球时的场景:“当你抛回正急速运行的球时,当你救起几乎掉在地上的球时,当你用不可思议的技巧接住几乎超出控制范围的球时,你的敏捷身手令人叹服。观众们都目瞪口呆,连其他一些正在比赛的选手也都停下了比赛,大汗淋漓地站在旁边欣赏你玩球”[29]。显然,这样的球戏同样与胜负无关,更像是杂技演员的精湛表演,娱乐的意味远远大于竞技。
3.3 社会教化
体育、游戏通过身体技能的习得、习俗规范的传递、社会角色的扮演和价值观念的养成等系统性的文化展示与表达,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规训功能。球类运动的结构性特点巧妙地融合了团队配合与个人技艺、固体球体形制与丰富游戏方式等特色,在古代社会各阶层与群体的文化传承和教育过程中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
希腊青年人玩的费尼达、罗马青年人玩的哈尔帕斯顿和特拉贡等球戏都强调团队之间的竞争与配合,而上文提到的俄皮斯库罗斯则干脆被称为青年人的比赛(Ephebike)或团队赛(Epikoinos)。参加者都是处于向成年人过渡时期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往往都生活在希腊的军国民教育结构艾弗比军团中。球类游戏的集体性更为斯巴达人所崇尚,斯巴达城邦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球类比赛,古典学者肯乃尔指出,斯巴达的体育教育体系规定了青年人的年龄等级,当青少年达到20岁时,就视为成年人(Eiren或者Sphaireis,有球手之意),青少年除了日常的球类游戏比赛外,每年盛大的“球手锦标赛”就是实现青少年社会身份与行为规范、价值理念转变的“毕业典礼”或成年礼[22]。《古希腊诗文选》中有一首诗歌就提到了成年仪式上的情形:“一位年轻人从艾弗比军团毕业了,他向神灵赫尔墨斯献上自己的制服和配饰。他清点了自己的宽檐帽、刮擦器、断了弦的弓和斗篷,然后是曾经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球”[20]。
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中,奔驰的马车、血腥的角斗、激烈的球戏、豪华的浴场让生活在高层的统治者们显示了奢华、权势、统治力,这种社会场景的设置却有另外的含义,娱乐表演性的罗马体育成为了教化底层百姓的麻醉剂,盛大的场面、刺激的赌博、集体的球戏、逍遥的温泉浴让那些被统治者们产生同贵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一样的集体认同与归属,而文化的认同与情感的凝聚对于任何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都是最为深厚的基础。难怪奥古斯都从一个对战车赛毫无兴趣的皇帝转变成奢华竞技表演的庇护者和拥趸,而“大部分罗马人则将一天中最为美好的漫长的时光挥洒在浴场和运动场边”[19]。
除了球类运动自身蕴含的社会教化的实质性和仪式性功能,球类文化自身的结构体系及其社会功能也常为思想家加以提倡和比喻,间接地承担着知识传播和道德教化的使命。犬儒学派哲学家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说:“我将采用斯多葛派大师克吕西波斯对施与善行和球类运动的比较。只有当两者技艺相当时,球才能保持运转而不掉落。这同样适用于人们的施与善行。除非施与善行的人和接受善行的人品格相当,否则善行就有可能偏离原本的想法和效果”[13]。希腊诗人赫昔俄德有着相似的结论:“我们愿意给予那些本身就是给予者的人,但绝不会有人给予那些有去无回、知恩不报之徒。那些有着慷慨本性的人就像从别处得到球之后、不是控而不传或传给技艺不精者、而是将其传给能够继续传回者的球手”[18]。普鲁塔戈用球戏的比喻以坚持认为演讲的听众不应该过于消极和被动,他认为既然球员应该在学会投球的同时也学会接球,在球戏中,选手应该在接到来球后要富有节奏地将其传给对方,演讲中的演说者和听众之间也应该保持这种节奏。
3.4 军事训练
“体育运动保持着人类对决斗意识的原始记忆,是体育运动存留下决斗形式的物质产品,是体育运动赋予了决斗精神的文明诗意,是体育运动搭建起决斗竞技的展示舞台”[3]。盖伦认为,球类运动尤其是哈尔帕斯顿的游戏结构(保卫自己的球、抢夺掷出去的球)对培养士兵的决斗意识和战争意识尤为有效,而且这种效果是其他体育活动无法取代的:“人们比较容易地理解球戏训练中两种重要的策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适时出击和用心防守。没有一项运动如此适合于培养人们的舍得和放弃的胸怀,以及对对手行动的预判力。其他大部分锻炼方法简单、枯燥,即便是冠冕赛会上的摔跤比赛带来更多的是肥胖而非卓越,大部分摔跤选手体态臃肿、呼吸困难。这些人对率军冲锋陷阵的将军们和对帝国的统治者而言毫无价值”[17]。
的确,从希腊时期的费尼达的场面看,球类运动对人的体力、精力和策略、战术要求甚高,公元前4世纪的喜剧诗人安提丰曾经提到自己因为玩球而脖子很痛、身体很累,他还对费尼达进行了如下的描述:“他抓住了球,笑着传给一名球手,同时躲闪开另外一个球。他将一名选手撞出界线,一名新的选手增加进来,并站好位置。此时,场下观众尖叫并呼喊起来:‘出界了、传给他、传过顶球、低一点、远了、近了、聚拢些’!”[25]一些记载基督教早期斯巴达球类运动的碑文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斯巴达球类比赛的队伍以排(Obai)为单位,这是斯巴达年轻人进行军事训练时的基本单位。
哈尔帕斯顿在罗马也非常流行,这种球类游戏融激烈的对抗、疾迅的传球、机智的接球、巧妙的闪躲、敏捷的跳跃于一体,几乎容纳了所有军事技能的要素,除了罗马帝国的国民们通过此锻炼而获得健康的体魄,在凯撒的高卢军团甚至将之列为军训项目,普鲁塔克记载到马其顿国王安提戈纽斯(Antigonus)很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士兵一边穿着铠甲、戴着头盔,一边投球。盖伦甚至认为球类运动是所有将军和士兵们的必修课。
4 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批判
4.1 负面评价举凡
依据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某文化的结构要素及其关系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调整与适应既有正面的意义,也会有负面的作用。作为生成于古代社会中的亚文化现象,球类文化同样受限于自身结构体系的阈限,在与其他社会设置的互动中展现出冲突与失范的一面。
盖伦等对球类游戏均衡健身、身心俱完式的夸赞并不能否认某些球类游戏的危险。在公元6世纪编撰的《罗马法典》中出现了球场伤人的描述:几个青壮年在球场玩球,突然其中一个人想去接球,却和一名男孩奴隶撞了个满怀。这名奴隶跌倒在地、摔断了腿。问题出现了,这名奴隶的主人是否应该按照罗马的侵权法《阿奎利亚法(Lex Aquilia)》向对方提起索赔呢?法官最后的决定是他不应该,因为这是个意外事故而非故意犯罪。虽然是一场意外,但从费尼达、哈尔帕斯顿等青少年的球类游戏中不难发现,频繁的身体接触与夸大的动作幅度是其明显的特征,所以,历史学家阿森纳乌斯也在亲身参与球类运动之后感觉到它相当耗费精力、容易使人疲劳,而且,会严重扭伤脖子。
除了身体伤害的潜在危险外,球类游戏的社会影响也存在负面的成分。逍遥学派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狄奥弗拉斯塔斯认为,玩球是趋炎附势之徒巴结权贵的手段之一,当这些人一旦拥有一个带球场的体育馆,便迫不及待地邀请达官贵人们前来打球[17]。上文提到的阿森纳乌斯虽然对哈尔帕斯顿这样的球类游戏很感兴趣,但他对球戏的评价也不高。亚历山大大帝招募了职业球手阿瑞斯托尼休斯以后,曾给予他很高的待遇,球手所在的雅典城邦除了赋予他公民资格外,还奖励他一顶桂冠,允许他参加公民议事大会,并在雅典所有的戏剧表演或竞技赛会的第一排预留了座位。阿森纳乌斯却把雅典人的慷慨与器重视为“晚期的希腊人把粗俗的技艺凌驾于文化信仰的举动”[26]。
球场的世界是欢娱的世界,也是个鱼龙混杂的场所,特别是在罗马公共浴场外的球场,各色人等充斥着球场。马提雅尔曾经描述了球场上两个不受人欢迎的人物,一个是来自梅洛吉尼斯的阿谀奉承的食客,他时常用左手或右手紧握着热乎乎的特拉贡球,以至于经常能够放下手中的球,并把它记在主人的得分数上,即便是当他洗完澡、换完衣服后,他还能拾起地上的佛里斯球,掷还给主人。一个外乡人为了博得球友们的同情和掌声而混一顿饭吃,这样的球戏的确变了味道。另外一个人是在哈尔帕斯顿球场的变态青年:这个满场跳跃的男同性恋者从安塔尼乌斯灰尘漫天的球场上抓起球,想通过这种的方法来使脖子变得强壮,无异于徒劳。显然,马提雅尔眼中的球场不是一个充满和谐、欢乐的世界。
4.2 边缘地位解析
文化生态学认为,随着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文化多样性的增加,系统的波动性导致系统的变动,人类文化结构组成部分也会呈现不均衡的状态,从互动中可以分辨出各类文化的吸引力和拒斥力,当某类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其他文化对它的拒斥力时,强势主流文化与弱势边缘文化的界限与差异便显露无疑。球类文化在古代西方体育文化系统中明显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无论是在强调田径、重竞技项目的古希腊还是强调战车赛、角斗赛的古罗马,球类文化从未跻身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序列,球类运动从未进入古奥运赛场即为例证。因此,揭开奥运身份壁垒之谜底,对理解球类文化的边缘地位大有裨益。
从球类文化的本质特性来看,以球为中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古希腊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悖离。古希腊个人主义的观念根植于希腊社会的历史,高山谷地和散布的岛屿形成了地缘层面的彼此疏离,正是这种条件催生了政治自立、经济自主的城邦体系,原子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强调公民个人权利自由的政治伦理相伴相随,“希腊人开创的民主制度的架构就建立在对个人责任感的信任与对个人判断力的信心之上的”[7]。在古希腊的文化叙事体系中,个人主义的核心地位也逐渐确立。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单个的英雄就是史诗的主题,对于一个缺乏经文的宗教民族而言,这些史诗作为精神导引和文化规范被一代代的希腊人所传习。而且,希腊的个人主义并非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个人追求卓越的行为才能使其正当化,个人的奋斗、探索、追求是赋予英雄的神圣使命,也是普通公民的群体想象。于是古代奥运会成为了体现古希腊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不可少的社会设置,古代奥运会历经千年,项目增增减减,但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个人之间的较量,审美抑或公平的目的,古希腊以裸体的形式将竞技场的个人主义演绎的淋漓尽致。反观球类运动及其文化特质,无论是费尼达、哈尔帕斯顿还是俄皮斯库罗斯、欧拉尼亚,都是群体的嬉戏或玩乐,即便是两人角逐的俄费德瑞斯莫斯,也需要球手的相互配合方可完成。因此,蕴含的集体主义思想与主流价值观的悖离是球类文化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从球类文化的社会属性来看,以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诉求与古希腊人崇尚的竞争精神不尽符合。贫瘠的土地条件使希腊人无法被动地依赖自然生活,而方便的海上交通又为希腊人征服自然进而征服世界打开了大门。在希腊城邦的海外扩张中,希腊人必须面对与自然和人的双重搏斗,在搏斗中希腊人懂得了通过竞争获取胜利的哲学,并将胜利化作一尊女神加以顶礼膜拜。古希腊伟大的诗人荷马不断地教导希腊人,要永远处于最佳状态并超越其他人。这种主张与儿童和青年的教育联系在一起,引导人们强身健体、提高智力,成为好公民。以公平为基础,在竞技场上的各种活动中,在决定国家大事的公民大会辩论中,在法庭的抗辩中,在节庆日的诗歌朗诵、戏剧表演中,古希腊人都表现出竞争的欲望。希腊人敢于竞争并乐于竞争,他们以竞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最终,竞争精神被制度化地潜置入古希腊的社会大厦”[23]。球类文化则蕴含更多的娱乐休闲的价值,埃及法老们雇用职业的耍球者供贵族王公们观赏消遣,瑙希卡公主们在海滩上用球嬉戏,罗马皇帝们虽热衷于此,也只成为注重游戏者个体技艺和敏捷身手的典范,却毫无竞争性可言。即使是在存在计算球弹起数量的阿波瑞阿克斯球戏和两队运动员同场较量的俄皮斯库罗斯球戏中,结果的重要性远远轻于过程,技艺谋略的衡量远远高于游戏结果的评定。斯巴达的球戏固然激烈,但成年礼式的仪式性功能显然弱化了人们对球类运动的竞争性诉求。
从球类文化的某些规则来看,以假动作欺骗对手的行为与古希腊的公平伦理观念存在矛盾。古希腊的竞争是有原则的竞争,即双方运动员都必须在公平的环境中使用公平的策略来实现最后的结果。因此,希腊人对奥林匹亚赛场上的身份欺骗、金钱交换、政治阴谋一概嗤之以鼻,并加以重罚。古代希腊人眼中的竞技倡导有道德、有尊严、完全尊重对手的比赛方式,而游戏却充满伪装、狡诈、虚伪、谎言和讽刺。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观念,古奥运的第一个项目场地跑拥有了五个要素:平行的跑道,一条白线严格划分跑道,有人的目光注视前方,没有任何形式的计谋,更别提任何形式的伪善、欺骗和侮辱了,参赛者赤脚比赛。与之相反,希腊学者塞莫斯·古里奥尼斯以希腊的球戏费尼达为例,认为费尼达在古希腊语中就是欺骗的意思:“在古希腊人看来,游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欺骗行为,是不能进入体育场这样的大雅之堂的。游戏者不能进入体育场就成为一种传统,在古希腊得到普遍遵循”[6]。
5 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传承
每一种文化模式内部必然具有自己的结构功能一致性,否则各种文化特质、文化集丛便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更不可能得以传承。球类文化的传承也因自身结构功能的一致性而成为可能。
在现代社会中,球类文化依然融合进社会生活的大系统,与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对球类运动的选择别无二致。在家庭娱乐中,成员们在落日的沙滩上围成一个圈,饶有兴致地玩着颠球、传接游戏。游戏中抛和接过程的技术会对人们的体力提出一定要求,人们可能会根据成功抛接球的次数来积分,但比赛结束,这些分数很快就会被忘记。那些还不能够加入正式体育比赛的儿童和青少年也有丰富的球类活动,这些青少年的球类游戏不同于海滩家庭的球戏,前者的规则更加精细和富有传统,群体的新来者要尽力掌握这些规则,游戏因此被一代代地传习下去。
然而,文化的超越性与自在性的永恒矛盾使得文化的变迁成为必然,在现代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内以自觉思维方式存在的人一定会试图超越以传统、习俗、常识等自在因素构成的文化图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变迁成为了文化传承的内部动力与主体需求。
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公学,一种名称为 Kingy的青少年球戏就被制度化、组织化地嵌入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整体设置中,甚至被冠以“国球”的美誉。脱胎于工业化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现代球类活动,必然超越了古代西方球类文化的松散、简陋特征,与制度化、科层制的时代特点相一致、相融合,一举跃入了近现代体育的中心与主流地位:它们被国家或国际的单项体育协会所组织,拥有广泛认可的规则,比赛竞争激烈,结果意义非凡。它会带来联盟中的积分,或进入锦标赛的下一轮,最终的目标直指冠军、奖杯、奖牌和奖金。当竞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这些比赛成为了观众的娱乐,并占据了体育新闻的头条和电视屏幕的中心。当掌握球类技艺的选手日渐脱离普通大众的生活层面,他们开始被当作明星运动员而加以欣赏和膜拜。这仿佛是一个文化的轮回,只不过观赏表演的人从埃及的法老变成了电视观众和现场球迷。但无论如何,穿越了数千年历史时空的球类文化依然留存在体育文化的宏大图景中,它丰富着人们的锻炼方式、填补着人们的闲暇时空、延展着人们的身体智慧、激发着古希腊人曾经推崇的的卓越品质——一种实现美与善并存的、被称之为“阿瑞特”(Arete)的人格理想。
结语
作为古代西方体育文明画卷中的一页,球类文化显然没有闪耀着古希腊人引以自豪的个人主义竞技哲学的光芒;相反,它浑身都浸润着埃及法老们曾经崇尚的身份制的社会品味和阶级属性,球类运动可以是希腊贵族们的游戏;可以是罗马长官们的玩物;可以是艾弗比军团的结业比赛、可以是斯巴达勇士们的操练科目,但它永远成为不了赫拉克勒斯们的宠儿,更难以跻身阿尔提斯圣域的竞技场。然而,球类文化却以一种顽强的生命样式散落在古代西方体育文化的生态群落里,无论是荷马史诗中的瑙希卡玩球、盖伦《用小球锻炼》中的猪膀胱制球,还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私人球场、罗马皇帝西塞罗的身体力行,抑或强调团队配合的俄皮斯库罗斯、注重个人谋略的费尼达,球类运动对身体能量的积蓄、对成熟心智的培育、对社会团结的整合充分证明了自身结构融入广阔社会历史系统的可能与自身功能承接复杂社会历史需要的实现。
总之,在古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整体图景中,球类文化无疑是边缘的、是少数的、是另类的、是弱势的,它的存在不是否定更不能遮蔽“依靠双脚获取胜利”的希腊体育精神,却恰恰丰富了盖伦式的、古代西方人民对多元身体哲学的诉求:身体是能动的、身体是变化的、身体是完整的、身体是均衡的、身心是合一的。现代人对球类文化的继承与传习将此种丰富性演绎到极致,从个人到国家的社会主体序列中,每个层面都能从球类运动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价值与意义,这或许就是球类运动从古至今都能保持无穷魅力的“文化秘诀”吧!
[1]郝勤.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21.
[2]霍布斯鲍姆,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2.
[3]刘欣然,黄玲.决斗的风范:从人类决斗精神中对体育运动的哲学解读[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2):162.
[4]卢元镇.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67.
[5]聂啸虎.欧洲古代休闲体育思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J].体育科学,2007,27(12):15.
[6]塞莫斯·古里奥尼斯著,沈健译.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7,43.
[7]斯蒂芬·伯特曼著,韩松译.奥林匹斯山之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73.
[8]王以欣.神话与竞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87.
[9]托尼·佩罗蒂提著,消雪译.天体奥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7.
[10]薛岚,董大肆.论球类运动的文化属性[J].体育科学,2006,26(12):20.
[11]易剑东.体育文化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182.
[12]ATHENAEUS.The Deipnosophists,Loeb Translation[EB/OL].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2009.
[13]BASORE W.Seneca:Moral essays de beneficiis[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8.
[14]DAVID MATZ.Daily Life of the Ancient Romans[M].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2008:67.
[15]GALEN.On the natural faculties[EB/OL].http://classics.mit.edu/Galen/natfac.html,2009.
[16]GIDEON NISBET.Greek epigram in the roman empire:martial’s forgotten rival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37-45.
[17]HARRIS H.A.Sport in Greece and Rome[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88,93,84.
[18]HESIOD.Works and days,translated by W.Hugh[EB/OL].http://www.sacred-texts.com,2009.
[19]JOAN PAUL.Ancient and medieval sport[J].J Sport History,1986,13(1):54-55.
[20]MACKAIL J.Select epigrams from the greek anthology[EB/OL].http://www.archive.org/,2005.
[21]NIGEL CROWTHER.Sport in ancient times[M].London:Praeger Publishers,2007:101,138.
[22]NIGEL KENNELL.The gymnasium of virtue: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sparta[M].Chapel Hill:University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39-40.
[23]NIGEL SPIVEY.The ancient Olymp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5.
[24]NIGEL WILSON.Encyclopedia of ancient Greece[Z].London:Routledge,2006:221.
[25]STEPHEN MILLER.Arete:Greek sports from ancient sources[M].Berkeley: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2004:178,120.
[26]SYNTHIA SLOWIKOWSKI.Alexander the Great and sport history:a commentary on scholarship[J].J Sport History,1989,16(1):74.
[27]Trigon:Roman ball games[EB/OL].http://www.aerobiologicalengineering.com,2009.
[28]WALDO SWEET.Sport and recreation in ancient Gree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96.
[29]WIGHT DUFF,ARNOLD DUFF.Laus Pisonis[EB/OL].http://www.archive.org,2009.
Study on Culture of Ball Games in Ancient Western World
WANGRun-bin1,XIONGXiao-zheng2,YANGLin3
Be born out of both producing implements’revolution and entertaining patterns’extension,culture of ball games had hard evolved at the edge of landscape of ancient western sports culture which focused on athletics philosophy.Structural characters of ball games culture are consisted of crude facilities and instruments,loose organization style and simple ideology.Functional characters of ball games culture are conveyed by cultivating sound body and soul,making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enlightening the people and consolidating military training.Because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deviations between recreation pursuing and competitive spirit,variances between game tricks and fair ethics,the culture of ball games had been difficult to merge into mainstream culture of ancient western sport.
ancient;western world;ball games;culture
G80-05
A
1000-677X(2010)02-0083-09
2009-12-02;
2010-01-08
王润斌(1981-),男,河南信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历史与文化,E-mail:wangrunbin2008@126.com;熊晓正(1951-),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体育历史与文化,E-mail:xiong5128@126.com;杨麟(1978-),男,辽宁抚顺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历史与文化,E-mail:bad007@126.com。
1.南昌航空大学体育学院,江西南昌330063;2.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教研室,北京100084;3.浙江工商大学体育部,浙江杭州310018
1.Sports School of Nanchang Aeronautics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2.The Olympic Studies Center of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3.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