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扑灰年画: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
2010-12-01焦宝
焦宝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长春 130012)
高密扑灰年画: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
焦宝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长春 130012)
高密扑灰年画是我国民间年画的一个独特品种,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其形式与内容、传承与变迁都具有其独特性,当中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
高密扑灰年画;神话叙事;乡土情境;女性;视觉主义
一、高密扑灰年画概述
山东潍坊的杨家埠、天津的杨柳青和苏州的桃花坞被称为我国三大年画产地。在潍坊年画当中,高密的扑灰年画更因为其历史悠久和工艺独特被誉为“中国一绝”。[1]高密扑灰年画始见于明代成化年间,在清代最为盛行,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日渐兴盛。到了清末,高密地区又兴起了半印半画和木版印刷年画。至20世纪40年代,高密共有一百五十多家年画作坊。目前,在高密地区经年制作扑灰年画的作坊大约有十家,而到了年前一段时间,则会有百余人家制作扑灰年画。关于扑灰年画确切的起源,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据传,扑灰是经高密大栏乡公婆庙村王姓人家发展创新而形成的。当时文人手工画生产效率极其低下,而民间尤其是春节期间对于年画有巨大的需求量,王姓人家正是看准了这一商机。扑灰年画制作简单,成本低,当然利润也不高。开始王姓人家为了生计,便临摹一些文人画和庙宇壁画拿到市场上去卖。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们便以文人画和庙宇壁画为基础,对其进行了借鉴、创新,从而创作出了最早的扑灰年画。“初期的扑灰年画大都是以神像、墨屏花卉为主。到明代中叶,‘墨屏花卉’己销行于市。”[2]
扑灰年画的名称缘起于它的制作工艺,主要是起稿方式的特殊性。它的制作是先根据所构思的题材内容,然后用柳枝①使用柳枝作材料可能与其质地有关。柳枝比其他树种如杨树、槐树木材纤维含量更高,是很好的薪炭材料,战国时期就有女人使用柳炭描眉的记载。烧制的炭条起轮廓,再用画纸在上面扑抹,一稿可扑数张,从而缩短了起稿的时间,提高了绘制效率。为了增加数量,还可在扑好的一张画稿上再用柳枝炭条描一遍,重扑,然后再粉脸、手,敷彩,勾线,开眉眼,涮花(或磕咸菜模花),描金,最后在重点部位涂上明油(酒精松香液、蛋白或骨胶水)。由于整套工序都带有“抹”的味道,故民间艺人们俗称扑灰年画为“抹画子”。“扑灰”正是指它的生产制作工艺而言。
二、高密扑灰年画研究现状
扑灰年画是一种如此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无论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还是美术学及美术史学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扑灰年画的研究目前还非常薄弱,比较容易见到大多是描述性的文章。他们将着眼点放在其地位、制作过程以及扑灰年画的商业流变等方面,能够以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视角来审视和研究扑灰年画的论文论著则几乎没有。其他涉及到扑灰年画则主要是一些年画史美术史的论著。2007年西北民族大学秦国栋先生的硕士论文《姜庄镇扑灰画的传承及演变研究》是国内唯一一篇从民俗学的视角来考察高密扑灰年画的专论。
本文拟以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考察高密扑灰年画的形式内容,解码高密扑灰年画的文化与话语。
三、神话叙事与扑灰年画中的灶神——扑灰年画的形式与内容
自人类学诞生以来,神话、巫术和宗教就一直是人类学最为关注和发掘的主题。[3]而高密扑灰年画当中就有相当部分的神话题材或者说是世俗化了的仙话题材,①关于神话与仙话,可以参加袁珂先生等神话学家的相关论述。实际上,年画题材当中以流传更广泛的仙话题材为主。比如“八仙屏”、“天女散花”、“三仙姑下凡”、“灶神”、“文武财神”等。这些传统的仙话题材在扑灰年画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具有功能主义的色彩。但是长期以来,神话在人类学家的眼中往往被视作是异文化的伪装:神话被归入“幻觉”的领域;它们表达了人幻想的本质;它们与历史相对,而历史讲述了人们过去“真实”发生的现实事件。神话不具有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色彩,但是却和“原始思维”联系。“原始思维”观念本身就表达出一种思维的理论,并设定存在一个随历史发展的理性进程,这一进程带有理智并依照理智进行。②相关论述参见布留尔《原始思维》以及荣格对于“原型”分析等著作。随着现代人类学思潮兴起,神话研究的研究方法进入了功能主义和形式结构主义分析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我们得以来分析扑灰年画的形式与内容③形式与内容分析的相关著述可以参见乔治·齐美尔的相关论著。齐美尔眼中的任意社会现象均具有不可分割的双重要素(类似于康德的表象和实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的关联,发掘其基础意义上的功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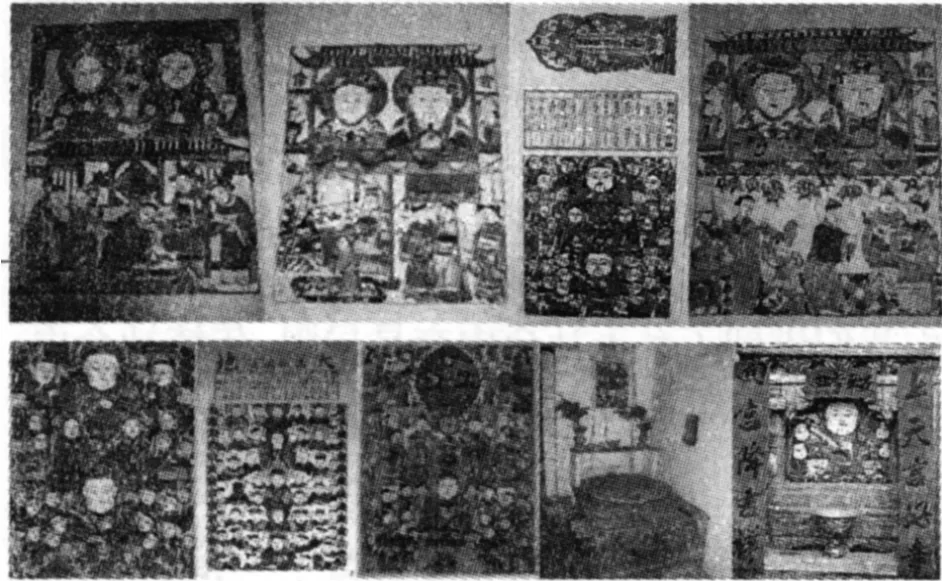
图1 :与扑灰年画有地缘亲近关系的杨家埠年画——灶神④据秦国栋注:灶王,所以成为年画中的抢手货,不能不说因为他极大地满足了乡民们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的需要。高密现在行销于市的是一种木版印制的“灶王”,它是在扑灰灶王、半印半画灶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密的扑灰“灶王”及后来的木版印制的“灶王”,依据的是古籍记载中的传说。《淮南子·泛论》中所载“: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祀于灶神。”神农便是灶王的化身。神农尝百草,发现五谷,又发明了能变生食为熟食的火,对老百姓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人们自然会记念他。总观以上传说,不管那种更为有道理,都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也许,人们祀奉的灶王,是三种传说的有机合成。高密的民间画师们不仅迎合了人们的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还在这种年画的样式上尽力搞得灵活多样,不仅有“二人小灶”,还有“二人大灶”,不仅画上一个一本正经的灶王画像,还在“灶王”顶上印上份指导农家生产的二十四节气图,以增加“灶王”对乡民们的吸引力。秦注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当今市场上,制作工艺相对复杂落后的扑灰年画已经越来越让位于木版年画,这种木版的灶王年画行销于山东中部民间,已不仅仅是高密一地。
以高密扑灰年画中的灶神年画为例。
灶神,民间也称灶王、灶王爷。灶王是唐以后民间对灶神的别称。案李廓《镜听》词“匣中取镜辞灶王。是称灶神为灶王,唐时已然。”[4]灶神被视做掌管一户福运的家神。它根植于民众日常生活,具有三种职能:一是掌管饮食,二是司掌命运,三是监察善恶。可见灶神是“检察员”,负责纪录人间善恶,自古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也是最贴近民俗生活的三大民俗神(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之一。祭灶虽然也列入官方祀典,但其民间意义更强。从古至今,人们都要举行一定的接灶仪式来恭迎灶神。[5]在高密扑灰年画兴盛区域范围内,即山东中部广大的乡村中,几乎家家供奉灶神,这是年画的一个重要市场,也是因此灶神成为年画的重要题材之一。
在山东民间,供灶神是小年,也即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民间的祭灶仪式丰富多彩,但一般程序则是分送灶神升天和接灶神两步。送灶神升天是在每逢农历的腊月二十三日。一般祭灶是焚香五根、黄表三张、小蜡一对,主供品是麻瓜糖,也有叫糖瓜的,其他则有茶、草料、皮豆、白面、火烧之类的物品以及清水一盂。茶是为了让灶王润口,草料为灶王坐骑之食,皮豆是给灶王的鸡饲料,火烧则用来给灶王喂狗。而这麻瓜糖则是给灶王吃的。小年的晚上燃起香烛,必须由当家的男子跪拜。当祭灶的仪式要结束时,主祭灶人先把贴了一年的灶神像揭下来。在送灶王爷升天前,大多数地方还要由主持祭灶的人对灶王爷说一番祭灶词,随着就“啪”的一声,把粘粘的麻糖粘在旧灶神像的“嘴”上,接着便烧掉,谓之升天,边烧边祷告:“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有壮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皇进好言。”有的地方是把粘粘的麻糖粘在灶门口。此举的意思是要封住灶王爷的嘴巴,不准他说坏话,只让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用意是请灶王爷吃了糖瓜,可以到玉皇大帝那里甜言蜜语,说得好听一点:多讲成绩,少说缺点;多讲光明,少说阴暗。送灶王升天后,还要接着在旧灶王的位置,贴上一张新请的灶王像,谓之换新衣,意思是已为灶王爷准备好了回来时穿的新衣裳。
接灶一般在除夕。程序上较送灶神要简单些,供奉品也要随意些,一般是在午夜人静时分,还是由当家男子来完成,也有部分地区把贴新灶神像的程序在这一日完成。
作为年画的灶神画像在这一灶神崇拜的民俗活动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媒介。其主要功用不在于提供审美愉悦,而是提供一种现实的文化功能,一种社会化过程中的中介职能。
根据齐美尔的描述,一定的文化形式为互动提供了中介,通过这一中介,个体才走到一起;这一文化组织就是他们社会交往的手段,也有助于在他们之间建立社会,并且声称具有共同的象征性现实。属于一个社会意味着采用相同的文化形式构建现实。[6]
在年底山东民间的大集上,往往能看到年画买卖,而这种灶神年画又往往成为最容易脱销的,并且买卖灶神年画与其他年画不同,不能说买,而要说“请”,这又是在一个文化社会,或者说在一定文化心理支配下的“人类学的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现象,也即对于形式背后的意义价值的确认。
四、社会阈限与扑灰年画中的乡土情境——扑灰年画的传承变迁
高密扑灰年画的生产区域相当集中,其传承情况便备受关注。“民俗的传承性,是指民俗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7]扑灰年画的传承与一般民俗艺术的传承相比较具有其特殊性。第一,扑灰年画制作工艺独特,需要专门技艺。民俗艺术,一般而言应当是民间相对比较普及、比较广泛的。但是对于扑灰年画来说,其传播范围是广泛的,但单就生产制作来说,却很难广泛推广。第二,扑灰年画制作比较而言手工性更强,而制作效率更低。交易和互动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但是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交易,则扑灰年画在市场当中属于一种不适宜大规模生产制作的艺术。其制作效率和交易利益决定了扑灰年画的传承只能是在处于相当少的数量上。这种传承上的特殊性主要是由扑灰年画的乡土性决定的。
实际上,扑灰年画的乡土情境随处可见。比如扑灰年画的重要题材:姑嫂闲话。亲属关系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领域之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亲属宗族关系,其复杂性更是具有独特性。在扑灰年画中,民间画师们就敏锐的捕捉这一类在乡土情境下随处可见而又十分重要的关系。姑嫂关系,是传统社会当中极具普遍性的家庭矛盾关系。传统社会中,这一关系之微妙使得它成为各种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而在高密扑灰年画的画师们笔下,小姑温文尔雅的紧靠着嫂子,而嫂子则娴熟敦厚的为小姑撑着伞儿,两人并肩缓行的场景出现了。这时候,“姑嫂闲话”不再是一种现实关系的简单映射,而成为具有教化意义和功用的书写。

图2 :扑灰年画名作《姑嫂闲话》与《三娘教子》
这种形式上的乡土话语,其内涵是乡土的文化价值。扑灰年画在乡土社会中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传承方式。最主要的一种便是师徒传承。前面我们讲到了乡土社会中交易局限。传统社会中,手工艺人地位非常低下,“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才成为一句俗语。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技艺的交流和传播,甚至造成某些绝技失传。在今天,传统的乡土社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上愈加严重的利益矛盾,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这种传统传承方式了。①这是秦国栋在高密姜庄镇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参见其论文:《姜庄镇扑灰画的传承及演变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7年民俗学硕士论文。
现代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关系网络,这与以宗族为单位、以宗法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具有本质不同。首先,手工艺人的地位上升了,不再是下九流,这就使得部分画师克服了心理障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学画。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传统社会中子承父业这种以血缘传承为核心的文化心理依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及其文化习俗,并强烈的地反映在姜庄镇扑灰年画中,扑灰年画具有的宗法色彩浓厚的师徒传承方式,在当今主要表现为家庭作坊式的家庭代际传承。
亲属关系的研究,包括相关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直到最近一直都是人类学调查和争论的中心。[8]扑灰年画行业中的父子传承模式一般都发生在世代经营年画的家庭作坊中,作坊的主要工作人员是家庭成员,一般由祖父或父亲做掌柜,管理作坊里的各项日常事务,从纸张、颜料的购买、帮工的雇佣到年画的买卖,都由其负责.其他家庭成员则在他的主持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个生产被安排得有条不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家庭作坊对外技术保密,对内却没有“传男不传女”、“传媳妇不传闺女”的限制,因此家庭作坊里常常出现一家男女老幼齐上阵的景观。一种家族传承的需要同时又构成了一家人亲属关系密切的网络,在一种需要支配下的个体互动成为亲属关系更加有“秩序”的安全带。这种模式在扑灰年画行业中是不少见的,比如《人民日报》就曾报道过高密扑灰年画名家吕蓁立老人一家。
五、女性形象与视觉主义——扑灰年画阅读与阐释
女性和性别在1972经由埃德温·阿代纳(Edwin Ardener)于《妇女的信仰与问题》一文提出。他阐述了民族志的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在民族志的文本中相当缺乏妇女的言行和思考以及理解。[9]我们可以说,在扑灰年画中的女性形象构成了扑灰年画对于女性和性别的阅读与阐释,在那里不缺乏妇女的言行和思考。
在传统的文本写作当中,女性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当做“他者”来书写。而在扑灰年画中不是这样。以前文的姑嫂闲话题材为例。在宗族社会当中,社会稳定依赖于关系的稳定。女性,即姑嫂二人,在这里不是被阐释与被熟悉的对象,而是主动参与到稳定关系的构建当中,也正是这样,扑灰年画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来说,承载着的教化意义和功用就远较《列女传》等“他者”文本书写来的亲切。
扑灰年画作为一种视觉存在形式,是人类行为中音——像维度的作用结果,作为一种可视符号,承载着丰富的信息。扑灰年画艺术的思维具有单纯视觉思维的原始性和象征性,比如以石榴果实多子来象征传统社会中“多子多孙”的愿望等。扑灰年画艺术的装饰特性给人以完整的视觉感受。装饰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元素有选择的运用到作品中,达到丰富形象、突出主题、美化作品的目的。扑灰年画在主题形象的周围,多以有特定象征含义的动物或植物花草填充,给人以丰满完美之感。为了追求这种构图,民间艺人往往有一些奇思怪想。采取对称、均衡、变化、统一的艺术规律,创造了出人意料的组合关系,加强了年画艺术形象的装饰感和完美感。以“姑嫂闲话”为例,只设置姑嫂俩人,构图十分简洁,但通过一些小装饰使画面给人一种丰满感,使人对姑嫂亲情产生敬慕之感。
作为视觉符号存在的扑灰年画,早期主调是水墨为主,视觉的冲击力较弱,但在长期发展中,形式和年画的功用互动,形成了以色代墨、着色浓重、色彩艳丽、形象追求动感、线条豪放流畅的特色,这种特色就适应了春节期间节日的欢乐气氛。
清代道光年间,高密扑灰年画与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相互影响,出现了半印半画的作品,版印线条,手绘色彩,这一方面摆脱了手工绘制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大大提高了年画的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10]但是,今天缺乏创新能力成为威胁其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尤其高密扑灰年画作为我国民间年画的一个独特的画种,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画种,其生存和发展就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1]窦吉进,伊红梅.高密有个扑灰年画世家[N].人民日报,2004-06-11;单应桂.谈谈山东民间年画[J].齐鲁艺苑,1983,(1).
[2]秦国栋.姜庄镇扑灰画的传承及演变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07年民俗学硕士论文.
[3][6][8][9]拉波特,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33,115,186,119.
[4]袁珂.中国神话大辞典[K].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294.
[5]高奇.走进中国民俗殿堂[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53.
[7]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0]郑军.高密扑灰年画的造型与色彩[J].山东社会科学,2007,(9).
责任编辑:陈冬梅
2010-09-07
焦 宝(1984—),男,山东淄博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战线》文学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传播学和词体文学。
K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0)05-001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