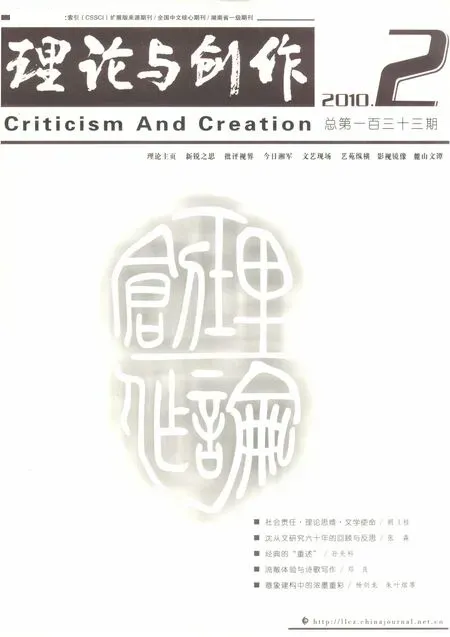成长的“代价”——电视剧《潜伏》的反成长叙事及其他
2010-11-25张丽芬
■ 张丽芬
近年来,谍战片风靡全国。从较早登上荧屏的《暗算》、《雪狼》到《潜伏》和《地下地上》,直至最近上映的《风声》、《秋喜》、《最后的较量》,谍战片以其情节的惊险离奇让观众胃口大开,欲罢不能。其中尤以2009年的《潜伏》堪称达到了谍战片的高峰,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有论者从艺术特征及营销模式的角度来总结该剧火爆的缘由,也有论者从日常生活美学的角度分析该剧浓郁的生活气息,甚至有论者撇开时代背景,侧重研究该剧所隐含的职场攻略。真可谓见仁见智。笔者发现,尽管众说纷纭,《潜伏》中余则成的反成长叙事却鲜有涉及,深究其来龙去脉,编导似乎并未重复一般谍战片固有的模式,并未止步于用惊心动魄的情节来塑造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高尚情操的革命者形象,而是站在人性人情的高度,在“假扮夫妻”这一新鲜外壳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这个“成熟”革命者的成长之痛,使观众被全剧的“信仰”之声激荡胸怀的同时,又产生些许疑虑:作为为革命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有功之臣余则成,为何不能在革命胜利的凯歌中与家人团聚,最终因为无法拥有普通人的幸福而遗憾终生?
《潜伏》和《青春之歌》一样,沿袭传统革命爱情小说的“爱情与革命顺生模式”①,即革命激发爱情,爱情催生革命。前者异于后者之处在于,虽然是一男三女的传统套路,却一反英雄救美的模式,成就了一段美人救英雄的壮举。左蓝作为小知识分子余则成的革命领路人,用爱情召唤恋人弃暗投明,余则成却言辞激烈地坦言自己的人生哲学:“我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信仰良心,信仰生活,信仰爱情!”余则成最初的梦想只是和恋人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无关政治,没有战争,这也是一个凡人的正常要求。这种朴素的人生观是战争中渺小生命的微薄要求,却在剧中被无限地延宕,甚至到剧终都未能实现,这一含泪的结局值得我们深思。
一、成长之喜
余则成在亲眼目睹国民党高层与日本人的黑幕交易后,对自己效忠的政党失去了信心,“八年来被骗的感觉,此时溢出了怨恨”。这种思想的转变很自然,李克农对他的训诫更是坚定了他的信念——“你的领导就是你个人的信念”。余则成终于在各方的感召下走上了“成长”的第一步,成为中共的内线。直到左蓝舍身保护余则成,这一壮举既保护了心上人又保全了革命同志,“红色恋人”和“革命领路人”的角色体验达到高潮,大无畏的革命气息充溢在他们的爱情世界里,可谓播下爱情的种子,收获革命的硕果。
左蓝的牺牲给余则成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以恋人留下的《为人民服务》为精神寄托,激情洋溢地反复诵读,此时短镜头快速迭加,一缕阳光照射在余则成的头部,象征了他的思想在腥风血雨中迅速成长,日益成熟,终于完成了从小知识分子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如果说左蓝是带领余则成的革命领路人,爱情催生了革命,那么对于翠平而言,她和余则成则是在革命火炉中共同成长,经过了千锤百炼,终于成就了他们坚如磐石的爱情,可谓革命孕育了爱情。“红色恋人”题材在电影史上屡见不鲜,如1958年《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与何兰芳,1998年《红色恋人》中的靳和秋秋,但余则成与翠平的组合却是一种另类。与以往“红色恋人”的夫唱妇随相比,余则成这个“丈夫”兼革命领导的角色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究其原因,不是信仰差异,而是性格角色的悖反,让他们成了一对特殊的“恋人”,而这也正是该剧匠心独具之处。外表文弱、举止文雅、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余则成与外表强悍、鲁莽直率、粗枝大叶的女游击队长翠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有人戏称为“小眼睛与大嘴的组合”,这就使本来惊心动魄的谍战剧中加入了妙趣横生的“佐料”,平添了几分喜剧意味。
翠平的“女强人”角色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翠平性格鲁莽、急躁、强悍,是个地道的村姑。在“夫妻”庆祝营救晚秋成功的晚上,余则成不胜酒力,先醉了;而翠平一个人能顶两个男人的酒量。第二天醒来,翠平笑他:“酒量怎么那么小?兔子一样。”余则成问:“我怎么上床的?”“我扛上去的。”“我睡衣怎么换的?”“我给你换的,裤子也是。”这段富有生活气息的诙谐对白将两人的个性展露无遗。翠平的敢爱敢恨、积极主动和余则成在爱情上的胆小怯懦、游移不定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场由革命引发的爱情长跑中,翠平始终扮演了主动者,而余则成只是在亲眼目睹了翠平“神枪手”的威风之后,才被她身上所具有的革命英雄主义气质所折服,由崇拜转化为爱情。第二,翠平是以根红苗正、一身正气的女游击队长的身份出场的,而此时余则成正迫切希望入党。因此,虽然余则成是翠平工作上的领导,但在资历上远不如翠平。翠平在小家庭中扮演了党组织临时代言人的角色,余则成才会面对翠平,举行神圣的入党宣誓仪式,这是余则成真正“成熟”的标志性事件。正是有了“党”的名义,翠平的“女强人”性格才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威性。这就突破了一般“革命爱情顺生模式”中的性别本质主义,即女性是感性、温柔、依赖的;男性是理性、勇猛、独立的。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相比,翠平行事果敢、坚毅、泼辣,内心又不失女性的细腻与柔情。林道静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三位男性都是以拯救者或精神导师的身份引领她走出困境,走向希望。余永泽不仅拯救了林道静的生命,还唤醒了她对青春和爱情的热望;卢嘉川把她从小家庭引向无限广大的革命世界,实现了思想上脱胎换骨的转变;江华带领她真正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成长过程。林道静的每一次成长都是被动的,需要外在的力量(男性)去推进,这与翠平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有着本质区别。翠平虽然因个性缺陷,一开始不适应潜伏的特殊要求,但她总能积极主动弥补过失(拿手雷与敌人拼命),并且在刺杀陆桥山的行动中成为革命英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她与余则成达成了一种互补和呼应。翠平正是以这种“强势”赢得了余则成的爱情并和他并肩在革命道路上茁壮成长。
余则成在完成革命成人仪式之后,继而成为晚秋这个极具小资情调的女孩的革命引路人。满怀青春梦想的晚秋一厢情愿地深爱着余则成,余则成虽不为所动,但当晚秋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时,他没有按纪律灭口,而是劝导她走上革命道路。晚秋政治身份的成功转变意味着余则成已经有能力作为独立的革命主体去感化激发更年轻一代的革命热情,使他们加入到革命大熔炉中,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则成已经成长为优秀的潜伏人员。
二、成长之“痛”
如果《潜伏》在完成革命主体成长的塑造之后,故事就戛然而止,那该剧不过是传统革命爱情故事的延续。难能可贵的是,导演并没有在此止步,给观众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进一步挖掘革命主体的成长之“痛”,以此表达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思考。
在龙一所著的短篇小说《潜伏》中,余则成是一个“老实、木讷”的知识青年,而翠平则是性格执拗、不会变通、甚至有些粗鲁的女人。生活在两个世界的陌生人却由于革命的需要扮成假夫妻,生活上的差异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使他们本应和睦友好的协作关系一再恶化,只因共同的革命事业,他们才在一起勉强过了两年。原本强壮的翠平在这度日如年的两年里,被内心的空虚和孤独折磨得形销骨立。可悲的是,余则成却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的老实和不善言辞,无法和“妻子”沟通。当最后生离死别的时刻,翠平突然提出了“跟你在一起住了两年,我已经没法再回去嫁人了,你一定要回来!”②的要求,这是女性维护自尊的本能要求,也是对爱的渴望和呼唤,而此时的余则成却不愿意给翠平留下微小的希望,哪怕他能九死一生地回来,“他也给不了翠平幸福,而他自己则会更不幸福”③。
在此,两性关系的强弱对比一目了然。同为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女性除了要坚守革命信念,还要遵守从一而终的贞节观;男性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以革命的名义逃避“家庭”责任。女性在此处于失语地位,而小说中翠平最终为革命献身可谓完美结局,既用生命践行了革命理想,又不必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背负起这段短暂“婚姻”的沉重十字架。
相比而言,电视剧《潜伏》并未以死亡作为结局,而是让战争的腥风血雨浇灌下矢志不渝的爱情在完成革命理想后依然要承受“生离别”的痛苦,余则成和翠平在飞机场上那无言的道别、那默契的眼神,以及翠平脸上由惊喜转为由衷的微笑,都彰显了这对患难夫妇在胜利前夕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此时,电视剧《潜伏》在革命主体完成成长、洗礼成熟后,并没有停留在《青春之歌》似的、表面的欢欣满足之中,而是延续了小说《潜伏》所传达出来的凄凉无奈的情绪以及个人在历史大潮中无力把握命运的悲哀感。导演希望人物成长,完成“革命成人仪式”,却不愿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麻醉大众,而是用凄凉的结尾传达对战争残酷、人生无奈的深刻理解,也传达出对战争意识形态违背人性、束缚自由的一种隐喻的洞察和透析。满怀期待的夫妇在革命胜利后盼来的却是永远的分离,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在此,高调的革命叙事出现了罅隙和张力。翠平被安排在一个小山村中,默默等待丈夫的归来,一个长镜头俯视挺着大肚子的翠平,她站在高高的悬崖边,远眺山间的那条蜿蜒小道,苍白的脸上写满了焦急与失落。而此时的余则成却远在香港,继续执行潜伏任务,而且已经被组织安排与另一位女“秘书”扮演假夫妻,而这个“秘书”正是晚秋。当余则成急切地询问翠平的下落时,那位和他联络的上级冷淡地回答:“找到了又能怎么样,你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最后一个镜头是在台北的余则成与晚秋一起挂好结婚照,余则成眼前闪过翠平的形象,泪水无声地划过他瘦削的脸庞。主人公的无奈与感伤呼之欲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由于天然的性别差异,翠平的命运将是永远的等待,甚至由于保密的需要被剥夺了继续革命的权利。而她深爱的丈夫却由于革命的需要和性别优势与别人组成新的家庭,女性在此处于失语地位,人性和情感被放逐,这种无情的放逐与崇高的革命目标合谋以彰显其合法性。在此,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话语处于权威、主导地位,个体话语和女性话语被强行压制、改造并缝合进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无声无息地滑落在历史的缝隙中。
编导之所以要安排这样的结局,可以借用布里恩·汉德森所说的:“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④与1958年《永不消逝的电波》和1998年《红色恋人》这些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相比,2009年的《潜伏》全剧虽然充满信仰的力量,洋溢着革命主体成长的欣喜,但结局突如其来的转折显示出编导对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的价值判断的游移,对传统的成长故事进行了消解,展示出战争的非人性的一面,从而与当下社会的流行价值观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暗合和呼应。“人的一切尊严都关联于对自由的爱,没有什么能比这种爱更深刻。”⑤当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在战争中被完全忽略,当九死一生的默默奉献换来妻离子散,我们无法不正视战争对人的尊严的剥夺和践踏。“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一切,不仅是最极端和最无限量的暴力形式,而且也是最极端和最无限量的反人格主义的形式。……军队与战争一样,全然不关注人的个体人格,人在那里只是非人性目标的一个部分和一种工具。”⑥在该剧中,危机四伏的“潜伏”只是战争这座巨大冰山下的一角,却已折射出编导创作时错综复杂的心态:在当下价值观多元化、碎片化的时代,如何去解读并还原历史真相是陶醉于革命乐观主义式的自娱自乐,还是揭开历史的伤疤,以新时代谍战片的形式直面战争的反人性,寄寓对个人与革命、历史关系的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潜伏》的成功可以说正是满足了当下民众的口味:既有打破日常平淡生活的惊心动魄的谍战因素;又在商业大潮的背景下重新发出震撼人心的革命信仰的召唤;此外,还在结尾保持了对历史和战争的反思,表现了普通个体在滚滚历史潮流中的无足轻重感和无力把握命运的悲怆感,这种反成长叙事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革命宏大叙事,表达了对战争本性的反思,同时也反映了商业时代的深层症候。
注 释
①马春花:《爱情与革命的抉择——论“十七年”女性文学中知识女性“成长/改造”模式》,《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
②③龙一:《潜伏》,《南京日报》2009年3月25日。
④布里恩·汉德森著,戴锦华译:《〈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
⑤⑥[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徐黎明译:《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