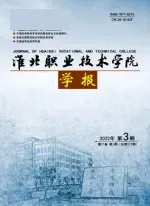奥古斯丁儿童教育理论述评
2010-08-15朱晓红
朱晓红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奥古斯丁儿童教育理论述评
朱晓红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通过对奥古斯丁《忏悔录》读解,对他的有关儿童教育理论,如教育与儿童本性的关系、教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教学中学生的地位、学习原则、教学内容的选择和非智力因素与教育等六个方面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进而认为奥古斯丁是欧洲中世纪前的一位最杰出的宗教教育家。
奥古斯丁;《忏悔录》;儿童教育
奥古斯丁(Aurelius Agustinus 345-430年)是古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教父哲学家的主要代表。他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早年在文法学校学习,当过修辞学教师,曾信奉摩尼教,并阅读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386年皈依基督教,回到故乡,并于395年升为希波主教。他的一生都从事于神学论述,是教父哲学的最大权威者。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瞩目奥古斯丁同时代的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cilianus),而对奥古斯丁的论著特别是对其儿童教育理论作系统研究的极少。本文通过对奥古斯丁原著《忏悔录》的读解,从诸如教育与儿童本性的关系、教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教学中学生的地位、学习原则、教学内容的选择和非智力因素与教育等六个方面对他的儿童教育理论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以期给奥古斯丁在古罗马教育史上的地位重新评价。
一、教育与儿童本性的关系
奥古斯丁认为教育目的在于使人和万物的神灵相结合,使人“凭仗天主赋予的理智,用呻吟,用各种声音,用身体的各种动作,极力表达心理的意念,企望自己的欲望得以满足。”[1]163他的这种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教父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教育目的是为了来生获得幸福,而不是为在现世得到任何裨益。这与他的哲学观点是并行不悖的。他极力宣扬“原罪说”,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有邪恶的观念本能地存在着,儿童的邪恶在他吮吸母乳时就表现出来了。由此,他认为学校有三件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戒尺、皮鞭、棍棒。他对自己说:“我年龄虽小,犯罪极大,确实应当受到惩罚。”[1]166因此,他一再说明体罚的合理性,再三呼唤无形的神来拯救有形的人的生命的灵魂。他谈到儿童具体的心智特点时认为,儿童在他的幼小的时候,信仰(对宗教和神的信仰)尚未形成,学习应由他们所具备的心理特点而定,教育应顺应自然,教给儿童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在《忏悔录》中客观地写到:“我酷爱拉丁文,但不是启蒙教师给我的那部分拉丁语法,而是有学问的人教给我的拉丁文学,对于读写和辨认那粗浅的拉丁文,我感到同学希腊文同样苦恼,同样麻烦”。[1]166-167尽管作为基督教思想家,他确认对神的信仰可以使充满“原罪”的儿童皈依神的灵光之下,但是,在儿童教育问题上,他还是承认儿童是“血肉之躯,不是一去不复返的风”,[1]167同时他也肯定了儿童本性在教育上的能动作用,表露了他在宗教思想禁锢方面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他并不是完全复述其先驱的思想观念,在顺应事实上作了很大的贡献。
奥古斯丁把儿童的多种秉性看成是一种错误,一种应得到净化的“原罪”,这是唯心主义的。他一面强调儿童的天赋秉性是应该净化的附属物,一面在自传中又谈到任何一个儿童都有这种自然属性。在他看来这种自然属性是一种惰性,是人对有趣的、有意义的东西的一种本能的心理倾向。但是,他也认识到了人必须要经历这一过程,这是他本人的一种进步。
二、教育的发展观
教育是年轻一代的发展工具和手段,发展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特点。但不同的时期,持不同哲学观的人在对教育发展观的看法上又不是一致的。奥古斯丁从他的教父哲学思想出发,在《忏悔录》里充分论证了人性本恶和体罚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儿童生来是邪恶的,带着满身邪气来到这个世界,从而在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取法于天上的神灵来净化自己,尽快地走出习俗之门。因此,奥古斯丁认为教育不能是儿童从先天的本性出发去咎由自取,而应该对儿童进行克制和约束,“这种强制限制了那种无拘无束的好奇心的不稳定性”。[1]166正是鉴于儿童要摆脱原罪,修正原罪走向灵魂的教育目的,奥古斯丁才竭力主张实行强制和压力甚至体罚,也正是通过这种方法能把儿童“从背离神的那种易于感染和甜蜜中召唤到神的身边。”[1]169因此,奥古斯丁的教育发展观很明显是“有限制才有发展”,这种发展是通过对儿童的约束而实现的。他认为“当儿童刚刚进入习俗之门……总极力求得别人称赞,因此……言辞典雅。主啊!在你看来,讨世人欢心等于被抛进了污秽的漩涡。”[1]173他非常重视教育使儿童沿着神的旨意去发展,而排斥形而上学的“欢心愉悦”,反对用习俗文学去感染学生,追求由神允许的实质性教育,即充满基督教思想的教育。与此同时,奥古斯丁再三强调教育的思想性。他认为一切教育其思想性是核心,这种观点至今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奥古斯丁所说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基督教义,他说:“不管什么书籍,如果没有提及那个圣名,不论内容如何翔实,文辞如何典雅,根本就不会得到我的欣赏。”[1]176
三、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
奥古斯丁主张通过体罚促进教学,他认为只要为神,为实现神赋予灵魂纵然挨打了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谈道“荷马捏造了这些故事,把凡人的过错归之诸神,我宁愿把神授美德加在自己身上”,[1]171-172从而确认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学习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信仰和爱好而进行的,外力只是起引导和监督的作用,绝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尽管他是从要求学生学习宗教教义出发的,但这种思想与当时其他教育家相比,在某种程序上说也是一种超前。
四、教学内容的选择
奥古斯丁最有见地的主张无非是教学内容方面。他认为,教会在建立自己学校之后,摆在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能不能吸收希腊—罗马文化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他对待异教的态度,很自然地为后代西方教会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方案。奥古斯丁认为作为教学内容诸如方法、修辞、逻辑等这类学问均是工具,可以为异教服务,也可以为本基督教服务,从形式上应予以保留,只不过在内容上应稍加修改。他还主张从异教教义中选择一些与本教义宣传教学有用的东西,编纂成小百科,供教会教学之用。奥古斯丁在谈到训练青年复述和改写诗歌的办法时说,“复述原诗或散文都应该体会人物的身份,这就出现了一种用妥当的字眼表达情感”[1]172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任何地方都有用处。
奥古斯丁这种“兼容并蓄”和辩证“扬弃”的观点在选择教学内容上直到现在依然是正确的。教学内容作为各种学校开设的学科科目和知识的体系,反映着一定阶层、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任何一个教派、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影响下一代的教学内容时,总要斟酌再三。奥古斯丁在当时已较透彻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在阅读那些虚浮文学时,“的确我在阅读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词,但是这些词在正经的典籍里也能学到,我承认这是儿童接受训练时最为稳定的方式。”[1]169-170因此,对待教学内容,奥古斯丁一贯坚持要认真选择,以其思想性为最基本的准绳。他说哪怕是最淫荡的故事,其中也不乏有许多文辞,“它们就像是精选的贵重容器”[1]177,但容器装上错误之酒就会与肮脏联系一起。奥古斯丁强调教学内容的思想性是积极的,但把它看成是选择教学内容的唯一标准却又是他消极的一面。他在对待异教文化的态度上比其他一些基督教的思想家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进步。
五、关于学习理论
奥古斯丁在他的著述中一再强调到“我最初是怎样学习说话的。”[1]163通过自己亲身经历,他生动地揭示了许多合理的学习理论。
首先,他指出婴儿学说话时,是根据成人言语及其身体倾向而获得的。他认为成人说出任何事情的名称,“身体总是向着那个事物……因此婴儿就推断出他们刚才说出的那个词就是他们倾向的那个事物的名称。”[1]163成人运用“自然语言”(这是奥古斯丁的命名,现常称体态语言),如面部表情、目光、身体其他部分的动作等表达内心的情感,因而幼儿从这些具体的形象中学习到许多抽象语言。由此,奥古斯丁认为直观性在幼儿语言学习中起突出的作用。
现代儿童心理学表明,幼儿言语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儿童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儿童“听到成人及其他,就点点滴滴地推断出这些词法是代表什么事物的符号。”[1]163并且逐步地由一些低级具体的词,发展到掌握低级抽象的词。奥古斯丁的语言学习的直观性原则到今天仍被广泛地运用在婴儿的母语和外国语的学习上,在实践中一再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科学性。
其次,奥古斯丁在学习方法和学习顺序上也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在儿童的语言学习中,无拘无束的好奇心比讨厌的强制更有力量。”[1]169他强调儿童的某些好奇心(求知欲)能加速学习进程,对学习起到了巩固和提高的作用。“在曾促我学习而不给我苦痛负担的情况下,我的确学习到了不少拉丁文”。[1]169因而,他非常珍视儿童的好奇心,主张利用这种强烈的学习动机去引导儿童。
奥古斯丁还就学习顺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儿童起初总是对一些描写得“淋漓尽致”、“娓娓道来”的诸如《荷马史诗》等一些具体的东西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然而,停留在这种水平自然是不足取的。因此,当他谈到西塞罗的哲学论文《霍顿西尼斯》(Hortensrius)时,不禁喟叹“这本书吸引我的已不是它里面优美的文字描述了,而是它的内容。”[1]175由此不难看出,奥古斯丁是主张从具体到抽象这一学习顺序的。但是,他毕竟不是个唯物主义者,一面描述了儿童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学习进程;一面又陷入矛盾的泥坑,继续鼓吹他的宗教思想,认为儿童学习那些世俗的“拉肢脱臼”的淫荡的故事不便去净化心灵,皈依神境。他一面苦盼基督用十字宝筏带他涉入神境,成为“上帝之城”的城民;一方面又不得承认自己也是不喜欢艰涩、抽象、枯燥乏味的拉丁语法的。
再次,奥古斯丁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产生新的学习欲望,要求见到“见不到”的东西,希望明了先前“懂不了”的理论。奥古斯丁说,他在儿童时期“……骄傲非凡、盛气凌人,不能理解圣经的文体和格调,不能体会圣经的义理,”在他决心研究圣经,探究它的内容之后,他才惊喜地发现,“刚入门时觉得隘陋,越朝前越觉得高深”,“圣经的意义随孩子的年龄而与日俱增。”[1]176姑且避开奥古斯丁的学习内容不谈,仅就他通过自己直觉体验提出的“学然后知不足”的学习理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六、关于非智力因素对儿童学习的影响
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在于理性,理性是为支持信仰的。所以他不强调智力因素对儿童学习的影响,而把非智力因素直接概括为兴趣、动机、情感、意志和性格等等心理因素,尤其强调情绪和情感,认为它是产生钻研动机的支持力量,只有学习能带给学生精神上的兴奋,学习活动才能逐步地形成良好的智力个性。作为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不可能对非智力因素作多么精深的论述,但是其中许多看法直到今天依然很有价值。
奥古斯丁总结他幼年的经历时说:“如果我不受约束,便不读书。”[1]166这句话的倾向我们不难看出,幼年的奥古斯丁同其他儿童一样彻头彻尾的兴趣就根本不在那些枯燥乏味的拉丁字母上。正因为这样,他认为:“没有人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能把事做好,虽然他做的是好事,”[1]166这就进一步论证了他的兴趣学习论观点。在他看来,兴趣是搞好学习的根本之所在,没有兴趣学习活动无法开展,没有兴趣就没有进步。
与此同时,奥古斯丁提出了精神上的压力与焦虑会对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人的无节制的喜爱就要成为他自己的苦难。”[1]166儿童本身就是错误的化身,总是需要教育的甘霖予以感化。因而,人生来就应该受约束,给予一定的压力,造成适当的内心焦急,以逐步培养儿童先前不曾具有的意志力。他说:“这种强制限制了那种无拘无束的好奇心的不稳定性。”[1]166尽管奥古斯丁毫不怀疑自己的观点,但是作为宗教领袖,他又认为“原罪”是人的本性。在教育上仅仅依靠儿童的觉悟,凭借他们自身的节制,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关键是“戒尺,皮鞭和棍棒”。他说三者是制服儿童、“把儿童从最初引诱中召唤回来”的根本之所在。
无疑,奥古斯丁坚持作为激发认识过程的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有一定影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过分地强调了外物对儿童的强制,暴露了宗教立场的本性,是不可取的。
奥古斯丁作为对后代欧洲影响最大的一位基督教父,他的神权至上的观点统治了他的整个思想。因此,他竭力强调用体罚的手段帮助儿童从“原罪”的约束下悔过自新,摆脱旧习俗的纠缠。同时,为了以严格的宗教体统去影响儿童,从而矛盾地游离于“兴趣学习观”内外,忽而指出其重要性,忽而连儿童游戏都被迥然划分在学习行为之外,忽略游戏与学习的一致性,尽管他自己也承认“我喜欢游戏,并为此而挨打。”[1]165但是,他又心甘情愿地接受打骂,认为这种打骂是帮助自己,是在拯救自己的灵魂。罗素认为,不注意心理发展的节律和性质是教育上呆板无效现象的重要根源。奥古斯丁认为忠守自己执着追求的教义,恰恰在此“犯戒”。但他在许多细节上仍没有全盘否认客观事实。因此,他在教学原则、非智力因素、教学内容的选择等诸方面都有许多合理的见解。他的儿童教育思想及其对待异教文化的态度支配了欧洲学校教育一千多年之久,直到主张自然教育反对体罚的卢梭的出现,才算终结。故而,我们认定奥古斯丁为欧洲中世纪前的一位最杰出的宗教教育家是符合事实的。认真研究奥古斯丁思想对认识欧洲文艺复兴前教育以及欧洲经院教学特点是很有帮助的。
[1]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忏悔录》译书[M]//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G610
A
1671-8275(2010)04-0088-03
2010-04-12
朱晓红(1969-),女,安徽黟县人,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师。
责任编辑:石柏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