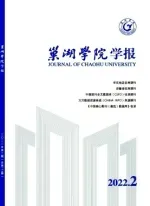镜中晚清
——《老残游记》中的晚清中国形象
2010-08-15王芳玲
王芳玲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镜中晚清
——《老残游记》中的晚清中国形象
王芳玲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晚清以降,中国形象成为一个重要话题。随着中国门户被打开,人们的现代意识慢慢产生,中国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意义更为突出。而在刘鹗的《老残游记》中,晚清中国形象主要是在他者之镜下形成,充当镜子的则是西方和日本,当镜子变化时,其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
老残游记;现代意识;镜中我;中国形象
1 引言
刘鹗的《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自问世之日起就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其“清官可恨”思想更被一再提及,但是对于刘鹗为什么要揭露清官之恶,以及与此相连的晚清中国形象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王一川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中虽有所提及,但其重心主要放在刘鹗对“古典型中国形象”的回瞥上,有关晚清中国形象的生成和变迁问题则略而为论。
中国形象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本文试图结合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来考察已经产生了现代意识的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晚清中国形象的认识,并把它置于中国由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嬗变,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性体验向现代性体验的转变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其生成与变化问题。
2 晚清中国形象的生成
中国形象并不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虽然人们心目中的中国或许有着具体的地域分界,但是它主要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一种认识。而从认识主体上来说,它一般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眼中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从第二层含义上来进行探讨。
中国人自我眼中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中国人对自我的认知。自我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而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则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捷径。库利把“自我”比成“镜中自我”,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人们是在想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中形成了自我的观念。这样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反映出对方的情况。[1]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主要是从镜子中获得的镜像,这种镜像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而充当镜子的则是他人,人们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当镜子变化时,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也会随之改变。
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形象从古至今不断地变化,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用以反观自身的镜子不同。晚清以前,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在地理位置上,是世界的中心,而在文化上,也是无可匹敌。因为与其他周边国家比起来,中国遥遥领先。这时候,落后的周边国家好比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反观到的是一个泱泱大国的形象。但是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的迷梦。西方人用他们的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也给中国人审视自身带来了另外一面镜子。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短短几年中,中国人经历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割地、赔款,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条约,甚至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这都证明了中国在与西方交往中的不断矮化。随着镜子的变化,中国人从这面镜子中反观到的自我形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再是曾经的“万方之主”,而变成了晚清的“老大帝国”。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点,中国人的现代意识渐渐产生,古典性中国形象终于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追问的空前急迫的重大问题。[2]
在西方这面镜子面前,人们揽镜自照不仅得出了与古代中国人不同的现代中国形象,而且每个人所看到的也不尽相同,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就有显著体现。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当时的中国就像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而在刘鹗的《老残游记》中,现代中国形象则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内涵。
在《老残游记》中,刘鹗主要用一则大船寓言来说明其眼中的晚清中国形象。在小说的第一回中,老残等曾借西方的望远镜看到一艘处于洪波巨浪中的危船。这艘船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它是从长山岛往这边来:“你望正东北的地方瞧,那一片雪白的浪花,不是长山岛吗,在长山岛的这边,渐渐来得近了。”
第二,这艘船的整体状况是大而破。“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原是只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只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只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算来这船便有八只桅了。”这艘船虽大却很破旧:“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第三,船上的人饱受风雨的摧残:“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计其数,却无蓬窗等件遮盖风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面上有北风吹着,身上有浪花溅着,又湿又寒,又饥又怕。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
很明显,这是一艘危机四伏、前途难测的危船,船上不但装了很多货物和乘客,而且本身也破烂不堪。这则深刻的大船寓言其实是刘鹗对晚清中国形象的想象,这种想象和古典型中国形象不同,它是刘鹗在现代意识产生以后借西方之镜的一种自我审视。在小说中,危船形象的捕捉靠的是西方的器具——望远镜,它代表的是西方的先进技术,没有望远镜,他们也就看不到处于危机中的大船,这也寓意着没有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刘鹗就不会得到与古代中国形象不同的现代中国形象。
这艘象征着晚清中国的大船在遭受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以后已经破败不堪,如何使它转危为安,重树大国之威是当时最紧要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则要找到其症结在何处,这也是从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最为关切的话题之一。刘鹗对此的看法在当时非常典型。在他看来,掌船的人并没有错:“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而是另有其因:“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么大的风浪,所以都毛手毛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哪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了。心里不是不想往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西南北,所以越走越挫。”刘鹗认为中国落后的症结并不在政体制度,而是遇到了新的状况,所以照着老方法来应对新危机已经行不通了。这新的危机自然是指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对中国的冲击。
正是因为刘鹗认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因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而不是皇权制度的缺陷,所以他一方面对管帆的人墨守陈规不知变动略有微词:“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在那里管,只是个人管个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彼此互不相观照。”另一方面又对那些试图推翻皇权制度的革命人士严厉抨击,认为他们是“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而“倘若这样做去,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
自认为找到问题症结的刘鹗,为危难中的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利用器物文明来达到自强制强的目的。在小说中,老残等人代表的就是先进的器物文明,所以他们才说:“实在危险得极!幸而是向这边来了,不过二三十里就可以泊岸了。”在看到大船因陷入混乱而不能靠岸时他们又主动送上代表西方器物文明的罗盘,希冀以此帮助大船转危为安,使中国摆脱危机。
由此可见,刘鹗认为中国之所以陷入困境并不是中国文化和制度的问题,而是器物层面的落后,只要将西方先进的器物文明嫁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就可以化解这场危机了。透过西方这面镜子刘鹗所看到的晚清中国形象只是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大国,因此文化和制度上无需变革。
刘鹗的看法其实和洋务派的主张不谋而合。他所秉持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器观念,认为器物只是奇技淫巧,不能和传统的道相匹敌,虽然可以利用,但是只能落实在技术层面,根本的价值观念无需改变,但是这种基于对中西文明的优劣理解所形成的晚清中国形象只是一种主观认识,它的正确与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3 晚清中国形象的变迁
刘鹗通过西方之镜,看到的晚清中国只是一个在技术层面上落后的衰败国家,因此只要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就能转危为安,重振大国之威。但是这只是很多包括刘鹗在内的晚清知识分子的片面想法,一旦新的镜子摆在刘鹗面前,他就会发现自己的认识和实际并不相符。而这新的镜子就是小说中大船正在遭遇的洪波巨浪,从现实角度来看,很可能是当时的日本。
其实在小说中,刘鹗已经多次暗示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在小说开始,老残等在发现危船之前,先看到的是另外一艘船:“你们看!东边有一丝黑影,随波出没,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有极细一丝黑线,在那天水交接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么”,有研究者认为,从地理位置上来判断,它应该是日本。[3]在小说的外编集中,刘鹗又借徳慧生之口表现了日本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中国对日本的疏于防范。而在现实中,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虽然让很多人产生了亡国的危机,可是他们认为只要采用西方的器物即可化解,但是甲午一战,中国惨败,器物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小说中众人对老残等送来解救危机的罗盘的拒绝其实影射的就是刘鹗曾经秉持的器物救国理想的破灭。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有识之士终于从文化大国的迷梦中醒悟过来,梁启超等纷纷走上了政体改革之路,实行戊戌变法。而在刘鹗看来,器物救国这一方案之所以失败,是某种因素阻碍了它在中国的实施,只要消除这些阻碍因素即可。这一阻碍因素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反只有以传统文化为根本,中国才能成为有根之木。所以,在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刘鹗屡次提及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小说中,治愈象征着黄河的黄大户的病,用的是大禹传下来的方子;自己随身携带的是诸如庄子之类的典籍;游览各种名胜古迹,鉴赏王小玉说书之美,并借黄龙子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儒释道三家的看法。如此种种,都表现了刘鹗对古典文化的眷恋与服膺。另一方面,现有的皇权制度也不是阻碍因素。在刘鹗看来,“驾驶的人并不曾错”,那些把矛头对准君权制度的人只能使“这船覆的更快”,而不会对其有任何帮助,所以刘鹗后来借黄龙子之口表达的对“北拳南革”的批评也是这种思想观念的体现。
刘鹗认为真正的阻碍因素是当时的下层官僚,即小说中的水手,他们不但直接残害人民,也是阻碍器物救国方案实施的元凶。在小说中,正是那些下等水手煽动群众,引起众怒,赶走了老残一行人。对此刘鹗深有体会,他曾多次建议利用外资、技术兴办实业,但是都被官府拒绝,最终没有被统治者采纳。[4]“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刘鹗继承了《左传》的春秋精义,认为只有将这些邪官扫除,国家才可以毫无阻碍地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此达到强盛的目的。因此,刘鹗接下来将小说的笔触主要放在了抨击当时的官僚制度上。
在晚清时期,猛烈抨击黑暗官场的并不止于刘鹗一人,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对赃官的描写惟妙惟肖,已经引起很大反响。刘鹗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将矛头对准在当时一些所谓的清官上,这是众人都没有注意到的:“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而“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所以小说力揭清官之恶,塑造了玉贤、刚弼的形象。在小说中,玉贤和刚弼在处理案件时,只是主观主义,刚愎自用,由此造成了无数冤案,很多人因此无辜丧命。而玉贤和刚弼显然只是当时黑暗官场的代表人物而已。
但是以玉贤和刚弼为代表的官僚体制其实本身就是中国封建官僚文化的一部分,这与刘鹗所赞同的封建政体制度是矛盾的。不过刘鹗在小说中借黄龙子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矛盾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官风只是一种虚幻的天理国法人情,所以需要革命党来破除它,以把真的天理国法人情呼唤出来,届时天下就会太平了。可见刘鹗认为现在的官场只是虚幻的文化制度,只要将这种虚幻的东西打破,代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制度即可。在《老残游记外编》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此吾中国之所以日弱也!中国有四长皆甲于全球:二十三行省全在温带,是天时第一;山川之孕育,田园之腴厚,各省皆然,是地理第一;野人之勤劳耐苦,君子之聪明颖异,是人质第一;文、周、孔、孟之书,圣祖、世宗之训,是政教第一;理应执全球的牛耳才是。然而国日以削,民日以困,骎骎然将至于危者。其故安在?风俗为之也。”对于刘鹗来说,中国天时、地利、人质、政教都是世界第一,使中国日益衰败的是恶劣的风俗,在此处风俗主要指腐败的官场。
刘鹗一方面抨击官场制度,认为其是虚幻的天理国法,一方面又执意维护当时的政体制度,因此如何遏制黑暗的官场风气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小说中,刘鹗主要采用了三种办法:首先是通过一己之力来救助能够救助的人,他自己也说这并不是长策:“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辈眼目中,尽心力替他做一下罢了。”这其实是在安慰自己,使自己不受良心的谴责而已。其次,求救于高官庄宫保,但是很显然,庄宫保虽然不像玉贤、刚弼那样刚愎自用,却因为自己的主观主义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他在得知玉贤、刚弼的恶劣事迹后并没有罢了他们的官,因为怕有损自己的声名。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他听信一面之词,废堤制河,葬送了十几万百姓的性命。因此老残的解决办法也就成了无根之木了。绝望中的老残只有将目光投向地狱,试图用这种极其虚幻的办法来达到警示人心的目的,但是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刘鹗根本就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
刘鹗之所以意识到实物救国方案的不可行主要是面对的镜子发生了变化,所看到的中国形象随之改变,虽然刘鹗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实业救国理想,秉承洋务派的思想观念,排斥康梁的变法主张,但他的实业救国理想在当时的政体制度下根本无法完成,而他对皇权制度的支持和官场制度的排斥,和变法派表面殊异,实质相同,这其实是是社会环境的束缚所致,刘鹗的思想虽然特殊,但是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
4 结语
刘鹗《老残游记》中的“晚清中国形象”是一种在外来文化之镜观照下的镜像,它的生成和历史场域中的中西关系的演变有关。当镜子变化时,这一形象也随之会发生变化。
当然,限于时代的限制,刘鹗对他深爱的祖国,不可能全面而彻底地挖出旧病根、指出新方向,他也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西方文化。但是《老残游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晚清中国的文学镜像,这个镜像是否符合客观历史已不重要,它至少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化互动过程中反观自身的一个断片,正是依赖于一个个这样的断片,中国人的现代意识才得以产生。
[1]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刘厚泽.刘鹗与《老残游记》[A].刘德隆等编.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C].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THE LATE QING IN MIRROR——THE IMAGE OF CHINA IN LAOCAN YOUJI
WANG Fang-l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The image of China became an important problem since the late Qing.With the door opened,the modern concept of people began to come forth slowly and the image of China changed radically. The image of China in Liu e’s Laocan youji mainly formed in the mirrors,and the mirrors are the West and Japan.When the mirror changed,the image changed with it too.
Laocan youji; modern concept; “looking-glass self”; Image of China
I207.4
A
1672-2868(2010)05-0060-04
2010-06-13
王芳玲(1987-),女,安徽淮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