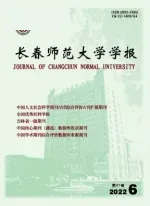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叙事结构及意象表现
2010-08-15王华权
王华权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沈从文是个多产的作家,留下的短篇小说在150篇以上,中长篇小说有10部左右。其中,最属沈从文“自己”的是包括《边城》《丈夫》《柏子》《贵生》等在内的描写湘西古老习俗和原始生命的乡土小说。沈从文曾说“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既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混合。”(《烛虚·小说作者和读者》)他写“实”,以展示湘西带有质朴的民族社会遗风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他写“梦”,从这种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中幻化出自在状态的纯人性和牧歌情调的纯艺术。沈从文以其独特的审美观照,把淡泊而又感伤的情怀从容不迫地渗透到人物、生活图景和风俗画等意象的土壤中,形成一种主客观的交融,成就一种小说散文化、诗化的艺术境界。
一、宗教与原始交织——浓郁的风俗背景
作品开头浓墨重笔描写风物风俗,并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使整个作品为风俗画所笼罩,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常用的手法。如《边城》一、二、三节,作者似乎无意于演绎一个故事,而徜徉于边城的风物风俗,写河街小饭店的鲤鱼豆腐、一半着陆一半在水的吊脚楼、搁着重百斤铁锚的河街、穿着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的中年妇女、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新年时的狮子龙灯等,无不写得逼真细致。小说摇曳多姿地点缀着、渲染着各种湘西古老风物风俗,浓郁的湘西气息扑面而来。
这种湘西的特质,为故事发展涂抹上了一层浓郁的地方色彩,散发着特有的魅力。这类作品打开了一副看似“新天方夜谭”,实为一个古老国度化外之境的人物山水风俗画,使读者在奇特中感到优美,惊愕时受到感染。
浓郁的地方色彩的形成还有赖于特定场面的选择。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多把故事放在水边,如果没有河水,就不会有沈从文的《边城》《柏子》等。这里非湘西特有的“物”——河水,因融入在作品中而具有当地的“风”了,成了构成浓郁地方色彩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了。沈从文曾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我作品的一切背景都少不了水”(《一个传奇的本事》)。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大段大段写水并不多见,可是偶尔点染的几笔,就给全篇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他笔下的湘西,使人在看惯了豪华都市的世俗人生后,一睹化外之地的宁静秀美和古朴奇幻。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风物、风俗描写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他小说的特有风貌就为这种风物、风俗描写装饰着,正如他所说的:“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沈从文在其乡土小说中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性,实要借湘西的宗教性、神秘性和原始性来完成他乡土小说的地方特色。如果说早期许钦文、王鲁彦、许杰等浙东乡土小说家作品的地方特色常带有民族的普遍性,那么沈从文笔下的乡土小说,由于湘西文化的相对封闭,而带有更多的历史沉积、远古遗风等,因而更多的是民族普遍性中的独特性。
其一,宗教性。沅水流域,自古以巫风称盛。《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做歌乐技舞以乐诸神。”对神和命运的崇拜和迷信同样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大量出现。在描写湘西社会特殊的“光和色”中,沈从文充分展示了由闭塞而保留的原始民间风俗,尤其是展示了把节目娱乐和宗教礼仪融为一体的带点神话意味的奇异风俗,从而也丰富了我国小说的生活领域和审美内涵。中篇小说《神巫之爱》就是把湘西的巫风、民间娱乐和男女的一见钟情相交织的风俗传奇。再如《阿黑小史》中老师傅的捉鬼,《贵生》中金凤的八字重、克父母、压丈夫等背后都折射着一个保留着浓郁宗教风气的宗法制社会。
其二,神秘性。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相当一部分都充满着一种神秘感。过于纯朴的民性、两者械斗第三者不许填刀的侠风、荒野恐怖的山野、暗滩隐藏的河流及放蛊、沉潭、赶尸等都使人不可思议。而《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更使读者联想到几千年前的《桃花源记》,这是个神秘的世界。
其三,原始性。在充满着宗教、伴着神秘性的风物风俗描写中,总是透现着一个古老而又原始的湘西。作者倾心于人与自然的契合,并从中发现独特的美来——纯朴的人性。因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几乎看不到现代文明的痕迹,有的只是水车、碾场、火炬、烟包,就是人间的关系也是那样得原始,似乎那里永远不会有奸商,即使卖身的也是能两相厮守。当然,这只是沈从文的一个梦。从而,其乡土小说透出特有的、自然的而又原始的美来。沈从文始终是个“乡下人”,他的作品即使是写“衣冠社会”,也只是与古老的湘西对照,实要写出故乡的土地和人民。“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边城题记》)从“野蛮”中见出雄强,从“平凡”中见出伟大,最终剥出原始纯朴的人性。因此,沈从文小说中,原始性与宗教性和神秘性相比较占有主体地位。原始性是其乡土小说的地方特色的基础,而宗教性只是其衍生。
二、场景与意境互动——小说诗化的叙事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意象构成涉及各个方面,包括题材、场面、人物、自然景物、色彩及音响等。在题材上多为湘西朦胧爱情故事。无论是三三还是萧萧、翠翠,她们的爱情更像一个梦,在意境上是虚幻的、缥缈的;在主人公的选择上,多为十五六岁的少女,如翠翠、三三、萧萧、夭夭,无不天真质朴,表现出阴柔美的特征。而自然景物多为青山翠竹,使作品荡漾着原始疏野的边地情调,在音响上又特别擅长写虫声。特别是在场面的选择上,沈从文的许多优秀篇章都以水为背景,使作品显出特有的美来。沈从文把这些具有相近内在性质的意象进行并置组合,用冲淡、宁静、不事雕琢的叙事方式,构成了原始、朴素、秀美、荒莽的特有意境。虽渐去渐远,因远而淡,但仍清宛可闻。
小说故事的发展似乎不是靠动作、情节的发展而深化,而是在特定的风俗画场景的不断重复出现中使情境浓化。如《边城》中的爱情故事,情节相当简单,翠翠的爱情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赛龙舟中孕育发展的。《长河》《黔小景》《丈夫》《柏子》等都用此手法,即在小说的开头用散文化的笔墨,在“非规定情境”中来演绎故事,从而使作品在情节和人物的有意识的淡化中,凸现出一种情境、意境来。
就小说的动作来说,这些都是可以从动作的链条上挣脱出来的,但沈从文这种刻意追求的独特好处在于,就场面讲,增加氛围;就主题讲,凸现一种情境和意境;同样就单篇小说来讲,衬托一种意境。正是赖于“非规定情境”这一独特的散文化和诗化的手法,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凸现出一种特有的情境、意境来。
创造艺术空白是沈从文创造意境的另一种主要方式。古人曾云:“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七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真正的艺术,不是百分之百的给予,而是有所保留的给予。情感的最大容纳处,不在于已说出的部分,更在于未说出的部分。
沈从文对空白的处理体现在其乡土小说的各个部分,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及作品的结构中都充满着想象的浮动性。单以结构为例,《丈夫》中最后一段即为典型。读者看不到丈夫和老七当晚是怎样的情景,走的时候又怎样,这一切都被沈从文省略了,而只是通过他人之口说出他们已经走了。极其寥寥的几笔,使读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极繁 (反复的风俗描写)和极简 (叙事空白)的对比中,我们至此似乎可以解读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了,他并不是不注重艺术提炼,也并不是缺少叙事描写的手法,而是有着独特的艺术追求。正如他所说的“我也不说小说需要很‘经济’的来处理一切,即或是一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是说要很‘恰当’。这个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的量上,就不容许不必怕数量的浪费。”(《小说作者和读者》)确实,沈从文作文不大有陈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的作文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体操”而已。
在这种表层意境中,通过意象的能指所指,引向人生命和社会历史的思索,进入深层意境。
在城市和乡村的碰撞中,沈从文痛苦地、孤独地承受着历史错位的心理反应,在城市的一隅吹奏出田园牧歌,搜索着纯朴的人性而又无奈纯朴人性美的丧失,沈从文是寂寞的,孤独的,怅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又如他感叹的,“美丽总使人忧愁”。
但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的画外旁白,他更愿意不动声色地贴近和融入。在意境上又表现为“无我”。
王国维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沈从文在其乡土小说中静静地关照着故乡的人事哀乐,“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边城·题记》)而不愿去打破其宁静的梦。但无我之境也并非“无我”,只是作者比较客观冷静地描绘,情感比较隐约地深藏。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表面看似无爱憎,处处无我,处处是一曲悠悠的田园牧歌,实则爱意流注其间,在“无我”中又处处“有我”。诚如沈从文说的“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习作选集代序》)
他的许多乡土作品都能显示这一特色。同样以《丈夫》为例,作者很客观地叙述了“丈夫”在船上忍气吞声,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男人把票子撒在地上捂着脸孔哭。五多和大娘都逃到后舱。五多想唱一个歌,但唱不出。第二天水保上船时只有大娘和五多,而老七夫妇已回故乡。从中找不出一句作者站出来向这对受尽摧残侮辱的年轻夫妇表示丝毫悲悯的话,沈从文只是不露声色地客观描述这自然人生的一角。但绝不是没有,只是这悲悯由五多去承受,作者的情感在这里和五多和读者融合了。沈从文在《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中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来表现的。”
即如《边城》那样“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刘西渭《咀华集·边城》)中,我们依然能体味出淡淡的哀伤。不仅是人生的不如意,也不单是人性美的丧失,而更是寄寓了沈从文对古老湘西及其人民命运的历史思索及其出路的找寻。“这地方人将来的命运,虽生活与自然相契,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泸溪·浦市·箱子岩》)在《边城》中,沈从文用浓重的笔墨不厌其烦地写赛龙舟,不也隐藏着作者对古老湘西一种出路的找寻?这是沈从文特有的深层。
三、人事与自然融合——“田园式”的抒情
将情感渗透到人物景物时,作者又娓娓而谈,自然透出。艺术在本质上要情感强化,但在表现上却要求有限制的传递。沈从文在情感流泻的分量上,既不是吝惜的,冷静里显着冷峻;也不是放纵的,瀑泻着情感的洪流。虽然没有大浪大起,却在轻快中含着感伤,热烈中透着悲凉,深致辽远,引起无尽的遐思。其具体手法有:
其一,将自然景观人格化。单单写景,并不足以构成意境,而一旦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意,达到人物两忘、境我浑一的境地,就构成了意境。这种将自然景物人格化的结果,是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变得深邃而辽远。如《边城》中“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嘘’啭着她的喉咙。“这里草莺似乎也通人性,感应着人物的心境。
有时,沈从文也让这种人格化的自然景物关照人物命运的发展,使作品的意蕴更加浑厚,甚至带上神圣色彩。如《边城》中,渡口的白塔,默默地矗立在那里,仿佛静静地关照着人事的演变,可是当翠翠的爱情面临危机,爷爷以衰老的生命再也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时,那白塔突然倒塌了,就如“爷爷“在风雨之夜的倒下。这里人事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景物的变化联系着人事的一举一动,从而曲折地传递着作者的感情。
其二,采用象征手法,使小说创造的意境,其含义高高溢出文字的表面,勾出繁复辽远的意蕴。《边城》不只是个爱情故事,作者是要从这个闭塞,人与人自然相契的田园社会里,找寻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并从中找寻情感的释放,“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沈从文具有“乡下人”的含蓄,他深深地同情他的乡民,但他不任爆发式的热情倾泻,也不把火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而是让感情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中缓缓流动,就像湘西的溪水,平平地流。这是沈从文特有的含蕴。
独特的艺术是永恒的。沈从文没有创造内蕴丰富的艺术典型,也没有描绘巨幅的社会历史画卷,而只是一往情深地以“乡下人”的眼光和情绪去精心构建属于他自己的湘西世界,频频回顾,以自己的形式去感知、找寻民间的古朴遗风和原始生命形式,竭力颂扬真善美的人性。这是沈从文的世界。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2]吴道毅.论沈从文作品的民族地域特色[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3]罗宗宇,刘鹏娟.论沈从文小说对民俗的叙事构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
[4]吴效刚,王玉括.论沈从文小说的叙述形态[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